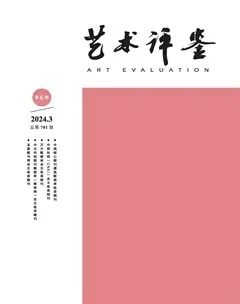民間舞“卡斯達(dá)溫”舞蹈表演形態(tài)探究
王伊菲
【摘?? 要】“卡斯達(dá)溫”是一種流傳于四川黑水縣的鎧甲舞,其舞蹈形態(tài)獨特,被列為首批國家級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名錄。為了更好地對“卡斯達(dá)溫”舞蹈文化進(jìn)行傳承和保護(hù),本文以四川省阿壩州黑水縣為田野考察地,進(jìn)行“卡斯達(dá)溫”舞蹈表演形態(tài)探究。古人云“知必知其事”,對于黑水縣“卡斯達(dá)溫”舞蹈表演的形態(tài)研究,主要將黑水縣“卡斯達(dá)溫”表演形態(tài)劃分成四個部分:“前歌后舞”的表演形態(tài)、“儀式性”活動的表演形態(tài)、“巫”與“武”的表現(xiàn)形態(tài)、踏地為歌“圈舞”的表現(xiàn)形態(tài)。
【關(guān)鍵詞】“卡斯達(dá)溫”? 舞蹈表演? 形態(tài)探究
文章編號:1008-3359(2024)06-0057-06
中圖分類號:J705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基金項目:本文為2022年度寧夏大學(xué)新華學(xué)院教育教學(xué)改革項目,項目名稱:《中國民族民間舞》課程質(zhì)量改進(jìn)路徑探析——以學(xué)生學(xué)習(xí)效果為中心,項目編號:2022xhjg002。
“卡斯達(dá)溫”舞蹈是四川省西北部黑水縣最為獨特的民間舞蹈。它從最初的儀式行為和勞動活動演變?yōu)橐环N民間祭祀性舞蹈,并在葬禮儀式和節(jié)日慶典上祈求平安和向佛陀敬獻(xiàn)。“卡斯達(dá)溫”舞蹈體現(xiàn)了當(dāng)?shù)丶谓q藏族豐富的文化和歷史,在2006年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名錄,遺產(chǎn)編號為Ⅲ-33。作為我國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之一,“卡斯達(dá)溫”目前在四川省黑水縣地區(qū)主要有三個重要分支,分布在紅巖鄉(xiāng)、維古鄉(xiāng)、扎窩鄉(xiāng),呈現(xiàn)出以戰(zhàn)爭、祭祀、狩獵為主要內(nèi)容的舞蹈表演,具有極強(qiáng)的地域性特征。由于黑水縣“卡斯達(dá)溫”舞蹈所在地區(qū)環(huán)境條件相對封閉,舞者多為半百老人,且傳習(xí)方式單一(多為父母輩言傳身教),舞蹈文字記錄稀少,導(dǎo)致“卡斯達(dá)溫”的傳承和保護(hù)愈發(fā)困難。對此,本文將以四川省阿壩州黑水縣作為田野考察地,通過結(jié)合舞蹈形態(tài)學(xué)、田野調(diào)查等理論和方法,以表演形態(tài)作為切入點,系統(tǒng)化地梳理和分析“卡斯達(dá)溫”舞蹈的表演形態(tài)特征,從而為更好地傳承和保護(hù)“卡斯達(dá)溫”舞蹈提供相應(yīng)的支持和輔助。
一、“前歌后舞”的表演形態(tài)
鎧甲舞的考察、研究過程中,發(fā)現(xiàn)文獻(xiàn)記載上古時期巴人助周滅殷的“前歌后舞”、屈原《國殤》所據(jù)“俗人祭祀之禮”,以及劉邦所見巴渝舞,無論在性質(zhì)還是形式上皆與“卡斯達(dá)溫”有極大的相似性。黑水縣“卡斯達(dá)溫”舞蹈表演形態(tài)特征可以追溯于漢代至唐代的“前歌后舞”表演形態(tài)特征。“前歌后舞”指戰(zhàn)場上前方有多少人征戰(zhàn),后方就有多少人歌舞,前方戰(zhàn)士奮勇殺敵,高呼口號,而后方鼓樂喧天,舞動身姿以鼓舞士氣,“前歌后舞”的表演形態(tài)特征大多出現(xiàn)于陣前舞蹈,具體形態(tài)特征如下:
第一,“前歌后舞”的陣前舞蹈是一種武舞。武舞在我國最早出現(xiàn)于公元前10世紀(jì)的戰(zhàn)爭活動,舞時手執(zhí)刀劍,通過模擬戰(zhàn)勝敵方的過程,表達(dá)內(nèi)心歡愉之情,以起到鼓舞人心、提振士氣的作用。其內(nèi)容一般為歌頌統(tǒng)治者的賢明,展示國家的軍事實力,以及炫耀戰(zhàn)士們的輝煌戰(zhàn)績。漢高祖劉邦觀看“前歌后舞”的陣前舞蹈后十分欣賞其勇猛銳志、勁健豪獷的風(fēng)格特點,并評論道:“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命樂人習(xí)之”。
第二,“前歌后舞”的陣前舞蹈呈現(xiàn)出集體而舞的形態(tài)特征。據(jù)載,巴渝舞蹈在漢代是“前歌后舞”陣前舞蹈的典型代表。這是因為巴人當(dāng)時生活在由強(qiáng)大的部族(如殷、周、秦、楚)環(huán)繞的環(huán)境中,生活艱難。為了生存和發(fā)展,他們必須凝聚部族內(nèi)各個成員勢力,以便受到外敵侵犯時拿起刀劍保衛(wèi)社稷。這種部落成員互相協(xié)作的精神在日常生產(chǎn)勞作中逐漸深入骨髓,并在舞蹈中得到體現(xiàn)。東漢班固在《漢書·禮樂志》中記載:“巴俞鼓員三十六人”。文字記錄鼓手有三十六人, 但難以考證其中是否包括伴奏和歌唱人員。但至少據(jù)此可知,參加人數(shù)眾多的武舞是一種集體舞蹈。西漢司馬相如在《上林賦》中詳細(xì)描述了武舞的壯觀景象:“千人唱,萬人和,山陵為之震動,川谷為之蕩波”。與“前歌后舞”的陣前舞蹈類似。
第三,“前歌后舞”主要特征為其所表演的內(nèi)容基本與戰(zhàn)事有關(guān)。表演者一般要身披鎧甲、手里執(zhí)盾,且表演者必須會唱戰(zhàn)歌,表演動作也多為戰(zhàn)場上擊殺、劈刺的動作。最初,“前歌后舞”的陣前舞蹈表演時間一般在開始戰(zhàn)爭之前,而當(dāng)其演化為宮廷樂舞后,表演也逐漸轉(zhuǎn)向在宮廷宴會上表現(xiàn)軍旅戰(zhàn)斗場面,以及歌頌帝王功德,即所謂表演時,舞者身披盔甲,手持矛、弩箭,口唱貢人古老戰(zhàn)歌,樂舞交作,邊歌邊舞。
第四,“前歌后舞”的陣前舞蹈在漢代宮廷宴會中得以發(fā)展,其受歡迎程度可謂世人皆知,陣前歌舞表演形態(tài)為:抗修袖以翳面、展清聲而長歌。左思在《三都賦·魏都賦》中,贊“前歌后舞”陣前舞蹈的演唱為“明而耀歌”,其中李善注:耀,謳歌,巴土人之歌也。何晏注:巴人謳歌,相引牽連手而跳舞。據(jù)此可知,“前歌后舞”的陣前舞蹈在演唱方面最突出的特色是表演者相引牽手,叫嘯謳歌。
“前歌后舞”的陣前舞蹈是漢代西南地區(qū)獨具代表性的少數(shù)民族民間集體武舞,它自漢至唐流傳千年之久,在中國舞蹈史上具有很大影響力。據(jù)前所述,“前歌后舞”的陣前舞蹈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前歌后舞”的巴渝舞蹈。西漢歷史學(xué)家司馬遷在《史記·司馬相如傳》中曾引《上林賦》對此進(jìn)行描述,其中,巴渝舞出現(xiàn)于晉人郭璞對“巴俞”的注釋中:“巴西閬中有渝水,僚人居其上,皆剛勇好舞,漢高募取以平三秦,后使樂府習(xí)之,因名巴渝舞也。”由此可知,巴渝舞蹈在漢晉時期因巴人居住在渝水地區(qū)而得名。
黑水縣“卡斯達(dá)溫”舞蹈表演形態(tài)與陣前舞蹈“前歌后舞”的表演形態(tài)特征頗具相似性。其一,“卡斯達(dá)溫”舞蹈同樣具有很強(qiáng)的武舞特征,且在表演時手持干戈。其二,黑水縣“卡斯達(dá)溫”舞蹈表演也屬于群體性舞蹈。在黑水縣,藏傳佛教是藏民的共同信仰,組織參與宗教信仰有關(guān)的歌舞活動是藏民義務(wù)。而戰(zhàn)爭性歌舞“卡斯達(dá)溫”關(guān)系到每個家庭與個人的生死存亡,部落中男女老少都會主動參加,由此,整個“卡斯達(dá)溫”舞蹈沒有旁觀者,只有參與者。據(jù)此可知,“前歌后舞”的陣前舞蹈與“卡斯達(dá)溫”在參與人數(shù)、參與動機(jī)上都有極為相似的集體舞特征。其三,“前歌后舞”的陣前舞蹈與黑水縣“卡斯達(dá)溫”舞蹈的服飾、道具較為相似。黑水縣“卡斯達(dá)溫”表演的服飾、道具大多為表現(xiàn)軍事場景服務(wù),其中部分與“前歌后舞”陣前舞蹈的服飾、道具類似。其四,“前歌后舞”的陣前舞蹈對黑水縣“卡斯達(dá)溫”舞蹈的演唱方式產(chǎn)生重要影響。
基于上述梳理與分析,可以發(fā)現(xiàn)“前歌后舞”的表演形態(tài)對黑水縣“卡斯達(dá)溫”舞蹈表演形態(tài)存在多方面重要影響。
二、“儀式性”活動的表演形態(tài)
鎧甲舞是一種從俗的說法,確切言之,指的是至今仍流行于藏、羌等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披甲而舞的儀式性活動。它們起源、盛行于巫文化時期,與狩獵、戰(zhàn)爭密切相關(guān)。從上一節(jié)的梳理和分析中得知,“卡斯達(dá)溫”舞蹈在古老時期是一種戰(zhàn)舞,而有戰(zhàn)爭的地方就避免不了犧牲,人們在祭祀死去的戰(zhàn)士時也會跳“卡斯達(dá)溫”,所以黑水縣“卡斯達(dá)溫”實際上同樣具有征戰(zhàn)后“儀式性”的喪葬祭祀活動形態(tài)特征。
在我國周代,凡有軍旅之事也要有相應(yīng)的一套祭祀禮儀。天子、諸侯親自率軍出征,首先要告祭祖廟。發(fā)生戰(zhàn)爭時,如果是將軍、大夫率軍出征,還得有一套相應(yīng)的授兵禮儀。軍隊來到所征伐之地宿營后,要祭祀戰(zhàn)神,稱為 “祃祭”。《說文》:“福,師行所止,恐有慢其神,下而祭之祃。《周禮》曰:祃于所征之地。”①戰(zhàn)爭中,軍隊到達(dá)所要征伐之地祭過戰(zhàn)神后,在選擇具體交戰(zhàn)日期時還要占卜,一般是占得吉兆后才可出兵。軍隊征伐歸來,進(jìn)入國都之后,先要到祖廟,把所遷之廟主奉還于宗廟,所遷社主奉還于社,同時要舉行祭祀,“儀式性”的表演形態(tài)多發(fā)生于祭祀活動中。
在阿諾爾德·范熱內(nèi)普的著作《過渡禮儀》中,提到人的一生中會有很多過渡儀式,如門與門坎、待客、懷孕與分娩、誕生、收養(yǎng)、童年、青春期、成人、升職受任、加冕、訂婚或結(jié)婚、喪葬、歲時等。喪葬祭祀儀式可以看作過渡儀式中的一種,是人們基于相信亡人靈魂不會失去的觀念和原始自然道德觀念而出現(xiàn)的一種帶有宗教性質(zhì)的生活習(xí)俗。亡人喪葬的習(xí)俗體現(xiàn)了一種觀念,即人們認(rèn)為人的肉體是生命的有機(jī)載體,人的死亡只代表肉體與靈魂分離。將人的尸體安葬,亡人的靈魂會到另一個空間過著與他生前一樣的生活,那么靈魂是生命載體的延續(xù)。上述的亡者靈魂不失的觀念在川西北少數(shù)民族的喪葬禮儀中也尤為顯著,而舞蹈正是他們喪葬禮儀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戰(zhàn)爭時期,“卡斯達(dá)溫”舞蹈會用于祭祀戰(zhàn)死的將士葬禮上,一般在亡者出殯、下葬,以及安葬后的祭祀禮儀中跳“卡斯達(dá)溫”,一整套程式化的喪葬舞蹈動作和歌曲,以及固有的表演流程寓意在戰(zhàn)爭中犧牲的戰(zhàn)士靈魂會永存,會被后人懷念歌頌。
與之類似的,國外劍橋?qū)W派“神話—儀式”學(xué)說的擁立者簡·艾倫·哈里森領(lǐng)導(dǎo)的劍橋儀式小組也著力證明舞蹈的起源在于儀式,而且是一種犧牲儀式。詹姆斯·喬治·費雷澤爵士的著作《金枝》中明確強(qiáng)調(diào),歐洲原始文化與其他原始文化之間沒有根本不同,歐洲的文化是由死亡和重生的儀式中發(fā)展產(chǎn)生的。
基于上述梳理和分析,可以發(fā)現(xiàn)黑水縣“卡斯達(dá)溫”作為“犧牲儀式”的祭祀舞蹈實際上也是一種風(fēng)俗和文化載體,喪葬祭祀也是“卡斯達(dá)溫”舞蹈的重要功能與意義。
三、“巫”與“武”的表演形態(tài)
“巫舞”是指巫覡祭祀活動中的舞蹈。原始社會早期,由于當(dāng)時的生產(chǎn)力低下,人類對宇宙間物質(zhì)運動的規(guī)律、自然現(xiàn)象等不能做出科學(xué)解釋,冥冥中好像有一種超自然的力量在支配世界,于是神鬼的概念便產(chǎn)生了。巫覡是被認(rèn)為能與神鬼交流和執(zhí)行它們意志的人,而“巫”是以舞來維持人神關(guān)系的。
“武舞”與“文舞”相對,始于周代,用于郊廟祭祀及朝賀、宴享等大典,舞時手執(zhí)斧盾,內(nèi)容為歌頌統(tǒng)治者武功。西周時期,“武舞”也常被作為一種搏殺技術(shù)的訓(xùn)練方式,并以集體的“武舞”演練方式來增強(qiáng)軍隊士氣。到了春秋戰(zhàn)國時期,在百家爭鳴的寬松學(xué)術(shù)環(huán)境下,武術(shù)的功能與形式開始朝著多樣化方向發(fā)展,“武舞”也逐漸成為具有一定娛樂性和競技性的民間武術(shù)。
黑水縣“卡斯達(dá)溫”屬于戰(zhàn)爭性鎧甲舞,因此更多地會呈現(xiàn)“武舞”的形態(tài)特征,不過在某些儀式上也會蘊(yùn)含“巫舞”的形態(tài)。本文通過研究“卡斯達(dá)溫”在黑水縣的發(fā)展歷史,追溯“巫舞”和“武舞”表演形態(tài)對“卡斯達(dá)溫”舞蹈形態(tài)形成的影響。
史冊記載,早在唐朝時期,岷江上游黑水地區(qū)曾是古羌人生活聚居的地方。唐貞觀二十一年(647年),“羌酋董和那蓬固守松則有功,于是拆松州之通軌縣置當(dāng)州,以和那蓬為刺史,后其子屈寧襲焉。”②當(dāng)州所轄四縣都在如今的黑水縣內(nèi),顯慶元年(656年)生羌首領(lǐng)董系北射內(nèi)附,以左封置悉州,以系北射為刺史。所轄左封、程軌兩個地方的絕大區(qū)域也在今黑水縣境內(nèi)。《舊唐書·東女國傳》記載,在唐朝時期,黑水地區(qū)有兩個以羌人為首的部落,分別是“白狗羌”和“南水羌”,至此可知黑水地區(qū)從唐朝開始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都是羌人生活的主要地區(qū)。
而后隨著吐蕃王朝軍事勢力逐漸強(qiáng)大,黑水地區(qū)和當(dāng)?shù)鼐幼〉那既顺闪送罗醭c唐王朝爭奪的對象。經(jīng)過“安史之亂”后,吐蕃王朝順利地對黑水地區(qū)進(jìn)行統(tǒng)治。直至公元9世紀(jì),吐蕃王朝的第九世贊普朗達(dá)瑪被殺,此時吐蕃王朝走向滅亡。遠(yuǎn)征的吐蕃軍隊常年居住于黑水地區(qū),與當(dāng)?shù)氐那济耠s居在一起,出現(xiàn)黑水地區(qū)羌人與藏人融合、羌文化與藏文化融合的景象。直到清朝時期,黑水羌族歸理番廳梭磨土司管轄,當(dāng)時的梭磨土司就是嘉絨藏人。自此以后,黑水地區(qū)接受嘉絨藏族土司、頭人統(tǒng)治,時間長達(dá)二百年。黑水地區(qū)的羌人也逐漸被藏化,所以現(xiàn)在人們稱黑水人為嘉絨藏族,也將黑水地區(qū)的鎧甲舞稱為嘉絨藏族“卡斯達(dá)溫”。因此,“卡斯達(dá)溫”是黑水人經(jīng)歷多年戰(zhàn)爭受羌族文化影響而產(chǎn)生的鎧甲舞。
“卡斯達(dá)溫”多為古代出征前勇士們?yōu)樽约耗軕?zhàn)勝敵人而禱告,眾鄉(xiāng)親為親人送去吉祥平安和祝福而跳的一種含有祭祀成分的舞蹈。表演時,勇士們頭上戴著牛尾的圓形帽,身穿牛皮制作的“甲衣”,手持長刀、戈矛、火藥槍等兵器,游寨內(nèi)邊歌邊舞。出寨后,在空地中圍圈而舞,寨子里的婦女也隨隊跳起送親人出征的舞蹈。其舞與男舞者的動作大體一致,在慢歌快舞的節(jié)奏中進(jìn)行。勇士們刀入鞘,槍柄落地,男女分別前呼后應(yīng),發(fā)出高亢雄厚的呼喊,表現(xiàn)了古代出征的悲壯情景。
黑水縣“卡斯達(dá)溫”主要源于戰(zhàn)爭,為了維護(hù)和鞏固民族團(tuán)結(jié),嘉絨藏族人民通過鎧甲舞儀式凝聚民心,體現(xiàn)了“武舞”的特點。在唐朝時期,黑水地區(qū)戰(zhàn)死的將士、民族的英雄、部落中德高望重的首領(lǐng)或老人舉行喪葬儀式時會跳“卡斯達(dá)溫”,因此鎧甲舞“卡斯達(dá)溫”具有“巫舞”祈禱、慰靈的功能,通過舞蹈活動祈求神明庇護(hù),同時達(dá)到慰藉英靈的作用,其表演形態(tài)在某種程度上與“巫舞”相像。
四、踏地為歌“圈舞”的表演形態(tài)
“卡斯達(dá)溫”除了具有上述舞蹈形態(tài)特征外,也具有“圈舞”的形態(tài)特征。圈舞是一種集體性舞蹈,也被稱為圓圈舞、連臂舞。“圈舞的基本形態(tài)是舞者手拉手、臂挽臂、踏地為歌,同時所有人合著節(jié)拍圍成環(huán)形,動作整齊一致、載歌載舞,場面大氣磅礴壯觀。”③
關(guān)于圈舞,其歷史可以追溯到青海地區(qū)大通縣孫家寨所出土的新石器時代“舞蹈紋陶盆”,該陶盆高14.1cm,陶口直徑29cm,陶底直徑10cm,陶身最大腹徑為28cm,是一件盆身畫有舞蹈紋飾的彩陶盆。陶盆的內(nèi)壁和外壁都有彩繪,外壁由三根橫向紋路平行構(gòu)成,內(nèi)壁的舞蹈圖案為圈舞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材料依據(jù)。紋陶盆內(nèi)壁的舞蹈圖由三組人物紋畫構(gòu)成,五個人為一組,臂連臂,且身體朝著同一方向,動作整齊劃一,五人的頭部微微傾斜,頭部旁邊有一帶狀物(猜測應(yīng)是發(fā)辮),五人中最外側(cè)的兩人手臂動作較為突出。陶盆上的紋畫真實記錄了新石器時代人們跳舞時的情景:舞者聚集在一起,像陶口一樣圍成一個圓圈,相互牽著手跳舞。由此可知,“早在原始社會,先民們就會為了圍篝火取暖的生活需求,以及交流情感、緊密團(tuán)結(jié)的精神需求而圍圈舞蹈。”④
從舞蹈形態(tài)上,黑水縣“卡斯達(dá)溫”融入了圈舞的典型形態(tài)特征,主要體現(xiàn)在:第一,“卡斯達(dá)溫”女性表演者最典型的上肢動作便是連臂,她們手牽手,唱著歌,腳下做著踏步緩慢移動,這與“圈舞”的基本形態(tài)十分相似。第二,“卡斯達(dá)溫”最典型的隊形便是繞圓,完全符合“圈舞”的形態(tài)特征。為了證實關(guān)于“卡斯達(dá)溫”的“圈舞”形態(tài)特征,筆者前往黑水縣與“卡斯達(dá)溫”省級繼承人曲讓老師進(jìn)行深度訪談,曲老師詳細(xì)介紹了“卡斯達(dá)溫”的圈舞形態(tài)特征,并提供了嘉絨藏族村民們在田野間跳“卡斯達(dá)溫”的照片,為本文的分析提供了有力佐證。“卡斯達(dá)溫”在表演形態(tài)中融入“圈舞”的典型形態(tài)特征,而“圈舞”的形式在“卡斯達(dá)溫”舞蹈表演過程中也占據(jù)著重要地位。
“卡斯達(dá)溫”具有“圈舞”的形態(tài)特征,主要是源于“卡斯達(dá)溫”舞蹈希望通過“圈舞”的形式,表達(dá)對于戰(zhàn)爭時抵御外敵入侵的“集體意識”和族人們“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文化意義。從調(diào)研中,可知唐至清時期黑水地區(qū)戰(zhàn)爭頻發(fā),黑水人信仰神靈,祭祀活動舉行得較為頻繁。在祭祀時,族人們圍繞著“圓心”不斷聚攏,仿佛在向神靈訴說大家共同的愿望、敬畏與哀傷。當(dāng)情感達(dá)到高潮時,人們便會情不自禁地聯(lián)袂集中,呼號頓踏,最終踏歌而舞。上文提及自唐至明清時期黑水地區(qū)的人們常年處于戰(zhàn)爭中,因害怕外敵入侵,具有強(qiáng)大的“集體意識”,所以他們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此時的鎧甲舞在戰(zhàn)爭中得以發(fā)展,使得“卡斯達(dá)溫”不僅在創(chuàng)作形態(tài)上保留“圈”的特征,而且在文化形態(tài)上亦傳承圈舞緊密團(tuán)結(jié)的精神。
因此,黑水縣“卡斯達(dá)溫”不僅融入圈舞的形態(tài)特征,也蘊(yùn)含“圈舞集體意識”的文化象征意義。雖然關(guān)于舞蹈藝術(shù)的起源存在很多說法,但眾多學(xué)者認(rèn)為“圈舞”產(chǎn)生最重要的原因應(yīng)為“集體意識”。在狩獵和勞作回來后,先民們會圍在篝火周圍共享食物,表達(dá)獵獲成功的喜悅之情。“而在飽食慶祝之余,大家呼號振臂、頓踏擊節(jié),逐漸形成‘圈舞雛形”。⑤由此可見,這里的“集體意識”與上文提及黑水人抵御外敵的“集體意識”是一致的。
五、結(jié)語
戰(zhàn)舞是從古至今就一直流傳下來的獨特舞蹈形式,黑水縣“卡斯達(dá)溫”舞蹈歷史悠久,承載和蘊(yùn)含著豐富的民族文化和當(dāng)?shù)仫L(fēng)俗。由于受到條件限制,關(guān)于“卡斯達(dá)溫”舞蹈表演形態(tài)的系統(tǒng)化記錄與分析并不多,也導(dǎo)致相關(guān)研究十分稀少。本文對“卡斯達(dá)溫”舞蹈形態(tài)進(jìn)行了相關(guān)梳理和分析,把黑水縣“卡斯達(dá)溫”舞蹈表演形態(tài)追溯到具有“前歌后舞”的陣前舞蹈形態(tài)特征;“儀式性”的祭祀活動形態(tài)特征;“巫舞”與“武舞”的表演形態(tài)特征;以及具有“圈舞”表演形態(tài)特點,揭示了“卡斯達(dá)溫”舞蹈形態(tài)形成主要是源于四川黑水地區(qū)在歷史上所經(jīng)歷的民族和部落戰(zhàn)爭,以及民族文化的融合,由此可知,“卡斯達(dá)溫”舞蹈形態(tài)離不開當(dāng)?shù)孛褡宓奈幕蜕鐣l(fā)展。
參考文獻(xiàn):
[1]陳禮斌主編.舞蹈教育與表演理論教程[M].秦皇島:燕山大學(xué)出版社,2019:6.
[2]劉燧.舞蹈表演與舞蹈藝術(shù)文化研究[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20:1.
[3]陳新宇.淺析道具在舞蹈表演中的作用[C]//中國教育發(fā)展戰(zhàn)略學(xué)會教育教學(xué)創(chuàng)新專業(yè)委員會.2020:1.
[4]羅雄巖.中國民間舞蹈文化教程[M].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01:50.
[5]巫允明主編.中國原生態(tài)舞蹈文化[M].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11:210.
[6]王克芬.中國舞蹈發(fā)展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72.
[7]楊曦帆.論四川嘉絨藏區(qū)鎧甲舞的藏傳佛教文化背景[J].西藏研究,2001(03):66-71.
[8]宋名筑.析民族管弦樂《卡斯達(dá)溫》[J].音樂探索(四川音樂學(xué)院學(xué)報),2004(03):66-68.
①馮瑤:《羌族鎧甲舞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xué),2007年,第6頁。
②《四川黑水河流域民間歌舞〈卡斯達(dá)溫〉》,成都:四川美術(shù)出版社,2007年,第13頁。
③張鈺璇、張鈺珺:《淺談圈舞繼承、發(fā)展的啟示》,《大眾文藝》,2011年,第15期,第94頁。
④邵明杰:《上孫家寨彩陶盆舞蹈圖案新論》,《四川文物》,2010年,第2期,第44—47頁。
⑤海維清:《淺談“圈舞”舞蹈文化遺存的萌芽與發(fā)展》,《大眾文藝》,2015年,第9期,第37—3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