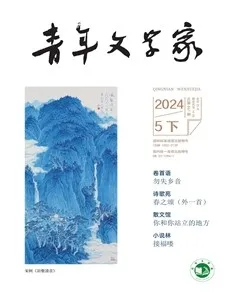《聊齋志異》中的生態美學思想研究
馮霞 楊淳


《聊齋志異》全書共491篇,其中寫狐仙的有70余篇,寫花妖的有4篇,寫牡丹仙女的有2篇。蒲松齡主要以花妖狐鬼為寫作對象,憑借豐富的想象和奇特的故事聞名于世。《聊齋志異》是我國古代自然寫作的典范。生態美學的研究對象是人與生態環境的審美關系,狹義的生態美學思想主要探討人與自然的關系,廣義的生態美學思想包括人與自然、人與自我、人與社會三個層面的關系。生態美學是一種建立在生態哲學基礎上的新型的審美觀,它突破了傳統的以人為中心的思維方式,而將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我的存在和外部環境的影響等因素有機地結合起來。
一、《聊齋志異》中的生態美學思想表現
蒲松齡在《聊齋志異》中描寫了人與社會溫情和諧的生態關系,構建了一個充滿溫情的社會。
(一)人與社會的和諧之美
生態美學強調人與社會的和諧,構造一個理想的社會供人生存是生態美學思想的一部分。
1.用知己之情構建和諧社會
《聊齋志異》中用人與人之間的知己之情構建了一個充滿溫情和正義的社會空間。《聊齋志異》共491篇,其中涉及科舉考試的有107篇,涉及知己之情的有70余篇。在古代社會,科舉考試是士人入仕的唯一途徑,功名就是衡量個體生命價值的標尺。蒲松齡作為一個科場屢屢失利的讀書人,內心迫切地需要得到肯定。因此,他在《聊齋志異》中用人與人之間的知己之情建構出一個人人互相欣賞、互相理解的社會空間。
寫知己之情的代表篇目當推《葉生》。在《葉生》篇中,知縣丁乘鶴十分賞識葉生的才華,也十分器重他。葉生因其的知遇之恩而“零涕不已”。葉生死后仍不忘魂從知己,最后教導丁乘鶴的兒子中舉。
中國傳統封建社會對人的價值評判標準十分單一和苛刻,要想獲得他人的認同就必須取得科舉考試的成功。但是,并非有才者就能高中,有時考官昏聵導致才子被埋沒,才華得不到認可。蒲松齡為不能在科舉中得到認可的落魄書生提供了一條新的道路,用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尊重打造一個充滿希望的社會,每個人都有知己可以賞識自身的才華,不用憑借外界的考核機制,僅僅是憑借自身才學就可以被他人認可。在這樣一個正向的社會空間,人人都被看見、被賞識、被認可,從而形成一個和諧溫情的社會。
2.用男女真情打造溫情人間
《聊齋志異》中重視男女的真情,用真情聯系人與世間的萬物。
男女真情是《聊齋志異》中占比很重的內容。《巧娘》中,傅廉與女鬼巧娘相戀遭到父親的反對,傅生卻始終堅信“彼雖異物,情亦猶人”。《樂仲》中,樂仲和瓊華的相敬如賓,黃生與絳雪的惺惺相惜。《花姑子》中,安幼輿因不能找到心愛女子花姑子的住所而患重病,花姑子寧愿犧牲自己的性命也要復活安生。《連城》中的磨難更加貼近現實,喬生和連城之間因為門第懸殊有了第一重阻礙,且連城已經和有錢的商人王化成定親,這是第二重阻礙,后來喬生割心頭肉給連城治病,連城用死亡抗拒無愛的婚姻,二人在地府相見并復活,終成眷屬。《連城》中,二人跨越階級貧富的限制超越了生死,展現男女真情的動人力量。
男女真情則可以跨越生死,天上人間都互相追隨,把“情”放在了高位,使真情具有感天動地的力量,這是對封建禮教人性束縛的解綁。男女的情感得到肯定,真情可以跨越物種,勾連起自然界的萬物,只要真情在,萬物可共生。《聊齋志異》突出男女真情的可貴,展現向善向美的人文關懷。
(二)人與自我的和諧之美
人類自我的精神生態也是生態系統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人在現實生活中不能得到滿足,就會回到精神世界尋求滿足。
1.對生存困境的超越
蒲松齡在《聊齋志異》中超越了自己現實生存中的困境,在書中找到心靈的慰藉。
蒲松齡19歲就考中秀才,但是在接下來的鄉試中卻屢屢落榜,最后60歲的蒲松齡終于放棄了科舉考試。他將屢試不中的悲痛寫入《聊齋志異》,所以,他的書里總是有那么多懷才不遇的書生才子。他們最后的出路往往是隱居山林,回到鄉村和自然界中,用自然界的山水安慰書生失落的內心。
《聊齋志異》中導致主人公生存困境的大多是黑暗的現實。《賈奉雉》中的賈奉雉不能中舉,但是比他更差的詩文卻能中舉,因此悲憤不平,心灰意冷。《成仙》中的周生因獄卒受到仇人賄賂而差點兒被打死,后來周生和朋友成生一起歸隱山林。《聊齋志異》通過營造仙境,滿足主人公的愿望,讓他們在欲望滿足之后大徹大悟,看破名利之后回歸自然。《白于玉》中的吳青庵本來刻苦讀書,想功成名就之后娶葛太史之女,但是在進入仙境之后,名利財色都得到了滿足而隨仙人游于昆侖山。《續黃粱》篇的主人公曾孝廉在夢中入宮并做了高官,但不久被皇帝流放,在路上被冤民殺死,在冥界被閻王懲罰生前的罪行,受盡折磨。他往日在朝廷作威作福,憑借權勢為非作歹,報應也十分慘烈。夢醒后,他淡泊名利,隱入山林。吳青庵和曾孝廉都曾有財有勢,但是在欲望都被滿足之后,領略的榮華富貴不過轉瞬即逝,只有回歸自然方得徹底的自由。蒲松齡用夢境和仙境滿足主人公的欲望,用他們的徹悟和歸隱表明外在的功名利祿不過是表象,只有在自然界中自由地生活,擺脫物質的束縛,才是人類自我最終的歸宿。
蒲松齡由積極入世到后來開悟歸隱,放棄對科舉名利的追求,把自己的情感投射在書里,把自己的心靈安放在自然里,得到內心的寧靜,從山水之間感受生命存在的意義。
2.對死亡的超脫
《聊齋志異》中創造了一個“樂死”的世界,創造了冥界地府等諸多死亡意象。蒲松齡直面死亡,用來生轉世與因果報應等方式使人的生命不因死亡而徹底斷絕,使生命處于一個循環的狀態。
蒲松齡在《三生》篇中讓人投胎為牲畜,受到鞭打驅役之苦,通過多次投胎轉世讓人的生命形態進行流動,人可以變為動物、植物及自然界的萬物,表明人與自然生物和諧一體,以及生命是一個持續的流動狀態,蘊含現代的生態美學思想。《陸判》篇的朱爾旦希望陸判官能延長自己的壽命,陸判官說:“生死一耳,何必生之為樂,死之為悲?”朱爾旦因此坦然面對死亡。陸判官用對死亡的豁達態度開解了朱爾旦,不把生死看作大事,不因生而快樂,也不因死亡而傷感,用無悲無喜的豁達態度超越生死的束縛。蒲松齡的思想和莊子的“齊死生”有相似之處,莊子認為死生一體。看破生死,那么功名利祿不過是滄海一粟,人若對生死通達,就獲得了徹底的自由。《章阿端》中的戚生和自己死去化鬼的妻子一起生活,“款若平生之歡”,當亡妻要去轉生的時候,戚生發出“本愿長死,不樂生也”的哀嘆。在《聊齋志異》中死亡不是一切的終結,而是再生的契機,如《葉生》中死去的葉生用靈魂的形式依舊可以中舉,死亡相當于給了他二次生命,依舊可以完成生前的愿望。用死亡完成對生命的救贖,用魂靈來超脫對死亡的恐懼,從這方面考慮,《聊齋志異》對人們有精神安慰的價值與意義。
二、《聊齋志異》中的生態美學思想成因
蒲松齡之所以能寫出花妖狐魅與人和諧相處,互為知己的故事,離不開道家思想與個人身世經歷的影響。
(一)受前代道家思想的影響
蒲松齡受道家的影響,描繪了一幅人與世間萬物和諧共處的大同社會圖景。蒲松齡使人與動物和諧共處,人與自然界中的動物植物甚至可以結為夫妻或者成為至交好友,和道家主張的萬物同一是一脈相承的。道家主張回歸自然,把人同世間的萬事萬物都融匯在“道”中,在“天籟”和“自然”中達到生命的和諧狀態。
《聊齋志異》中也有類似的故事體現道家回歸自然的思想,比如《黃英》篇中的菊花精怪都姓陶,種植菊花、喜好菊花,是菊花的化身,兩姐弟的人物原型就是隱士陶淵明。這個故事無疑寄托了蒲松齡對于道家文化的認同。以老莊為代表的道家文化在兩千年前就致力于思考人與自然的關系,提出“天人合一”等一系列熱愛自然、保護自然、尊重自然的生態思想,是我們不可或缺的生態美學的精神財富,對于中國乃至世界的生態美學思想提供建構意義。蒲松齡的花妖狐魅與人類和諧共處的生活圖景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老莊哲學的影響。
(二)個人身世經歷的影響
在《聊齋志異·自志》中,蒲松齡自白“知我者”在“青林黑塞”。蒲松齡在《聊齋志異》中數次發出知己難求的感嘆,最后只能在青山綠水的自然界中與花妖狐魅成為精神上的知己,以“青林黑塞”為代表的自然寄托了自己的理想。發出這種感嘆與蒲松齡坎坷的科舉經歷與曲折的人生境遇有關。對于生活中的挫折與苦難,蒲松齡只能在孕育花妖狐魅的自然界中得到療愈和抒發。因此,《聊齋志異》中描寫了很多窮苦書生得到佳人青睞,在花妖狐魅化身后的美人幫助下科舉中榜而功成名就的故事。蒲松齡的感情生活也十分的貧乏,其妻劉氏是一個平凡樸素的女子,二人在生活中相互扶持,但在精神上的溝通卻十分貧乏。且蒲松齡離家為吏,二人長年分居兩地,身處異地他鄉、客居他人屋檐之下的蒲松齡,生活得十分孤獨寂寥。因此,《聊齋志異》中才會產生一篇篇抒寫男女真情的愛情故事。
三、《聊齋志異》中的生態美學思想價值
《聊齋志異》中生態美學思想與后世的不少作品有相通的地方,后世作品繼承了其作品中的生態美學思想并繼續加以發揚。
(一)提供生態美學創作實踐的重要范例
蒲松齡從非人類世界出發來思考人和自然萬物的生存問題。蒲松齡通過構建一個萬物有靈的世界,使《聊齋志異》成為一個生態美學創作實踐的重要范例。
《聊齋志異》中包含了敬畏自然的內涵,表現出對生命及生命相互關系的理解,要求人類尊重所有生命,要求人類順應自然,做到物我合一。《聊齋志異》中大量描寫人與社會和諧共生的內容,其對人自我生存困境的超越及對直面死亡恐懼的超脫,這些內容都是值得現代人借鑒和思考的。
(二)展現“愛生”的生態美學思想
《聊齋志異》中人與自然萬物和諧共生的故事讓人和自然界的生命進行連接,產生生命共通共感的情節和當代倫理學一脈相承,書中建構了一個人與自然合二為一的世界,是中國古人“愛生”傳統的延續。
《聊齋志異》的故事不再局限于人類,涵蓋了宇宙之間的各種生物。蒲松齡站在動植物的角度思考故事,展現了動植物本身所具有的特點與性格,不違背它們的物性。這種與自然萬物密切接觸的眼光使得生活中尋常的事物都能成為審美的對象,蜜蜂、老鼠、虎、墓地、古寺都能演繹出一段奇妙的故事。儒家自古就有“質于愛民,以下至于鳥獸昆蟲莫不愛”(董仲舒《春秋繁露·仁義法》)的“愛生”傳統,佛家也有愛護生命的“愛生”文化。蒲松齡吸收“愛生”的文化傳統,讓故事中主人公展現惻隱之心,對自然界的動植物有愛護幫助的同情心,使得生命可以突破困境,甚至還有再生的機會,展現出作者對生命的珍惜之情。蒲松齡喜愛自然的性格讓他所寫的故事充滿對自然生命的關注與愛護,這正是《聊齋志異》中生態美學思想的體現。
對于人類自身而言,自然界的萬物都是他者。蒲松齡對于他者有關懷愛護之心,正因為他看到他者的價值,才會讓植物、動物都進入他創作的理想世界,生態美學中對生命的關懷在《聊齋志異》中得以展現。《聊齋志異》中的對自然界萬物生命的關懷、人與自然界生死與共的感情和生態美學文化具有同一性,既是對傳統文化的繼承,也對后代生態美學建構有補充和啟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