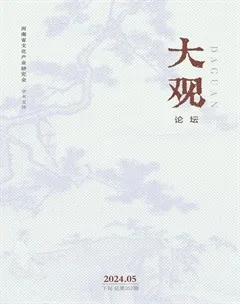趙孟頫“書畫本來同”的審美意趣研究
王耀輝
摘 要:“書畫本來同”理論是趙孟頫重要的繪畫理論之一,在元代繪畫發展的過程中產生了廣泛影響,并被后來者所推崇。結合趙孟頫作品的特點對“書畫本來同”進行理論分析,旨在探討“書畫本來同”在繪畫中的體現,揭示趙孟頫繪畫作品中所蘊藏的“書畫本來同”的審美意趣。
關鍵詞:趙孟頫;“書畫本來同”;中國畫;書法;書畫
趙孟頫,字子昂,謚文敏,一生“榮際五朝、名滿四海”。其身份特殊,乃宋太祖之子秦王德芳后裔。趙孟頫才華橫溢,青年時便享譽四方,為“吳興八俊”之一。身為宋皇室后裔的他,卻在仕元的背景下引領了元代繪畫的發展,被董其昌推為“元代冠冕”。趙孟頫在中國藝術史上成就斐然,在書畫上有大量作品傳世,無論是書法還是繪畫,都對當時及后世有著深遠影響。在繪畫理論方面亦是如此,良好的藝術成長經歷使趙孟頫對書畫具有獨到的見解,其中“貴有古意”和“書畫本來同”理論對后世的影響尤為深遠。“貴有古意”思想主要體現在繪畫品評、思想內涵方面,貫穿趙孟頫對所有藝術的理解和指引。而“書畫本來同”更偏向繪畫實踐的技法層面,是趙孟頫關于繪畫的一則重要論述,用淺顯易通的古詩方式闡述了書法用筆的基本內涵,是趙孟頫引領元代繪畫發展、開拓元代文人畫的重要理論之一。兩則理論相輔相成,乃趙孟頫繪畫理論體系的兩大支柱。
一、趙孟頫“書畫本來同”理論分析
清代石濤言“筆墨當隨時代”,特殊的文化背景對文藝有著深刻影響。藝術風格雖沒有明確的時間界限,但是放眼每個歷史時期的文藝發展,其特點又是那般鮮明,例如唐詩、宋詞、元曲等等,這也是為什么解讀作品前要先了解其時代背景。趙孟頫生活于宋末元初時期,當時社會動蕩不安,“隱逸”思想盛行,尤其是失意的文人們,他們寄情山水、托物言志,暗諷元代社會。文人士夫們寄情筆墨,在橫涂豎抹之間釋放他們的情感,例如“元四家”之一的倪瓚曾言“仆之所謂畫者,不過逸筆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娛耳”,使野逸一脈在這個時代迎來了大發展。各個行業的發展充滿坎坷,藝術的發展也急需扭轉頹勢,宋末“纖細、濃艷”的畫風是趙孟頫所反對的。他針砭時弊,提出“貴古”思想,以正“簡率雅正”之風氣。趙孟頫提出的“書畫本來同”理論暗合了文人士夫的心境,其也引領了元代“墨花墨禽”的時代風格。
歷朝歷代都或多或少掀起過復古運動。倡導者試圖以“復古”的大旗開拓新的風尚,這與傳統文化有很大關系。趙孟頫便是這樣,他對元代文藝事業的貢獻離不開他對“崇古、復古”的推動,這主要體現在他“貴有古意”的論述上,即“作畫貴有古意,若無古意,雖工無益。今人但知用筆纖細,傅色濃艷,便自為能手。殊不知古意既虧,百病橫生,豈可觀也?吾所作畫,似乎簡率,然識者知其近古,故以為佳。此可為知者道,不為不知者說也”。由此可知,趙孟頫的“貴有古意”顯然不是照搬照抄,而是借古開今,扭轉時弊,開拓新風。
趙孟頫的書法理念與繪畫思想都屬于崇古一脈。他針對當時的藝術氛圍提出了一系列類似主張,以圖扭轉、引領當時書畫的發展和變革。他在書法方面同樣高舉復古旗幟,主張遠師晉唐,遍臨二王、褚遂良、智永等諸家,認真鉆研,融會貫通,也有了自己的風格和特點,且真、草、隸、篆、行皆通,傳世作品眾多,著名的有《洛神賦》《湖州妙嚴寺記》《前后赤壁賦》《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等。從趙孟頫巨大的作品量以及他的論述資料可以得知,趙孟頫在書法方面用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來反思和總結,并引領了元代書法的發展。趙孟頫的成就在書法史上是少有的,對后人產生了深遠影響,并且獲得了極高的評價。
趙孟頫在繪畫上力追唐宋,在探索實踐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繪畫風格。至元代,中國傳統繪畫體系基本完備,前人在理論和實踐層面皆留下了豐碩成果。趙孟頫“書畫本來同”的理論繞不開文人士夫繪畫的發展。文人畫由來已久,自元朝之前的唐宋就已發端,但是富貴妍麗的畫風歷來被皇家所重視。縱觀中國美術史,文人畫的高峰在元代,是當時畫壇的主流。在古代能詩善文的人并不多,多是文人、士大夫,這類人還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書法造詣頗高,因此文人畫歷來主張“以書入畫”以及“不求形似”。趙孟頫自然也是其中的一分子。但是在趙孟頫之前的諸家,仍不免落于形似的窠臼,這一點從畫家文同的《墨竹圖》中便可以看到。在這一方面,學者王連起表示:“只有到了趙孟頫,才完成了蘭竹題材從‘畫到‘寫這個從自在到自覺的認識上的飛躍。”研究趙孟頫的作品不難發現,其同之前的文人畫家神交已久,有學者表示“趙子昂有條件觀覽蘇東坡的枯木竹石作品并有所取法,是可以想見的。分析趙孟頫枯木竹石之作,不難看出他對蘇東坡的繼承與變異”[1]。對比趙孟頫的《蘭花竹石圖》《秀石疏林圖》與蘇軾的《瀟湘竹石圖》《枯木怪石圖》不難發現,二者在構圖、筆墨、韻味上有相近之處。
“書畫本來同”理論以七言古詩的形式呈現,“石如飛白木如籀,寫竹還應八法通”這兩句為“書畫本來同”論述的上闋,從客觀層面論述了書法與具體物象之間的關系。趙孟頫將畫“石”與“飛白”書相結合,將“木”與“籀”書相結合,將寫“竹”與“永”字八法相結合。通俗地講,趙孟頫將“飛白書”“籀”“八法”作為自身以物傳情而達到“天人合一”的外化手段。后人也多有類似的論述,如:柯九思運用書法畫竹,認為“寫竹干用篆法……木石用折釵股、屋漏痕之遺意”;楊維楨指明“士大夫工畫者必工書,其畫法即書法所在”;明代董其昌指出“士人作畫,當以草隸奇字之法為之”[2]。
然而趙孟頫并不是第一個對飛白書展開論述的人,宋代米芾就曾言“江南陳常以飛白筆作樹石”,至趙孟頫則進一步推動,形象而具體地表達了書法與繪畫的直接關系。在元代這一現象更加廣泛。趙孟頫所提到的“飛白”為東漢蔡邕所創,張懷瑾《書斷》載:“蔡邕作《圣皇篇》,篇成,詣鴻都門上。時方修飾鴻都門,伯喈待詔門下,見役人以堊帚成字,心有悅焉,歸而為飛白之書”。“飛白”書具有灑脫、蒼澀、渾然天成的特點,與石頭斑駁干澀的形象氣質較為吻合,二者的美感特點有相似之處;而“木如籀”的“籀”書即籀文,也叫籀書、大篆。大篆結體可參照《石鼓文》。從現存資料來看,大篆石鼓文字形結體自然、古樸厚重,與趙孟頫作品中的古木形象較為接近,趙孟頫的巧妙嫁接拉近了書畫之間的關系,在“不求形似”上推動了書法意味的融入。
“寫竹還應八法通”中的“竹”是指竹題材作品。在中國畫的歷史長河中,竹畫數量巨大,名家輩出,風格迥異,自唐起就有蕭悅、程修己等人,宋代則有文同、蘇軾等人。中國人對竹題材具有別樣的情思,竹子與人的情感、人品、道德取向有很強的關聯,內含著中國文化的精髓,承載著傳統文化中“堅韌、虛心、不畏嚴寒、寧折不屈”的優良品質。竹題材在文人畫中更是十分常見,例如在畫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同的《墨竹圖》。北宋的文人畫思潮就是以蘇軾評述文同的作品為起點的,蘇軾與米芾等人推動了文人畫的發展。蘇軾竹題材的畫作也有很多,例如藏于中國美術館的《瀟湘竹石圖》。發展至元代,竹畫更是蔚然成風,趙孟頫也不例外,佳作頻出,且和管道升合作了若干作品。元代除了趙孟頫、管道升二人外,畫竹名家輩出,例如柯九思、倪瓚、顧安、吳鎮等等。顯而易見,在這樣的環境中,墨竹作品量巨大,且墨竹畫諸事完備。
“寫竹”之“八法”可以參考“永”字八法,即書寫“永”字時的八種用筆。以《蘭亭序》“永和九年”的“永”字書寫為例,順序為:側,側鋒鋪毫;勒,逆鋒急回;弩,曲中見直;趯,駐鋒提筆;策,起收得力;掠,力要送到;啄,快而峻利;磔,逆鋒輕落。永字八法的書寫符合竹畫“八面出鋒”的特征,趙孟頫進一步點明了書法用筆與繪畫用筆之間的共性。
二、“書畫本來同”在作品中的具體體現
書法在繪畫中的運用,歷來都是中國繪畫、中國書法藝術的討論核心。張彥遠言“無以傳其意,故有書;無以見其形,故有畫”,無論是當代還是古代,都有大量的論述從不同的角度涉及二者,如畫家從實踐造型的角度,書法家從篇幅、結體的角度,史論家從書畫史的角度,等等。其中與趙孟頫相關的也有很多,例如:明代唐寅言“工畫如楷書,寫意如草圣”,郭若虛在《圖畫見聞志》中寫道“畫衣紋林木,用筆全類于書”。這些都是類似于趙孟頫“書畫本來同”的論證[3]。
“書畫本來同”論述以題跋的形式落于趙孟頫的《秀石疏林圖》畫尾,該作品的題材為竹子、土坡、亂石。趙孟頫對此類題材作品較為偏愛,翻開繪畫資料以及歷代畫論,不難發現趙孟頫竹石枯木的繪畫題材在元代就廣受推崇,但現存類似風格作品的數量并不多,據王連起考證有《蘭花竹石圖》《枯木竹石圖》《窠木竹石圖》《古木竹石圖》等,除部分真跡外,還摻雜了后人偽造的贗品,如《秀石疏林圖》《竹樹野石圖》《山雞棘竹圖》等[4]。趙孟頫以書入畫的代表作品多采用書寫性線條,線條的不同質感體現了他對毛筆這一工具超強的控制力,也體現了他的書法功底和審美追求。
《秀石疏林圖》中的線條質感多樣,是張彥遠“運墨而五色具”的客觀體現,整張作品的墨色自由灑脫,焦、重、濃、淡、清運用合理,粗、細、剛、柔之間富有節奏的韻律。趙孟頫通過個人審美,運用線條將不同的物象藝術性地表現了出來,創作出了一幅幅富有古意和美感節奏的作品。結合趙孟頫“貴有古意”思想中的“吾所作畫,似乎簡率”來欣賞這幅作品,不難發現趙孟頫的“簡率”風貌。趙孟頫在表達物象時書寫性極強,能體會到筆墨流淌、滲透之感,而不僅僅停留在物理層面的表達,實現了畫理與物理的結合。因此,援書入畫也是其追求“不求形似”“簡率古意”的手段,體現了趙孟頫對繪畫的深刻認識和審美追求,同時也暗合張彥遠“上古之畫,跡簡意澹而雅正”的審美內涵和風格態勢。
中國畫與書法的工具都是毛筆,這與西方繪畫不同,因此中國畫和西方繪畫在作品面貌上產生了諸多差異。中國畫發展至今,無論是寫實的工筆,還是抽象的寫意,都會強調書法的練習。錐子型毛筆這一工具在中國人手里,可以產生千變萬化的形象。黃賓虹提出了“五筆”之說,即“平(如錐畫沙)、圓(如折拆股)、留(如屋漏痕)、重(如高山墜石)、變(四時疊運)”,這些用筆在書法里也能找到類似的。部分學者認為書畫二者分別具有各自的評價體系,并無相通之處。這樣的說法未免有些偏激。就對毛筆的控制而言,在如今高校中國畫的教學中,學生初用毛筆皆會有手抖、手痛的表現,在這種情況下,教師一般會督促他們加強書法的練習。而在經過一段時間的練習后,學生在繪畫中的控筆能力顯著提升。可見,書法的練習對繪畫控筆能力的提升有重要作用。因此,書畫之間必然存在著某些聯系,而至于品評、風格等,可能有些不同。
除客觀用筆的技法和變化外,中國畫還賦予了用筆諸多內涵,且將其與墨并稱為“筆墨”。翻閱歷代畫論不難發現,關于筆墨內涵的論述比比皆是,例如清代笪重光的“墨以筆為筋骨,筆以墨為精英”、沈宗騫的“筆為墨帥,墨為筆充”等等。在歷代畫家、史論家眼中,筆、墨不僅僅是工具,它們同梅、蘭、竹、菊一樣被人格化和理想化了。趙孟頫《秀石疏林圖》中對枯木、竹石的描繪,既是筆墨的外化形象,又是趙孟頫筆性、心性的跡化。
趙孟頫的“貴有古意”論述影響深遠,其“簡率”的表達更是與張彥遠“上古之畫,跡簡意澹而雅正”的論述有一定相似之處。不難看出,趙孟頫在書畫上“崇古、復古”的主張也是沿著畫論文脈這一條線得出的。而趙孟頫枯木竹石一類的作品皆為“簡率”的代表性作品,可見“貴有古意”中的“簡率”與“書畫本來同”有著本質上的聯系。“書畫本來同”傳達著“簡率古意”“不求形似”“天人合一”的審美意趣。趙孟頫所闡述的“書”與“畫”的關系,進一步說明了中國傳統的“書”與“畫”各成體系又密不可分。回望中國美術史可以發現,擅畫者皆能書,擅書者皆能畫,例如王維、蘇軾、米芾、文徵明、朱耷、潘天壽、吳昌碩、齊白石等等。
參考文獻:
[1]薛永年.趙孟頫的古木竹石圖與書畫關系[J].收藏家,2021(10):147-152.
[2]王秀金.探析趙孟頫“書畫同源”思想[J].美與時代(中),2021(12):12-13.
[3]周積寅.中國畫論輯要[M].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2005:531-552.
[4]王連起.師古還是求新:趙孟頫的藝術與時代[M].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19:56-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