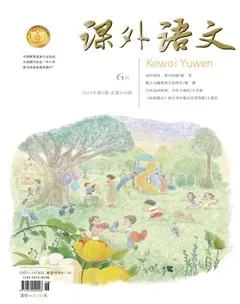把握線索,條理清晰
嚴婧靚

記敘文是“三大文體”(另外兩個是說明文和議論文)之一,記敘文是“以記人、敘事、寫景、狀物為主,以寫人物的經歷和事物發展變化為主要內容的一種文體形式”,是作者把自己的親身感受和經歷,通過生動、形象的語言,描述給讀者,讓讀者對所寫之事、人、物無形當中產生深刻的印象。記敘文包括的范圍很廣,嚴格意義上來講,初中教材中的記人記事類文章,如日記、游記、傳說、新聞、通訊、小說等,都屬于記敘文的范疇,更是中考最常見的文體考查類型。在這樣的背景下,記敘文的寫作顯得尤為重要。
但是要寫好記敘文并不容易,前文我們談及記敘文不但形式種類多,而且不同的形式有不同的寫作技巧和特色。比方說,通訊類的如《誰是最可愛的人》,作者魏巍將目光觸及抗美援朝戰爭中的人物與故事,讓人感動和敬佩;小說類的如《范進中舉》,作者以范進這個人物為中心,寫了范進以及他身邊的人的幾件事情,讓人唏噓和感嘆……雖然形式種類不同,但是有一點務必要做到,那就是要把握敘述的線索,這樣才能跟隨作者的思路抽絲剝繭理順故事的各個環節,這樣寫出來的文章才能條理清晰。
那么,什么是線索呢?線索就是貫穿全文始終、串聯情節發展的一條脈絡,它能把所有的材料、情節、人物聯結成一個有機的整體,能夠讓整篇文章條理清楚,層次清晰。在現實當中,很多同學的作文缺乏線索,作文的情節發展就欠缺邏輯性,可見,線索是多么重要。那么記敘文的線索有什么類型呢?
一、線索的外顯——明線
所謂“明線”,就是“明眼人”能夠看得見、梳理得明明白白的東西,具體說來可以細分為:
(一)以具體的物品為線索
在寫作的時候,我們可以以一個具體的或有某種象征意義的實物貫穿全文,將各種人或事都集中到它的周圍,以此來展開故事情節。比方說,在著名的童話故事《皇帝的新裝》里面,“新裝”就是一個重要的物品線索,它貫穿著這篇童話的始終,從兩個騙子粉墨登場謀劃制作“新裝”開始,一直到兩個大臣監督“新裝”,到兩個騙子制作“新裝”,再到皇帝展現“新裝”,最后到揭秘“新裝”,“新裝”這個物品始終存在,并將各種人或事都集中到它的周圍,以此來展開故事情節。“新裝”也諷刺了皇帝的昏庸及大小官吏的虛偽、奸詐,可謂是意蘊十足。這就給我們以啟發。我們面對一篇中考作文的時候,在確定中心之后,不妨設置一個具體的物品,以此開展記敘文寫作。比方說在2023年的上海卷以“會心之樂”為標題的作文當中,一個考生以當地最美味的食物——豬肉丸子作為線索,串聯起兒時的小院子和現在生活的小區,兩個生活圈子記載著兩個不同時代的人和事,讓人頓覺時代生活的進步和美好。
(二)以具體的事件為線索
這里的“事件”主要以某一種中心事件為線索。情節通常包括事件的開端、發展、高潮、結局等幾部分。有些文章事件本身便是線索,如莫懷戚的《散步》一文,就是以“散步”這一事件作為線索,文章緊緊圍繞散步這一中心事件,寫了事情的起因(過了冬天,但母親身體不好,要母親多走走)、經過(散步中發生走大路或小路的分歧)、結果(母親順從孫兒,走小路),三件事件串聯在一起,表達了和諧、孝順的主題。
(三)以具體的人物為線索
這一點非常容易理解,顧名思義,就是在記敘文當中,以刻畫人物為中心,但需要指出的是,人與事是密不可分的,畢竟敘述事件的目的就是呈現人物的個性和品質。比方說在朱德的《回憶我的母親》中,作者以“母親”為線索,記述了在“我”童年時和少年時代,母親對“我”影響較大的幾件事。在2023年北京卷《我讀到的北京》的一篇作文中,一個小作者就是緊緊圍繞一個工人伯伯來寫,寫他無私奉獻砌損壞的花壇,寫他樂觀豁達面對眾人的不解,兩件小事都薈萃到他高尚的人格上面來,讓人動情和贊嘆。
(四)以具體地點為線索
這里說的是以地點的轉換來安排文章的結構和層次,其中地點就是敘事的線索。在魯迅的兩篇文章中就有這樣的線索安排。其一是《藤野先生》,它以“我”的活動地點為線索安排情節,從東京到仙臺,再到北京層層地點變化展開描述。其二是《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這篇文章的標題自身就是地點的轉換,兩個地點成了魯迅一生當中難忘的記憶。2023年南京卷出現了這樣的一篇滿分作文——《大西北的獨家記憶》,小作者回顧了自己暑假的一個親身經歷,從蘭州到武威再到甘南,從黃土高原到敦煌壁畫再到連綿草原,小作者見證了光輝燦爛的歷史文化,非常貼合題干的要求,顯得情真意切。
(五)以具體時間為線索
顧名思義,文章是以時間的推移來組織材料,于是,“時間”就成為貫穿全文的一條線索。散文式的記敘文《金色花》就是其中的典型,這篇文章以孩子的口吻來寫,主要寫孩子變成金色花后與媽媽一天的游戲玩鬧,文章當中有幾個推動故事情節發展的時間標志——“當你沐浴后做禱告”“吃過午飯”“黃昏時”,這些詞語表示一天內時間的推移,讓我們感受到一種濃濃的母子之情,也體現出“我”對母親最圣潔、最美麗的愛。在2023年北京卷《我讀到的北京》中,一個學生以“穿越者”的身份,記錄了自己三次“穿越”北京的時間——鴉片戰爭、1949年國慶、北京奧運,這就是用時間的順序寫就的創新之作。
二、線索的內在——暗線
所謂“暗線”,就是那些并不能通過文本的字里行間看出的線索,一般指人的情感態度和思想觀念,而這比較“隱晦”,需要我們非下一番功夫不可。這里,我們可以通過兩篇文章來作為示例進行分析:
第一,是史鐵生的《秋天的懷念》。作者沉浸在自己雙腿癱瘓的不幸之中,忽略了母親的感受。他并沒有真正理解自己母親的悲傷,作者對母親的態度一直都在發生著變化。例如他從漠視到理解,從理解到頓悟,從頓悟到愧疚,從愧疚到自責,從自責到懷念,這一系列的轉折作為作者的、文章的情感線索,歌頌了真摯的、純真的母愛,表達了對母親深切的懷念和無盡的愛,讓人也產生了深刻的共鳴,遙遠的古代那句傳誦的詩篇似乎也在耳邊傳響——“游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
第二,是魯迅的《阿長與〈山海經〉》。作者對阿長的態度也在不斷“演化”當中,開始的時候,由于長媽媽“常喜歡切切察察,向人們低聲絮說些什么事”,有時也能引起點家里的“小風波”,因此,“我”憎惡她、討厭她;后來,發現她迷信,不但禮節多,規矩也多,于是,“我”顯得十分不耐煩;在她為“我”購買了《山海經》之后,“我似乎遇著了一個霹靂,全體都震悚起來”,衍生了“空前的敬意”;到最后,發出由衷的祝福——“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懷里永安她的魂靈”。一連串的情感的態度的變化,表達了“我”對長媽媽的尊敬、感激、懷念和祝愿之情,顯得情真意切。
需要指出的是,要想一篇記敘文出色,所設置的線索應不止一條,我們需要將明線和暗線相互交織在一起,比方說《藤野先生》(暗線是表達了對藤野先生高尚人格的贊美)和《阿長與〈山海經〉》(明線是阿長這個人物和《山海經》一書),這樣寫出來的記敘文更加引人入勝,不但讓人對人物饒有興致,還會顯得情節跌宕起伏,讓人沉迷于故事情節當中。無獨有偶,在2023年懷化卷《那夜的月圓》當中,小作者巧設了“月亮”這個事物,寫父親經歷一年的顛簸生活回到了故鄉跟家人團聚,這是一條明線,但是實際上,文章中還有一條暗線——由己及人,祝愿天下的家庭都能團團圓圓,家庭和睦,代表著中華民族幾千年的祈愿和追求,讓人拍案叫絕。
眾所周知,閱讀時需要我們抓住文本的線索,只有這樣才能掌握段落結構,領會文本的中心思想。寫作文時,也是一樣,只要設定了作文的線索,在實際的寫作過程中就能做到圍繞中心,組織材料,使文章中心明確、條理井然,顯得內容集中、脈絡清晰。因此,在實際的寫作中,我們需要用一根“線”把事件按一定順序連起來,讓這些材料表達一個完整的意思,這根“線”就是記敘文的線索。如果有好的材料加持,再加上有使之連貫的線索,那么文章就會形式上動人,情節上感人,就像一串美麗的珍珠一樣散發著光芒,引發讀者的深切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