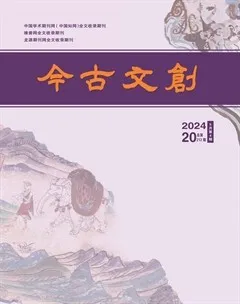中國古典 “ 扇 ” 意象的隱與顯
廖銀潔
【摘要】“扇”是生活器具與文化象征結合的典型之一,我國自古就有文學作品中的“扇”意象與作為扇書扇畫藝術載體的“扇”物象。本文主要探討“扇”的文學意蘊和審美意蘊的發展路徑與呈現方式,以此來觀照中國傳統內斂、藏鋒、空遠的文化心態和審美傾向。
【關鍵詞】“扇”;象征;隱;審美觀照
【中圖分類號】I207?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4)20-0035-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20.011
“扇”是自古流傳至今的生活器具,它自堯舜時期就已經出現,古籍中有“舜作五明扇”的記錄。在我國古代,“扇”主要分為用于宮廷儀式的儀仗扇,與用于納涼避暑、以實用性為主的扇子,按照其形狀或制作材料,又可以細分為紈扇、團扇、羽扇、蒲扇、折扇等不同種類的扇子。
回顧文學史,作為生活器具的“扇”作為意象首次進入文學創作領域,可以追溯到西漢班婕妤創作的五言詩《怨歌行》,此詩以物喻人,開啟了“扇”作為女子閨怨意象的傳統,其后,許多男性詩人也以“扇”意象擬作代言體表達女子閨怨。但“扇”意象的內涵并未止步于此,文人畫師在“扇”的器具性、象征性、審美性的基礎上,以不同的延展方式,深化了“扇”意象的文學意蘊和審美意蘊,具體呈現于“扇”意象“隱”與“顯”不同的表現形式上,反映了不同時期的文化心態與審美傾向。
一、秋風團扇:器具性的隱與顯
西漢班婕妤的《怨歌行》是現存最早的詠扇詩,《樂府詩集·相和歌辭》解釋道:“漢成帝班婕妤失寵,求供養太后于長信宮,乃作怨詩以自傷。托辭于紈扇云。” ①《怨歌行》全詩為:“新裂齊紈素,鮮潔如霜雪。裁為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飆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怨歌行》前兩句描寫了合歡扇的制作過程,及其潔白、圓整的扇體特征,后兩句表現出一種憂慮不安的心態,擔心涼爽的秋風到來之際,自己將無用武之地,被棄于篋笥之中。整首詩以詠物來比擬人,結合創作背景,后人將其解讀為班婕妤失寵后的哀怨之情,“霜雪”自比詩人品質的高潔,“合歡”“明月”隱藏了詩人對圓滿愛情的向往,“棄捐篋笥中”揭示了深宮女子容顏不再、終將被拋棄的悲劇命運。從此詩之后,“團扇”就與“明月”、“秋風”的自然意象聯系起來,“團扇”寄托了對圓滿如明月的向往,“秋風”隱喻著女子被拋棄的命運,“秋風團扇”共同營造了哀婉、悲涼的情感氛圍。
此后,大量仿擬《怨歌行》的代言體出現,以“團扇”為典故,表達被代言女子的閨閣愁怨,例如蕭綱《有所思》寫道:“掩閨泣團扇,羅幌詠蘼蕪”,徐湛《賦得班去趙姬升詩》寫道:“今日悲團扇,非是為秋風”,但大多創作并未脫離女子哀怨之情的范疇。
班婕妤出身名門,入宮前深受詩書禮儀文化的熏陶,后人給予了班婕妤很高的道德評價,傅玄作《班婕妤畫贊》稱贊道:“斌斌婕妤,履正修文。進辭同輦,以禮匡君。納侍顯德,讜對解紛。退身避害,志邈浮云”。可見,班婕妤是一個被典型化的道德女性,符合儒家對女子溫厚端莊的道德要求。班婕妤的高潔品質、“團扇”因秋風見棄的無奈命運,使得文人們紛紛將“團扇”所蘊含的閨怨之情延伸到君臣關系之中,唐有李白寫道:“芙蓉老秋霜,團扇羞網塵”,宋有辛棄疾寫道:“年年團扇怨秋風,愁絕寶杯空”。“團扇”以典故和比擬的修辭進入詩境,表達詩人被棄、不被重用的無奈、哀傷,由深宮冷院的閨怨之情到文人士子懷才不遇的失落之意,“團扇”意象的象征性逐漸確立起來。“秋”意之悲涼滲透進了“團扇”的感情基調之中,抒情主人公卻不過分執著于見棄的命運,表現出一種“哀而不傷”的詩歌傳統。
由于漢代的政治教化影響,漢代另有一部分文人另辟蹊徑,將“團扇”由被迫隱匿的客體,逆轉為主動選擇隱匿的主體,從這一層面上,賦予“團扇”以“知進退、守規矩”的儒家道德要求。例如東漢崔骃《扇銘》云:“翩翩此扇,輔相君子。屈伸施張,時至時否”,傅毅《扇銘》云:“冬則龍潛,夏則鳳舉。知進知退,隨時出處”,文人將“扇”抵御炎暑的實用功能提高到“輔相君子”的政治高度,“潛舉、屈伸”表示士人應時而動的主觀選擇,因此,“扇”的用與不用象征著士人知進退、守禮節、懂得潛藏的政治智慧,所謂“知進退”暗含了儒家等級鮮明、尊卑有序的政治理念。“扇”因其器具實用性的“藏”與“用”與歷代士人“出世”與“入世”的人生選擇兩相呼應,深化了“扇”意象的政治內涵,又為文人政治化的傳統增加了新的表達意象。
二、名士美人:象征性的隱與顯
除去避暑納涼的器具價值外,“扇”因其形貌、質地的優美精致,且隨侍于人左右,具有很好的裝飾性,成為古代服飾的重要配飾之一,并且使用“扇”不同的動作姿勢會影響人的儀態之美,“扇”逐漸成為了不同社會身份、不同性別群體的符號與象征。
“扇”往往與宮女、閨閣女子或妓女的日常裝扮聯系起來,“扇”可視為女子閨閣之物,用來遮掩容貌,維護未出閣女子的矜持端莊,晏殊云“仙女出游知遠近,羞借問,饒將綠扇遮紅粉”,女子為了遮羞,以“扇”遮掩美麗容貌,更顯得女子的嬌媚可愛。女子以扇遮面的動作,具有“猶抱琵琶半遮面”、欲說還羞的表現效果,與中國古典的含蓄美、蘊藉美相通。“扇”的掩面功能,還可以延伸到南北朝至唐宋的“卻扇”婚俗,“卻扇”是婚禮的重要儀式,女子出嫁時須手執紈扇或花扇,由新郎家“卻扇”,也稱為“去扇”或“除扇”,《世說新語·假譎》載“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 ②,梁何遜《看伏郎新婚詩》寫道:“何如花燭夜,輕扇掩紅妝”,這都是傳統“卻扇”婚俗的記錄與寫照。到南宋時期,“卻扇”習俗逐漸被“蓋頭”所取代,“扇”的遮面功能卻得到了延續。新娘“遮面”,新郎“卻扇”,賦予了“扇”以象征性,婚禮中新娘面龐由隱到顯的儀式性動作,象征著閨閣女子出閣、嫁為人婦的過程。
梁簡文帝《舞賦》云:“扇才移而動步,鞞輕宣而逐吟。”南北朝秦樓楚館中的舞妓已將“扇”作為歌舞表演的藝術道具,伴隨著翩翩起舞的曼妙舞姿,“舞扇”的動作姿態得到了更為動人的藝術彰顯。“扇”與身體動作的聯接使其成為舞姿的重要表現形式,與女性的動作儀態之美互相映襯,展現了女性欲說還羞的風致。
不同于閨閣女子的閨閣之“扇”,舞妓以“扇”遮面無關乎維護女子矜持,“扇”與歌舞結合,更在于以“遮面”的姿態達到“傳情”的表達效果,表現女性柔媚婉轉的風韻。“扇”由女性情感的隱匿轉向男女戀情的情感互動,更加張揚肆意,以至發展到宮體詩中的艷情詩,往往以“扇”來喻男女情愛,情感表達更加露骨,不受封建禮法制約。如蕭綱《和徐錄事見內人作臥具詩》“且共雕暖爐,非同團扇捐”,庾肩吾《和徐主簿望月詩》“愿以重光曲,承君歌扇塵”等,都或隱或顯地表現了男女之間的情愛。
“扇”也是男子身份的符號與象征,相較于女子的“隱”,與男子有關的“扇”意象具有更加開闊、張揚的“顯”的氣質。裴啟《語林》記載:“諸葛武侯與宣皇在渭濱,將戰,宣皇戎服蒞事,使人密覘武侯,乃乘素輿,著葛巾,持白羽扇,指麾三軍。眾軍皆隨其進止。宣皇聞而嘆曰:‘諸葛君可謂名士矣。” ③諸葛亮儒雅睿智、運籌帷幄的儒將形象,臨危不懼、安然自如的名士風流,在一次次文學描繪的疊加中,與“羽扇綸巾”的外表形象逐漸重合起來,“羽扇綸巾”成為了諸葛亮固化的人物形象特征。“扇”意象因此帶有了士人理想的色彩,多有文人將自己指麾三軍、征戰沙場的政治理想寄托于“扇”意象的書寫之中,蘇軾的“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晁補之的“想東山謝守,綸巾羽扇,高歌下,青天半”,都表現了對“羽扇綸巾”所象征的建功立業的政治理想的神往,與現實中自己仕途不順、懷才不遇的郁結無奈之情。
《語林》中載荀彧與孔嵩之語“昔與子搖扇俱游太學” ④,早在魏晉時期,由于崇尚清談,好品評人物,重視人物外在的風神氣質,“扇”已經成為名士風流的身份象征,體現了一種雅致的文人意趣。“扇”的名士氣質便寓于“搖扇”這一風流儒雅、閑逸灑脫的動作之中,羽扇更給人以飄飄欲仙、超脫凡世的凌云之感,“扇”可視為一種動作道具,輔以展現男子展扇、搖扇動作儀態的雅致超脫。李白所作的“懶搖白羽扇,裸體青林中。脫巾掛石壁,露頂灑松風”,其飄逸灑脫、不為禮法拘束的風度與魏晉時期的竹林七賢形成了跨越時空的呼應。
與男子相關的“扇”意象多為“羽扇”,表現了“扇”意象張揚、開闊的一面,徐徐搖動的羽扇無意間彰顯了文人閑適自若的氣度、飄逸灑脫的風神,使“扇”成為了儒將謀士、風流名士的符號象征,這種符號意義的影響甚至延續到了現代,在現代影視作品中,也常見“扇”與文人俠客身份之間的符號聯系。
“扇”的象征意義是中國古典“物我合一”藝術傳統的體現,使用“扇”的動作姿態使得“扇”與身體儀態相聯結,成為一種身體表現形式或身體符號,文人將主觀化的情思與氣質賦予“扇”意象之上,“扇”意象的物象特征進一步與“人”的氣質相結合,使得“扇”意象的文學意蘊逐漸內化于物,并深化拓展,展現出不同時代、不同性別群體的象征意義。
三、扇書扇畫:審美性的隱與顯
中國的“扇”藝術源遠流長,魏晉時期,王羲之在蕺山老婦的竹扇上題字使其身價倍增,這可能是扇書最早的由來,唐代的《紈扇仕女圖》證明了唐代已有在扇上作畫的先例。古代文人題字作畫最常用的扇當屬紈扇與折扇,因其材質最便于書寫。
“扇”以其“顯現”的展示功能成為書畫藝術的載體,“扇”藝術是扇形扇體的物象之美與扇書扇畫的藝術之美的融合,二者的主次關系在一開始并不平衡。在唐代,繪畫藝術的獨立性并未完全形成,在扇上題字作畫更多是為了給空白的扇面補白,書畫起到了填充與裝飾的作用,圖案多為山水、花鳥、人物等,人們更重視“扇”的實用功能與象征意義,書畫的呈現當是為文人雅士增添了幾分審美意趣。在宋代,由于書畫藝術的發展與宋人審美心態的變化,扇畫逐漸成為了一種獨立的繪畫藝術;在明清時期,日本的折扇工藝經朝鮮傳入中國,折扇成為扇藝的主要扇類,商品經濟的發展、市民階級的擴大使得以折扇為主要載體的扇書扇畫在平民中大受歡迎,許多民間的文人畫家都是扇畫藝術的高手,扇藝由貴族階層、文人雅士慢慢下潛到平民百姓的生活之中,并與民間藝術相結合;以至于現代,大量扇書扇畫作品依然在文玩古董市場上流通,“扇”完全脫離了實用性,成為了具有文化價值和審美價值的藝術品。
在扇書扇畫藝術的發展過程中,書畫藝術逐漸脫離裝飾附屬的地位,并得到了藝術性的彰顯,但不同于大篇幅的書畫作品,扇書扇畫的審美性還在于與“扇”這種物象形式的深層意義的融合。與最開始的門扉形狀的戶扇不同,魏晉兩漢時期流行的團扇形狀特征明顯,自班婕妤的詠物詩開始,文人們紛紛歌詠團扇飽滿如滿月的圓整,崔骃《扇銘》云:“有圓者扇,誕此秀儀。晞露散霾,擬日定規”,明清時期流行的折扇展開也如半弧形,“圓”是“扇”最為顯著的外觀特征和物象意義,這與中國傳統天圓地方、中庸、圓融的文化觀念與審美傾向相契合,“圓”是審美形式,“藝”是審美內容,“圓”影響著“扇”藝的審美特征,使其蘊含有中國人特有的、不顯山不露水的含蓄內斂之美。
扇形不僅隱含有獨特的文化審美意蘊,還是扇書扇畫藝術審美結構的內在肌理,扇面以方寸之地展現無限神韻。唐代張彥遠所作的《歷代名畫記》載“梁肖賁曾于扇上畫山水,咫尺內萬里可知” ⑤,凸顯了扇面的有界與山水意境之無界的對比。畫家如何利用有限的平面空間去展現無限的三維空間,這考驗畫家的構圖功底與審美表達能力,尤其是折扇的紙面有細密的褶皺,更不利于畫家的發揮。扇面的邊界其實是一種畫框效應,以畫框結構畫面,畫師在構圖中須創造合理的留白以引出更為空遠的意境。蘇州園林的圓窗設計與扇面藝術有異曲同工之妙,每一個窗口就是一幅精心結構的園林景觀圖,以“扇”形構圖豐富了園林建筑的美學意蘊。折扇扇面的波折還為扇畫的結構增添了動勢和生機,成熟的畫家善于利用扇面的波折構造出山水景觀的波瀾起伏之勢、花鳥魚獸的栩栩如生之形,以動造勢,更將折扇上有限的空間引向觀者想象中的無限空間。
扇畫扇書等扇面藝術的審美性是以扇形的象征性、有界性為肌理結構的。在扇藝的審美獨立化過程中,“扇”物象也逐漸審美化、藝術化,作為被觀賞、把玩的純粹藝術品而存在。“扇”意象在詩歌傳統中獲得的符號性與承載的情感心志逐漸淡化,“扇”作為物象的審美本體價值得到凸顯,觀者在審美過程中,以凝神靜思的審美專注,去體味物象之形、物象之景的審美韻味。物象之景即是通過扇面呈現的、顯性直觀的審美體驗,物象之形是以留白、動勢為結構、以含蓄內斂為特征的隱形的審美體驗。扇面以顯性的呈現作用展現了扇藝“藝”的一面,扇形以隱性的心理審美結構顯現了扇藝“形”的一面,一隱一顯,互為觀照,共同造就了扇藝獨特的審美表現形式。
四、結語
“扇”的秋藏夏用,遮面藏羞、圓整規制,隱含著中國古典“藏”的智慧,因為“藏”所以在政治上懂得收斂鋒芒、待時而動,遵循儒家中庸圓融的處事之道,在審美上,追求一種不顯山、不露水的含蓄內斂之美,在藝術表現方式上,以有形化無形,以有限呈現無限,以留白掙空遠意境,追求凝神靜思、以我觀物的審美心態。
“扇”作為文學意象與審美物象,以或“隱”或“顯”的呈現方式,通過器具性、象征性與審美性的延伸路徑,即從“以物喻人”到“物我合一”,再到“以我觀物”,此三種“扇”與“我”的不同關聯,體現了中國古典的內斂、藏鋒、空遠的文化心態和審美傾向,另外還被賦予了男女傳情的情愛色彩、文人入世的政治理想色彩,以及名士的自我彰顯色彩,除含蓄美之外,另辟張揚、開闊之氣。
注釋:
①(宋)郭茂倩:《樂府詩集》,中華書局1979版,第610頁。
②徐震堮:《世說新語校箋》,中華書局1984版,第482頁。
③(晉)裴啟撰,周楞伽輯注:《裴啟語林》,文化藝術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頁。
④金濤聲:《陸機集》,中華書局1982版,第4頁。
⑤(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人民美術出版社1964版,第13頁。
參考文獻:
[1]向素萍.宋詞中扇意象所蘊含的文化意味[J].襄樊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9,(05).
[2]劉艷萍.漢魏六朝扇文化的流行及其藝術表現[J].安徽文學,2017,(07).
[3]劉亞男.漢魏六朝詠扇詩文研究[D].西北師范大學,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