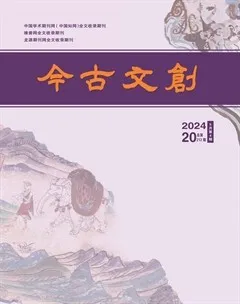司馬遷對墨子義利觀的繼承與發展
【摘要】先秦諸子對義利思想的闡發各有側重,其中墨子的義利觀表現出義利并重的理念,同時他將其與社會治理聯系在一起。從《史記》中的人物形象以及經濟理論能夠看出司馬遷繼承了墨家的為天下之公利,“強本節用”的義利思想,并且司馬遷也將義利觀念與社會治理緊密聯系起來。司馬遷還在墨子義利觀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司馬遷認為逐利乃人之本性,他提出了逐利的方法以及基本的原則。
【關鍵詞】司馬遷;墨子;義利觀;繼承;發展
【中圖分類號】B82?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4)20-0080-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20.026
基金項目:寶雞文理學院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研究生創新科研項目“司馬遷與墨子義利觀共通性研究”(項目編號:2023wcy006)。
墨子和司馬遷是在各自領域有建樹的大家。墨子創立了墨家學派,司馬遷完成了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二者對后世的影響都非常深遠。二者的思想體系中都包含著義利觀念。雖說司馬遷的思想集百家于一身,但在義利方面,司馬遷義利觀念很大比例地承繼了墨子的義利思想——義利并重、強烈的平民意識以及與社會治理聯系密切的經濟思想。
《史記》中對墨子的表述僅僅二十幾字,并將其安排在《孟子荀卿列傳》的篇尾,而未單獨為墨子作傳。基于此,清人孫詒讓說:“墨蓋非其所喜。”(《墨子后語》)但細觀司馬遷《史記》能夠看出司馬遷與墨家墨子關系并非“不喜”一詞所能簡單概括。鄭杰文在《中國墨學通史》中說:“《史記》論墨引墨18次”“我們今天看到的《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中的墨子傳記,應是殘篇而不是原貌。”[6]186-190徐華在《史記論墨志疑》中繼承了這種余緒,還有文章也對二者的關系存疑[10][11],結合當時的文化環境來看,司馬遷很難不受到墨學的影響。加之,司馬遷在《史記》當中表露出來的義利思想,義利并重的態度恰與墨家是一致的。基于司馬遷義利思想與墨子的共通性以及文化環境的影響,本文試以司馬遷對墨子義利思想的繼承與發展進行論述。
一、司馬遷所處時代的文化環境
后人所以為的西漢文化國策只尊儒,但實際上司馬遷所接受的文化是多元的。公元前191年,漢惠帝廢除秦“挾書令”,由此先秦諸子學說再一次獲得了新生。再加之,司馬遷出生在史官世家,師承大家,壯游山河,人生經歷離奇跌宕。揚雄在《法言·問神篇》載:“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與?曷其雜也!”[7]司馬遷也說自己要“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1]。
西漢初期,統治者延續了黃老之術,西漢王朝得以調整,國家相對穩定。隨著時間的推移,黃老之術已不能夠適應漢代發展,大一統是大勢所趨。秦末社會動蕩,加之焚書坑儒,珍貴典籍多有亡佚,各學派自己原本的學說不夠完備,諸子學派需要吸收各家學派精進自家之思想。“世之顯學”的儒墨兩家也不例外,在西漢前期的著作中儒墨同稱的表述是多見的,如陸賈的《新語》其《思務》云“是以墨子之門多勇士,仲尼之門多道德”[6]176,賈誼《過秦論》中稱“非有仲尼、墨翟,陶朱,猗頓之富”,鄒陽《獄中上書》“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于讒諛”…… “也正是因為西漢時期的這種‘援墨入儒的情況,使得時人開始習慣于‘儒墨同稱,墨家思想也逐漸被儒家思想融合,形成了更為完善和系統的儒學”[9],司馬遷在《平津侯主父列傳》中也將儒墨兩家并稱,寫到徐樂上疏說道“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后,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1]他的父親司馬談也曾寫道:“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1]。
綜上,司馬遷生活的時代的墨子所存的文獻是豐富的。他所在時代的文化環境,他的家學淵源以及他在《史記》中的引墨、論墨的現象,這些都可以表明司馬遷對墨家思想是熟悉的。就義利思想而言,司馬遷義利并重,注重義利對社會的治理,這不同于儒家式“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孟子·梁惠王上》)的排利,也不同于法家的重利輕義。義利并重的態度恰與墨家是一致的,司馬遷的義利思想是在墨子義利觀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而成的。
二、司馬遷對墨子義利觀的繼承
(一)墨子的義利觀
墨子義利觀的出發點是“兼愛”,如梁啟超在《墨子學案》中評價道:“墨學所標綱領,雖說十條,其實只從一個基本觀念出來,就是‘兼愛。”[2]
墨子的義利觀與社會生活息息相關,最先體現在政治生活方面。墨子所處的時期,大概在戰國初年。當時中國社會正在經歷翻天覆地的變化,周王室勢力衰落,各諸侯國戰亂不斷,封建制度正在逐步形成。“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1](《太史公自序》)在這種社會背景之下,墨子提出了相應的主張。他認為“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 [2] (《墨子·兼愛上》)墨子希望兼愛能夠治理天下,他所求的義利是天下之義利。
墨子的義,可以用他的話來總結“義,政也”“義,利也”。[2] 《墨子·經上》)“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有義則治,無義則亂。”[2](《墨子·天志中》)“仁者之事,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為,不利人乎即止。”[2](《墨子·非樂上》)義是治理天下的方法,只有這樣人民才能安居樂業,社會得到有效治理,最后交天下之利,義利統一。在《墨子·公輸》中,楚國的公輸般發明了一武器,便就打算進攻宋國,墨子聽說這件事情后就前來阻止,他用自己的防御術演習了一遍戰爭過程,說服了楚國。他的戰爭策略主張非攻;他不想勞民傷財,所以他主張節用、節葬、非樂。墨子建構的世界從實用的角度出發,他所求的利即展現了他的義。他希望“欲人之有力相營,有道相教,有財相分也。又欲上之強聽治也,下之強從事也”[2] (《墨子·天志中》),大家共同努力,社會各階層各行其是,這樣才是理想的社會。
墨子的功利是直白的,他希望以義來治理社會,而實現眾人之利。“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2] (《墨子·兼愛中》)
《墨子》一書中體現了他的經濟思想。《非樂上》篇中他提出:“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2]力便是物質生產,墨子認為物質生產是人生存的前提條件。墨子所處的時代還是以農業為主的時代,雖然他從事過手工業,做過小生產者,但他還是視農業為本。“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為養也。故民無仰則君無養,民無食則不可事”。[2] (《墨子·親士篇》)五谷還是根本。再就是墨子的“強本節用”思想。《墨子》中專有《節用》篇,其中關于衣食住行的度,墨子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且他還提出了節用的標準:“凡足奉為民用則止;諸加費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為”[2]《墨子·節用中》。墨子注重致富,同時也希望有能力的人在自己致富之余還能夠幫助他人,“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免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2] (《墨子·非樂上》)
墨子的義利思想從兼愛出發,義利并重。他提出兼愛,希望最后能夠興天下之利;他是中國最早的游俠,有俠肝義膽之氣,他重視物質生產,尚儉,司馬遷如是。
(二)司馬遷對墨子義利思想的繼承
首先,司馬遷也希望興天下之利。他在作品中表露出對黎民百姓的關懷,歌頌有深明大義之人。司馬遷將《伯夷列傳》作為傳記之首,旨在宣揚義之精神,伯夷叔齊二人最后“義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1]。項羽是《史記》中被司馬遷濃墨重彩所渲染的人物,李長之在《論司馬遷人格與風格》一書中指出“《項羽本紀》和《李將軍列傳》——也便是《史記》中最精彩的、最炫耀人的文章了!”[3]項羽在與劉邦相持之時,他欲與漢王決戰雌雄,“毋徒若天下之民父子為也”[1];四面楚歌之時,他悲歌慷慨,泣行數下,左右皆泣;自刎烏江之時,不忍殺騅,為他人德。他與部下推衣甘食,他在鴻門宴對劉邦的仁慈,他與劉邦對決時的遵守諾言,在烏江自刎時的與亭長,與愛馬,與愛人別,最后舍身就義。正如司馬遷在《刺客列傳》中所說“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1]項羽、刺客都做到了不欺其志,司馬遷自身如是。《游俠列傳》一篇,司馬遷毫不吝嗇地對具有大義品質的游俠進行贊美“今游俠,其行雖不軌于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1]在《刺客列傳》《游俠列傳》等篇章中,司馬遷借用這些不能夠在歷史上揚名的人的義舉說明了何為義。司馬遷所贊揚的這些有義之士身上都有著為天下的共同點,是大義,最終惠及的是普通民眾,求的是天下之利。
司馬遷也像墨子一樣重視義利思想對于社會的治理。求富的心理,能夠使個人和社會都快速發展,利用眾人求富的本性可以教化百姓。“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仆,物之理也”[1] (《貨殖列傳》),基于此人性,個人才有發展的動力。經濟地位決定個人的社會地位,國家也如此。齊國富強則“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矣”[1];越國富強則“觀兵中國,稱號五霸”[1]。于個人言,管子位在陪臣,富于列國之君;子貢到達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的地位;烏氏倮“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1]。
其次,對于百姓的教化,不應該是苦口婆心的勸導,而應順其人性。“富者,人之情性也”[1]既遵循人的本性,也尊重經濟的發展規律,再有社會上的各行各業,也就做到了道之所符,自然之驗,社會也就形成了一個良性的循環“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各勸其業,樂其事”。[1]
司馬遷重視經濟,肯定追逐利益的正當性,這一點與墨家直白的功利性如出一轍。作為人的本性,趨利又有什么錯呢?從上古至今,皆如此,“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夸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1]。他道出了一個亙古不變的道理“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1]。王侯將相,三教九流,無一不是逐利之人。“由此觀之,賢人深謀于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于富厚也……終不余力而讓財矣”[1]。不管是賢人、隱居之士、沖鋒陷陣的士兵、閭巷少年、趙女鄭姬、游閑公子……“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1],司馬遷寫出來的眾生逐利圖,不管是何等身份,做何種事情的人,都是為求富益貨爾。
三、司馬遷對墨子義利觀的發展
司馬遷認識到了經濟與文化之關系。墨家實行兼愛的思想希望最終導利于百姓,由上而下,最終建立良性運轉的社會。除去政治作用,司馬遷將其與文化聯系。司馬遷肯定經濟是根本的,禮義廉恥建立在溫飽之上,“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1]“禮生于有而廢于無”[1]。溫飽之后呢?只有當人富有之后才會想著多做仁德的事情,這樣也能夠區別出君子和他人的區別。“人富而仁義附焉”[1],人若富有了,那么仁義自然而然就歸附了,“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1]如果身處貧賤,但滿口仁義,這樣的人值得羞愧。由此來看他歌頌那些富有但是有德行的人,經濟基礎是根本,但是也應是與精神相互映照的,所以那些富有且有德行的人最后能夠“素封”。
司馬遷提出了求富具體的方法和途徑,以供后世觀采。墨子雖然認識到了物質生產的重要性,但是他沒有提出具體的方法和途徑。他將求富的途徑歸為三類即本、末、奸,“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1]。這三種致富方式,農業還是根本的。“是以無財作力,少有斗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1],但常理還是在沒錢的時候出力,積攢了一定錢財之后玩弄才智技巧追求更大的財富,到富足時再追時逐利。在這三類致富途徑中司馬遷也進行了比較“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1]相對于農業,工商業才是窮人致富的途徑,他司馬遷還指出了獲利的標準“佗雜業不中什二,則非吾財也。”[1]一個行業能夠獲得的利潤還不足十分之二,那就不是能夠致富的行業。至于求富的方法,司馬遷認為勤儉節約,精打細算是發財致富的正路,但是想要真正地致富還得靠出奇制勝“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1]。
司馬遷考慮到了影響經濟的具體因素。如對市場和交通的思考,“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馳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諸侯強族于京師。”[1]開放市場,發展交通是商品進行流通的條件。朱公“以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1],富甲一方。
其次,地理環境對人們職業選擇或者習性的影響。關中周邊地區因為土地狹小,商業資源豐富,所以人們玩弄奇巧,從事商業。“長安諸陵,四方輻湊并至而會,地小人眾,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1]“土地小狹,民人眾,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1] “人民矜懻忮,好氣,任俠為奸,不事農商”[1]。這里講到河南、河東還有河內地區的人民由于土地狹小,人口眾多,多以節儉之風盛行,那里的人民強直、好勝,大都不愿意從事商業。關中地區周圍以及三河地區附近,是歷代帝王建立都城的地方,所以人口聚集密度大,人地矛盾較為突出。然而,楚越之地,地廣人稀,沒有凍餓之人,也沒有千金之家。由此觀得,司馬遷在當時已經洞悉地理環境對人們經濟活動的影響。
司馬遷對墨子義利觀的發展主要是將其義利觀細化,他們二人都義利并重,且認識到經濟對于社會發展的重要性。司馬遷他將義利觀念進行細化,并且所看到的方面也更加地全面。這與時代和司馬遷的人生經歷密不可分,正是基于吸收和發展,司馬遷才建立了見識卓遠的義利觀。
四、結語
義利思想在中華文化的發展史中一直爭論不斷,影響著世人的價值選擇。義和利本身就屬于一個事情的兩個方面,二者的統一才應該是義利觀的最終走向。司馬遷和墨子無疑走在了世人的前端,他們以高瞻遠矚的目光將義利思想統一于他們的文字之中。司馬遷的義利思想吸收了墨子思想的精華,不管是對人物的塑造,還是將其與社會治理的密切聯系,還是他在墨子基礎上的發展都踐行了義利并重的理念。放眼今天,他們二人的經濟思想仍然適用于當代社會。司馬遷以他那悲天憫人的情懷還有洞察世事的智慧,踐行了他的創作宗旨,也成就了他“一家之言”的義利思想。
參考文獻:
[1]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2006.
[2]墨翟.墨子[M].方勇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15.
[3]李長之.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278.
[4]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M].北京:中華書局,1989: 709.
[5]任繼愈主編.墨子大全[M].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23.
[6]鄭杰文.中國墨學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86-190.
[7]汪榮寶.法言義疏[M].北京:中華書局,1987.
[8]楊光熙.司馬遷的思想與《史記》編纂[M].濟南:齊魯書社,2006.
[9]張一博.西漢儒家學者“援墨入儒”思想研究[D].吉林師范大學,2023.
[10]聶韜,聶應德.《史記》與墨子探析[J].社會科學研究,2011,(06):128-130.
[11]鄭杰文.《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載墨子傳記為殘篇說[J].中國文化研究,2005,(01):16-23.
作者簡介:
卜曉蓉,女,漢族,陜西榆林人,寶雞文理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古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