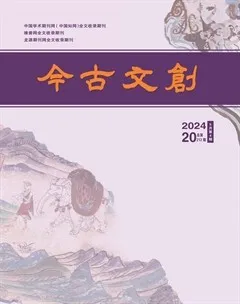中華書局《夔州府志》三種版本對比研究
曾香依
【摘要】地方志是記載一地古今綜合情況的志書,可以說是一個地方的百科全書。中華書局《夔州府志》有正德、乾隆、道光三個版本,其中明朝正德版《夔州府志》十二卷,內容簡略,清朝乾隆版和道光版《夔州府志》在內容和體例上更為完善,體現出清代修志事業的成熟。
【關鍵詞】《夔州府志》;版本;體例;校勘
【中圖分類號】K29?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4)20-0071-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20.023
地方志因其所載內容廣泛,包括行政建制、天文、地輿、山川、建置、賦役、兵防、人物等各個方面,反映出不同歷史時期各個地區的社會、政治、經濟等多方面的情況,一向被譽為“博物之書”。終明一代,夔州府所修的府志共有以下3部:“正德年間知府吳潛修纂本、嘉靖年間知府張廷柏修纂本、萬歷年間知府郭裴修纂本,但張本和郭本均已散佚不可考,唯正德時期的吳潛所纂《夔州府志》流傳下來” ①。清朝國家修撰的《大清一統志》充分為各省地方志的修纂提供了范本,清朝乾隆版和道光版《夔州府志》就是在此基礎上有所改進的。故本文將以中華書局版明代正德《夔州府志》(下簡稱正德本)、清代乾隆《夔州府志》(下簡稱乾隆本)和清代道光《夔州府志》(下簡稱道光本)三種版本做比較,試從作者與版本、體例、內容和校勘等方面來分析地方志的發展變化。
一、作者及版本介紹
明朝正德年間的《夔州府志》,成書于明正德八年(1513),由時任夔州府知府的吳潛親自督導,集合全府十二縣力量進行編修。吳潛,字顯之,江西臨川人,正德本卷八“職官題名”有提及,稱其“由進士、前工部郎中,正德四年升,十二月到任。” ②乾隆本卷六“宦績”載其“正德間守夔,愛民教士,善政良多。” ③志書首附有夔州府地理總圖和所屬十二縣地理圖,后分載十二卷。中華書局出版的正德本,其整理者在目錄前說明選取版本為“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上海古籍書店據寧波天一閣藏明正德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二一·五公分,寬一四·六公分”;在目錄后載有“明正德《夔州府志》點校領導小組名單”;在點校本之后附有明正德《夔州府志》的原文,采取一版面四圖的方式。在點校本之后附有點校后記,載有正德本點校過程及過程中遵循的原則,可總結概括為:志書整理是以1961年12月上海古籍書店據寧波天一閣藏明正德刻本影印的《夔州府志》為藍本,由中共奉節縣委常委、縣政府督導,從2008年12月開始對其進行點校,2009年5月完成整理初稿,并于2009年11月進行第一版印刷,附錄明正德《夔州府志》原文及點校后記。
清朝乾隆年間的《夔州府志》,成書于乾隆十二年(1747),由崔邑俊修,楊崇、焦懋熙纂。崔邑俊,在乾隆本卷之五“秩官”中載“崔邑俊,山西貢生,雍正十三年任” ④,而后又在卷之六“宦績”中載“崔邑俊,夔州府知府,字碩秀,山西大同府陽高縣貢生。” ⑤楊崇,夔州府奉節縣儒學教諭,四川鄰水舉人。焦懋熙,國子監肄業期滿拔貢候選儒學教諭,夔州府奉節縣拔貢。該志共10卷,相較于正德版《夔州府志》,新增星野、疆域、城池、祠廟、武功、武略、貤封、仙釋等內容。乾隆本在目錄之前載有“乾隆《夔州府志》點校工作機構”及“重印乾隆《夔州府志》序”,并且將正德本書末所附的“整理說明”提前至書首。“整理說明”的內容由以下九方面構成:以國家圖書館影印的乾隆《夔州府志》為底本,與海南出版社影印出版的故宮博物院編乾隆《夔州府志》對校;體例盡可能與原書保持一致;行文與現代不一致的舍棄;文字使用現行語言文字規范;標點根據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2011年12月頒布的《標點符號用法》標點;校勘盡可能搜集相關典籍進行校勘,如“衍文”“訛字”等,說明校勘的理由;箋注根據實際需要做出必要的簡明注解;輿圖根據實際情況重新拼合;附錄將影印的國家圖書館藏乾隆《夔州府志》原文附后,以便查閱。乾隆本點校是由奉節縣地方志部門和重慶三峽學院文學院合作進行點校,其點校活動是在整理出版明正德《夔州府志》和清道光《夔州府志》之后開始的,于2015年9月進行第一版印刷,附錄國家圖書館藏清乾隆《夔州府志》原文,采用一版面兩圖方式。
清朝道光年間的《夔州府志》,成書于道光七年(1827), 由恩成修,劉德銓纂。⑥該志共36卷,首1卷,首一卷載有志序、職名、目錄次序解,正文36卷實則每卷細分為一門。與前兩志書不同,道光本新增水利志、蠲政志、榷政志、鹽茶志、武備志、置郵志、封蔭志、金石志等。道光本在編訂形式上與乾隆本相似,即在目錄之前載有“道光《夔州府志》點校工作機構”“重印道光《夔州府志》序”及“整理說明”。不同之處亦存在,其一,中華書局本道光版《夔州府志》以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于1992年8月聯合出版的光緒十七年補刻的道光《夔州府志》影印本為底本,與國家圖書館藏刻本對校;其二,道光本原書目錄中并沒有《藝文志》細目,點校本目錄將《藝文志》細目編于總目錄之下;其三,點校本之末并未附原文,僅在書首附有原文一頁,采用一版面兩圖方式;其四,由奉節縣地方志辦公室于2010年5月與重慶三峽學院文學院與新聞學院合作進行點校,并最終于2011年12月進行印刷。
二、體例
所謂志書體例,“是一地政區范圍內古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習俗、人物、奇聞異事等情況的表現形式及其原則規范,是方志區別于其他著述的獨特標志” ⑦。中國方志發展的繁榮階段自明代開始,這一時期方志的數量和質量呈正比發展,地方官紳文人都踴躍參與其中,他們的思想價值觀念、學識才華、身份地位都會影響方志的內容和體例的編修,從而使其修成志書風格類型有不同特點。
因纂修人對方志性質、作用等看法不同,將其分為歷史、地理和實用三派。張安東論述為:“歷史派認為編纂方志應當遵循史學編纂的方法;地理派則主張纂修人重點記錄自然地理概況;實用派則介于歷史派和地理派之間。” ⑧正德本、乾隆本和道光本這三本志書的體例有一定的重合性,如都具有山川、形勝、風俗、城池、物產、祠廟、人物、藝文等內容,但隨著時代需要,體例或形式有一定的變化,如正德本和乾隆本都是綱目體形式,道光本則是平目體形式。平目體志書,即志書內容分為多個類目,平行分布,彼此之間并無統攝關系,此體例在清代前期應用極為廣泛,但因體例影響久遠,在清代中后期也有一些志書采用這種體例;綱目體志書,即志書各個類目有總綱或大綱統攬,分門別類,該體例直至宋代,才隨著纂寫的需要,應用越來越頻繁,明清時期成為志書編纂的主要體例。兩種體例各有優劣,平目體由于并列諸門,無所統攝,極易造成分類繁雜,而綱目體雖然門類層次分明,但也容易造成歸類混亂,有悖志體。道光本對所分36細目進行撰寫,除是為符合清朝《一統志》的體例標準,亦是對前兩部志書分類缺點進行改進與歸納。例如前兩部志書對于人物的記載具有重復性或混亂性,正德本將“人物”“科貢”“薦舉”“孝節”“義勇”分屬同一卷,乾隆本則將“秩官”“宦績”“科貢”“人物”“孝友”“忠義”“貞節”等分屬三卷,其中把正德本中“孝節”分為“孝友”“貞節”兩目,可見當權者對于女性節烈的重視性,實屬鞏固統治的政治舉措。道光本則分將其為“秩官”“政績”“選舉”“封蔭”“人物”“流寓”“列女”七目,分類細致,人物少有重復,其中“列女志”還可作為研究清朝白蓮教起義等逆賊反叛的輔助性材料。值得注意的是道光本,其中點校本目錄將《藝文志》細目編于總目錄之下,“藝文門收載最多,雖僅歸為一卷,字數卻多達二十六萬余字,超過全書三分之一” ⑨,所收詩文上至春秋戰國,下訖清道光年間,涉及民生建設、風景山川等方方面面。“地理派所修志書,在體例上與歷史派并無多大差別,不同之處在于內容的側重點,歷史派重視人物、職官和藝文,而地理派雖然也有這些內容,但其側重點更多地放在建置、沿革、疆域、水利等方面” ⑩,由上述“藝文志”“職官志”“人物志”等方面在志書中所占比例所知,正德本、乾隆本和道光本的纂修人員均體現歷史派的修志思想。
從體例上看,“方志向著獨立門類及精細化的趨勢發展是合理的,合乎科學性的要求,是方志發展的必然反映。” ?這三部中華書局本志書在卷首都有序文,但乾隆本及道光本兩本清志在各細目之前綴小序以明體例及修志理念,如乾隆本卷之三《賦稅》前所附小序言,“三農生九谷,商賈通貨財,《周禮》所載,班班可考……商旅咸愿出途,作《賦稅志》” ?;道光本卷九《賦稅志》前所附小序,“夔郡山多田少,瘠多沃少,田惟下上,賦惟下中,今猶古也,祭祀官祿,兵餉役食,取給于斯,作《賦稅志》” ?;明正德本卷之四《賦稅志》前則未綴小序,這顯示隨著方志學的發展,體例也愈加完善。
三、校勘
許逸民對其定義為:“校勘是文獻整理的重要方法之一,點校則是當代通常采用的古籍整理形式,點校本則是經過標點和校勘的新版古籍整理圖書。” ?版本作為十項文獻整理方法中的又一重要方法,與校勘關系最為密切。前文已然論述中華書局版正德本、乾隆本及道光本的版本問題,以下則針對此三志書在點校中出現的問題及遵循的原則進行論述。
點校人員在正德本的點校后記中明確列出其在整理志書過程中所遵循的幾項原則,其中與點校原則前文已有論述。盡管如此,正德本相較于乾隆本和道光本來說,點校問題仍不少,曾有學者以此志本為對象,從文獻整理的角度,對其中點校及排版等出現的問題進行舉例分析,得出此點校本存在62處失誤。?本文由此總結得出此點校本存在以下幾種類型的失誤:一為文字的訛誤、脫衍、誤倒、失校、誤刪(改);二為斷句不當、標點符號的失誤;三為底本有誤;四為排印錯訛導致圖文不符。
乾隆本在其“整理說明”中明確列出其“校勘”遵循原則,即“盡可能搜集相關典籍進行校勘,如‘衍文‘訛字等,一般說明校勘的理由。藝文志中一些流傳比較廣泛的文、賦、表、記、詩、詞、歌等,個別字句略有差異,在不影響文句理解的情況下,一般照錄原文,不做校注,也不修改。” ?對比正德本點校原則,二者的區別在于,乾隆本會搜集相關典籍,擇取對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及理校法進行校勘,并且采取頁下注的方式呈現。采取對校法進行校勘的釋例在書中占比最大,如乾隆本卷之四“祀典”第112頁“社稷之神,曰:惟神奠安九土,粒食萬邦,分五色以表分圻” ?,據道光《夔州府志》卷十九“典禮志”及各府縣志俱將“分圻”作“封圻”。正德本則在其“點校后記”中明確將點校工作重點集中在對底本的標點和校勘上,刪除全部注釋和未做交代而增補的內容,刪去《大事記》等。
道光本與乾隆本在“校勘”中所遵循的原則大致相同,只細微處有些許差異。道光本同樣會搜集相關典籍,擇取對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及理校法進行校勘,并且采取頁下注的方式呈現。道光本采取對校法進行校勘的釋例在書中占比沒有乾隆本重,且選取地對校本子也不似乾隆本那么單一。陳垣先生在其“校法四例”中就已說明“對校法,即以同書之祖本或別本對讀,遇有不同之處則注于其旁”。?由此可見,對校所選本子并非只選取其祖本才可,選用與之有關的其他優秀本子即可,如道光本卷九“賦役志”第95頁“縣屬底鋪、二溪、青蓮、古峰、哨樓、十里、么塘、仙女、銅鑼、拖板、二道、馬鞍、香店、王家坪、紅巖十五鋪” ?,校注者選用光緒版《奉節縣志》對校得出此書所在十五鋪與道光本有差異,分別是“東底塘鋪、二溪鋪、青蓮鋪、古墳鋪、十里鋪、西底鋪、么塘鋪、仙女鋪、銅鑼鋪、拖板鋪、二道鋪、北底鋪、馬鞍山鋪、香店鋪、王家坪鋪。”此外,道光本與乾隆本還有一不同之處在于,因道光本單獨將“藝文志”編于總目之下,道光本校勘時將詩詞序言、注文及其他說明性文字用小五號仿宋字與五號宋體字的正文加以區別,且其序言、注文、說明文字以及按語在書中較乾隆本占比更多。例如,道光本卷十九“典禮志”第181頁“籩各八,用竹(以絹飾里、頂及緣,皆鬆以漆,紅色,通高五寸四分,深八分,口徑四寸六分,足徑四寸,蓋高一寸九分,徑與口徑同,頂正圓,高四分)” ?,校注者用“()”將對“文廟祭器”的說明性文字囊括,且將祭器的顏色、形狀、尺寸及材料極為精準的進行說明。
通過對正德本、乾隆本以及道光本的校勘情況總結出以下幾個特點:一為更會甄別採納已有的校勘成果,而非單純將目光聚焦文本字詞錯訛之處。例如,正德本工作重點在對原文的斷句及繁簡字的轉化上,故而書中的注釋極少;乾隆本和道光本注意到這一缺陷,在校勘過程中采用已有的成功校勘成果,如中華書局點校本《明史》《漢書》《晉書》等,就算一時間沒足夠依據判斷是非,卻也能夠校出異同。二為所選校勘人員更為專業化,正德本的校勘工作主要由縣志辦工作人員以及退休中學教師完成,不可否認其專業性,但是乾隆本以及道光本的校勘以重慶三峽學院文學院,尤其是“中國古典文獻學”的班底為依托,相比較而言,乾隆本與道光本的校勘人員專業性更強。三為校勘錯訛更少、成果更為顯著。正德本甫一印行,即有專業人士寫出專文來修改書中錯訛,這與乾隆本和道光本印行之后在學界產生的效果無法比較。
四、結語
通過對中華書局版三種《夔州府志》的對比分析可知,因國家統治、政府管理等多方面需求,志書本身內容在前志的基礎之上愈加詳備,體例亦日臻完善。同時,隨著方志學理論的成熟,學界對于方志研究的關注度提高,中華書局在點校志書方面更為專業,這體現在選取對校版本權威化、點校原則精細化、點校人員專業化等多方面。
注釋:
①熊茂松:《〈夔州府志〉修纂源流考》,《圖書館學刊》2014年第5期。
②(明)吳潛:正德《夔州府志》,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140頁。
③④⑤??(清)崔邑俊修,楊崇、焦懋熙纂:《乾隆〈夔州府志〉》,中華書局2015年版,第191頁,第174頁,第194頁,第74頁,第112頁。
⑥⑨金恩輝、胡述兆:《中國地方志總目提要》,漢美圖書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1516頁。
⑦黃葦:《方志學》,復旦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300頁。
⑧張安東:《清代安徽方志研究》,黃山書社2012年版,第302-304頁。
⑩熊茂松:《明清〈夔州府志〉與夔州社會文化史研究》,四川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74頁。
?刁美林:《清代藏書目錄著錄方志特色研究》,《故宮學刊》2019年第1期。
???(清)恩成:道光《夔州府志》,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89頁,第95頁,第181頁。
?許逸民:《古籍整理釋例》,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116頁。
?郭作飛:《明正德〈夔州府志〉點校讀補》,《重慶三峽學院學報》2011年第4期。
?(清)崔邑俊修,楊崇、焦懋熙纂:《乾隆〈夔州府志〉》,中華書局第2015年版,整理說明。
?陳垣:《校勘學釋例》,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12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