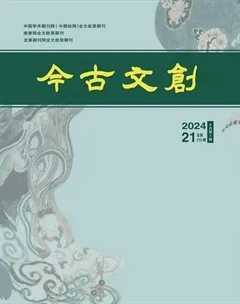人文與科技的較量
【摘要】汪彥中的小說集《異變》描繪了科技時代背景下科技發展中的矛盾、倫理和人的異化等一系列問題,深入探討了科技發展的“方向”問題。當人的主體性被機器所取代時,人類所構建的道德、倫理將會被消解,人類也將會失去自己成為人的根基。在科技多元化的今天,保持人類的主體性,還應思考科技時代下的人文情懷。
【關鍵詞】人文;科技;汪彥中;《異變》;惡托邦
【中圖分類號】I207? ?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4)21-0013-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21.004
基金項目:陜西理工大學2023年校級研究生創新基金項目“新世紀中國科幻小說的惡托邦敘事研究”(項目編號:SLGYCX2331)。
一、科技時代的道德倫理
《異變》是汪彥中的一部小說集,收錄了《異變》《訪客》《二次遺書》等十一篇科幻小說作品。人工智能、太空旅行、基因工程、人腦移植……等科學技術元素是小說的顯要特征,讀者可以通過這些科技元素來理解和解讀這個時代。
受“科學人生觀”的影響,普及科學知識,已不再是科幻小說的中心任務,“‘科學人生觀是一種立足于‘剖析人生,反映社會的創作觀。它標志著科幻由科學普及的中心視點轉移到人性和現實的中心視點從重視科學內涵轉變到重視藝術內涵”。[1]231科幻小說的主要任務已經變成了反映現實社會和體現其藝術價值,新世紀科幻小說中的“科技”更多與當下對接,“如果在過去的科幻寫作中,‘科技還可以被簡單處理為一個遙遠的故事背景,那么在‘科技不再指向未來而是內嵌于此時此刻的當下,‘科技自身所包含的重要文化倫理議題則需為王威廉一類深具現實關懷的作家所清理”。[2]110汪彥中也是具有現實關懷的作家,對科技發展中的矛盾、倫理和人的異化等一系列問題,同樣有著關注和思考。
在科幻作品中,人類憑借科技的力量,已經能行前人所不能行之事。《訪客》中的科技水平已經可以將人類大腦轉移至機器當中,《伶盜龍復活計劃》里恐龍復活是完全可以實現的,并且可以隨意改造成人們想要看到的模樣。《警車傷人事件》中警車的智能系統已經被生物大腦所替代,機器擁有著人類的大腦,其能力甚至超越人類,《天國之路》里人類已經可以探索極為遙遠的星球,科技極大提高了人類對宇宙的認識,讓人類擁有了更加廣闊的空間。
小說中的人類似乎走上了一條“邪路”,《訪客》中的教授利用人腦移植機器的技術逃脫了法律的制裁,雖然他的目的是為了人類,最終也拯救了人類,但其中的一些像宗教活動般的科技崇拜場景,是對科技至上主義的諷刺。作者在《球體》中提醒讀者應當對自然有所敬畏,科研工作者發現了一個球體遠古遺跡,并對球體進行了解密,不料卻像打開了潘多拉魔盒一般,不僅整個團隊全部喪生,危機甚至波及了整個世界。《警車傷人事件》則是對人工智能的思考,小說中的計算機及部分警車有人腦一樣的生物大腦,有著思考能力,終于為了獨立而反叛人類,人類對它們也無可奈何,但這場“獨立戰爭”最終因計算機沉迷游戲,像一出鬧劇一樣而收場。這似乎是一個經典的機器反抗人類的“古老”話題,但生物大腦沉迷游戲的收場方式也是對人類沉溺于網絡世界的諷刺。
現實世界中,科技的進步,幫助人類了解和征服自然,科技與自然的關系,也一直是科幻作者的創作題材之一,“1968年臺灣作家張曉風寫的《潘渡娜》揭示了人類的本性和科學性之間的矛盾……醒來之后的科學家說出的一段話表現出了作品的思想內涵:‘讓一切照本來的樣子下去,讓男人和女人受苦,讓受精的卵子在子宮里生長,讓小小的嬰兒把母親的青春吮盡,讓青年老,讓老年人死。大仁,這一切并不可怕,它們美麗,神圣而莊嚴”。[3]67汪彥中的小說也有類似的表達,在《伶盜龍復活計劃》中,為了利益的最大化,科學家對尚需深入了解的恐龍隨意進行基因改造,最終一條真正的伶盜龍出世,殺死了那些“冒牌貨”并飛走,故事結局給人留下了懸念,是像“侏羅紀公園”中的改造恐龍一樣大殺四方,還是和人類能夠和諧相處呢,同樣預示著濫用技術可能會造成一些未知的后果。《異變》中的科學家為了科學研究,進行了違背倫理的太空實驗,制造出了不可控制的怪物,對此,科學家非常興奮,竟然繼續加大力度進行“科學實驗”。在這一刻,科技失去了它本來應有的功能,變成了滿足部分人好奇心的工具。
在這一刻,讀者不禁要詢問,科學研究的意義是什么,科學研究者為何會做出背離人類道德倫理的研究,或許汪彥中的《癥候》會有答案。這是一篇有關精神幻覺的小說,小說中現實和幻覺交織在一起,讓人難以分辨,小說中的人物因難以辨別現實和虛幻而喪生。所有人從來沒有懷疑過自己眼前的是否是幻覺,正如前幾篇小說中,每個人物都認為自己做的事情都是理所當然或是不得已而為之,沒有人會認為自己有錯,所有人都已經忘了初心,忘記了“自己”。于是,科技語境下“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要到哪里去”等經典哲學問題再度被提出。
二、科技時代下的“方向”
人類對科學技術的追求與反思從未停止過,“自啟蒙運動以來,對技術的追求和反思就一直構成現代思想的關鍵辯證法。總體來說,人本主義哲學家們對現代技術能夠為現代生活提供倫理性改善持悲觀的態度”。[4]76但無論如何悲觀,不可否定的是,科技已經與人類社會交織在了一起,不可分割,“如今的世界,技術力量已無處不在,微觀層面的生活感覺變化有一種升級為宏大理念革新的趨勢。什么是人、什么是生命、什么是死、什么是情感、什么是藝術、什么是自由等一系列支撐現代人生活信念的知識,都面臨著新的歷史性變革,現代性知識也不例外”。[5]119所以,科幻作品更多需要從人本身出發,思考人類與科學技術的關系。作為新世紀的科幻小說作家,汪彥中的小說更多是思考身處科技時代的人類“要到哪里去”的問題。
《天國之路》表達出作者對這一問題的思考,科技會讓人類走向何方,人類的精神會因此變得純粹還是發生異化。小說主人公是一位宇航員,和三位隊友一起搭乘宇宙飛船被派往名為“天國”的外太空基地,卻不料這是一場徹頭徹尾的陰謀,飛船內被有計劃的“缺衣少食”,為了食物,四人互相殘殺,以求生存,因為只有經過生死考驗,異常冷酷并失去人性,才能在“天國”生存,“天國”上的工作人員都是通過這種方式篩選出來的。小說在結尾留下了懸念,主人公是選擇用生命毀滅“天國”,捍衛人的尊嚴,還是丟棄人性,在“天國”生存下去。
以科技時代作為背景,整個故事是荒誕的,荒誕是作者對故事人物生存狀態的否定,“這種極致化的書寫,寫出了作為此在的個體去感受本真存在狀態時的可能性境遇。這種可能性生活是荒誕的。透過這種荒誕,可以了解哲學上所謂的本真存在并不可靠。”[5]118小說中所發生的事件,是對未來可能的一種想象。作者進行假設,在未來,科技的發展可能會失去理性,通過荒誕,讓一系列事件以極端的形式出現,例如刻意讓宇航員在飛船中互相殘殺,只是為了培訓一名合格的工作人員,這是一種夸張,以此來否定以失去理性為代價的科技發展。除此之外,《伶盜龍復活計劃》中脫離人類控制的伶盜龍以及《變異》中無法消滅的巨大怪物,都是作者運用用荒誕的手法,表達出對非理性科技的否定,同時告訴讀者,科學技術應當有其合理的發展方向。
我們似乎可以從小說《夜眼》中看到作者對科技發展方向的看法,遭遇失業的主人公吳星,為了維持生計,不得不進行違法的“黑飛”活動,用先進的無人機配送外賣,無意間卷入了一場殺人案,經過一番的內心掙扎后,決定報警,并戴罪立功,協助警察成功抓捕了犯罪團伙。這篇小說非常難得地對科技進行了正面描寫,雖然《訪客》和《同溫層食堂》中的科技也發生了積極作用,但《訪客》中一些如宗教般的描寫場景頗具諷刺意味,而《同溫層食堂》中的科技只是一個背景板,不是作者主要描寫的內容。
《夜眼》的故事背景離當下并不遙遠,無人機在現實中已經存在,配送外賣、警察抓捕犯人,都貼近現實生活。通過寫實,可以讓讀者更容易理解作者的想法,故事中,先進的無人機一開始進行著“黑飛”的違法活動,隨著故事情節的推進,無人機成了破案的重要助力,這一轉變的根源在于主人公善良的天性,通過“黑飛”送外賣也只是為了生計,主人公發現惡性事件后,即使知道會失去自己賴以為生的工具甚至是被處罰,仍選擇向警方提供信息。當然,除了主人公和他的無人機,成功破案還與具有正義感和堅持不懈的青年警察有關,人本身才是破案的關鍵,科技只是輔助工具,人使得工具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人應當控制和支配科技,而并非科技控制人。《天國之路》詮釋了科技控制人的世界,人會像“天國”工作人員一樣喪失人性,小說主人公如果選擇與“天國”同歸于盡,代表了這個非人性世界的毀滅。如果選擇活下去,他則會喪失作為人的資格。
在作者看來,當人的主體性被機器所取代時,人類所構建的道德、倫理將會被消解,人類也將會失去自己成為人的根基,文明將會蕩然無存。在科技多元化的今天,保持人類的主體性,還應思考科技時代下的人文情懷。
三、科技時代下的人文情懷
科幻小說是關于未來的想象,可以向當下的人提供有關未來的經驗,想象是否能夠指導現實,學者吳巖認為:“科幻作品中的想象如果說對現實有益,那么這是因為這種想象讓人離開現實。而科幻的作用比實現某種預言要復雜且豐富得多。撫慰人的心靈,提供多種可能的未來藍圖,建立信心,增加生活驅動力,造福個體和種群等都是想象的功能所在。”[6]27無論是烏托邦、反烏托邦還是惡托邦,都是對未來某種可能的預測。而這一可能,植根于現實,源于科技社會和人文社會的沖突,當二者產生沖突時,一個烏托邦或惡托邦社會才會在科幻作家的筆下誕生,正如劉易斯·芒福德在《烏托邦的故事》中寫道:“只有當現實世界與烏托邦世界之間出現巨大沖突,我們才能意識到烏托邦意志在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才會把我們心中的烏托邦視為一種獨立存在的現實。”[7]03
出于對現實沖突的思考,汪彥中小說筆下的社會,部分頗具惡托邦意味,“惡托邦具有強烈的‘批判現實主義色彩,攻擊的目標相對具體而狹窄,它揭示一種隱匿在現實內部的疾病,預示如果不采取措施將不可避免可怕的惡果,以此促成積極行動的意識。”[8]301現實中,當下的人過多沉迷于網絡虛擬空間中,導致現實生活中所建構的道德倫理和價值觀受到了沖擊,科技逐漸有脫離人文情懷的趨勢,汪彥中筆下的惡托邦小說,正是對缺乏人文情懷社會的警示。
《異變》系列的“訪客”中,當權威教授不被人理解時,拒絕質疑自己的人來訪,只選擇與相信自己人接觸,形成了一個“科學宗教”,“教徒們”對他奉若神明,科學本與宗教相對,但這一刻,科技與宗教崇拜竟是如此融洽的合為一體。一個缺少人文情懷,技術至上、科技崇拜的社會一旦形成,人類耗費數百年所建立的現代化社會將會迅速分崩離析,再次回到“中世紀”社會。作者在小說中描述了一種將大腦轉移至機器中的技術,這一技術表現了當下人對生命意義的疑惑,可以延伸出一個關于人本身的問題:失去身體,被異化后只剩下意識的人還能稱之為人嗎,人稱之為人,最重要的究竟是什么。“在計算機、網絡、虛擬世界、基因克隆等高科技產物的影響與沖擊下,傳統意義上的人正在被改寫,人類正在運用日漸發達的人工智能與機器對客體(身體)實施前所未有的控制與改造。人與動物、人與機器、物質與非物質之間的界限日益模糊,生命經驗與自然身體的脫離、‘身體是什么‘什么構成了身體‘身體的意義何在成了后人類社會中人們普遍的焦慮。”。[9]171
大家可以從《警車傷人事件》來分析這個問題,小說中的電腦已經是真的“腦”,擁有生物大腦的它們相當智能,不僅能和人交流,有報復心理,擁有獨立和自由的意識,還能為同類兩肋插刀,那么,它們算是人類嗎?擁有人類般大腦的智能機器和擁有機器身體的人,哪個才是人?前者當然不是人類,但是后者也可能已經脫離了人類范疇。當人類失去了身體后,也就失去了自己作為人的獨特性,也失去了倫理和人性,對于這種人性主體缺失的未來,人們應當警惕。
汪彥中的小說不全是具有“惡托邦”色彩,《同溫層食堂》中就向大家展示了科技時代的“人文情懷”。小說中的大廚是人類感性的代表,他一直生活在“地上”,還保留著人類豐富的情感,每天都變著花樣給空間站的研究人員烹調食物。而上一任大廚,由于空間站這種冷冰冰的環境,受到了影響,發生異化,日復一日烹調同樣的食物,他代表著受科技影響而異化的人。
這二人是一種鏡像關系,都是因為“地上”出現變故,需要用錢才選擇到同溫層空間站工作,所以二人有著相似的經歷。但新一任大廚沒有被環境所異化,他放棄了上一任大廚留下來的固定菜譜,用自己的人文情懷改變了環境。在現實社會中,不同國家和同民族都有各具特色的飲食習慣,飲食文化是人類文明的代表之一,小說中的食物代表著人類的倫理、道德以及價值觀。食物拯救了科學工作者,即人文情懷讓科學回到了原有的軌道,避免了惡托邦社會的發生。
烏托邦和惡托邦都是科幻小說家們的一種假設,科技的發展可能會破壞人固有的道德、倫理和價值觀,使人喪失主體地位,但這只是未來的可能之一。未來也有可能是人文情懷和科技相結合,共同發展,使人類邁向一個嶄新的未來,這也是作者所呼吁的。
參考文獻:
[1]王衛英.中國科幻小說的文學價值與審美批評[J].中州學刊,2018,(01).
[2]唐媛媛.作為“同時代”文化鏡像的寫作——評王威廉新作《野未來》《你的目光》[J].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3,(02).
[3]湯哲聲.20世紀中國科幻小說創作發展史論[J].文藝爭鳴,2003,(06).
[4]楊慶祥.后科幻寫作的可能——關于王威廉《野未來》[J].南方文壇,2021,(06).
[5]唐詩人.以未來為經驗:論王威廉的“純文學科幻”[J].當代作家評論,2022,(03).
[6]吳巖.論中國科幻小說中的想象[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8,(12).
[7](美)劉易斯·芒福德.烏托邦的故事:半部人類史[M].梁本彬,王社國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
[8]歐翔英.烏托邦、反烏托邦、惡托邦及科幻小說[J].世界文學評論,2009,(02).
[9]肖薇.從去身化到具身化的反思——劉宇昆科幻小說“未來三部曲”中的現實主義與反烏托邦[J].廣西社會科學,2019,(03).
作者簡介:
李琰,男,陜西安康人,陜西理工大學人文學院在讀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