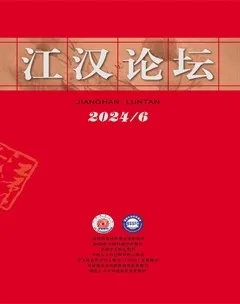江南文化的特征與精神內涵
摘要:江南文化的特征與精神內涵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江南文化特征是指在與其他區域文化比較中歸納出的帶有顯著性或符號性的地域文化事象,所要說明的是“何為江南文化”;而江南文化精神則是指在江南文化發展過程中具有連續性、指引性的精神動力和思想基礎,所要闡明的是“何以為江南文化”的問題。前者是表征,后者是內核。基于此,江南文化特征可歸納為水鄉文化,開放包容、適時順變、持續創新,崇文重教和追求精細雅潔生活方式四個方面;而江南文化的精神內核則可凝練為經世致用精神、敢于質疑和挑戰權威的批判精神以及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關鍵詞:江南文化;特征;精神內涵
中圖分類號:K2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54X(2024)06-0126-09
一、問題的提出
目前學術界對于江南文化的特點或精神特質的總結已有不少成果,如熊月之為上海書店出版社策劃的“江南文化研究”叢書撰寫的總序中,將江南文化特質概括為四個方面,即開放包容、擇善守正;務實創新、精益求精;崇文重教、堅強剛毅;尚德重義、守望相助。景遐東通過考察江南文化的形成過程,指出江南文化的特征主要表現為:一是人性普遍較靈秀素慧,利于藝術;二是氣質心胸曠放、豪邁勇武;三是普遍崇文、重視文教;四是具有開放性與包容性;五是鮮明的宗教特質。(1) 莊若江認為,江南文化的精神內涵主要表現為務實進取、經世致用,兼收并蓄、開放善納,智慧靈動、善于變通,崇文重教、詩禮傳家,詩性審美、精細雅致等方面。(2) 胡發貴指出江南文化的精神特質主要有“南方之強”、啟蒙精神與經世致用情懷。(3) 劉士林在批判經濟學的江南研究和歷史學的江南研究遮蔽了“江南文化的詩性內涵”的基礎上,提出“江南文化本質上是一種以‘審美—藝術為精神本質的詩性文化形態”的命題,認為“江南詩性文化是江南文化的核心內涵與最高本質”。(4) 毫無疑問,各位學者都是基于自己多年的研究積累并博采眾長而提出對于江南文化特征或精神特質的認識,不管是否能成為共識,自有其合理性。不過,我們認為江南文化的特征與精神內涵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應該首先加以厘清。江南文化特征是指在與其他區域文化比較中歸納出的帶有顯著性或符號性的地域文化事象,所要說明的是“何為江南文化”;而江南文化精神則是指在江南文化發展過程中具有連續性、指引性的精神動力和思想基礎,所要闡明的是“何以為江南文化”的問題。前者是表征,后者是內核。兩者雖有聯系,但存在明顯區別,不可混為一談。
二、江南文化的特征
江南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因此其與構成中華民族文化的其他各支文化存在共同點,但是,作為一種區域文化,由于所處的自然地理環境與社會歷史背景的不同,江南文化又形成了區別于其他區域文化的特點。當然這種特點只是相對的。區域文化的個性并不意味著某種絕無僅有的屬性和特征,而是指某一區域的人們能夠根據自身所處的自然社會環境,使文化生長的共性中那些具有活力或積極意義的要素得到最充分的發揮。(5)這是我們理解江南文化特征的前提。
(一)水鄉文化是江南文化的底色
正如“大漠孤煙”“古道西風瘦馬”這樣的詞語或詩句,能夠讓我們聯想到北方塞外;而“杏花春雨”“小橋流水人家”則是一種江南意象,是給人們最為直觀、最為深刻的江南印象。
江南地區氣候溫暖濕潤,雨水充沛,瀕江靠海,河流湖泊星羅棋布、縱橫交錯,構成燦爛多姿的水鄉景觀。水鄉澤國既是江南文化賴以生存發展的基礎,也是江南文化的存在方式。清代蘇州人袁景瀾說“東南之利,莫大于水矣”(6),水對江南文化的發生、發展、塑造所施與的影響,涉及到生產、生活、文化等各個方面,成為江南文化之魂。
江南尤其是太湖地區素稱魚米之鄉,自古以來即種植水稻,是我國稻作農業的發祥地之一。早在新石器時代遺址中,考古工作者即已普遍發現了稻谷遺存。到春秋時代,吳、越兩國的水稻種植業大為發展,成為社會生產的主要部門。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江南農業經濟得到快速發展,出現了“谷帛如山,稻田沃野,民無饑歲”的繁盛局面。隨后,江南地區農業生產由粗耕轉變為精耕,生產力水平不斷增長,在全國的經濟地位逐步提高,尤其是唐宋以后,江南經濟持續發展,終于成為國家的財政支柱和經濟中心。北宋著名水利學家郟亶曾經說過,天下之利,莫大于水田。水田之美,無過于蘇州。水稻的種植離不開水,因此江南農業生產的發展與水利的興修是同步進行的。從文獻記載來看,江南地區大規模的開河筑渠之舉代有所聞,春秋吳國開胥溪與筑邗溝、東漢馬臻“創立鏡湖”、隋代開挖江南運河、五代吳越國整理塘浦、宋代修筑圩田等,均是眾所周知。尤其吳越至宋代,“五里七里一縱浦,七里十里一橫塘”規格化的塘浦圩田體系,更成為江南農業文化的一大獨特景觀。水利是農業的命脈,農業是經濟的基礎。江南人民在長期的生產實踐中,利用土地肥沃、氣候溫潤、水利發達的自然條件和優勢,發展以水稻為主要內容的農業文化,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創造了中國農業文明的輝煌。
江南文化的水鄉文化特性,還突出地表現為魚文化的豐富多彩。據說吳國之吳與蘇州之蘇(蘇)即由魚生發而來。農業文明之前,人類經歷了一個以采集、漁獵為生的時代。特別是水鄉地區,漁獵在人類的生活中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漁業是從人們捕魚摸蝦開始的。隨著人們捕魚經驗的積累、漁獵工具的改進,捕魚量大為增加,于是逐漸發明了魚的人工飼養。從捕撈天然魚類到人工飼養,是漁業史上的一次重大飛躍。江南地區人工養魚始于何時,學術界尚無定論,但一般認為始于春秋吳越時期。不過,吳越時期的筑城養魚,與其說是人工養魚的開始,毋寧說是人工養魚的普及時期。世界上最早的養魚專著——《養魚經》據說即出于越國謀臣范蠡之手。書中論述了養殖對象、魚池建造、密殖混養輪捕、良種選留及產卵孵化等方面的問題,應該說是對前此人工養魚經驗的一大總結。這樣的著作只有在人工養魚已經普及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出現。此后,江南地區的農業盡管有起有伏,而漁業卻日趨興盛,所謂“魚、鹽、杞、梓之利,充仞八方”,《舊唐書·李乂傳》中說,江南水鄉,采捕為業,魚鱉之利,黎元所資,土地使然,有自來矣。江南水產豐富,魚類眾多,其中有不少名品蜚聲海內,以致成為朝廷貢品。由于漁業產量的增加,魚被大量投入市場,以至吳人買賣魚類,不是論斤秤兩或按條折價,而是以斗數魚,大出大進。這一方面是因為捕撈能力的增強,從內陸拓展到了海上;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人工養魚的推廣普及所致。由于漁業是江南地區生產的一個重要門類,故魚與人們的生活關系密切,不僅表現在飲食中,所謂“吳地以船為家,以魚為食”,各種水產魚饌是江南人的共同所好,而且表現在民俗、建筑等方面。如蘇州人立夏日風俗有見“三新”,其中有黃魚、海螄與鰣魚組成的“河三鮮”;蘇州的陽澄湖大閘蟹名聞遐邇,國學大師章太炎夫人湯國梨有詩云“不是陽澄湖蟹好,人生何必住蘇州”,而吳地人為了食蟹方便、顯示優雅,還發明了專門用具“蟹八件”,用銅或銀制作,舊時還以之作為姑娘結婚時的陪嫁品之一。蘇州園林中不僅有眾多的魚形圖案、漁網紋鋪地、魚形建筑與裝飾,還取有不少與“魚”或“漁”相關的名稱,如網師園的“網師”,即取漁隱之意,此外還有“魚樂”“鳶飛魚躍”等。在勞動生產過程中,漁民們觸景生情,往往即興自編自唱船歌,以此表達自己的喜怒哀樂。這些船歌是吳地漁民富有特色的文化創造,是吳歌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江南水鄉還孕育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橋文化與船文化。江南地區的橋梁不僅數量眾多、類型齊全,而且橋名、橋聯等蘊含著豐富的歷史文化底蘊,反映出江南人的審美情趣。唐代詩人杜荀鶴一首《送人游吳》詩膾炙人口,詩中稱:“君到姑蘇見,人家盡枕河。古宮閑地少,水港小橋多”。十分典型地反映出蘇州的水鄉文化特色。蘇州人家,臨街枕河,“家家門前泊舟航”。有水之處必有橋,蘇州的橋,精致小巧,似繁星點點,遍布城鄉,其數量之多、分布之密,非他處可比。作為一種散布于江南水鄉的地域景觀,橋梁是歷史的濃縮、文化的積淀。江南地區橋梁眾若繁星,橋名燦如花錦,大凡所稱,必出于典。有的以人物命名,有的關乎歷史故事,有的歌頌盛世、取其吉祥,有的與生產、商業活動有關。可以說,江南地區橋梁的名稱,蘊含著豐富的文化內涵,是一部化石般的地域文化辭典。與中原人躍馬橫刀、縱橫馳騁的景觀形成對比,江南人“以船為車,以楫為馬”,形成了水鄉船文化景觀。江南地區出門見水,非舟莫辦,故有“不可一日廢舟楫”的說法。因此,造船業歷來興盛,并且憑借發達的造船業,江南地區溝通了與海外的聯系,而作為中國乃至世界航海史上的壯舉,明初的鄭和下西洋也是從江南太倉啟航的。由于“吳兒駛船如駛馬”,生產與生活均離不開船,經過長期的積累、沉淀,形成了許多與船有關的風俗習慣與信仰。漁船是漁民的生活空間,漁船的建造是漁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從開工到下水,一般要舉行開工、定圓、下水三次慶典,既有吳地建房喜慶、祝愿的程序,又有濃厚的祈神色彩;漁民在水上打魚,經常會遭遇風浪,翻船溺死者屢見不鮮,因而在漁船上忌諱與翻、沉有關的語言和行為;水產是漁民的主要食品之一,漁民吃魚也有種種規矩和禁忌。
俗語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水鄉地理環境孕育、滋養了豐富多彩的江南文化,水鄉文化特性在江南社會、人們生產和生活的各個方面均留下了深刻印記。甚而言之,水鄉文化特性還滲透到了江南文化的深層結構,如吳語的溫婉柔軟,昆曲、評彈、越劇等戲曲的柔婉悠揚,吳人的清麗秀美幽雅從容等,無不融入了水的靈性。水,既是江南文化生成、發展的重要條件,又是江南文化自身特色的重要表現。
(二)江南文化具有開放包容、適時順變、持續創新的特性
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江南文化的面貌不斷變化、更新,物質方面從相對落后發展為財富之區,精神方面從為人鄙視的蠻夷之邦轉變為世所公認的人文淵藪,行為方面從崇尚武力轉而為崇文尊道,表現出由野蠻到文明、由落后到先進的發展軌跡。其所以如此,即與江南文化具有開放包容、適時順變的特性有關。
江南文化的開放性早在其萌芽時期即已表現出來。從淵源而言,江南文化是多元文化融合的結晶。浙江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前后相承,脈絡清晰,后來夏禹的后人建立越國,形成南北融合的越文化。至春秋晚期,越王勾踐在來自楚國的范蠡、文種等人的幫助下逐漸強大,經過臥薪嘗膽,終于打敗吳國,并通過徐州會盟成為諸侯霸主。所以,有學者認為,至少從春秋后期起,越族已開始與華夏族融合。(7) 而在吳地,寧鎮地區的新石器文化與太湖地區新石器文化早就開始了接觸,但促成吳文化形成的契機卻是由于周人的介入。商代末年,地處西北的周族首領之子太伯、仲雍南奔荊蠻之地,建立吳國,標志著吳文化的形成。吳國建立以后,加強了與中原文化及周邊文化的交流,使得吳文化的面貌漸漸發生了變化。逮至春秋,吳國名君壽夢執政以后,吳國與中原地區的交往更為密切,史載他曾“朝周適楚,觀諸侯禮樂”,并先后會盟中原諸侯。在觀賞了中原禮樂以后,壽夢為中原先進文化的魅力所傾倒,大發感慨:“孤在蠻夷,徒以椎髫為俗,豈有斯之服哉?”(8) 因而歸國以后,勵精圖治,建立晉吳聯盟,發展國力,短短幾年間,即與西鄰楚國展開了激烈的爭戰,“蠻夷屬于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于上國”。(9) 同時在國內倡導學習中原文化,這從其幼子季札精通中原禮樂文化方面可以得到佐證。闔閭也是一位深受中原文化熏染的吳國君主,繼位以后,先后任用來自楚國的伍員、齊國的孫武等人,以中原先進國家為榜樣,進行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的改革,取得了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南伐越人的顯赫功績。以此為基礎,吳王夫差通過黃池之會,最終確立了霸主之位。由此可見,正是吳國統治者采取了主動學習、積極吸取中原文化的政策,才一改吳文化的落后面貌。在與中原諸國及楚、越等國文化的碰撞、交流過程中,吳文化自身也不斷進步、升華。
吳、越兩國滅亡后,江南地區被納入秦漢統一王朝的版圖。江南文化在潛移默化之中,接受著中原文化的滋潤,特別是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士民大量南下,不僅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管理經驗,增加了江南地區的勞動人手,從而促進了江南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而且使中原地區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明深入江南,為江南文化補充了新鮮血液,激發了江南文化的生命活力。江南文化在保持區域特質的前提下,與中原文化逐漸趨同,顯示出多彩的風姿。如熊月之在“江南文化研究叢書”總序中所指出的:“西晉永嘉之亂、唐代安史之亂與宋代靖康之亂,使得中原大量人口向江南遷移。北人南遷不是難民零星遷移,而是包括統治階層、名門望族、士子工匠在內的集群性遷移,是包括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文化知識、價值觀念、審美情趣等在內的整體性文化流動,即所謂‘衣冠南渡,這對江南影響極大……但對于江南而言,則是一種全面的文化開放與交流交融”。(10) 誠然如此,每一次北人南遷和中原文化的南來,都促進了江南社會經濟的進步與文化的發展,也正是在與北方文化的沖突、交流與融合中,江南文化去蕪取精、不斷升華,實現自身的蛻變與超越。可以說,沒有北人南遷和“衣冠南渡”,就不會引起經濟重心與文化重心的南移,江南地區也不可能成為全國的經濟中心和文化中心。
由此可見,江南文化在六朝、唐宋時期經歷了幾次蛻變和自我更新的過程。面對中原文化的沖擊和挑戰,江南文化適時順變,以開放的姿態迎接挑戰,積極吸取中原文化的先進成果,相與融合,不斷改造提升自身品質,從而使江南文化舊貌換新顏。以此為契機,江南經濟文化走上了持續發展的道路,以嶄新的姿容出現在世人面前。進入近代,江南文化再次發生巨變。面對資本主義列強的堅船利炮,江南人最先睜眼看世界,憑借沿江傍海的優勢,江南地區成為西學東漸的橋頭堡。一批力倡改革、主張學習西方先進文化科學技術的思想家和改革派人物率先在這片土地應運而生,王韜、馮桂芬、薛福成、馬建忠等即是杰出代表。在他們的影響下,江南文化主動融攝外國先進的科學技術和思想文化,在江南誕生了一批最早的近代企業和文化機構。江南地區之所以最早走上近代化之路、江南文化之所以最先開始近代化歷程,開放包容、適時順變、持續創新的特性即是其主因之一。
(三)崇文重教是江南文化的突出特點
先秦秦漢時期,江南地區崇武尚勇,“輕死易發”“好相攻擊”成為江南民風的顯著特色。雖然期間亦曾出現過太伯“端委,以治周禮”,季札觀樂,見解高明,被稱為吳國君子,言偃從游,“得圣人之一體”,“而吳知有圣賢之教”等崇文之例,但不足以反映社會風氣的主流。漢代以后,江南地區好學尚文之風漸興,尤其隨著北方先進文化的傳入,江南民風有了很大改變。在這樣的背景下,文人學士輩出,在文學、藝術、學術等各個方面均取得顯著成績,如顧野王學識淵博,于歷史、地理、文學、書畫藝術均有很高造詣,而以語言文字學成就最為突出,所著《玉篇》30卷,是我國現存最早的楷書字典;西晉時期的陸機,在詩歌、散文方面均有建樹,被譽為“太康之英”,所撰《文賦》是第一篇完整而系統的文學理論作品,對后世文學創作和文學理論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繪畫、書法藝術漸趨成熟,涌現出一批書畫名家,王羲之、王獻之父子成為魏晉新書風的代表人物。由此尚武之風漸湮,崇文風氣盛行,《隋書·地理志》中的記載典型地反映了這一變化過程:雖說江南地區“其人并習戰,號為天下精兵”,但就其總體情況而言,乃是“其人君子尚禮,庸庶敦龐,故風俗澄清,而道教隆洽”。至明清時期,江南之人“敏于習文,疏于用武”、人文昌盛的情況,終為世人矚目,成為公論,所謂“吳為人材淵藪,文字之盛,甲于天下。其人恥為他業,自髫齔以上,皆能誦習,舉子應主司之試,居庠校中有白首不自已者。江以南其俗盡然”。(11) 與此相應,江南地區人文薈萃,文風日熾,成為“禮義之區,儒雅之藪”,逐步確立起在全國的文化中心地位。
江南地區的人文興盛,首先表現為教育的發達。南方教育的勃興,由蘇州發端。宋仁宗時,范仲淹知蘇州,創建府學,延聘教育名家胡瑗主持。后胡瑗又主持湖州州學,結合蘇州的實踐,創立“蘇湖教法”,以“明體達用”為宗旨,實行分齋教學,因材施教,培養出大量才俊。在慶歷興學運動中,范仲淹將胡瑗及其教學方法推薦給朝廷,得到宋仁宗的采納。朝廷在京師設立太學,延聘胡瑗為教官,仿效蘇湖教法訂立太學制度,從而使得“蘇湖教法”產生了全國性的影響。以此為契機,北宋時各級官學推行全國,江南各州、縣均設立學校,所謂“天下郡縣學莫盛于宋,然其始則亦由于中吳。蓋范文正公以宅建學,延安定胡先生為師,文教之事自此興焉”。(12) 在江南地區經濟發展、文化興盛的社會背景下,江南各地的地方官員無不以重教興學為己任,“重學校,禮文儒”成為眾多地方官的行為選擇。明代蘇州人王锜在《寓圃雜記》卷5《蘇學之盛》中提及“吾蘇學宮,制度宏壯,為天下第一”,說明蘇州地方官府在學校教育方面不吝投入,當然成效也極為明顯,“人才輩出,歲奪魁首”。江南核心地區固然如此,邊緣的徽州又未嘗不是如此,道光《休寧縣志》中說,新安自南遷后,人物之多,文學之盛,稱于天下。當其時,自井邑田野以至遠山深谷,居民之處,莫不有學有師,有書史之藏。除了官辦的學校以外,還有官民合辦的書院以及私學性質明顯的族學等培育人才的機構。據研究,明代江、浙兩省書院數分別為119所、170所,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103所;清代全國平均數為229所,而江蘇則有253所,浙江更多達336所。(13) 族學是宗族特有的設教體制,據有人對地方志的不完全統計,清代江、浙兩省的族學至少有804所,其中江蘇有441所、浙江有363所。(14) 由書院與族學的普及情況,可見江南地區的文教發達之盛況。
其次表現為讀書風氣濃厚。由于江南地區崇文尊教風氣的流行,擔任地方守土之責的官員固然認識到“化民成俗,莫先于興學育材”,而那些大家巨族、書香門第乃至于缺少功名背景的普通家庭也無不抱定“科甲仕宦,顯親揚名,皆從讀書中來”的宗旨,由是汲汲于學。這一點在江南地區的家譜家訓中表現得尤為明顯。浙江海寧查氏家族是一個簪纓相繼、文脈不絕、名人輩出的文化望族,有“一門十進士,叔侄五翰林”之稱,被康熙皇帝譽為“唐宋以來舊族,江南有數人家”,其家族聲譽綿延的重要原因便是歷代家訓強調子孫讀書修身,“勵學型家”,“凡為童稚,讀書為本”,“不可不學,以延讀書種子”。(15) 江蘇常州惲氏家族有“著姓甲于常州”之譽,名碩相望,代有達人,其家訓中強調“禮教不可失,故子孫雖愚,經書不可不讀”。(16) 蘇州家訓眾多,上至權貴下及平民之家均有家訓存留,其中的訓子言論,最為強調讀書,要求子孫以讀書為務,所謂“子弟第一以讀書為本”“人生至樂,無如讀書,至要,無如教子”。(17) 徽州處于江南的邊緣之區,好學讀書之風也大量見于時人記述和家訓,甚至表于門楣,如明代歙縣鹽商程文博臨終前告誡其子“繼志莫如讀書”;(18) 清代績溪東關《馮氏家訓》中指出:“一族之中,文教大興,便是興旺氣象。古來經濟文章無不從讀書中出”。在明清徽商留存下來的宅第中,常可見到“幾百年人家無非積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讀書”“欲高門第須為善,要好兒孫必讀書”等楹聯。(19)
正因為如此,江南地區成為人才匯聚輩出之地。經過長期開發,江南地區的自然、人文環境得到很大改善,享有“天堂”“樂土”的美譽,吸引了大量的外地士人前來居住,“天下賢俊多避地于此”,號稱“士大夫淵藪”。明清時期在蘇州等地廣為流傳的《勉學歌》,所述“書中車馬多如簇”“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千鐘粟”“書中自有黃金屋”,典型地反映了江南人視讀書科舉為出人頭地、光宗耀祖、實現自身價值的心理訴求。正是在這種價值觀的支配下,江南地區通過讀書、科舉而步入仕途或精研學問者大量涌現,甚至出現了狀元潮涌的奇觀。
(四)江南文化崇尚精細雅潔的生活方式
不同的地理環境和歷史文化傳統,造就了差異多元、豐富多彩的生活方式。在生產力水平低下、經濟落后的背景下,解決溫飽是人們生存的第一需要,而在經濟發展起來以后,人們開始追求高品質的生活,正所謂“倉廩實知禮節”。唐宋以后,江南地區山川清嘉、環境優美、經濟發達、文化興盛,人們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生活品質大為改善。盡管江南地區內部也存在地域、城鄉等方面的區別,但無不表現出對精細雅潔生活方式的追求和欣賞。
江南文化崇尚精細雅潔的生活方式,體現在衣、食、住、行、玩等各個方面。衣必錦繡,食必應時,居必園林,玩必古董,常年追求山水林下之樂,在日常生活的細節上下功夫。既往研究大都從奢侈消費的角度看待這些問題,但如果換個視角,這又何嘗不是江南大眾對精細雅潔高品質生活的追求呢?
江南地區的飲食文化最為典型地反映了江南人的精致生活。江南人對飲食的講究是其他地方難以并論的。明清之際松江人葉夢珠《閱世編》卷9中詳細記載了吳地民間宴會的變化過程:“肆筵設席,吳下向來豐盛。縉紳之家,或宴官長,一席之間,水陸珍饈,多至數十品。即士庶及中人之家,新親嚴席,有多至二三十品者,若十余品則是尋常之會矣。然品必用木漆果山如浮屠樣,蔬用小磁碟添案,小品用攢盒,俱以木漆架架高,取其適觀而已……崇禎初始廢果山碟架,用高裝水果,嚴席則列五色,以飯盂盛之……順治初,又廢攢盒而以小瓷碟裝添案,廢鐃碗而蔬用大冰盤,水果雖嚴席,亦止用二大甌。旁列絹裝八仙,或用雕漆嵌金小屏風于案上,介于水果之間,制亦變矣。……康熙之初,改用官式花素碗,而以露莖盤及洋盤盛添案。三四人同一席,庶為得中。然而新親貴客仍用專席,水果之高,或方或圓,以極大磁盤盛之,幾及于棟。小品添案之精巧,庖人一工,僅可裝三四品。一席之盛,至數十人治庖,恐亦大傷古樸之風也”。(20)他們不僅賽食品之豐盛,而且比器皿之精美、形式之美觀,菜、蔬、果與碗、碟、盤的種類、顏色、形狀等搭配俱有講究,并隨時代變遷而變化。江南地區四季分明,不同季節有不同的蔬菜果品,每當新鮮蔬果上市,人們爭相品嘗,謂之“賣時新”,清人顧祿《清嘉錄》卷4說,蔬果、鮮魚諸品,應候迭出,市人擔賣,四時不絕于市。而夏初尤盛,號為“賣時新”。說明吳人喜食新鮮果蔬,且自明至清早已成為民間習俗。江南水鄉,水產是人們日常的菜肴。蘇州民間食魚亦按時序,民諺有云:正月塘鯉魚,二月鱖魚,三月甲魚,四月鰣魚,五月白魚,六月鳊魚,七月鰻魚,八月鲃魚,九月鯽魚,十月草魚,十一月鰱魚,十二月鯖魚。既順應魚產時序,亦出于養生考慮。明清時期江南文人著有多種食譜、菜譜或相關小品文,如袁枚的《隨園食單》、李漁的《閑情偶寄》“飲饌部”等,講究烹制之法,追求口腹之欲,總結養生之道,將烹飪之技、飲食之道與生活審美相結合,在中國飲食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雖然江南人的精致更多地反映文人士大夫階層的生活,往往被視為“文人品味”,但實際上帶有一種全民參與的意味。換而言之,對精致文化的追求并不限于文人士大夫階層,而是風靡江南城鄉、遍及社會各個階層群體。如服飾方面,明代后期松江人陸楫謂:“今天下之財賦在吳越,吳俗之奢,莫盛于蘇杭之民,有不耕寸土而口食膏粱,不操一杼而身衣文繡者,不知其幾何也”;(21) 乾隆《安吉州志》卷7《風俗》中說,城市衣紗羅者頗多,服尚時式,即使在鄉村也是如此。再如妝飾,江南地區早有以鮮花妝飾的時尚,“吳城大家小戶婦女,多喜簪花”;(22)南京婦女以鮮花助妝也是一種時尚,金百捱《金陵竹枝詞》有云:“白門時樣髻梳叉,秋日飄香艷似霞。動費千錢人不識,晚妝頭上數枝花”。花可插在頭上,亦可掛在身上,至今蘇州街頭賣茉莉鮮花掛飾的小販也時有所見。頭上插花或身上佩花,既助妝容,亦能起到類似香水的作用,微風拂過,香氣宜人。鮮花既能作為個人妝飾,也能作為居家裝飾,美化環境,提高生活質量,文震亨《長物志》卷2稱,茉莉、素馨、夜合夏夜最宜多置,風輪一鼓,滿室清芬。凡此可見,江南之人的日常生活,由俗趨雅,是其追求精細雅潔生活方式的必然結果。
當然,江南文化還具有其他的特征,如已被人們所提及的靈動變通、擇善守正、堅強剛毅等,但有的難以具體論證,有的與其他區域文化相比表現未必突出。而上述所論,應是能夠得到人們首肯并形成共識的。
三、江南文化的精神內涵
江南文化之所以后來居上,發展為令世人矚目的先進文化,固然有多種原因,但其精神內涵無疑起到了更為重要的促進作用。
(一)崇尚實學的經世致用精神
經世致用就其核心要義而言,是指經邦治國、濟世安民的學問,其中包含著“重實用、重實踐的理念,家國天下情懷和入世擔當的精神”。(23)經世致用思想是傳統儒家的核心思想,但在江南地區得到了最為顯著的傳承與弘揚。
早在東漢時期,會稽上虞人王充的思想學說中即表現出了“經世致用”精神,一是體現于他兼融儒法的政治觀,認為學術旨在治國,儒法皆應實用;二是體現于他對待文章用世的態度,《論衡·自紀篇》中提出,文章“為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為用者一章無補”。這是典型的學以致用思想,并為后世江南經世致用精神的勃興提供了思想資源。(24)
南宋浙東地區出現了以薛季宣、陳傅良、葉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以陳亮為代表的永康學派和以呂祖謙為代表的金華學派,合稱浙東學派。浙東學派或稱“事功學派”。學界一般認為,經世致用思想即發源于浙東學派的“事功之學”。永嘉學派的開創者薛季宣以經世實用目的為旨歸,超脫程氏洛學性命義理的糾纏,“倡導一種更為平典質樸的、以古制的考訂為手段的‘確實有用之學,以求在現實政治事務的合理措置中收到其價值的實效”。(25)這一治學途徑與目的,被陳傅良、葉適等人繼承,開辟出以經濟世務為特征的“事功之學”。
宋明理學雖然是儒學發展的新形態,卻與原始儒學的精神逐漸背離,走向讀書窮理、靜敬修養的極端,甚少考慮治世、民生事務,使學術與事功判若兩途;與此同時,宋明兩朝覆滅于文化落后的少數民族的慘痛歷史教訓,引發了明清之際一大批官僚學者與思想家的震撼與反思,他們或從學術或從思想上進行撥亂反正,提倡“經世致用”的實學。明末東林黨領袖人物高攀龍,不滿于江河日下的社會現實以及王學末流空談心性的弊端,明確提出“救世”主張,指出讀書“須要句句反到自己身上來看”,“一面思索體認,一面反躬實踐”,“學問不貴空談而貴實行也”,要求“學者以天下為任”,“立朝居鄉,無念不在國家,無一言一事不關世教”。(26)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的昆山人顧炎武,治學以“明學術,正人心,撥亂世,以興太平之事”為宗旨,曾自言“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故凡文之不關于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而既以明道救人,則于當今之所通患,而未嘗專指其人者,亦遂不敢以辟也”。(27)所以,顧炎武弟子潘耒在《日知錄序》中稱,顧炎武治學“尤留心當世之故……經世要務,一一講求”,“事關民生國命者,必窮源溯本,討論其所以然”。(28)同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的余姚人黃宗羲批評理學末流“束書不觀,游談無根”的惡劣學風,反復強調經世致用的為學原則,如《留書·科舉》中提出要“通今致用”,《今水經序》中主張“儒者之學”應以“經緯天地”為追求,“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為民用”。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指出,明末清初的儒學者對于明朝之亡,認為是學者社會的大恥辱、大罪責,于是拋棄明心見性的空談,專講經世致用的實務。這樣的學者還包括后來的戴震、章學誠以及乾嘉時期江南地區的眾多考據學者。盡管“經世致用”成為一股普遍的思潮流行廣泛,但無疑以江南地區最為突出,不僅信奉人數多,且影響大,傳承明顯。由于受到明末以來實學學風的影響,許多儒者改變了自己的治學方向,致力于自然科學的研究和傳播,明末清朝的自然科學家為人稱道者也大都出自江南地區,如徐光啟(上海人)、潘季馴(烏程人)、徐霞客(江陰人)、王錫闡(吳江人)、梅文鼎(宣州人)、李善蘭(海寧人)、華蘅芳(無錫人)等等。這樣的傳統薪火相傳,賡續不斷,直至現代江南地區仍是產生全國兩院院士最多的地方。正是基于經世致用精神,江南地區經濟發達,文化興盛,學術繁榮,科技進步,成為全國的先進區域。
(二)敢于質疑和挑戰權威的批判精神
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對“南學之精神”進行過全方位、多角度的分析,其中說“其對于北方學派,有吐棄之意,有破壞之心”,便是指江南文化中所具有的基于獨立思考的批判精神。
江南文化這種基于理性、無視權威的批判精神,其來有自。眾所周知,自西漢董仲舒提出“獨尊儒術,罷黜百家”建議并被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地位與思想影響日益擴大,其所提出的“君權神授”“天人感應”理論風行一時,因其強調天人之間的互動關系,引領了神秘主義在政治哲學領域的復興,后來并發展為讖緯神學,導致政局的變動,禁錮了人們的思想。基于這樣的時代條件,王充以其批判精神和科學精神對天人感應、世俗迷信、鬼神和先秦儒家等展開針砭批判。如針對天人感應論,王充在《論衡》一書中明確表示,天無意志、天道自然,災異現象并非天神的責罰譴告;他雖然對孔子甚為推崇,但并不迷信,在《論衡·問孔》中對孔子所稱“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的天命論提出質疑,并通過多個事例證明孔子不能“生而知之”或“神而知之”,甚至斥責“孔子之言何其鄙也”。在當時儒學獨尊、奉孔子為圣人的時代背景下,這需要多么大的勇氣!王充的思想及其批判精神,在歷史上產生了很大影響,后來者對其思想雖頗有微詞,但對其批判精神卻頗為認同。
江南文化不尚權威、敢于挑戰權威的批判精神,在明清時期表現得尤為明顯。明朝建立后,程朱理學成為官方意識形態,導致思想僵化,故步自封,“其在俗儒,率外心以求知,終其身汩溺于見聞記誦;而高明之士,又率慕徑約,貴自然,淪入于二氏而不自覺”,(29)圣道傳承岌岌可危。明代中期浙江余姚人王陽明本著傳承圣道的使命感,起而創立了以“良知即天理”“知行合一”“明德親民”為主要命題的“陽明心學”。任何思想理論的創造都是建立在批判性地繼承既有思想資源的基礎上,陽明心學亦是如此。雖然對陽明心學與程朱理學的關系,學界眾說紛紜,但不可否認,陽明心學是對程朱理學的發展,盡管這種發展建立在王陽明對程朱理學尤其是朱子學的批判基礎上。王陽明早年究心于朱子學,但“格致”和“讀書”求理均遭失敗,經過自己的實踐與思索,他抓住了從心上做功夫的“格物致知之旨”,發現“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誤也”。可以說,沒有對朱熹學說的質疑與批判,就不會有王陽明的“龍場悟道”。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黃宗羲、顧炎武等人,崇尚實學,不僅在學問上多有創見,更對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展開激烈批判。如黃宗羲認為,君主是私欲的化身,視天下財物為己有,視天下人民為囊中物,“荼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因此,君主是天下萬惡之源,所謂“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30) 正如學者所指出的,“黃宗羲此類議論,矛頭所向,顯然是封建專制集權,而皇權是這一制度的政治核心和要義,故抨擊皇權的邪惡,無疑即是否定封建集權制度的合理性。其思想的革命性意義,深得后來改良和維新派的贊賞,成為中國走向近代化的重要理論資源”。(31)
清朝建立后,仍以程朱理學為國家意識形態,朱熹的地位大為提升。乾隆稱:“我圣祖將朱子升配十哲之列,最為尊崇,莫不奉為準繩。”(32)在當時的背景下,質疑程朱理學是嚴重犯禁的。但著名思想家、徽州休寧人戴震卻敢于挑戰權威,對程朱理學進行了全面系統的批判。如在理欲觀上,從“理存乎欲”出發,對程朱理學“以理殺人”作了深刻揭露和激烈批判,“其所謂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謂法。酷吏以法殺人,后儒以理殺人,浸浸然舍法而論理,死矣,更無可以救矣”。(33)因此,近代著名學者胡適稱其為反抗程朱理學“排斥人欲的禮教的第一人”。(34)
與戴震略相前后的浙江會稽人章學誠力主“六經皆史”說,雖然這一觀點并非章學誠獨創,但其“孔子有德無位,即無從得制作之權,不得列于一成,安有大成可集乎”一語,明顯具有貶低孔子之意,且批評了孟子所說“孔子之謂集大成”的觀點,由此否定了道統的存在價值,將那些自認為真理掌握者拉下神壇。
自此以后迄至近代,江南地區的大量知識分子以及仁人義士,無不對專制統治以及所奉行的儒家思想或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展開激烈的批判與抗爭,舉其影響大者有龔自珍、馮桂芬、秋瑾、章太炎、張謇、胡適、蔡元培、魯迅等人。如馮桂芬,有學者評價其“是中國近代史上提出全面系統變法思想的、力主在多方面向西方學習的、注意消解變法之古今中西矛盾的、具有開拓意義的、務實、深刻、影響深遠的大思想家”(35);至于魯迅,更被毛澤東推崇為“不僅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
江南文化中敢于質疑和挑戰權威的批判精神,反映了江南文化對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的不懈追求,成為江南人勇于創新的不竭動力。
(三)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工匠精神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生產生活中的積淀,需要通過造物技藝表現出來。明代萬歷年間的王士性曾經指出,江南人“既繁且慧,亡論冠蓋文物,即百工技藝,心智咸儇巧異常。雖五商輳集,物產不稱乏,然非天產也,多人工所成,足奪造化”。(36)說明江南地區百工技藝突出,工藝制造巧奪天工。誠然,江南地區是百工技藝之鄉,民間手工藝歷史悠久,門類眾多,佳作迭現。尤其在明清時期,蘇州的民間工藝臻于鼎盛,乾隆《元和縣志》卷10《風俗》說,吳中男子多工藝事,各有專家,雖尋常器物,出其手制,精工必倍于他所。女子善操作,織纴刺繡,工巧百出,他處效之者,莫能及也。江南百工不僅技術精湛,而且品類繁富,計有22個大類,超過3500個品種。諸如蘇繡、制玉、緙絲、蘇扇、蘇燈、蘇雕等“蘇式”“蘇作”產品,形成品牌,譽稱天下。
“蘇作”“蘇式”品牌的形成,源于江南匠人的“工匠精神”。自唐宋以后,江南經濟發達,人文蔚起,逐漸成為全國的經濟、文化重心所在。崇尚文教的風氣,培養了江南人的“工匠精神”,凡事認真對待,一絲不茍,精益求精。明代張瀚《松窗夢語》卷4中的一段話,典型地反映了江南文化的這一特點:吳制服而華,以為非是弗文也;吳制器而美,以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吳服,而吳益工于服;四方貴吳器,而吳益工于器。吳人制造的服飾華麗精致,制造的器具精美漂亮,由此造成了全國各地對“蘇作”“蘇式”“吳品”“吳樣”產品的追捧。時語有“破歸破,蘇州貨”之說,“蘇作”產品成為質量的代名詞。如蘇州號稱“繡市”,蘇繡技藝精湛,有“精細雅潔”之譽;吳中執扇“尤稱絕技”;書畫裝幀,明代即有“吳裝最善,他處無及焉”的評價,清代更有“裝潢以本朝為第一,各省之中以蘇工為第一”的說法;玉器制作,有“良工雖集京師,工巧則推蘇州”的美稱;蘇州竹器與揚州木器并列,“可謂甲于今古,冠乎天下矣”。基于這樣一種“工匠精神”,明清時期的蘇州造就出一批能工巧匠,如陸子岡之治玉、朱碧山之治金銀等,“俱可上下百年保無敵手”。同時出現了很多質量精、聲譽好、受到消費者歡迎的品牌行業與店鋪,如有益齋藕粉、陸稿薦蹄子、孫春陽南貨、雷允上藥材、汪益美布匹、褚三山眼鏡等,其中雷允上藥材、陸稿薦蹄子等至今仍在影響著蘇州市民百姓的生活。唯其如此,明清時期的蘇州人掌握了審美評價的話語權,引領著全國時尚審美的潮流,明人王士性《廣志繹》卷2說,姑蘇人聰慧好古,善操海內上下進退之權,蘇人以為雅者,則四方隨而雅之;俗者,則隨而俗之。蘇州文化這種做事態度認真、講究產品質量、追求精致典雅的特點,與現代中國所倡導的“工匠精神”正相契合。
蘇州固然突出,江南其他地區亦不遑多讓。因應各地的資源優勢以及民間文化傳承,江南地區的造物技藝呈現出百花爭艷、各擅勝長的局面。宜興紫砂始于宋,盛于明清,歷代名師輩出,制器技藝精巧,以茗壺最具代表性,融諸藝于一體,形神兼備,曾在1915年美國舊金山“太平洋萬國巴拿馬博覽會”獲頭等獎。南京云錦表現出“內容美、構成美、色澤美、材質美和織造美”的特點,“具有深厚的文化內涵和精湛的技藝水平。這是歷代藝人不斷創新精神的積淀,是云錦工藝的精華所在,是民族文化的瑰寶”。(37)浙江青瓷前后延續3000余年,期間不斷創新,改良工藝,尤以龍泉青瓷最為著名,“南宋龍泉青瓷在造型與紋飾上表現出深厚的民族傳統,熟練的藝術技巧以及優美簡潔的藝術風格,簡練、明朗、大方、精致、端巧是南宋龍泉青瓷的裝飾手法”(38)。嘉靖《浙江通志·地理志》稱其“粹美冠絕當世”。著名陶瓷研究專家陳萬里曾評價說:“一部中國陶瓷史,半部在浙江;一部浙江陶瓷史,半部在龍泉”,“龍泉窯是中國瓷業史上最后形成的一個青瓷名窯,其文化內涵豐富,生產規模極為壯觀……是中國青瓷工藝發展的歷史總成”。(39)
工匠精神的核心要義,包括厚積薄發、不懈追求,一絲不茍、精益求精,勤于學習、推陳出新,德藝兼修、敬業奉獻等方面,既是一種工作態度,也是一種生產技能,更是一種文化追求。工匠精神鍛造了江南人勇于創造、善于創造的創新能力,成為江南地區長期處于全國領先地位的強力支撐。
注釋:
(1) 景遐東:《江南文化傳統的形成及其主要特征》,《浙江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4期。
(2) 莊若江:《江南文化的精神內涵及其時代價值》,《江蘇地方志》2021年第1期。
(3) 胡發貴:《江南文化的精神特質》,《江南論壇》2012年第11期。
(4) 劉士林等:《風泉清聽——江南文化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頁。
(5) 王友三主編:《吳文化史叢》上冊,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頁。
(6) 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卷11,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17頁。
(7) 楊寬:《戰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67頁。
(8) 趙曄:《吳越春秋》卷2,張覺譯注:《吳越春秋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頁。
(9) 《春秋左傳·成公七年》,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50頁。
(10) 郭驥、邵文菁等:《孕育與蛻變:從江南文化到海派文化》,上海書店出版社2021年版,第2頁。
(11) 歸有光:《震川先生集》卷9 《送王汝康會試序》, 《歸有光全集》第5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05頁。注:本文引用時重新標點。
(12) 鄭元祐:《吳縣儒學門銘》,徐永明校點:《鄭元祐集》卷7 《僑吳集·銘》, 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第153頁。
(13) 鄧洪波:《中國書院史》,東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261—263,405—407頁。
(14) 張帥奇:《清代江浙族學與家族文化的傳承》,《西安文理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2期。
(15) 查元偁:《查氏族譜增輯》卷9、13,道光八年刻本。
(16) 《惲氏家乘》卷1《祖訓》,轉引自周煥卿:《傳承與改良:明清以來常州民間家訓研究》, 《聊城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3期。
(17) 王衛平、李學如主編:《蘇州家訓選編》,蘇州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3—14頁。
(18) 民國《歙縣志》卷8《人物志》, 轉引自李琳琦:《徽州教育》,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5頁。
(19) 李琳琦:《徽州教育》,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6頁。
(20) 葉夢珠:《閱世編》,參見王衛平:《中日地方志與江南區域史研究》,蘇州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71頁。
(21) 陸楫:《蒹葭堂雜著摘抄》,收入《中國野史集成》第37冊,巴蜀書社1993年版,第3頁。
(22) 顧祿:《桐橋倚棹錄》卷12《園圃·鬢邊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68頁。
(23) 王杰:《中國文化中的經世致用思想》,《中國領導科學》2021年第3期。
(24) 吳光:《浙江儒學總論:從王充到馬一浮——論浙江儒學的思想特色與精神價值》,《浙江社會科學》2020年第6期。
(25) 董平:《浙東學派及其歷史發展》,浙江師范大學江南文化研究中心編:《江南文化研究》第1輯,學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28頁。
(26) 參見王衛平:《實念與實事:晚明高攀龍的救世理念與實踐》,《中國史研究》2015年第3期。
(27) 《亭林文集》 卷4 《與人書三》,《顧炎武全集》第2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39頁。
(28) 潘耒:《日知錄序》,《顧炎武全集》第18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頁。
(29) 《王陽明全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第1743頁。
(30) 《黃宗羲全集》第1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3頁。
(31) 胡發貴:《試論江南文化的啟蒙精神》,《金陵科技學院學報》2014年第1期。
(32) 王先謙、朱壽鵬:《東華錄·東華續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89頁。
(33) 戴震:《孟子字義疏證》,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74頁。
(34) 胡適:《戴東原的哲學》, 北京大學《國學季刊》1925年第2卷第1號。
(35) 熊月之:《馮桂芬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頁。
(36) 王士性:《廣游志》卷下《物產》,周振鶴編校:《王士性地理書三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27頁。
(37) 周勛初主編:《中國地域文化通覽·江蘇卷》,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516頁。
(38) 黃威越:《南宋龍泉窯青瓷的藝術特征》,《陶瓷研究》2018年第1期。
(39) 轉引自胡少芬:《淺談龍泉青瓷的文化內涵》,《陶瓷科學與藝術》2022年第3期。
作者簡介:王衛平,蘇州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江蘇蘇州,215031。
(責任編輯 張衛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