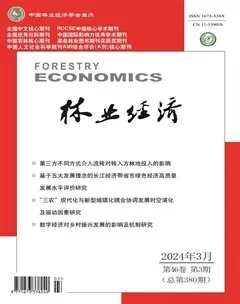數字經濟對鄉村振興發展的影響及機制研究
張芳山 李露瑤 陳杰



摘要:近年來,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對鄉村振興發展的影響極大。文章選取2011—2022年中國30個省份的面板數據,采用熵權法和固定效應模型,探究數字經濟對鄉村振興發展的影響機制和程度,并創新性地使用隨機森林模型,深入考察影響鄉村振興發展的數字經濟各項指標的重要性。研究發現:(1)數字經濟發展對鄉村振興工作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影響效應為0.4100。(2)數字經濟對林業大省鄉村振興的促進作用較其他地區更為顯著,影響系數為0.5700,說明數字經濟在林業經濟的應用已取得了顯著成效。(3)數字經濟影響鄉村振興最重要的因素是企業擁有網站數和信息從業人數,重要性分別為13.62和11.61,農村電商有望成為鄉村振興的新增長極。(4)數字經濟對鄉村振興的促進作用有明顯的區域異質性,影響系數分別為東部地區0.6450、西部地區0.2560、東北部地區0.2350、中部地區0.1970。文章聚焦于數字經濟各個維度指標的重要性比較以及林業經濟大省和其他省份的異質性分析,深化了相關研究內容,彌補了現有文獻對林業經濟大省數字經濟研究的不足。基于此提出政策啟示:鄉村振興工作中應利用好數字經濟這一推手,重點推動農村電子信息制造業和農村電商,推進林業大省和其他地區鄉村振興工作低成本、高質量發展。
關鍵詞:數字經濟;鄉村振興;熵權法;面板數據計量模型;隨機森林模型
中圖分類號:F323; F4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338X(2024)3-078-19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農民用水合作組織發展遲滯的生成邏輯與破解機制研究”(23CJY058),河南省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項目“河南農民用水合作組織發展遲滯的生成邏輯與優化路徑研究”(2024-ZZJH-145),河南省軟科學研究計劃項目“河南省推進糧食主產區利益補償的阻礙與破解對策研究”(242400411160)。
Research on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digital economy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development
ZHANG Fangshan, LI Luyao, CHEN Jie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Trade, He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450001)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been booming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has been positively impacted by it. By selecting the panel data of 30 Chinese provinces from 2011 to 2022, the entropy weighting method and fixed-effects model were used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and degree of 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random forest model was innovatively used to examine in depth the importance of the various indicators of digital economy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1)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had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with an impact effect of 0.4100.(2)The promotion of digital economy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forestry provinces was more significant than other regions, with an impact coefficient of 0.5700, indicating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economy in the forest economy had achieved significant results.(3)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of digital economy affec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were the number of websites owned by enterprises and the number of information practitioners, with the importance of 13.62 and 11.61, respectively. Rural e-commerce was expected to become a new growth pole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4)There was obvious regional heterogeneity in the promotion of digital economy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with impact coefficients of 0.6450 in the eastern region, 0.2560 in the western region, 0.2350 in the northeastern region, and 0.1970 in the central region, respectively. The article focused on the importance comparison of the indicators of digital economy in various dimensions as well as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between large forestry provinces and other provinces, which deepened the relevant research content and made up for the lack of existing literature on digital economy research in large forestry economy provinces.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proposed som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Rural revitalization work should make good us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s a driving force, focusing on the promotion of rural electronic information manufacturing and rural e-commerce, and promoting the low-cost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work in large forestry provinces and other regions.
Keywords:digital economy;rural revitalization;entropy weight method;panel data econometric model;random forest model
1引言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學習運用“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工程經驗有力有效推進鄉村全面振興的意見》指出:要學習運用“千萬工程”蘊含的發展理念、工作方法和推進機制,把推進鄉村全面振興作為新時代新征程“三農”工作的總抓手,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因地制宜、分類施策,循序漸進、久久為功,集中力量抓好辦成一批群眾可感可及的實事,不斷取得實質性進展、階段性成果。近年來,數字經濟興起為我國鄉村振興戰略的實現提供了一條新時代道路。自2019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數字鄉村發展戰略綱要》提出“到2025年數字鄉村建設取得重要進展”戰略目標以來,我國鄉村振興工作中處處可見數字經濟的影子。2023年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發布的《數字經濟促進共同富裕實施方案》也明確提出要“加快鄉村產業數字化轉型步伐,深入實施數字鄉村發展行動,以數字化賦能鄉村振興”。2024年3月5日商務部等9部門聯合印發的《關于推動農村電商高質量發展的實施意見》強調“發展農村電商,是創新商業模式、建設農村現代流通體系的重要舉措,是轉變農業發展方式、帶動農民增收的有效抓手,是促進農村消費、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有力支撐”。根據商務部《2023年中國網絡零售市場發展報告》,2023年全國農村網絡零售額達到了2.5萬億元,同比增長12.9%,比2014年增長近13倍;全國農產品網絡零售額達5870.3億元,同比增長12.5%,約是2014年的5倍。農村電商的跨越式發展正是數字經濟在鄉村振興工作中的縮影。與此同時,隨著Web3.0、ChatGPT等數字經濟新興應用場景的興起,如何抓穩數字經濟這一推手,充分發揮數字經濟在鄉村振興工作中的積極作用,成為關注的重點。這對于賦予我國鄉村振興穩定且強大的內生活力、圓滿完成2025數字鄉村建設目標、促進鄉村振興戰略快速優質實現具有重要意義。
為深入探究數字經濟與鄉村振興戰略之間的內在耦合關系,尋求鄉村振興發展的創新路徑,本文依托2011—2022年中國30個省級行政區的面板數據集,運用熵權法從電子信息制造業、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企業數字化轉型等多個關鍵維度出發,同時兼顧鄉村產業興旺、生態環境宜居、鄉風文明進步與治理體系有效四大核心領域,分別構建反映區域數字經濟綜合發展水平和鄉村振興整體狀況的指數體系。在堅實的數據基礎上,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嚴謹剖析數字經濟發展程度與鄉村振興水平之間的潛在關聯性,并通過隨機森林模型得到數字經濟各二級指標對鄉村振興工作的重要性程度,深度挖掘我國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部四大區域在數字經濟驅動鄉村振興進程中的異質性特征。
本文的學術貢獻在于:不同于以往研究只注重數字經濟與鄉村振興戰略間的影響機制,而是借助先進的隨機森林模型這一機器學習模型,切換現實視角,立足于政府施策角度,精準刻畫評價數字經濟水平的19個指標對鄉村振興的影響。在前人確定數字經濟能促進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基礎上,研究數字經濟對林業大省和非林業大省鄉村振興的異質性。研究發現,數字經濟在助力鄉村振興的過程中,農村電商發揮了最大的作用,且數字經濟對林業大省的鄉村振興有更顯著的促進作用。
2文獻回顧與評述
鄉村振興戰略的核心是在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的原則下,確保在要素配置、資源條件及公共服務供給上對農村優先保證和傾斜。近年來,數字經濟以其獨特優勢,在推動鄉村數字化轉型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已有研究普遍認為,數字經濟能夠有效促進鄉村振興戰略實施,助力鄉村生活水平提升。數字經濟一方面能夠提升公共行政效率,進而賦能農業農村組織內部的分工協調、提升組織管理效率、促進農村流通高質量發展(Sidorenko et al., 2019;任保平,2024;張曉林,2024);另一方面能夠提升政府鄉村建設規劃和鄉村數字普惠金融的質量,推動農業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縮小城鄉貧富差距(Kosorukov, 2017;Kolobkova et al., 2021;Liu et al., 2023;Wang et al., 2023;Wu et al., 2024)。
數字經濟形成數字賦能,通過城鄉技術、資源、市場流通,推動鄉村資源優化配置,加強城鄉市場有效對接,促進鄉村產業融合,推動鄉村產業發展(田野等,2022;馮伯豪等,2024)。科技創新、組織創新、模式創新等都成為數字經濟促進鄉村振興質量明顯提升的重要中介變量(張蘊萍等,2022;劉釩等,2023)。為了進一步提高數字經濟對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促進作用,一些學者從新經濟地理理論、產業融合理論、價值鏈升級理論和制度經濟學理論等理論角度分析后認為,應該加快推動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優化公共資源配置,從而提高農業技術水平,加大數字經濟應用場景宣傳,進而實現小農戶對接大市場,提升鄉村振興工作質量(Yin et al., 2021;陳中,2022;張蘊萍等,2022;劉曉菲,2024)。
數字經濟建設以及其對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影響均表現出顯著的區域異質性(殷浩棟等,2020;張蘊萍等,2022;馮伯豪等,2024)。全陽等(2023)、孫亞男等(2023)研究發現,東南沿海數字鄉村高質量建設呈現出多元化形式,內陸省份的數字經濟建設則相對遲緩。數字經濟與鄉村振興協同發展水平在空間上呈現“東高西低”和“相似集聚”的基本格局。數字經濟與鄉村振興耦合協調度東部地區各省份間差距顯著高于西部地區和中部地區,但是整體上呈現出明顯的在提升中趨同的演變特征。另外,數字經濟同樣賦能林業高質量發展,數字經濟與林業高質量發展的融合度決定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協同效應,融合度越高,越有利于提升協同效應促進鄉村振興(張翰丹等,2023)。
已有研究結果主要建立在主成分分析法、投入產出法、熵值法和固定效應模型等研究方法上。很多學者應用主成分分析法測算數字經濟綜合得分,或者應用投入產出法對我國數字經濟發展進行多維度考察(趙濤等,2020;孟雪辰等,2022;程廣斌等,2022)。鄉村振興綜合指數評價體系測算中較多學者應用熵值法(王亮等,2023;徐雪等,2023)。數字經濟與鄉村振興的關系研究則更多地應用個體固定效應模型(潘明清等,2023)、中介效應模型和逐步回歸法等計量經濟模型(劉亞男等,2022;田野等,2022;王永芳等,2024)。例如,楊建仁等(2023)運用Kernel密度估計模型結合BEA測算方法測算中國省域數字經濟規模及其與鄉村振興之間的關系。
綜上所述,已有文獻采用多種方法對數字經濟與鄉村振興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基本形成數字經濟會促進鄉村振興的結論。但是,相關研究內容仍有深化空間:(1)已有研究缺少對數字經濟和鄉村振興評價指標中各個要素重要性的權衡,造成研究結論集中于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等層面,對研究結論的深化和政策的現實指導作用不足。(2)已有研究缺少對不同經濟類型省份的異質性分析,大多集中于東部、中部、西部行政區域的異質性討論,但是由于林業經濟與農業經濟在地域性、周期性、季節性上的不同,林業大省和農業大省的數字經濟與鄉村振興可能表現出不同的關系,有必要進行異質性探討。因此,本文創新性地運用隨機森林模型精確識別并衡量數字經濟建設在鄉村振興工作中各個要素的重要性,力求為實踐層面的數字鄉村建設和鄉村振興戰略實施找準重心和突破口。同時在此基礎上,系統深入地展開不同經濟類型省份的異質性分析,明晰林業大省和農業大省兩者之間的差異,力求為科學規劃與高效推進我國數字鄉村建設、全面提升鄉村振興戰略實施成效提供有力的數據支持和決策依據。
3理論分析框架與研究方法
結合已有研究成果可知,數字經濟在推動鄉村振興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為了使數字經濟與鄉村振興之間的傳導機制更為健全和明晰,本文對數字經濟發展影響鄉村振興的直接作用、各因素影響權重和區域異質性進行探討。由此構建我國30個省份的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基于機器學習的隨機森林模型、決策樹以及異質性分析。
3.1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為了深入研究數字經濟發展與鄉村振興之間的深層次關系,本文從數字經濟發展對鄉村振興發展的推動作用、變量差異性和區域異質性三個方面論述理論分析框架及研究假設,并以此為基礎闡釋本文的研究方法和模型構建。
3.1.1數字經濟對鄉村振興促進作用的理論分析
數字經濟主要從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個方面影響鄉村振興。第一,在產業興旺方面,數字經濟為鄉村提供了更多的發展機會。鄉村可以通過電子商務平臺將農產品銷售到全國乃至全球,推動農業產業的現代化和規模化。同時,數字經濟也催生了鄉村旅游、鄉村文創等新興產業,豐富了鄉村經濟的內容和形式(曾祥明等,2024)。第二,在生態宜居方面,數字經濟有助于提升鄉村的生態環境質量。通過數字化監測和數據分析,可以更有效地管理和保護鄉村的自然資源,實現可持續發展,推動鄉村綠色建筑和綠色能源的發展,提高鄉村居民的居住質量(雷搏等,2023)。第三,在鄉風文明方面,數字經濟有助于傳承和弘揚鄉村文化。通過數字化技術記錄和展示鄉村的歷史、傳統和習俗,讓更多的人了解和欣賞鄉村文化,進而推動鄉村文化的創新和發展,為鄉村注入新的活力(王麗等,2023)。第四,在治理有效方面,數字經濟可以提高鄉村治理的效率和透明度。通過數字化平臺,可以實現信息共享、數據互通,提高鄉村治理的精準性和針對性,以推動鄉村治理的民主化進程,增強村民的參與感和獲得感(陳建珍,2022)。第五,在生活富裕方面,數字經濟為鄉村居民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和收入來源。通過發展數字經濟產業,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才和資源流向鄉村,促進鄉村經濟的繁榮和發展,提高鄉村居民的生活品質,讓他們享受到更加便捷、舒適的生活(郭露等,2023)。因此,提出假設H1。
H1:數字經濟的發展對鄉村振興工作產生極為重要的影響。
法國經濟學家弗朗索瓦·佩魯提出的增長極理論強調,在有限資源條件下,通過聚焦關鍵領域和節點能夠實現經濟的跳躍式發展。在鄉村地區發展數字經濟的資金等資源十分有限。因此,為了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打造數字經濟推動鄉村振興新的增長極,提出假設H2。
H2:構成數字經濟的不同變量對鄉村振興工作的重要程度不同。
3.1.2區域間數字經濟對鄉村振興作用機制差異的理論分析
根據資源分配不平衡理論,資源要素的分配不均勻會導致不同經濟體之間的發展程度不同(馮云廷等,2019)。由于各省份外界因素的變化,數字經濟和鄉村振興之間的發展會表現為時間上的階段性和空間上的差異性。地理位置優越的省份由于數字經濟發展的基礎條件相對較高,在鄉村振興的發展上具有更高的起點,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能夠驅動鄉村振興各產業部門迅速轉型升級,逐步推進鄉村振興。依據資源分布不均勻理論,各省份之間推動鄉村振興發展的資源分布不均,導致部分地區數字經濟發展較快,部分地區久滯不前,出現區域異質性(馮伯豪等,2024),并且數字經濟對林業經濟高質量發展有顯著促進作用(王一萌等,2023),因此,提出假設H3。
H3:我國東部、中部、西部、東北部地區和林業大省數字經濟對鄉村振興的促進作用存在區域異質性。
3.2研究方法
根據理論分析框架以及研究假設,數字經濟對鄉村振興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不同的數字經濟變量對這種促進作用的重要性不同,而且這種促進作用存在區域異質性。本文通過熵權法這一客觀賦權法分別得出數字經濟和鄉村振興綜合指數,并選擇固定效應模型對兩者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劉亞男等,2022)。在此基礎上,借鑒田小文等(2023)的做法,引入隨機森林模型對數字經濟的變量進行重要程度排序,并創新性地使用決策樹對隨機森林結果進行檢驗。此外,借鑒馮伯豪等(2024)的方法進行區域異質性檢驗,以對不同地區之間、林業與非林業大省之間的差異做出規范化分析。
3.2.1熵權法
本文利用熵權法通過數字經濟和鄉村振興綜合得分作為最終衡量結果的變量依據。熵權法的基本思路是根據指標變異性大小來確定客觀權重。若某個指標的信息熵越小,表明指標值的變異程度越大,其提供的信息量越多,在綜合評價中所起到的作用也越大,其權重也就越大。本文在單一衡量數字經濟和鄉村振興的綜合指數時,分別利用正向指標與負向指標來判斷信息熵進而得出權重大小,最后得出綜合指數得分。
第一步,標準化。為了消除不同變量之間量綱不同的影響,首先對數據進行標準化,如式(1)至式(4)所示。
正向指標使用式(1)和式(2)。
式(1)至式(4)中,XHit、Mhit分別表示在數字經濟第H個與鄉村振興第h個三級指標下第i個省份第t年的指標數值,YHit、Nhit分別表示在數字經濟與鄉村振興標準化后第H個、第h個三級指標下第i個省份第t年的指標數值。
第二步,求各指標在各方案下的比值,如式(5)、式(6)所示。
式(5)中,pHit表示在數字經濟第H個三級指標下第i個省份第t年的數值占數字經濟全部數值的比例;式(6)中,qhit表示在鄉村振興第h個三級指標下第i個省份第t年的數值占鄉村振興全部數值的比例。
第三步,求各指標的信息熵。根據信息論中信息熵的定義,一組數據的信息熵如式(7)、式(8)所示。
式(7)、式(8)中,EHij, Fhij≥0。若pHij, qhij= 0,定義EHij, Fhij= 0。EHit是根據第二步所得出的數字經濟每個指標在每個樣本上的權重所計算出來的熵值,n為省份總數;Fhij同理。
第四步,確定各指標的權重。根據信息熵的計算公式,計算出各個指標的信息熵。信息熵計算各指標權重如式(9)、式(10)所示。
式(9)、式(10)中,K、k分別為數字經濟與鄉村振興的指標個數,即K = H , k = h,L、l分別為數字經濟與鄉村振興各指標總數。
第五步,計算每個方案的綜合評分,如式(11)、式(12)所示。
式(11)、式(12)中,SHij、Ghij分別為數字經濟與鄉村振興的各方案綜合評分。
3.2.2固定效應模型
通過熵權法得出數字經濟和鄉村振興綜合指數后,本文通過豪斯曼檢驗最終確定采用固定效應模型來深入研究數字經濟對鄉村振興的促進作用,如式(13)所示。
式(13)中,i為省份;t為時間;GEE為各省份綠色發展水平;DEG為各省份數字經濟發展水平;Bit為控制變量的合集;β0、β1、β2為系數;μi為個體固定效應;δt為時間固定效應;εit為隨機誤差項。3.2.3隨機森林模型
由固定效應模型得出數字經濟與鄉村振興之間的聯結機制后,再通過隨機森林模型評價數字經濟不同指標變量對鄉村振興的重要程度。固定效應模型更關注總體效應,而隨機森林模型則進一步深入到特征層面,揭示影響的細節。固定效應模型提供了數字經濟對鄉村振興總體上的因果關系,而隨機森林模型則提供了這種關系在具體特征層面上的細分,兩種模型結合起來可以更全面地理解數字經濟對鄉村振興影響的復雜性。
隨機森林模型是一種集成學習方法,用于解決分類和回歸問題。它由多棵決策樹組成,每棵樹都獨立訓練。在分類問題中,隨機森林模型通過投票來確定最終的分類結果,其中“隨機”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它會隨機選擇用于訓練每棵樹的數據樣本;二是對于每個節點的特征選擇,它也會隨機選擇一部分特征進行考慮。這種隨機性有助于減少擬合,并且使其對于高維數據和大量訓練樣本的情況表現良好,結果更加可信。重要性評價原理為:數字經濟變量在模型中為正確識別鄉村振興發展水平樣本所提供的信息量越多,則該自變量的重要性就越高。
第i個數字經濟變量的特征Ci的重要性計算公式如式(14)所示。
式(14)中,r為有序放回的次數,errOOB1ij與errOOB2ij分別為j次加入噪聲前后的袋外數據誤差。
4指標體系構建、數據來源與描述性統計分析
基于包容性增長理論,數字經濟在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一定會帶動鄉村這一經濟弱勢群體的發展。在這一過程中會使數字經濟與鄉村振興之間產生互動關系。本文以30個省份為數據樣本構建指標體系,并對數據進行描述性統計和專業化處理,最終得到我國數字經濟綜合指數與鄉村振興綜合指數,在此基礎上通過豪斯曼檢驗確定計量模型,進行計量分析。
4.1指標體系構建
數字基礎設施為數字經濟提供著堅實的基礎設施保障(趙亞輝等,2023)。目前,移動電話普及程度、互聯網普及程度、信息傳輸廣度等是數字經濟評估指標體系的重要指標。這些指標已經被廣泛應用于國內相關數字研究中(李春娥等,2023)。在此基礎上,本文選取移動電話普及程度、互聯網普及程度、信息傳輸廣度、信號覆蓋廣度、互聯網寬帶基建和數字服務投資力度等6個二級指標作為測量數字基礎設施的關鍵指標。除此之外,數字產業化是擴大產業規模和提升產業種類的核心(王軍等,2021)。本文借鑒陳晶晶等(2024)的方法,選取郵電業發展水平、電子信息制造業發展水平以及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3個二級指標,測量我國數字產業化發展水平。產業數字化是產業鏈進行數字化轉型、升級和再造的重要過程(湯淥洋等,2023)。產業數字化主要集中于企業化發展程度和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兩大方面。數字普惠金融作為數字技術與傳統金融有機結合的平臺,為企業數字化發展提供有力支撐。因此,本文選取企業化發展程度和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2個二級指標作為衡量產業數字化的核心指標。
4.2數據來源與描述性統計分析
在對數字經濟水平的衡量上,本文采用《中國統計年鑒》《中國信息產業年鑒》《中國第三產業統計年鑒》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和信息化部統計分析數據、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數據庫統計的中國30個省份(由于西藏自治區和港澳臺地區2011—2022年每一年的數據均有大量缺失的情況,故將其舍棄)從2011年到2022年的省級經濟指標,建立如表1所示的省級數字經濟指標體系。
本文將《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中的鄉村振興戰略規劃主要指標涉及到的五個主要方面: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作為衡量鄉村振興發展的一級指標。以賈晉等(2018)、沈劍波等(2020)所建立的鄉村振興水平評價指標體系為基礎,在五個維度下選取24個三級指標衡量鄉村振興發展水平。數據來源方面,本文采用《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農村統計年鑒》和《中國工業統計年鑒》中的中國30個省份從2011年到2022年的省級鄉村振興指標,建立如表2所示的省級鄉村振興指標體系。
依據劉釩等(2023)的研究,本文選取政府干預程度(財政支出/國民生產總值)、信息化水平(郵電業務總量/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地區生產總值(人均地區生產總值指數,上年=100)、對外開放程度(貨物進口總額/貨物出口總額)、創新水平(國內發明專利申請受理量(件)取對數)、產業結構(第三產業產值/第二產業產值)、稅負水平(稅收收入/地區生產總值)、環境規劃(工業污染治理完成投資額/工業增加值)、能源結構(地區電力消費類/全國電力消費量)、城鎮化水平(城鎮人口所占比率)和經濟發展水平(人均國內總產值/人均地區生產總值指數,2000年=1)11個控制變量,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各省統計年鑒和公報等(對部分省的殘缺數據通過插值補全)。
描述性統計如表3所示(因文章篇幅限制,指標貢獻度低的未列入)。表3中,S3~S16反映數字經濟指標,其差異較為顯著。快遞量、電子信息制造業收入、電子信息制造業企業個數、軟件業務收入、企業擁有網站數和電子商務交易額等指標差異大。除光纜線路密度和移動電話基站密度、電子信息制造業企業個數、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從業人數和有電子商務交易活動企業比重外,其余指標峰值和平均值均較大。標準差顯示互聯網寬帶接入端口密度、電信業務總量、快遞量、電子信息制造業收入、電子信息制造業企業個數、軟件業務收入、企業擁有網站數和電子商務交易額等指標離散程度好,表明數字產業發展不平衡,主要體現在發展中心和業務范圍以及電子信息技術方面,與當前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現狀相符。S20~S42為鄉村振興指標,其差異較大。農業機械總動力、糧食人均占有量、農作物受災面積、鄉村文化站數量占鄉鎮數量比重、土地有效灌溉面積、農民人均純收入、社會商品鄉村零售額等指標峰值相對較大。農作物受災面積峰值變化大可能與人類活動有關。其他指標峰值相對增加,呈現穩定狀態。從平均值看,農業機械總動力、鄉村文化站數量占鄉鎮數量比重、土地有效灌溉面積、農民人均純收入、社會商品鄉村零售額、人均住宅建筑面積等指標領先,其余較低。這主要得益于國際環境和社會進步,全球經濟發展向好。同時,農業技術逐步完善,符合農民人均收入增加的實際狀況。標準差顯示各指標差異大,第一產業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農業勞動生產率、文盲人口占1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粗離婚率、城鄉居民生活差距程度等指標聚合度較好,差距保持相對穩定。其余指標差距大,可能與農村經濟發展資源分布不均勻和各地發展水平不同有關,符合當前我國鄉村振興發展現狀。
5經驗性結果分析
通過對數字經濟指標體系、鄉村振興指標體系以及固定效應模型指標體系的構建,利用熵權法分別得到數字經濟綜合指數和鄉村振興綜合指數。進而通過Stata15.0與Rstudio,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隨機森林模型和異質性檢驗分別對本文3個假設進行驗證。
5.1熵權法結果分析
通過熵權法得到數字經濟綜合指數和鄉村振興綜合指數之后,以兩大綜合指數為基礎對各地區進行排名。通過兩大指數排名變化可以大致將30個省份分為三類。第一類是以北京、上海為代表的數字經濟高度發達地區。此類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一直位居全國前列,但是鄉村振興水平排名卻呈現下降趨勢。原因在于截至2011年,這類地區的鄉村發展水平已經通過各方面的影響達到了領先水平,因此數字經濟的發展對這類地區的邊際效用不顯著。第二類是以江蘇、浙江為代表的產業結構先進的地區。此類地區在2011—2015年鄉村振興與數字經濟的排名變化基本同步,但2015—2022年兩者之間的關聯則明顯減弱,說明數字經濟對鄉村振興的推動作用在2015年前后在這類地區達到了帕累托最優狀態。第三類地區則是經濟相對落后地區。此類地區有著廣大的落后農村,進步空間大,所以當這類地區的數字經濟有所發展時,他們的鄉村振興排名基本按照相同的趨勢變化。
5.2基準模型結果回歸結果分析
在進行基準回歸之前需要對自變量和控制變量進行多重共線性檢驗解決其內生性問題,基于一個自變量的前提下,本文只考慮控制變量之間的多重共線性,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
表4檢驗結果顯示,回歸模型所有變量的VIF值均低于10,說明回歸模型中控制變量無多重共線性。之后利用豪斯曼檢驗確定利用固定效應模型探究數字經濟對于鄉村振興發展的影響,結果如表5所示。
豪斯曼檢驗的P值為0.0002,小于顯著性水平0.01,因此拒絕原假設(選擇隨機效應模型),選擇固定效應模型。
在確定選擇固定效應模型后,本文將鄉村振興綜合指數作為被解釋變量,數字經濟綜合指數作為核心解釋變量。同時使用11個控制變量對其進行分析控制,防止其他因素的干擾和異方差對于估計結果的影響。本文對控制變量采取了對數處理,同時進行縮尾處理。基準模型回歸結果如表6所示。
通過對計量模型的逐步控制,發現數字經濟在不同條件下均對鄉村振興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無論是僅控制省份、加入控制變量,還是累加個體控制,數字經濟的正面效應均保持顯著。這表明數字經濟是鄉村振興發展的重要推動力,且這一結論在各種控制條件下均得到驗證。
5.3穩健型檢驗
穩健性檢驗可以通過更換數值變量,即對原先的數值進行調換,采用對數或者某種形式重新使用數據分析。本文采用對數形式重整數據進行穩健性檢驗,結果如表7所示。由于文章篇幅限制,列(1)為未加入控制變量的結果,列(2)為加入控制變量后的結果,由于結果無影響,列(3)中不再放入控制年份的結果。由表7回歸結果與前文所得的結果整體均為顯著性正值,數字經濟對鄉村振興有著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驗證假設H1成立。研究結果得到驗證,回歸結果趨于穩健。
5.4隨機森林模型結果分析
在實證分析中已經得出數字經濟發展指標對鄉村振興有著顯著性影響這一結論。為了更好地提出針對性建議,本文引入隨機森林模型。通過隨機森林模型得出數字經濟發展具體指標對鄉村振興的重要性排序,以求對癥下藥和降低實施成本。
為了探究數字經濟各個三級指標對鄉村振興的重要性程度,本文以鄉村振興熵值平均值為依據進行鄉村振興程度劃分,平均值及以上地區記為“成果良好”,平均值以下則記為“成果一般”。
模型采用分類回歸樹算法(Classification and Regression Tree),分裂準則選擇基尼系數(Gini index)。由于模型設置為二分型,所以在隨機森林性能評估上采用平衡準確度(BalancedAccuracy)、召回率(recall)和F1分數(F1 score)3個指標,除此之外,本文還引入受試者工作特征曲線(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指標來評價模型性能。另外,實驗將數據按照7 : 3的比例劃分訓練集和測試集,經過十折交叉驗證最終將嘗試的最大特征數設置為6,決策樹使用50000棵(其余參數均為默認設置)。
模型輸出結果顯示,重要性最高的三個變量分別為:企業擁有網站數(S14)、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從業人數(S13)、電子信息制造企業個數(S11)。其重要性程度分別為13.6217,11.6068和8.6542,驗證假設H2成立。這三個變量均與農村電商發展相關,說明農村電商在鄉村振興過程中的作用尤為重要,在鄉村振興的過程中應該首先關注農村電商的資金投入和政策措施。
最后對模型進行性能評價,如表8所示,各項性能評價指標均高于80%,說明模型的性能良好。
5.5決策樹驗證
為了使隨機森林結果更加直觀,單獨創建一棵決策樹來觀察分類,設置決策樹的訓練集和測試集比例為7 : 3。決策樹綜合準確率為93.9%,準確性良好,具備研究條件。經過剪枝后輸出決策樹,如圖1所示。

圖1決策樹輸出結果顯示,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從業人數(S13)與有電子商務交易活動企業比重(S15)的重要性更高,這與隨機森林模型的重要性評分相符。兩個模型互相印證進一步提高了結論的準確性。最后結果說明農村電商對鄉村振興分類貢獻度十分明顯,所以在推動數字鄉村振興的過程中要關注電商發展。政策資金人才應該適當向網站建造和農村電商傾斜,打通新的農產品銷售渠道。
5.6異質性檢驗
在已知數字經濟會對鄉村振興產生正向推動作用并且在鄉村振興工作中扮演極為重要角色的情況下,本文選擇進一步探究不同區域之間的異質性,利用異質性檢驗將其可視化。異質性分析結果如表9所示。與穩健性檢驗一樣,考慮到文章篇幅限制,只放入數字經濟與鄉村振興的結果。
在進行異質性分析的同時,為了更好地反映鄉村振興的發展現狀,本文依據《2023年中國國土綠化狀況公報》,將吉林、遼寧、山東、河南、重慶、四川劃分為林業大省,并通過文件中的國土綠化狀況作為衡量林業經濟的發展指標反映鄉村振興發展現狀。從表9中可以看出,數字經濟對于林業大省的鄉村振興發展起著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影響系數為0.5700,僅次于東部地區。由此得出結論,數字經濟在促進鄉村振興的過程中林業經濟承擔著至關重要的銜接作用。因此,在鄉村振興工作中各地應充分發揮林業經濟的作用,讓林業經濟成為新的鄉村振興著力點,實現環境與經濟的協同發展。
另外,從表9中可以看出,東部地區、西部地區、中部地區、東北部地區數字經濟對于鄉村振興發展均有正向促進作用,并且這種促進作用在東部地區十分顯著,中部地區和東北部地區的促進作用相對一致,西部地區偏弱。綜上,在數字經濟推動鄉村振興發展這一機制中的確存在區域異質性,東部地區的影響系數為0.6450,說明東部地區的數字經濟與鄉村振興工作已經取得了較深的融合。而中部地區、西部地區和東北部地區的影響系數分別為0.2560、0.1970和0.2350,其影響系數不顯著說明這三個區域的數字經濟與鄉村振興的融合程度存在著很大的進步空間,驗證假設H3成立。
6研究結論、討論與政策啟示
數字經濟在鄉村振興工作中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前沿性、優越性和創造力。本文基于包容性增長理論下“數字經濟發展—電子信息制造業與電子商務革新—鄉村振興”三位一體的嚴謹理論分析框架,通過2011—2022年中國30個省份詳實的面板數據分析,深入探討了數字經濟在推動鄉村振興進程中的引擎作用,精細剖析了林業經濟大省和其他省份以及各行政區域間存在的異質性,深度考察了數字經濟發展不同指標對鄉村振興的重要性,從而為我國構建一個深度融合現代科技元素、彰顯地域特色、促進共同富裕的新型鄉村經濟體系提供堅實的理論支撐與實踐導向。
6.1研究結論
本文以2011—2022年中國30個省份數字經濟與鄉村振興的發展為研究對象,探究數字經濟發展對于鄉村振興工作的影響效果、空間效應和差異表征,得出4點結論。
(1)數字經濟可以顯著促進鄉村振興的發展。在數字經濟對鄉村振興影響的分析中,通過分別控制省份和控制變量,得到0.6090和0.5690的顯著系數,同時控制省份和時間,得到0.4100的顯著系數,具備統計學和經濟學意義。
(2)數字經濟對林業大省的鄉村振興貢獻巨大,顯示出林業經濟在這一進程中的核心地位。未來應充分利用數字經濟的強大引擎,深度賦能林業經濟,將其作為推動鄉村振興的核心策略。這意味著要通過技術創新和數字化轉型,提升林業產業效率,挖掘其在綠色經濟中的潛力,以實現可持續發展和鄉村振興的雙贏局面。
(3)企業擁有網站數、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從業人數、電子信息制造業企業個數是數字經濟發展促進鄉村振興最為重要的三個變量,重要性系數分別為13.6218,11.6068,8.6542,這三個變量與農村電商的發展息息相關,說明電子信息制造業和電子商務是數字經濟賦能鄉村振興的主要方式。
(4)我國數字經濟在推動鄉村振興方面呈現出明顯的區域差異。具體而言,東部地區、西部地區和東北部地區的數字經濟對鄉村振興的促進效果要顯著強于中部地區。實證結果顯示,東部地區的顯著系數高達0.6450,而西部地區和東北部地區則為0.1970和0.2350。盡管中部地區的顯著系數為0.2650,但與其他地區相比,其影響相對較弱。盡管東北部地區、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的個別影響系數在統計上不顯著,但考慮到整體效應的顯著性,有理由相信這三個地區的數字經濟依然對鄉村振興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此外,由于各地區之間存在經濟聯系,數字經濟的益處不僅局限于單個地區,還能促進不同地區間的交流與合作,從而全面推動鄉村振興的進程。
6.2討論
本文將研究視角聚焦于數字經濟的19個指標的重要性比較和異質性分析,探討數字經濟對鄉村振興的影響和不同區域間的影響差異。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完善并明晰數字經濟推動鄉村振興的傳導路徑,分析數字經濟與鄉村振興的學理邏輯,將數字經濟的19個指標有機融入研究框架設計中,拓展數字經濟對鄉村振興影響的研究視角,使研究更具有深度和創新性。
(1)研究結果表明,數字經濟對鄉村振興發展有顯著促進作用,林業經濟大省效果更為顯著。這與張蘊萍等(2022)、潘海嵐等(2023)、簡鄒玲等(2024)的研究結論相似。隨著鄉村地區數字經濟的發展,鄉村振興水平的確會隨之提升。但不同地區兩者之間的關系有異質性,其中東部地區和林業大省的農村地區利用數字經濟的成效已經顯現,而中西部和東北部農村地區與數字經濟并未深度融合。原因在于大部分東部地區的經濟較其他地區更為發達,數字經濟的發展領先于其他地區。中西部和東北部農村地區由于農村數量多,基礎設施不完善導致數字經濟未充分對鄉村振興賦能。林業大省的農村地區則主要擁有林業經濟基礎,隨著數字經濟賦能林業的應用場景的拓展,這些地區能夠進一步通過林業經濟推動鄉村振興發展,從長遠來看仍然具有一定發展空間。
(2)實證檢驗發現,數字經濟通過將現代信息科技與農村發展創新結合,推動了農村產業結構升級,提高了生產效率。一方面,數字經濟通過技術升級、創建數字平臺以及產業轉型,優化了農村產業結構,提高了鄉村發展的質量,促進了鄉村振興發展(陳中,2022;劉曉菲,2024);另一方面,數字經濟發展構建了一個“虛擬世界”,通過虛擬空間發展優勢解決鄉村振興發展的難題,著重解決數字經濟在鄉村發展的技術滯后問題,極大地促進了農村市場經濟的發展(王勝等,2021)。
(3)研究結果表明,農村電商的建設與發展是數字經濟推動鄉村振興的核心要素。這與Song等(2023)的結論和商務部等九部門最新印發《關于推動農村電商高質量發展的實施意見》的文件精神不謀而合。已有研究表明數字經濟能夠顯著促進鄉村振興戰略,但僅關注數字經濟與鄉村振興這兩大方面,并未考慮到具體傳導機制下的關鍵因素,本文則深度識別了在促進作用機制下最為核心的影響因素,即農村電子信息制造業、農村電商以及鄉村振興的載體林業經濟。此外,在明晰傳導路徑的基礎上,本文發現農村電商作為核心因素在解決農產品銷路以及成本問題上起到關鍵性作用,可以有效帶動農村產業發展,促進鄉村振興。
(4)異質性分析結果顯示,數字經濟在東部地區對鄉村振興的促進作用明顯大于中部地區、西部地區和東北部地區,林業經濟大省相比其他省份的促進作用更強。這與田野等(2022)、劉釩等(2023)、馮伯豪等(2024)的研究結果相似。另外,研究同時發現,數字經濟在經過完整的發展周期后已經對林業大省的鄉村振興水平產生了正向的推動作用,數字經濟在林業經濟中的應用已取得顯著成效,這與許琴琴等(2023)的結論一致。此外,已有文獻的異質性分析僅僅關注數字經濟與鄉村振興發展的單邊關系,本文則深度研究了在不同區域的基礎上,我國林業大省與非林業大省數字經濟與鄉村振興之間的交互關系。研究結果亦表明,數字經濟發展能作用于林業大省的林業經濟,而林業經濟作為鄉村振興的關鍵載體,會進一步帶動鄉村經濟發展。
本文研究不足之處在于:第一,對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評價停留在省市整體區域層面,未細化至縣域層面的分析,今后研究可以聚焦于縣級數字經濟與鄉村振興耦合聯系,提高研究精度。第二,由于2011年之前的指標數據比較久遠,僅選取2011—2022年的數據進行分析,后續研究可隨時間推移來增加測度時間段,以便更清晰地觀察數字經濟對鄉村振興影響的演變情況。
6.3政策啟示
本文致力于探索鄉村數字化轉型與鄉村振興戰略的深度耦合路徑,旨在為全面提升鄉村產業體系現代化、優化鄉村基礎設施建設品質、強化鄉村治理體系效能提供科學指導,并通過科技創新和制度改革雙引擎驅動,有效促進農民收入增長,以加速推進我國鄉村振興進程,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貢獻具有參考價值的智慧。基于此,本文提煉出4點核心政策啟示。
(1)未來的林業經濟應當積極擁抱數字化轉型,特別是林業大省,應積極推動林業與數字技術的緊密結合,使其成為鄉村振興的重要支柱。通過數字技術優化林業管理,提升資源利用效率,既能保護生態環境,又能推動經濟增長。這樣一種綠色發展的模式,將實現環境與經濟的和諧共生,踐行“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念,實現“人不負青山,青山定不負人”。
(2)構建數字經濟導向型產業激勵機制。引導數字經濟企業向鄉村地區延伸,讓數字經濟為鄉村振興賦能,形成新時代鄉村振興新路徑。
(3)聚焦核心領域并優化資源配置。在推進鄉村數字化建設的過程中,應重點關注電子信息制造業企業的集聚程度、信息化水平以及電子商務活動的活躍狀況。打造健全的地區性農村電商平臺,拿出切實福利吸引一批有先進技術、有創新想法的年輕人回鄉發展,擴展帶貨渠道。
(4)推動區域間數字經濟發展資源均衡協同發展。中西部及東北部鄉村地區應積極承接東部地區的數字產業轉移,并通過制定激勵政策和完善基礎設施吸引數字企業落戶,讓社會資本促進鄉村振興(羅萬云等,2023)。
參考文獻
陳建珍.淺析數字技術賦能鄉村振興[J].農家參謀, 2022(24):89-91.
陳晶晶,田貴賢.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測度及空間動態演變研究[J].浙江萬里學院學報, 2024, 37(1):19-29.
陳中.數字經濟助力鄉村振興:核心機理與靶向對策[J].新經濟, 2022(11):106-112.
程廣斌,李瑩.基于投入產出視角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區域差異及效率評價[J].統計與決策, 2022, 38(8):109-113.
馮伯豪,王曉紅.數字農業助推鄉村振興的影響機制及政策建議[J].西安財經大學學報, 2024, 37(1):119-129.
馮云廷,翟婧彤,計利群.創新能力、經濟結構與城市興衰[J].財經問題研究, 2019(2):113-121.
郭露,王峰,曾素佳.數字經濟、鄉村振興與農民高質量就業[J].調研世界, 2023(1):1-10.
賈晉,李雪峰,申云.鄉村振興戰略的指標體系構建與實證分析[J].財經科學, 2018(11):70-82.
簡鄒玲,張陽麗.數字經濟賦能鄉村振興:內在機理、制約因素與推進路徑[J].當代農村財經, 2024(2):18-23.
雷搏,陳樹文.加快數字鄉村建設賦能鄉村振興[J].農業經濟, 2023(9):76-77.
李春娥,吳黎軍,韓岳峰.中國省域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綜合測度與分析[J].統計與決策, 2023, 39(14):17-21.
劉釩,于子淳,鄧明亮.數字經濟發展影響鄉村振興質量的實證研究[J].科技進步與對策, 2023(12):1-11.
劉曉菲.數字經濟賦能鄉村經濟振興路徑研究[J].對外經貿, 2024(2):55-58.
劉亞男,王青.中國鄉村振興的時空格局及其影響因素[J].經濟問題探索, 2022(9):12-25.
羅萬云,郭世豪,賈鋮.社會資本能否降低農戶相對貧困脆弱性?——基于生計策略轉型視角[J].林業經濟, 2023, 45(12):30-53.
孟雪辰,鄭浩.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多維度測算研究[J].秘書, 2022(5):26-39.
潘海嵐,黃秋妍.鄉村數字化何以緩解農村家庭多維相對貧困?[J].林業經濟, 2023, 45(11):28-49.
潘明清,范雅靜.數字普惠金融助推鄉村振興的機制與效應研究[J].宏觀經濟研究, 2023(3):35-47.
全陽,溫艷萍,崔希洙.數字經濟對林業碳匯增量影響及路徑研究——基于有調節的中介效應模型[J].林業經濟, 2023, 45(9): 23-38.
任保平.雙重目標下數字經濟賦能我國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機制與路徑[J].東岳論叢, 2024, 45(1):41-48, 191.
沈劍波,王應寬,朱明,等.鄉村振興水平評價指標體系構建及實證[J].農業工程學報, 2020, 36(3):236-243.
孫亞男,費錦華,王藝霖.中國省域數字經濟規模測算及空間分異研究[J].統計與決策, 2023, 39(6):92-97.
湯淥洋,魯邦克,邢茂源,等.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測度及動態演變分析[J].數理統計與管理, 2023, 42(5):869-882.
田小文,戴言,伯樂.“快樂購”且“精致窮”:消費主義對Z世代主觀幸福感的影響[J].消費經濟, 2023, 39(4):81-93.
田野,葉依婷,黃進,等.數字經濟驅動鄉村產業振興的內在機理及實證檢驗——基于城鄉融合發展的中介效應[J].農業經濟問題, 2022(10):84-96.
王軍,朱杰,羅茜.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及演變測度[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 2021, 38(7):26-42.
王麗,滕慧君.數字經濟賦能鄉村振興的傳導機制與實踐路徑[J].農業經濟, 2023(8):61-62.
王亮,昝琳.數字普惠金融對鄉村振興的影響研究[J].金融理論與實踐, 2023(4):77-87.
王勝,余娜,付銳.數字鄉村建設:作用機理、現實挑戰與實施策略[J].改革, 2021(4):45-59.
王一萌,任芳容,田澤.江蘇省數字經濟與林業產業發展的灰色關聯度分析[J].中國林業經濟, 2023(1):78-82.
王永芳.數字經濟、農民創業與鄉村振興[J].江蘇商論, 2024(1):28-34.
徐雪,王永瑜.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耦合協調發展的時空格局及影響因素[J].統計與決策, 2023, 39(5):50-55.
許琴琴,舒斯亮.數字經濟對林業產業發展的影響——基于門檻效應分析[J].林業經濟, 2023, 45(10):82-96.
楊建仁,何芳健,王鶴.信息化建設、數字經濟與鄉村振興[J].統計與決策, 2023, 39(22):51-56.
殷浩棟,霍鵬,汪三貴.農業農村數字化轉型:現實表征、影響機理與推進策略[J].改革, 2020(12):48-56.
曾祥明,胡元.數字技術賦能鄉村振興的關鍵點與發展進路[J].貴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24(1):43-53.
張瀚丹,李婭.數字經濟與林業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關系研究[J].林業經濟, 2023, 45(11):50-72.
張曉林.鄉村振興戰略下數字賦能農村流通創新發展機理與路徑[J].當代經濟管理, 2024(1):1-8.
張蘊萍,欒菁.數字經濟賦能鄉村振興:理論機制、制約因素與推進路徑[J].改革, 2022(5):79-89.
趙濤,張智,梁上坤.數字經濟、創業活躍度與高質量發展——來自中國城市的經驗證據[J].管理世界, 2020, 36(10):65-76.
趙亞輝,周博.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多維度測度與研究[J].國際金融, 2023(12):28-38.
Kolobkova V A, Romanov A A, Frolova E A. Digital Technologies in the Hotel Industry: New Prospect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J]. Socio-economic Systems: Paradigms for the Future, 2021, 314(6):387-394.
Kosorukov A A. Digital government in the practice of modern public administration Digital government model:Theory and practice of modern public administration [J]. Journal of Legal, Ethical and Regulatory Issues, 2017(4):81-96.
Liu Y, Wan Q, Chen W.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s a Catalyst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An Empirical Analysis from the County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in Hubei Province [J]. Journal of Knowledge Economy, 2023(10):1-33.
Sidorenko E L, Bartsits I N, Khisamova Z I. Efficiency of digital public administration:Theoretical and applied aspects [J]. Issues State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2019(2):93-114.
Song Y, Li L, Sindakis S, et al. Examining E-Commerce Adoption in Farmer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Role of Social Networks: Data from China [J]. Journal of Knowledge Economy, 2023(5):6-43.
Wang X, Chen J.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Indirect Empowermen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the Digital Economy-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s Domestic Economic Cycle [J]. Journal of Knowledge Economy, 2023(8):45-72.
Wu M, Ma Y, Gao Y, et al. 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income inequ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biased transform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J]. Empirical Economics, 2024(2):6-47.
Yin X, Meng Z, Yi X, et al. Are "Internet+" tactics the key to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s rural ethnic minority area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Sichuan Province [J]. Financial Innovation, 2021, 7(30):2-21.
(責任編輯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