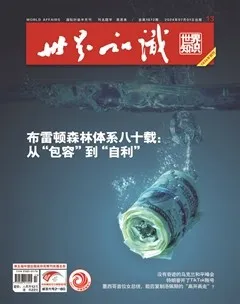莫迪組建新政府,正式開啟第三任期
劉宗義

2024年6月9日,印度總理莫迪宣誓就職新一屆政府總理,開啟他的第三個總理任期。
6月9日,印度總理莫迪在新德里宣誓就職,正式開啟他的第三個總理任期,其領導的全國民主聯盟(NDA)政府也已組建完成。本屆印度人民院(議會下院)選舉結束后,由于NDA獲得293席,相比2019年大選減少60席,而莫迪所在印度人民黨(印人黨)僅獲240席,未達獨立組閣所需半數(272席),“莫迪光環不再”“印人黨雖勝猶敗”的說法開始在國際輿論中流行。然而,印人黨及印度教民族主義在印度的基本盤實際并未被削弱,印人黨在以莫迪為首的新政府中仍處于絕對主導地位。莫迪新內閣成員名單公布后,其第三任期內外政策走向也已現端倪。
印人黨基本盤未變
雖然國際輿論認為莫迪與印人黨在本屆大選中“雖勝猶敗”,但這更多是針對選前印人黨期望單獨拿到370席以上的目標而言,印人黨若能以空前的壓倒性優勢單獨組閣,那隨后其將更容易修憲,實現“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種語言、一種宗教、一場選舉”(“五個一”)的宏大政治目標。實事求是地說,在以最大反對黨印度國民大會黨(國大黨)為首的反對黨聯盟“印度國家發展包容性聯盟”(INDIA)發動空前動員、絕地反擊,而印人黨母體組織國民志愿服務團(RSS)在大選的前幾個階段并未傾力支持的情況下,印人黨仍能拿到240席(國大黨為99席),且得票率為36.6%,只比上屆的37.3%稍有下降,這說明印人黨作為印度第一大黨的根基并未被動搖。而從包括國大黨在內的其他反對黨在選戰中多次運用帶有印度教民族主義色彩的口號,并在勝選后大多絕口不提印度穆斯林在此次大選中的貢獻來看,印度教民族主義在印度社會盛行的趨勢也難以扭轉。
從公布的莫迪新政府要職名單來看,在71名內閣成員(除總理外)中,有61人來自印人黨。同時,內政、外交、國防、財政、交通等關鍵部門也全由印人黨把持,原國防部長拉杰納特·辛格、原內政部長阿米特·沙阿、原財政部長西塔拉曼、原外交部長蘇杰生及原交通部長加德卡里全部留任。而在組閣談判期間,被印度輿論稱作“能改變游戲規則的造王者”,即同屬NDA陣營并在大選中獲得16席的泰盧固之鄉黨(TDP)與獲得12席的人民黨(聯合派)(JD〈U〉),在新內閣中僅獲民航部長、漁業與畜牧業部長等非關鍵職位,這說明莫迪及印人黨在NDA乃至印政壇中仍具有不可撼動的地位。
驕傲自滿下的策略性失誤?
印人黨在本屆大選中的收獲之所以未達預期,與其吹噓虛假經濟發展成就吸引選民,但忽視了民眾對日益惡化的失業、通脹與貧富分化的不滿密切相關。據世界銀行數據,在過去莫迪執政的十年中,除受新冠疫情影響的年份外,印度的年均經濟增長率不到6%,低于1991~2013年間國大黨執政時印度經濟增速。同時,莫迪政府明顯未能履行其大力發展“印度制造”的承諾,未能促進印度制造業實質發展并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此外,過去十年,莫迪政府所推崇的經濟增長模式也伴隨著驚人的經濟不平等現象。據《世界不平等報告》(2021),2012~2020年間,占印度人口1%的最富有人群所擁有的財富份額從30.7%增至42.5%,而占印度人口50%的最基層人群所擁有財富份額從6.4%降至2.8%。
但問題是,在上屆大選前夕,這些問題也基本存在,但印人黨當年利用印度教民族主義情緒,對巴基斯坦發動跨境“外科手術式打擊”,作為對2019年2月印度準軍事部隊在印控克什米爾地區普爾瓦馬遭遇恐襲的“報復”,成功轉移了大選辯論焦點。而在本屆大選前夕,莫迪與印人黨也曾試圖轉移印度選民的關注焦點,但成效不大。其原因在于,除經濟問題外,莫迪與印人黨在選戰中也存在因自滿導致的關鍵性策略失誤。
首先,因急于求成過早暴露了最終政治目標。莫迪與印人黨在宣傳上追求“五個一”的修憲目標,企圖將印度變成一個以印度教為基礎、更加中央集權的國家。這一選戰策略激起國大黨等反對黨的求生欲望,促成了反對黨的大團結。在反對黨的宣傳下,大選成為所謂“民主與獨裁”“宗教與世俗”之爭。反對黨聯盟與印度穆斯林群體暫擱分歧,絕地反擊,團結一致維護印度憲法、世俗主義和所謂的“民主”。

2024年5月4日,印度總理莫迪在北方邦坎普爾市參加競選集會。
其次,印人黨追求“一黨獨大”,破壞了與RSS及一些盟黨的關系。莫迪和沙阿企圖將印人黨打造成不受RSS控制且獨立性更強的政黨,推舉大量新人替換老一代政客參選,摒棄了RSS的集體決策傳統,這使印人黨與RSS關系緊張。事實上,自2014年莫迪上臺以來,RSS與印人黨的關系就漸行漸遠,這在莫迪第二任期內表現得尤其明顯。在2014年和2019年大選中,RSS發動基層組織為莫迪與印人黨助選是其獲勝的關鍵。而在本屆大選中,RSS直到5月中旬看到印人黨選情不妙才發起動員,這是印人黨丟掉大量席位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時,印人黨追求“一黨獨大”,也破壞了其與“濕婆軍”等盟黨的關系。2022年,印人黨為在孟買所在的馬哈拉施特拉邦追求“一黨獨大”,采取手段分裂“濕婆軍”,造成雙方聯盟破裂,這是今年其在馬邦丟失大量席位的重要原因。
再次,印人黨修改征地法等主張觸動了大地主利益。莫迪和沙阿主導的印人黨主要代表古吉拉特邦等地巴尼亞商人階層的利益,其修改土地法和勞工法等法律的主張,觸犯了北方邦、拉賈斯坦邦等地大地主的權益。在大地主的鼓動下,依附于他們的農民群體不會選擇印人黨,這是其在印度人口第一大邦北方邦丟失大量席位的一個重要原因。
最后,選戰前莫迪政府面對美西方表現出的“戰略自主”,使美西方對其主導下印度的發展方向深感擔憂。美西方并不希望印度實現真正的崛起,更不希望印度成為“第二個中國”。美西方對莫迪政府在人權、跨境“暗殺”海外錫克教分離主義運動領導人、逮捕德里首席部長兼反對黨平民黨主席凱杰里瓦爾等問題上不斷批評打壓,這在實際上鼓舞了反對黨聯盟的士氣。
不過,考慮到莫迪與印人黨以選票為主導的驅動力,印人黨若修正了上述問題,在五年后的新一屆大選中仍有可能重新贏得單一多數黨地位。
新政府具有政策延續性,但或面臨更多掣肘
從莫迪新政府的人員任命情況來看,關鍵崗位人事的延續性表明其內外政策也將保持一定的延續性,但同時也將有所調整。
首先,莫迪與印人黨將充分照顧聯盟黨派的政經關切,并與RSS開展緊密合作。為維持新政府的穩定,莫迪與印人黨將充分照顧泰盧固之鄉黨、人民黨(聯合派)等關鍵盟黨的關切。例如,泰盧固之鄉黨要求莫迪政府在芯片、智能手機等制造業領域加大對其所在的安得拉邦的政策傾斜和投資;人民黨(聯合派)要求莫迪政府加大對其所在的比哈爾邦農業和農民的政策傾斜。為維持并提升在印度北方印地語核心區的影響力,莫迪政府還將改善同RSS的關系,并在該區域繼續奉行強硬的印度教民族主義政策,甚至有可能會挑起與穆斯林群體的沖突,以顯示其重要性和政綱的正確性。若如此,這些政策也或將產生外溢效應,對印度與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國等穆斯林國家的關系造成影響。
其次,新政府將延續莫迪第二任期的主要經濟政策,繼續加大制造業發展力度,但可能向農業和農村傾斜。印度選票政治的特質不僅體現在政治方面,也或將充分體現在經濟方面。一些直接牽動巴尼亞工商壟斷資產階級利益的關鍵經濟改革,如征地法、勞工法和農業法案改革等或將難以繼續推進。在這種情況下,美西方對印度經濟發展的期待將降低,外來投資將減少,從而導致印度經濟發展速度下降。事實上,印度外來投資減少的跡象在2023年已非常明顯。但為實現“印度制造”等強國目標,莫迪政府或將大力扶持西部及南部沿海地區巴尼亞壟斷寡頭的發展,并在后者能發揮直接影響力的邦大力推動制造業發展,同時還將照顧城市買辦婆羅門和農村大地主的利益。但由于一些地方邦并非由印人黨執政,中央政府推行政策落地會比較困難。不過,莫迪仍然希望印度成為具有吸引力的投資目的地,因此或將對西方資本更加友好,而西方資本對阿達尼財團等印度壟斷財閥的滲透也會加強。
最后,印度外交政策將表現出明顯的延續性。在內政難以出彩的情況下,莫迪政府將會把外交作為重點。印度將繼續推行其借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美競爭之機,利用“印太戰略”與美遏華,推動全球產供鏈向印度轉移,實現印度經濟騰飛和大國崛起的大戰略,并將繼續在南亞和印度洋地區排擠中國影響力,與中國爭奪“全球南方”話語權。本屆大選結束后,美西方曾大力贊賞所謂印度“民主”的勝利,雙方矛盾或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緩和,印度所處的國際環境可能會更加寬松。但由于印度人民院出現“懸浮議會”,美西方或能更加方便地利用國大黨等反對黨或印人黨的中小盟黨牽制莫迪政府,影響其外交決策,若如此,莫迪政府親美西方的政策可能會被進一步強化。
(作者為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南亞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