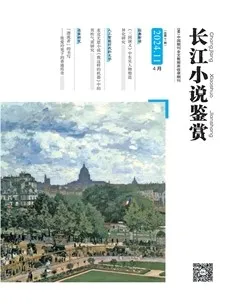《云影·古堡·湖光》中納博科夫的飛散意識
[摘要]納博科夫是20世紀最重要的俄裔美國作家。《云影·古堡·湖光》寫于1937年,其語言藝術與飛散意識備受評論界關注。本文試圖從弗洛伊德暗恐理論的角度解讀《云影·古堡·湖光》中納博科夫的飛散意識。小說展現了主人公瓦西里·伊萬諾維奇非家幻覺的原因、癥狀、治愈,以及最后的精神崩潰。在這一過程中,瓦西里作為在戰爭中死去的俄國士兵的復影,一系列俄國田園風景被建構為銜接空間。納博科夫從瓦西里的個人危機介入對俄裔飛散群體的集體創傷的思考,描述他們所患有的集體病癥,即因被迫遠離家園而形成的暗恐心理。通過暗恐式書寫,納博科夫展現了俄裔飛散群體的精神危機與生存困境,傳達了他作為俄裔飛散作家因非家幻覺而無法抵御的失落感與文化焦慮。
[關鍵詞] 納博科夫 飛散意識 暗恐 復影 銜接空間
[中圖分類號] I06? ? ? [文獻標識碼] A? ?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4)11-0063-04
一、引言
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1899—1977)是20世紀最重要的俄裔美國作家,在俄羅斯文學和美國文學中都占有極重要的位置。《云影·古堡·湖光》寫于1937年,是納博科夫最著名的短篇小說之一。小說講述了年輕的代理人瓦西里·伊萬諾維奇從柏林到俄國的火車之旅。在1936年或1937年,瓦西里在俄國流亡人士舉辦的慈善舞會上意外獲得一張旅游券。盡管他試圖通過多種手段退掉這張突如其來的邀請函,結果都不盡人意。無奈之下,瓦西里只好踏上這輛從柏林開往俄國的列車。《云影·古堡·湖光》自發表后廣受學界關注,國內外批評界對這部作品進行了各種各樣的解讀,多從不同維度分析小說中的藝術特色和微觀主題。然而,目前鮮有論文從心理分析視角出發探討這位俄裔飛散作家的創作意圖。本文試圖借助弗洛伊德的暗恐理論,分析暗恐/非家幻覺,即壓抑復現在主人公瓦西里·伊萬諾維奇身上的體現,探究瓦西里暗恐心理的成因、癥狀、治愈,及最后的精神崩潰,并解析納博科夫暗恐書寫背后的飛散意識。
二、瓦西里的壓抑復現
在《云影·古堡·湖光》中,納博科夫以第一人稱全知視角塑造了一個典型的俄裔飛散者形象。瓦西里·伊萬諾維奇是一名飛散在柏林的俄國年輕人,一日在俄國流亡人士舉辦的慈善舞會上偶然中了一張旅游券。從瓦西里收到這張從柏林到俄國的旅游券開始,戰死的俄國士兵作為瓦西里被壓抑的恐懼的象征,在瓦西里的生活中多次復現,揭示了其暗恐的原因和癥狀。
首先,瓦西里的暗恐來源于他對死亡和遠離家園的恐懼。弗洛伊德指出:“暗恐是一種恐懼情緒,源于很久以前就認識和熟悉的事物。”[1]在小說中,瓦西里在旅途中不自覺地將當前陌生的俄國與記憶中所熟悉的故鄉進行比較。暗恐就建構在熟悉的與不熟悉的并列、家與非家的二律背反中[2]。每到一個車站,瓦西里總會觀察一些毫無意義的小東西,辨認其外觀特征。瓦西里的視線聚焦在等車的小孩子中,他竭盡全力去尋找一些非同尋常的命運軌跡。透過這些孩子們,他仿佛看到了一張舊照片。在照片右排最后,一個男孩子的臉上被打了個小白叉,并寫著 “一個英雄的童年” [3]。在這里,小說使用了暗恐式的復現。瓦西里突如其來的看似陌生的驚恐經驗,實質可以追溯到他心理歷程上的某個源頭,也就是當他聽到這位俄國士兵死訊時的負面情緒,確切地說是瓦西里自己對于被迫離開家園和死亡的恐懼。在這個意義上,在戰爭中犧牲的俄國同學成為瓦西里內心恐懼的隱喻,進入瓦西里的無意識,成為自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每當瓦西里在陌生的孩子們身上尋找熟悉的蹤跡時,他曾忘卻的、壓抑在無意識中的恐懼開始在意識中重復。
其次,瓦西里的暗恐心理是在特定的情境下被喚醒的。瓦西里多次復現俄國士兵的經歷,這種重復的沖動來源于他看似已經忘卻的創傷記憶。弗洛伊德將早期經歷過而后來被遺忘的那些印象命名為創傷[4]。瓦西里所受的巨大創傷已在他心中形成心理歷史,被壓抑的事情并未真正忘卻,而是在忘記狀態下的記憶留存。在故事伊始,瓦西里與俄國士兵經歷了相似的事件,都是被迫登上列車離開家園前往俄德邊境。士兵無法擺脫被征召入伍的命運,背井離鄉參加戰爭。而瓦西里想盡辦法也無法取消這張開往俄國的旅行票,正如瓦西里心中所念,這趟旅行是命運女神強塞給他的[3]。在這一移置的時刻,當瓦西里察覺到記憶中俄國士兵的蹤跡時,無意識中的壓抑在相似的情景下被喚醒,以不自覺的方式復現,即瓦西里被迫離開柏林的經歷復現了記憶中俄國士兵的遭遇。因此,當他登上開往俄國的列車時,一股荒唐感和恐怖感開始在心中暗暗縈繞。
再次,在故事的開頭,瓦西里曾試圖通過家的蹤跡壓抑自己的非家幻覺。瓦西里在無意識中將這次旅行與曾給他帶來幸福、象征著俄國故鄉的各種形象聯系在一起,他沉思這場旅行是否能給他帶來快樂。這種快樂的源頭類似于“他的童年”“俄國抒情詩”“夢中傍晚的天際線”,抑或“他暗戀了七年的那位女士”。在過去的歲月里,這位女士已然成為他人生奮斗的目標[3]。在小說中,另一個男人的妻子可以解讀為俄羅斯的象征,即遠方的家園。這是作為在德國的俄國難民無法接近的實際的地緣所在,也是瓦西里心中所向往的舒適美好的想象空間。
最后,戰死的俄國士兵作為被壓抑的恐懼的象征,在瓦西里的生活中并非以原有形式復現,而是以其他的、非家的方式復現家的某些痕跡。瓦西里的暗恐具有再創造的特點。火車上同旅的8個德國人本來同瓦西里的過去無關,但是由于“恐懼”這個母題,瓦西里在從柏林開往俄國的火車上所遭受的苦難,成為俄國士兵在俄德戰場上經歷的復現。在這個意義上,瓦西里成為照片中犧牲的俄國士兵的復影,同行的8個德國人則是戰場上德國士兵的復影。瓦西里將壓抑的關于俄國士兵的記憶,在無意識間不自覺地演了出來。此外,弗洛伊德強調復影在壓抑復現過程中的暗恐作用[1]。小說中,瓦西里連續不斷出現的驚恐情緒表明瓦西里作為受害者被創傷的經歷反復折磨,影響著他的日常生活和性格塑造。因此,以另一種形式親身經歷士兵的人生后,瓦西里面臨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機,他再也無法控制這股反復出現的恐怖情緒。
三、非家的俄國田園風景
納博科夫采用飛散的視角,拋棄二元對立,將俄國田園風景作為銜接空間。小說中的田園風景應被視為俄國的縮影,它既是超越時空的銜接空間,也是治愈瓦西里暗恐的心理空間。小說通過虛構的風景揭示了納博科夫作為精神流亡者的非家幻覺。
根據霍米巴巴所言,“銜接空間”是一個“移動的瞬間”,它消除了時間和空間的界限,接納著古往今來的各種復雜意象,從而營造出一種家與非家之間的曖昧感[5]。在納博科夫的文學作品中,風景的想象無異于銜接空間的建構[6]。《云影·古堡·湖光》通過巴巴意義上的銜接空間并列著兩個世界,一個是當下經歷的,一個是記憶中經歷的,兩者奇妙交融。根據弗洛伊德所說,當想象和現實的界限消失,恐怖情緒應運而生[1]。當瓦西里進入田園風景中時,記憶與現實相重疊,熟悉與不熟悉相并列,家與非家相關聯。隨著隱蔽的、私密的記憶暴露出來,瓦西里的非家幻覺油然而生。
在小說中,銜接空間也被建構為治愈瓦西里暗恐的心理空間。火車沿途的俄國田園風景形成了一系列的銜接空間。火車之旅伊始,當一種難以形容的奇異恐懼感襲上心頭,瓦西里立即說服自己從飛馳的火車窗口欣賞沿途的風景。花草覆蓋的河岸、樹林、峽谷和云朵治愈了他的心靈[3]。在這片由云影、城堡、湖光構成的俄國田園風景中,湖邊小旅館里隱約像是俄國老兵的店主成為死去的俄國士兵的復影。俄國老兵與瓦西里在銜接空間的共存,讓瓦西里陷入一種幻想,幻想自己回到了童年,回到了俄國同學的身邊。雖然銜接空間只是關于當下的,但只有在這個轉瞬即逝的時刻,瓦西里接近理想家園的迫切愿望才能得以實現。瓦西里告訴他的同伴,他寧愿將來留在這里,也不愿回到柏林[3]。
俄國田園風景建構的銜接空間將瓦西里與俄國士兵、陌生與熟悉、現在與過去聯系在一起,從而將壓抑的恐懼逆轉回意識中。因此,離開銜接空間的痛苦放大了瓦西里的不安全感,當他被迫遠離田園風景,回程中被同行的德國旅客毒打,他遭遇著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機。在這個意義上,虛構的俄國田園風景背后承載的也是作者納博科夫隱秘的非家幻覺。這個由陌生元素虛構的異鄉實質建立在記憶中所熟悉的故鄉之上。不熟悉的其實是熟悉的,家與非家相輔相依,故土成了納博科夫心中難以釋懷的束縛[6],同時田園風景成為納博科夫文學創作中俄羅斯文化的記憶之場。對納博科夫這樣的現代飛散作家來說,家園不僅是自己離開的地緣空間,也是在跨民族關聯中為自己定位,為政治反抗,為建構文化身份而依屬的心理空間。在小說中,納博科夫以建構俄國田園風景式的銜接空間,給予俄裔飛散群體跨民族和跨文化的生存空間。因此,在故事結尾,當瓦西里被驅逐出連接家與非家的銜接空間時,他無法再次接近理想化的家園,也難以在未來的柏林生存下去。
四、納博科夫暗恐式書寫背后的飛散意識
在《云影·古堡·湖光》中,納博科夫以居住在德國的俄國僑民生活為題材,通過瓦西里的個人危機將小說文本同俄裔飛散群體的歷史相關聯。納博科夫通過在放逐中對俄羅斯和歐洲的再造,展現了他文學創作中獨特的飛散特性[7]。小說描寫了瓦西里暗恐的成因、癥狀、治愈,及最后的精神崩潰,展現了納博科夫作為俄裔飛散作家,因與家園隔絕引起的無法抵御的失落感。同時,在小說中,通過展現德國主流文化對俄裔飛散群體文化的沖擊,納博科夫批判了隱含著同化概念的國家意識,表達了自己作為俄裔飛散作家的文化焦慮。
納博科夫以第一人稱敘述視角,從揭露瓦西里所代表的個體的危機進入對俄裔飛散群體和文化的思考。在小說中,主人公瓦西里與“我”互為復影。弗洛伊德認為,互為復影的兩者擁有“心靈感應”,共享知識、情感和經驗,進而產生身份認同,從而將異質的自我代替真正的自我[1]。在小說中,暗恐的心理過程在瓦西里和“我”之間轉移,類似的境遇和命運也在當中出現。瓦西里和敘述者的身份相同,都是生活在德國柏林的俄國僑民,壓抑著遠離家園的驚恐情緒,將云、堡、湖組成的俄國田園風景作為治愈主體暗恐心理的銜接空間。“我”和瓦西里之間復影關系的實質是自我主體中的自我與他者,小說中表達意義的創傷并非直接作用于“我”,而是來自作為他者的瓦西里。瓦西里的聲音作為他者的聲音代表著自我主體中的他者,這種他者通過心靈感應擁有自我主體創傷的記憶[8]。在這個意義上,瓦西里與納博科夫互為復影,小說的暗恐式書寫承載著作者本人的飛散意識。納博科夫通過隱喻的形式將自己本人的流亡經歷植入他流亡生活早期的文學虛構中,形成他對創傷的記憶和情感表述[9]。在小說中,瓦西里念念不忘的那位女士與瓦西里的關系也折射出作者本人與俄羅斯故土之間的關系。正如納博科夫在他的自傳中所言:“我第一次自覺的返回……不是絕不會發生的莊嚴的還鄉,而是在我長年的流亡中它永不終止的夢。”[10]想象的家園概念在此涵蓋的不僅是客觀所在,更多的是納博科夫對歷史和創傷記憶的隱喻,而這張去往俄國的旅行票正是承載納博科夫創傷記憶的變體。
納博科夫的暗恐美學不局限于個人心理層面,它能夠指向更大的范疇。恐懼不安元素一旦出現,就會形成心理歷史。這種元素既存在于個人,也存在于文化[2]。小說使用暗恐的敘述方法,個體的負面情緒將過去和現在連接起來。通過回溯歷史,納博科夫揭露了俄國僑民的創傷經歷,指出瓦西里所患有的暗恐心理是一種集體病癥。作為俄裔飛散作家,納博科夫責無旁貸去描寫俄裔飛散群體的流亡現實,延續他們被切斷的歷史,從而延續他們共同體的生活[11]。在小說中,納博科夫通過揭露個人的、私密的驚恐經驗,指向歷史和文化的危機與沖突。小說的另一個主題顯然是反對集體暴力。在整個旅程中,瓦西里在身體和精神上都受到了集體暴力。納博科夫批判以群體規范來衡量個體價值的集體暴力給人們帶來的創傷[12]。同時,從文化的角度來看,集體暴力則表現為德國主流文化與俄裔飛散群體的邊緣文化這兩種異質文化之間的沖突。納博科夫采用飛散視角,客觀地觀察生活在文化移位狀態的俄裔飛散群體。瓦西里精神上受到的暴力正是源于文化差異,這體現在飲食、文學、娛樂方式等眾多方面。瓦西里在旅途中不斷被要求拋棄俄國傳統,接受德國流行的享樂方式。納博科夫試圖從飛散視角挑戰某些以同化意識為目的的國家文化界限,小說揭露了僑民文化不斷被主流文化改變和同化的現實,傳達了納博科夫作為俄裔飛散作家的文化焦慮。
五、結語
納博科夫作品中展現的精妙的語言技巧和飛散意識一直以來廣受文學評論家的關注。在《云影·古堡·湖光》中,納博科夫將本人的流亡經歷以一種隱喻的形式置于文學虛構中,形成了他對創傷的記憶和情感表述。小說系統展現了瓦西里暗恐的原因、癥狀、治愈,及最后的精神崩潰,其中瓦西里作為在戰爭中死去的俄國士兵的復影,一系列俄國田園風景被建構為銜接空間。小說從人類社會的心理機制出發,解讀了以瓦西里為代表的俄裔飛散群體的創傷經歷,描述了他們所患有的集體病癥,即因被迫遠離家園而形成的暗恐心理。納博科夫通過暗恐書寫,描述了俄裔飛散群體的精神危機與生存困境,傳達了他作為俄裔飛散作家因非家幻覺而無法抵御的失落感與文化焦慮。
參考文獻
[1] Freud S.The Uncanny[A]//David H.Richter.The Critical Tradition:Classical Texts and Contemporary Trends[C].Boston:Bedford/St.Martins,2007.
[2] 童明.暗恐/非家幻覺[J].外國文學,2011(4).
[3] Nabokov V.Could,Castle,Lake[A]//Dmitri Nabokov.The Stories of Vladimir Nabokov[C].New York:Vintage Books,1995.
[4]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文集11:圖騰與禁忌[M].邵迎生,譯.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
[5] 何暢.“非家”的風景——納博科夫筆下的風景想象[J].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013(6).
[6] 吳迪等.外國文學經典生成與傳播研究(第八卷)當代卷(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
[7] 童明.飛散[A]//趙一凡.西方文論關鍵詞[C].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5.
[8] 王卉.創傷小說的倫理意義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2.
[9] 韓悅.創傷與文化記憶:納博科夫早期流亡小說的俄羅斯主題書寫[J].外國文學動態研究,2022(5).
[10] 納博科夫.說吧,記憶[M].陳東飆,譯.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98.
[11] 納博科夫.菲亞爾塔的春天[M].石枕川,等譯.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3.
[12] Assa P F.Nabokov the Psychologist[J].Nabokov Studies,2017(1).
(特約編輯? 張? ? 帆)
作者簡介:何韶婷,西安外國語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