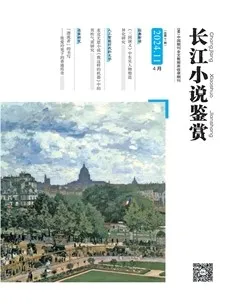阿米里·巴拉卡早期詩歌的精神生態(tài)研究
陳曉君 李鴻雁
[摘要] 美國著名非裔作家阿米里·巴拉卡早期創(chuàng)作的詩歌反映了20世紀(jì)五六十年代麥卡錫主義對(duì)民眾思想的禁錮、工業(yè)文明對(duì)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破壞以及二戰(zhàn)后傳統(tǒng)價(jià)值觀的崩塌等傷痛,呈現(xiàn)了美國大眾由此遭受的精神的“真空化”、存在的“疏離化”、生活風(fēng)格的“齊一化”等現(xiàn)代精神病癥。巴拉卡對(duì)當(dāng)時(shí)普遍存在的精神生態(tài)危機(jī)的關(guān)注與思考體現(xiàn)了他對(duì)人類精神生態(tài)的人文關(guān)懷。
[關(guān)鍵詞]阿米里·巴拉卡? 早期詩歌? 精神生態(tài)? “垮掉的一代”
[中圖分類號(hào)] I06? ? ?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 A? ? ?[文章編號(hào)] 2097-2881(2024)11-0120-04
20世紀(jì)以來,工業(yè)文明的繁榮發(fā)展給人類帶來了富足的生活。但與此同時(shí),環(huán)境的惡化、戰(zhàn)爭(zhēng)的殘酷也讓人類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難,隨之而來的是信仰的喪失、價(jià)值觀的崩塌以及人性的異化,人類已經(jīng)“丟失了自己的精神家園”[1]。因此,生態(tài)學(xué)逐漸成為學(xué)界研究的熱點(diǎn),受到了廣泛關(guān)注。著名學(xué)者魯樞元在《生態(tài)文藝學(xué)》一書中將生態(tài)學(xué)分為自然生態(tài)學(xué)、社會(huì)生態(tài)學(xué)和精神生態(tài)學(xué)三個(gè)部分,其中精神生態(tài)學(xué)被定義為“一門研究作為精神性存在主體(主要是人)與其生存的環(huán)境(包括自然環(huán)境、社會(huì)環(huán)境、文化環(huán)境)之間相互關(guān)系的學(xué)科”,一方面關(guān)涉到“精神主題的健康成長(zhǎng)”,另一方面關(guān)涉到“一個(gè)生態(tài)系統(tǒng)在精神變量協(xié)調(diào)下的平衡、穩(wěn)定和演進(jìn)”[2]。魯樞元認(rèn)為,精神領(lǐng)域內(nèi)的污染比人們想象的還要嚴(yán)重,現(xiàn)代人表現(xiàn)出來的精神癥狀主要包括精神的“真空化”、行為的“無能化”、存在的“疏離化”等。
阿米里·巴拉卡是美國黑人藝術(shù)運(yùn)動(dòng)的主要倡導(dǎo)者、黑人美學(xué)的創(chuàng)始人,“對(duì)20世紀(jì)后半葉以來美國非裔文學(xué)傳統(tǒng)的重構(gòu)和美國大眾文化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3]。20世紀(jì)50年代,巴拉卡以“垮掉派詩人”的身份開啟其文學(xué)生涯。受當(dāng)時(shí)“垮掉的一代”的創(chuàng)作影響,巴拉卡早期的許多詩歌(1957—1965)①,關(guān)注個(gè)體的孤獨(dú)感與疏離感,刻畫資本主義文明下美國大眾的精神生態(tài)困境。美國著名非裔文學(xué)批評(píng)家本斯頓認(rèn)為,在“垮掉派詩人”中,“沒有人比巴拉卡更加深切地感受到或記錄到靈魂被疏遠(yuǎn)的痛苦和欲望”[4]。巴拉卡早期的詩歌折射了20世紀(jì)五六十年代人們精神生態(tài)失衡的普遍現(xiàn)狀,展現(xiàn)了其對(duì)人類精神生態(tài)的關(guān)懷。
本文將根據(jù)魯樞元的精神生態(tài)學(xué)理論,結(jié)合“垮掉的一代”的社會(huì)文化背景,分析巴拉卡早期詩歌所呈現(xiàn)的精神的“真空化”、存在的“疏離化”以及生活風(fēng)格的“齊一化”的現(xiàn)代精神病癥,并揭示其中蘊(yùn)含的精神生態(tài)思想。
一、精神的“真空化”
人類在享受工業(yè)文明帶來的豐富物質(zhì)時(shí),卻忽視了自身的精神需求。于是,“現(xiàn)代人既失去了動(dòng)物的自信的本能,又失去了文化上的傳統(tǒng)價(jià)值尺度,生活失去了意義,生活中普遍感到無聊和絕望”[2],由此導(dǎo)致了精神的“真空化”。為了填補(bǔ)真空,人們往往會(huì)走上自戕或害人的道路。
生活的倦怠與無聊在巴拉卡早期的詩歌里隨處可見。在組詩《贊美蘭尼·普》里,巴拉卡具體地記錄了自己一周百無聊賴的生活。詩人雖然努力讓自己忙碌起來,嘗試過外出打獵、帶家人看比賽、和家人看書等積極的活動(dòng),但還是會(huì)感到無聊,覺得自己被生活的空虛所困住。他不得不“整天都干著同樣的事情”或迫不得已“早早上床睡了”以消磨時(shí)間[5],日子過得渾渾噩噩,整首詩也因此彌漫著怠惰的消極情感。顯然,巴拉卡十分厭惡這樣空虛、無聊的生活,但又苦于無法改變現(xiàn)狀,體現(xiàn)出深深的無力感。
由于難以從精神的真空中解脫出來,巴拉卡這一時(shí)期的詩歌經(jīng)常流露出對(duì)死亡的渴望與想象。本斯頓認(rèn)為:“這些詩歌中的說話人實(shí)際上處于一種癱瘓狀態(tài),從而不可避免地產(chǎn)生了對(duì)死亡的迷戀。”[4]在無所事事的日子里,傷感和憂郁將詩人籠罩。從早上睜開雙眼開始,一種“無法提及”“像時(shí)間一樣抽象的事物”[6]伴隨著詩人左右。詩人不由自主地開始思考一年四季是如何流逝的,回憶自己的年華又是如何枯萎干涸的,他清醒地意識(shí)到自己所擁有的美好事物早已消失殆盡。于是,為了暫時(shí)逃避現(xiàn)實(shí),巴拉卡只好閉上雙眼,想象自己走進(jìn)了一片波濤洶涌的海域,然后躺進(jìn)大海里、被海浪淹沒,隨著生命的消逝、軀體漂浮于海面之上。對(duì)死亡的迷戀與幻想緩沖了思考現(xiàn)實(shí)的痛苦,成為巴拉卡的避難所。
巴拉卡對(duì)生活的倦怠與困頓在很大程度上來源于麥卡錫主義。20世紀(jì)50年代初,冷戰(zhàn)興起,為了遏制蘇聯(lián),以麥卡錫主義為代表的反共浪潮席卷全美:大眾被迫接受忠誠委員會(huì)的審查與聯(lián)邦調(diào)查局的監(jiān)視,成千上萬的人受到匿名指控、被剝奪就業(yè)機(jī)會(huì),社會(huì)秩序遭到嚴(yán)重的破壞。文藝界也無法幸免,大量的左翼書籍被列為禁書,知識(shí)分子失去了言論自由,被迫沉默,而當(dāng)時(shí)反主流的“垮掉的一代”成員,如金斯伯格與凱魯亞克均受到了政府“嚴(yán)重的歇斯底里式的恐怖性威脅和迫害”[7]。巴拉卡本人也曾遭受過麥卡錫主義的迫害。在搬去格林威治村之前,巴拉卡曾是美國空軍的一員,但由于軍方收到了對(duì)他的匿名指控,并隨后在他的床位上搜出了有關(guān)左翼文學(xué)雜志的信件,他最終被軍隊(duì)開除。麥卡錫主義讓整個(gè)社會(huì)陷入了恐慌、緊張的氛圍之中,人們不僅失去了言行自由,而且難以在社會(huì)中實(shí)現(xiàn)自己的價(jià)值,最終只能悲嘆人生。生活變得枯燥無味,甚至是失去了意義,人們更多地感受到了精神的困惑、個(gè)人價(jià)值的泯滅以及生存的困境。
二、存在的“疏離化”
魯樞元將存在的“疏離化”分為人與自然的疏離、人與人的疏離,以及人與自己內(nèi)心世界的疏離,而“現(xiàn)代人在遭遇三重疏離后,生命中一切積極的、向上的、富有創(chuàng)造性的動(dòng)機(jī)幾乎全被瓦解,剩下的只有無法排遣的軟弱、孤獨(dú)、空虛、絕望”[2],這些在巴拉卡早期的詩歌里都有所體現(xiàn)。
1.人與自然的疏離
過去,人類生活在自然的懷抱中,“隨時(shí)都在與充滿生機(jī)的自然進(jìn)行著對(duì)話和交流”[2]。但隨著工業(yè)文明的發(fā)展,各種有形、無形的障礙將人與自然相隔絕,現(xiàn)代人因此很少能夠像過往那樣與自然親近。
20世紀(jì)五六十年代,美國工業(yè)高速發(fā)展,機(jī)器逐漸主宰人們的生活,整個(gè)社會(huì)的物質(zhì)水平得到極大的提高。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下,當(dāng)時(shí)的知識(shí)分子群體,尤其是“垮掉的一代”的成員,開始更多地關(guān)注生態(tài)問題,思考人與自然的關(guān)系。作為“垮掉派詩人”,巴拉卡敏銳地感知到所謂的工業(yè)化、都市化是以犧牲生態(tài)環(huán)境為代價(jià),造成了人與自然的隔絕,破壞了兩者的和諧共生。《昨天在找尋你,今天你來到這里》里記錄了自然景象被工業(yè)文明吞噬的一幕:“我站立在郵箱上/揮舞著我黃色的T恤/看著灰白色的水庫/順著中央大街延展。”[5]詩人站在郵箱上,企圖從高處看到更多的風(fēng)景,但望到的只有那了無生氣的灰白色水庫一直沿著大街延展,單調(diào)無比;而原本的自然景象,如綠樹、藍(lán)天、鳥兒,早已消失不見,人類再也不能感受、親近自然。深感失望的詩人于是發(fā)出呼喊,稱這一切都是“惡之花”,“冷冰冰的,了無生氣”[5]。
2.人與人的疏離
在以往的年代,“關(guān)愛、同情、人際間真誠無私的合作互助”[2]隨處可見。然而,隨著鼓勵(lì)“競(jìng)爭(zhēng)”與“拼搏”的社會(huì)氛圍日益濃厚,以及科學(xué)技術(shù)的迅猛發(fā)展,人與人之間產(chǎn)生了疏離,彼此間的關(guān)系也不可避免地發(fā)生了異化。
二戰(zhàn)后,為了爭(zhēng)奪霸權(quán),美國政府將昔日反法西斯盟友的蘇聯(lián)描繪為敵對(duì)勢(shì)力,這種轉(zhuǎn)變影響了民眾的自我身份的認(rèn)知。隨后,麥卡錫主義的盛行使得社會(huì)氛圍緊張,人們之間的信任受到猜疑和污蔑的侵蝕,自由、平等的價(jià)值觀受到踐踏。在這種背景下,“垮掉的一代”成員以極端行為表達(dá)對(duì)傳統(tǒng)倫理道德觀念的不滿和反抗。“沒有人真的在乎。/我的妻子懷上了她的孩子。”[5]妻子懷孕本該是一件值得重視和喜悅的事情,但丈夫卻滿不在乎,認(rèn)為妻子懷孕與他沒有關(guān)系,沒有展現(xiàn)出絲毫作為丈夫和父親的責(zé)任與關(guān)心。人類似乎喪失了表達(dá)愛的能力,無法再像從前那樣與他人建立起親密的情感聯(lián)系,即使是與最親近的家人和朋友之間也存在著疏離。
3.人與自己內(nèi)心世界的疏離
人與自己內(nèi)心世界的疏離具體表現(xiàn)在“信仰的喪失、理想的喪失、自我反思能力的喪失”[2]。在巴拉卡早期的詩歌中,人與自己內(nèi)心世界的疏離更多地體現(xiàn)為“理想的喪失”這一方面。
詩人有著追求藝術(shù)的理想,并認(rèn)為自己才華橫溢,即使是從未涉獵過的畫畫,他也大膽斷言自己“比列奧納多更好。比博斯更強(qiáng)。勝過霍加斯。超越克萊恩”[5],能夠堪比歷史上最偉大的畫家們。但是,麥卡錫主義讓包括詩人在內(nèi)的當(dāng)時(shí)大多數(shù)人難以實(shí)現(xiàn)自我的價(jià)值,郁郁不得志,而詩人生活環(huán)境惡劣,一家人擁擠在狹小的公寓里,就連屋頂壞了也無法及時(shí)修繕,讓自己遭受了“一場(chǎng)如期而至的感冒”[5],生活迫切需要得到改善。因此,詩人要承擔(dān)起養(yǎng)家重任的現(xiàn)實(shí)與追求藝術(shù)的理想產(chǎn)生了沖突:“我試著把某件雕塑做了,/但是沒有任何結(jié)果。不可能/同時(shí)既搞藝術(shù)/又賺錢。”[5]詩人天真地希望通過藝術(shù)創(chuàng)作來賺錢養(yǎng)家,一舉兩得,但是雕塑作品的失敗讓他意識(shí)到自身貧窮的條件是無法支撐真正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自己應(yīng)該放棄追求藝術(shù)的理想,通過別的方式養(yǎng)家糊口。由于無法同時(shí)肩負(fù)賺錢和藝術(shù)創(chuàng)作,詩人徹底放棄了自己的理想。更重要的是,這種與自己內(nèi)心世界的疏離還引起了“自我肯定的坍塌”[2]。昔日那個(gè)意氣風(fēng)發(fā)、不可一世的詩人如今陷入了自我懷疑之中,認(rèn)為自己并沒有能力改變生活,并嘲諷自己只是個(gè)“出身卑賤饑腸轆轆的落魄者”[5]。為了謀生,他只能去做一些與藝術(shù)追求格格不入、狼狽不堪的生計(jì)。
三、生活風(fēng)格的“齊一化”
注重高效率的工業(yè)文明催生了現(xiàn)代社會(huì)生活的“齊一化”,即使是在地球上兩個(gè)相隔千里的角落,依舊可以發(fā)現(xiàn)相似的穿著、習(xí)俗、語言等。于是,“歷史形成的各種文明與文化開始同自己的根源相脫離,他們都融合到技術(shù)-經(jīng)濟(jì)的世界中,融合到一種空洞的理智主義中”[8]。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將文化工業(yè)稱為“大眾欺騙的啟蒙”[9],認(rèn)為文化工業(yè)正在以統(tǒng)一的文化觀念、文化方式占領(lǐng)人們?nèi)康臉I(yè)余生活,個(gè)人的思考以及個(gè)性的展現(xiàn)因而沒有了時(shí)間與空間。
在這樣的社會(huì)環(huán)境下,拒絕隨大流顯得軟弱無力。因此,人的個(gè)性逐漸泯滅,這首先體現(xiàn)在生活習(xí)慣的同化上。在《贊美蘭尼·普》中,詩人詳細(xì)地描述了自己妹妹的生活喜好:“我妹妹開著一輛綠色捷豹/我妹妹每月做兩次頭發(fā)/我妹妹是一名小學(xué)教師/……我妹妹討厭吵鬧不休的黑人。”[5]詩人的妹妹深受美國主流文化的影響,完全接受了白人主流文化的價(jià)值觀和生活方式,積極地模仿白人的生活習(xí)慣以融入美國主流社會(huì)。但詩人顯然對(duì)此感到十分擔(dān)憂,他發(fā)現(xiàn)妹妹失去了自身作為黑人的特性,不僅把黑人普遍擁有的卷發(fā)拉直,在外貌上被白人界定的審美標(biāo)準(zhǔn)同化,甚至在價(jià)值觀上也被同化,對(duì)于同種族的其他黑人持有厭惡、排斥的態(tài)度,認(rèn)為黑人“吵鬧不休”[5],并拒絕給他們上課。在白人主流文化的影響下,詩人的妹妹難以欣賞黑人文化的價(jià)值,并憎惡與自己本民族有關(guān)的一切,自我認(rèn)知遭到扭曲,迷失了方向。詩人把這種在白人主流文化侵蝕下失去民族特性的黑人稱為“假黑人”[5]。
生活風(fēng)格的“齊一化”還體現(xiàn)在人們的思維方式方面。20世紀(jì)五六十年代,廣播、電視等現(xiàn)代化媒介發(fā)展繁榮,人們接收到了前所未有的豐富信息。但顯然,過多的信息已經(jīng)把他們淹沒,讓他們失去了獨(dú)立思考的能力:“有誰曾停下來想起過拉蒙特·格蘭斯頓的神勇?/(據(jù)我所知:只有杰克·凱魯亞克和我。/你們其他人也許曾了解過此人,是通過WCBS電視臺(tái)和凱特·斯密斯,/或者其他同樣無趣的途徑。)”[5]格蘭斯頓是漫畫《影子俠》中的英雄,擁有操縱他人心智的超能力。該漫畫于20世紀(jì)30年代被改編為廣播節(jié)目,并大獲成功。詩人發(fā)現(xiàn),人們?nèi)缃癫⒉皇怯H自在漫畫中了解到格蘭斯頓,而是通過電臺(tái)節(jié)目或流行歌手得知,對(duì)英雄角色的認(rèn)知與思考只是來自他人的灌輸,人云亦云,而關(guān)于英雄的核心特質(zhì)卻茫然不知,大眾的認(rèn)知趨于同質(zhì)化。詩人認(rèn)為,如今只有他和凱魯亞克還保持著清醒,不會(huì)盲目地被美國主流文化裹挾。
在巴拉卡看來,出現(xiàn)這種現(xiàn)象是因?yàn)槊绹髁魑幕趯?duì)大眾思想進(jìn)行操縱。他指出,統(tǒng)治階級(jí)借用各種現(xiàn)代化媒介技術(shù),通過電影中行俠仗義的英雄人物、廣播節(jié)目主持人的故事講解、報(bào)紙和連環(huán)漫畫故事中的魔術(shù)師魔力、宗教人士的電視布道、政客們?cè)陔娨曋星缮嗳缁傻奶摷傩麄鞯仁侄危瑐鞑ヒ庾R(shí)形態(tài)。巴拉卡的觀點(diǎn)揭示了統(tǒng)治階級(jí)利用意識(shí)形態(tài)國家機(jī)器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美國民眾對(duì)自我的認(rèn)同,導(dǎo)致他們更傾向于接受主流文化價(jià)值觀和道德規(guī)訓(xùn),從而失去了對(duì)自我真實(shí)追求的堅(jiān)持。
四、結(jié)語
20世紀(jì)五六十年代,美國經(jīng)濟(jì)發(fā)展繁榮、科技進(jìn)步迅猛,呈現(xiàn)出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但背后卻孕育著重重危機(jī)與矛盾:麥卡錫主義的迫害、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惡化、傳統(tǒng)價(jià)值觀的崩塌等,物質(zhì)文明與精神文明之間出現(xiàn)了極端的不平衡,大眾對(duì)生活感到悲觀厭倦,卻又無可奈何,由此陷入了精神困境。
作為美國邊緣群體的一員,巴拉卡有著強(qiáng)烈的孤獨(dú)感與疏離感。在“垮掉的一代”時(shí)期里,巴拉卡敏銳地察覺到當(dāng)時(shí)的大眾處于一種壓抑、凝滯、空虛、蒼白的精神病態(tài)之中,并在其早期的詩歌創(chuàng)作中給予了關(guān)注。無疑,巴拉卡是一名具有生態(tài)意識(shí)的詩人,其早期的詩歌折射了當(dāng)時(shí)人類精神生態(tài)失衡的普遍狀況,體現(xiàn)了他對(duì)現(xiàn)代精神生態(tài)危機(jī)的擔(dān)憂與思考。
注釋
① 哈里斯將巴拉卡的文學(xué)生涯劃分為四個(gè)部分:“垮掉的一代”時(shí)期(1957—1962)、過渡時(shí)期(1963—1965)、黑人民族主義時(shí)期(1965—1974)以及第三世界馬克思主義時(shí)期(1974— )。基于此,本文將巴拉卡于“垮掉的一代”時(shí)期和過渡時(shí)期創(chuàng)作的詩歌作為其早期的詩歌進(jìn)行討論。
參考文獻(xiàn)
[1] 紹伊博爾德.海德格爾分析新時(shí)代的科技[M].宋祖良,譯.北京:中國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1993.
[2] 魯樞元.生態(tài)文藝學(xué)[M].陜西:陜西人民出版社,2000.
[3] 譚惠娟,羅良功,王卓,等.美國非裔作家論[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6.
[4] Benston K W. Baraka: The Renegade and the Mask [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6.
[5] Baraka A. The LeRoi Jones/Amiri Baraka Reader [M]. New York: Thunders Mouth Press,1991.
[6] Baraka A. SOS: Poems 1961—2013 [M]. New York: Grove Press,2014.
[7] 邵崇忠.正面社會(huì)能量的流轉(zhuǎn):論金斯伯格詩歌中的反“麥卡錫主義”書寫[J]. 外國語文研究(輯刊),2022(1).
[8] 卡爾·雅斯貝斯.時(shí)代的精神狀況[M].王德峰,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
[9] 霍克海默,阿道爾諾.啟蒙辯證法:哲學(xué)片段[M].渠敬東,曹衛(wèi)東,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責(zé)任編輯? 余? ? 柳)
作者簡(jiǎn)介:陳曉君,廣州大學(xué)外國語學(xué)院,研究方向?yàn)槊绹膶W(xué)。
李鴻雁,廣州大學(xué)外國語學(xué)院副教授,研究方向?yàn)槊绹膶W(xué)。
基金項(xiàng)目:教育部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研究項(xiàng)目“阿米里·巴拉卡詩學(xué)研究”(18YJA75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