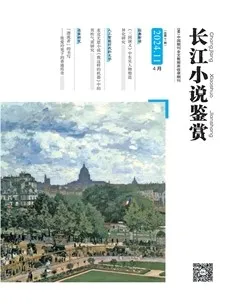森鷗外和魯迅小說中的“狂人”形象比較研究
[摘要]魯迅動筆翻譯森鷗外《沉默之塔》的時間和他創作《狂人日記》《藥》的時間幾乎重疊,在這三部作品中均有出現的“狂人”形象也具有許多共同點。但與森鷗外的“狂人”相比,魯迅的“狂人”更具革命性和戰斗性。可以說,魯迅結合本國的時代背景和自己的親身經歷,以徹底揭露舊時代中國的病態社會、喚起民眾的覺醒為目的,對森鷗外的“狂人”形象進行了進一步的改造和發展。
[關鍵詞]森鷗外? 魯迅? 狂人? 比較文學
[中圖分類號] I06? ? ? ?[文獻標識碼] A? ?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4)11-0084-04
一、“狂人”之經緯
魯迅的“狂人”形象首次登場于1918年發表的《狂人日記》中。《狂人日記》憑借日記體這一新穎的文學形式和獨具特色的人物形象,一經發表便引起了文學界和學術界的廣泛關注,作為小說主角的“狂人”也成了各國學者討論和研究的對象。
魯迅曾在評價自己的作品時寫道:“一八三四年頃,俄國的果戈理就已經寫了《狂人日記》;一八八三年頃,尼采也早借了蘇魯支的嘴,說過‘你們已經走了從蟲豸到人的路,在你們里面還有許多份是蟲豸。你們做過猴子,到了現在,人還尤其猴子,無論比那一個猴子的。而且《藥》的收束,也分明的留著安特萊夫式的陰冷。但后起的《狂人日記》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卻比果戈理的憂憤深廣,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1]由此可見,外國作家及其作品對魯迅文學創作的影響是客觀存在的。
李冬木曾經針對“狂人之誕生”撰文指出,“狂人”在文學作品和評論中頻繁登場,是明治文學的一種突出現象。魯迅在日本留學期間受到“狂人”言說的洗禮,完成了自我的確立,并帶著一個完整的“狂人”雛形回到中國。他筆下的“狂人”是中國現代文學移植外國思想和文藝、將其本土化的結果[2]。針對“狂人”的演變歷程,李冬木另撰《“狂人”的越境之旅》指出,今野愚公翻譯果戈理的《狂人日記》,是“狂人”入境日本的開始。松原二十三階堂創作的《狂人日記》,使“狂人”完成了日本的本土化轉型。此后,契訶夫《六號室》譯本的出現和二葉亭四迷《二狂人》的發表,引發了文藝界的“狂人”熱潮。魯迅親自見證了“狂人”的越境,并最終通過翻譯和創作將“狂人”帶到中國[3]。此處有兩點值得格外關注。其一,魯迅“狂人”的誕生與其日本留學期間的見聞有著密切聯系;其二,魯迅引進“狂人”的方式有兩種,即翻譯和創作。
結合以上兩點,筆者將目光轉向森鷗外。魯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說來》一文中明確表示,他在日本留學期間喜愛的日本作家是夏目漱石和森鷗外[4]。這份喜愛與森鷗外和魯迅在時代背景和個人身份上的共同點有著密切聯系,他們身處新舊思潮激烈碰撞的社會轉型時期,既有傳統文化的深厚涵養,又因其海外留學經歷,受到新文化、新思潮的熏陶,對傳統表現出反叛的傾向。兩位作家都是醫學出身,轉向文壇,兼任政府官職,因此他們在剖析社會現實和官僚政治時,總帶著醫學者的冷靜,以獨特的視角對保守、反動勢力進行辛辣的諷刺。
1910年的“大逆事件”以及日本政府的禁書行為引起了森鷗外的強烈不滿,他于同年11月發表《沉默之塔》,通過派希族統治者封禁自然主義和社會主義作品、殘殺“危險書籍”讀者的故事,揭露了反動者以“危險的洋書”為借口迫害革新者的真相。魯迅對這些不滿感同身受,他于1921年親自動筆翻譯《沉默之塔》,并將其收入1923年出版的《現代日本小說集》中,以他山之石,批判反動者對于“走新路”的人的迫害。兩位文豪在靈魂和思想上的共鳴由此可見一斑。
巧合的是,魯迅翻譯的《沉默之塔》和幾乎同時期創作的《狂人日記》《藥》中都出現了“狂人”形象。這不免讓人產生疑問,魯迅是否同時以翻譯和創作的形式將留學期間接受的“狂人”帶到中國?森鷗外的《沉默之塔》是否是魯迅“狂人”的來源之一?本論文將重點圍繞這兩個問題展開討論。
二、森鷗外和魯迅小說中的“狂人”
《現代日本小說集》和《吶喊》分別于1923年6月和8月相繼出版,可以說,魯迅翻譯《現代日本小說集》所選入作品的時間和他創作《吶喊》系列文章的時間幾乎是重疊的。正如崔琦所言:“魯迅在創作《吶喊》的同時,曾翻譯了大量外國的小說和劇本,其規模和數量遠超創作……翻譯和創作同行,是《吶喊》時期的一個重要文學現象。”[5]因此,可以合理推斷,魯迅在創作《吶喊》所收錄文章的過程中極有可能受到同期翻譯作品的影響。
1.《沉默之塔》中的“狂人”
《沉默之塔》寫于1910年,是森鷗外對所謂“大逆事件”以及“危險的洋書”的回應。《沉默之塔》的主要情節是:派希族內部發生了血腥的爭斗。一部分青年由于閱讀有關自然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危險書籍”被同族人殘忍殺害,他們的尸體被運到沉默之塔中喂食烏鴉。“危險的洋書”的創作者、翻譯者、讀者都成了罪人,文藝的世界亦成為充滿疑慮與恐懼的世界。
于是,崇拜個人主義、又用革命家來做小說主角的阿爾志跋綏夫被批判為“連精神都異樣”的危險分子;講述貴族小姐與仆人相愛、傳播平民主義的斯忒林培克被人疑心“當真發了狂”;宣揚“超人”、此岸哲學的尼采則是“頭腦有些異樣”,“終于發了狂”。對于這些離經叛道、走著新路的“狂人”,反動統治者是必然要為他們定下莫須有的罪名趁機加以迫害的。這個罪名,可以是閱讀、傳播“危險的洋書”,可以是發表過激言論、有不檢的舉動,也可以是思想、精神有異端。所謂“狂人”,也不過是一個迫害的名目罷了。
2.《狂人日記》中的“狂人”
《狂人日記》是《吶喊》的開篇之作。小說以“日記”為載體,講述了“狂人”的所見所聞與所思所想。“我”從幾十年的昏昏沉沉中蘇醒過來,決定勸說周圍人改掉吃人的習俗。大哥聽了“我”的勸告,不但不悔改,反而為“我”扣上一個“瘋子”的頭銜,想以懲惡揚善為借口順理成章地吃掉“我”。
魯迅通過講述這個略顯荒誕的故事,深刻揭示了封建社會吃人的本質。“狂人”是那個蒙昧時代的可悲的覺醒者,他因為反對封建統治,并覺察到封建社會以虛偽的“仁義道德”之名,行“吃人”之實的殘忍行徑,成為眾人眼中的異類,被冠以“迫害狂”“瘋子”之名,受到警誡和迫害。
3.《藥》中的“狂人”
魯迅的《藥》以“買藥”“吃藥”“茶館談笑”“上墳”這四幕短劇的形式,向讀者展示了革命者與窮苦大眾的雙重悲劇。小說由一明一暗兩條線索組成,華小栓是明線的主角,夏瑜是暗線的主角。夏瑜作為暗線的主角,卻只是出現在人們的談話中,沒有得到任何正面、直接的描寫。為革命拋頭顱灑熱血的英雄,始終與民眾有著一層可悲的障壁。夏瑜在入獄之后勸牢頭造反,宣傳民主思想,甚至同情毆打他的獄卒,這些行為在民眾看來毫無疑問都是“狂人”之舉。作者借三位角色之口,連用三句“瘋話,簡直是發了瘋了”“發了瘋了”“瘋了”表現民眾的詫異與不解。甚至在夏瑜死后,他的墳仍然與窮人的叢冢隔著一條“自然的界限”[6]。
綜上,《沉默之塔》《狂人日記》和《藥》中出現的“狂人”形象在出現時間和內涵上具有一定的聯系性。森鷗外和魯迅筆下的“狂人”,看似離經叛道,不守規矩,實際上,他們是時代的先覺者,是沉默、病態的社會的真正“解藥”。“狂人”因為產生了新思想,想要走新的路,所以與舊社會格格不入。
三、“狂人”形象的異同
如前所述,《沉默之塔》《狂人日記》和《藥》中出現的“狂人”形象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由于作者自身的革命性和戰斗性等因素,森鷗外和魯迅筆下的“狂人”又有著微妙的差異。
1.“狂人”形象的共同之處
“狂人”所處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可以用沉默和黑暗來概括。
《沉默之塔》的開篇便是一段細致的景物描寫。沉默之塔聳立在黃昏的天空里,呈現出單調的灰色,乏力的馬拖著沉重的車,晚潮遲鈍緩慢地拍打著海岸。整段描寫營造出一種死氣沉沉、黑暗肅殺的氛圍,生動表現出高壓政策下社會和思想界的壓抑。魯迅的《狂人日記》和《藥》中對這種沉默與黑暗有著相似的刻畫。例如,狂人在懷疑身邊的眾人吃人時,感到周圍的環境“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藥》中的華老栓為兒子買藥而出門的那個秋夜,“街上黑沉沉的一無所有”,“有時也遇到幾只狗,可是一只也沒有叫”。夏四奶奶在墳地以為夏瑜顯靈而哭訴時,周圍亦是“死一般寂靜”。森鷗外和魯迅的寥寥幾筆,便勾勒出一幅象征著黑暗與死亡的殘酷畫卷,將極度壓抑下令人戰栗的沉默傳遞給每一個讀者。
兩位作家不僅在小說基調上存在相似性,還默契地選擇了墳地和烏鴉這兩個意象進一步表現“狂人”所處環境的沉默與黑暗。沉默之塔是派希族統治者用來存放死尸、喂食烏鴉的場所,與《藥》中的墳地發揮著相似的作用。運進沉默之塔里的馬車走了又來,“貨色很不少”,《藥》中西關外的墳地亦是埋到層層疊疊,“宛然闊人家里祝壽時候的饅頭”。塔里裝著的是閱讀危險書籍、“紊亂社會秩序”或被意外牽連的家伙,墳地里埋著的則是意圖謀反、受了死刑的犯人或窮苦百姓。可以說,沉默之塔和墳地象征著禁錮與死亡,表現出反動統治者對“狂人”的殘酷鎮壓和對窮苦大眾生命的漠視。接著,兩位作家又默契地使用“烏鴉”來打破“墳地”的沉默與寂靜。《沉默之塔》中,烏鴉在塔的周圍不斷翻飛,發出聒噪的叫聲,享用尸宴。《藥》中的烏鴉則在夏四奶奶希望破滅之后忽然“啞”的一聲大叫,張開雙翅如箭一般向遠處的天空飛去。烏鴉作為一種食腐動物,常與墳地、尸體等相伴出現,在寂靜的墳地之中,烏鴉聒噪的叫聲為其增添了一絲恐怖詭異的氣息。
2.“狂人”形象的不同之處
《沉默之塔》中,“我”從始至終都是一個旁觀者,客觀敘述派希族的內斗,發表對于政府封禁洋書和壓制思想行為的主觀看法,并未直接參與到反抗和斗爭中,做出“狂人”的行為。對于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我”同樣持一種感興趣但未必認同的旁觀者態度。總的來說,森鷗外筆下的“狂人”是“我”在報紙上間接接觸的“狂人”,因此,作為旁觀者的“我”和作為反抗者的“狂人”之間有著一種微妙的距離感。“我”和“狂人”共同追求的是思想和文藝創作上的自由,提倡文藝革新和思想解放,這種反抗和斗爭局限于文藝和思想的范疇。
《狂人日記》中,“我”便是“狂人”,是故事的主角,也是所有事件的親歷者。與《沉默之塔》中的“狂人”相比,《狂人日記》里的“狂人”更具革命性和戰斗性,他是親自參與斗爭的革命者,他勇敢地揭露封建社會的吃人真相,勸告眾人改掉吃人惡習。與森鷗外的“狂人”相比,魯迅的“狂人”直接挑戰根深蒂固的封建專制制度和作為剝削工具的封建禮教,他顯然觸及了社會架構中比文藝和思想更加深刻、更為根本的存在。
再看魯迅的《藥》,無論是小說第一節“古軒亭口”處對夏瑜原型秋瑾的緬懷,還是第四節作者為夏瑜的墳憑空添上一圈紅白的花,都可以看出作者對革命烈士的崇敬和認同。夏瑜所反抗的對象也顯然超越了文藝和思想的范疇。無論是向獄卒宣傳“大清的天下是我們大家的”,還是同情愚昧的民眾,都充分體現出夏瑜作為“狂人”從事革命的徹底性,也反映出魯迅作為啟蒙作家推動社會變革的訴求。
綜上,森鷗外的“狂人”是文藝界的革新者,他們反對的是政府不合理的思想鎮壓行為,追求的是思想和文藝創作上的自由,缺乏觸碰社會制度的決心和勇氣。魯迅的“狂人”是“鐵屋子”里蘇醒的革命者,他們反對的是中國幾千年來的封建剝削制度,追求的是徹底的社會變革和個體解放。
3.異同形成的原因
如前文所述,森鷗外和魯迅由于所處社會背景的相似性和多重身份的重疊,在思想上存在共鳴,這是他們筆下的“狂人”形象存在相似性的主要原因,在此不再贅述。本節主要探討兩位作家筆下的“狂人”形象不同之處的成因。
竹盛天雄曾敏銳地指出:“在森鷗外的精神世界中,政治家的想法、文學者的見識和科學者、歷史學者的感觸以一種微妙的形式共存。他作為官僚必須捍衛國家的秩序,作為科學家和文學者又要推進日本的現代化。”[7]因此,這種個人自由與國家秩序之間的矛盾和對立自然而然地滲透到森鷗外的文學創作中,使他的創作立場和寫作手法呈現出調和與妥協的曖昧。即使是《沉默之塔》這部最具現實批判性的作品,森鷗外借“狂人”表達的也僅限于對思想鎮壓行為的抗議和對思想解放的呼吁,不會觸及封建制度的根本。
魯迅同樣身處社會發生劇烈變革的時代,但與日本表面的繁榮不同,中國面臨的是極為深重的民族危機。面對“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鐵屋子”,魯迅自然不會像森鷗外一樣對政府改革抱有不切實際的美好幻想,他反抗封建制度的立場也更為堅定。從魯迅的個人經歷來看,他雖出生于封建氣息濃厚的富裕家庭,但家道中落的過往讓他深刻體會到社會的人情冷暖,對國民精神的劣根性有著更為清醒的認識。他雖然曾經在北洋政府的教育部任職,但如魯迅自己所言,只是“不入鞠躬或頓首之列”的區區僉事[8],與政府、官僚沒有多少瓜葛,自然不會因為身處“體制”之內尋求妥協與調和。
四、結語
如孫郁所說,在魯迅的精神世界中,學術研究與創作、翻譯活動是互相交織、滲透的,譯文中的思想常常會轉化到魯迅同期的文學創作中[9]。森鷗外和魯迅都是借“狂人”啟蒙民眾、改良社會。可以合理推斷,《沉默之塔》這一篇譯文中的思想極有可能以“狂人”的形式轉化到了魯迅同期創作的《狂人日記》和《藥》中。
如魯迅所說:“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所寫的事跡,大抵有一點見過或聽到過的緣由,但決不全用這事實,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發開去,到足以幾乎完全發表我的意思為止。”[4]可以說,魯迅結合本國的社會背景和自己的親身經歷,以徹底揭露舊時代中國的病態社會、喚起民眾的覺醒為目的,對森鷗外的“狂人”進行了進一步的改造和發展,創造出了一個更具革命性和戰斗性的“狂人”。這也體現出魯迅通過翻譯外國文學作品,“換自己身上的血,將雜質剔除,引來鮮活的存在”的初衷。魯迅的作品跨越時代與國度的局限,具有普世的價值。他從世界各國的文學作品中汲取養分、獲取靈感,又創作出足以反哺世界文壇的優秀作品,是真正意義上的具有世界性的作家。
參考文獻
[1] 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説二集」序[M]//魯迅全集·第8巻.東京:學習研究社,1992.
[2] 李冬木.狂人の誕生:明治期の「狂人」言説と魯迅の『狂人日記』[J].佛教大學文學部論集,2019
[3] 李冬木.〈狂人〉の越境の旅:周樹人と〈狂人〉の出會いから彼の「狂人日記」まで[J].佛教大學文學部論集,2021.
[4] 魯迅.我怎么做起小說來[M]//魯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5] 崔琦.從《游戲》到《端午節》——試論魯迅翻譯與創作之間的互文性[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6(3).
[6] 魯迅.藥[M]//魯迅全集·第l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7] 竹盛天雄.森鴎外の現代小説:一九一〇年前後の問題(物語と小説の歴史)[J].日本文學,1959,8(9).
[8] 魯迅.從胡須說到牙齒[M]//魯迅全集·第l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9] 孫郁.魯迅的譯介意識[C]//北京魯迅博物館.紀念魯迅逝世七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魯迅博物館,2006.
(責任編輯? 夏? ? 波)
作者簡介:錢浩宇,北京外國語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