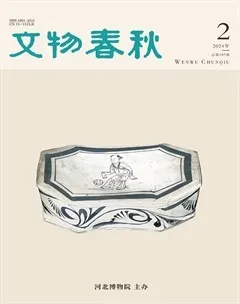河北地區秦代郡縣的考古新發現
呂蘇生
【關鍵詞】秦代;郡縣;河北地區
【摘要】近幾十年來,大量秦簡、封泥等考古資料的發現和相關研究成果為秦代在今河北地區的郡縣設置研究增添了新資料。通過對這些考古材料和研究成果進行全面系統整理和總結,并結合文獻資料一一進行分析考證,將今河北地區已知秦代郡縣數目由《中國歷史地圖集》中的11郡20縣增加到13郡60縣,填補了一些歷史空白,同時更正了過去的一些錯誤看法。
近幾十年來,云夢秦簡、里耶秦簡、岳麓秦簡、張家山漢簡《秩律》簡的發現,西安相家巷大量秦代封泥、徐州西漢初年楚王墓封泥的出土,以及一系列戰國及秦代兵器、貨幣、陶器銘文的面世,陸續揭露了大量秦代行政區劃的信息。同樣的,有關秦代今河北境內的郡縣設置也有許多新的發現,可更正之前的很多錯誤認識。如:《漢書·地理志》(下文簡稱《漢志》)以恒山、清河二郡為漢高帝置,而出土文物卻證實此二郡確為秦代設置;原來認為秦時巨鹿郡一直存在,現在卻發現秦后期巨鹿郡已經廢除,其地被析分為清河、河間二郡;原來認為秦河內郡全部在今河南境內,現在卻發現河內郡也有部分屬縣在今河北境內;原來秦恒山郡僅知有東垣、石邑、井陘、曲陽、曲逆、苦陘6縣,現在又增添新發現的奴盧(即盧奴)、安國、新處、南行唐、靈壽、九門、平臺7縣;等等。下面采用文獻資料與考古資料相結合的辦法,全面、系統地整理和總結有關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對目前已知的今河北省境內的所有秦代郡縣一一進行分析考證,將秦代郡縣數由《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二冊“秦代山東北部諸郡”圖[1](下簡稱《地圖集》)中所載11郡20縣提升為13郡60縣,以盡可能地填補歷史空白,更正以往的一些錯誤看法,以期恢復或接近歷史的真相。不當之處,請大家批評指正。
一、邯鄲、河內、上黨諸郡
1.邯鄲郡,《漢志》注云:“趙國,故秦邯鄲郡。”據《史記·秦始皇本紀》,秦滅趙在秦王政十九年(前228),邯鄲郡亦當置于此年。《史記·靳歙列傳》有靳歙“降邯鄲六縣”的記載,說明至秦末邯鄲郡仍然存在。秦封泥有“邯鄲造工”“邯造工丞”[2]256—257,可證此郡確為秦郡。《地圖集》中,邯鄲郡屬縣列有邯鄲、鄴縣、武安、信都、鄗縣5縣。根據新出土的考古材料推斷,其中鄴縣當屬河內郡,武安當屬上黨郡,信都當屬清河郡(詳見下文)。因此,目前所知秦邯鄲郡之屬縣共5縣,除《地圖集》所載邯鄲、鄗縣2縣外,還有近年來新發現的柏人、封斯、房子3縣,皆在今河北省境內。
邯鄲,治今邯鄲市區,郡縣同治。《史記·陳涉世家》記“武臣到邯鄲,自立為趙王”,《史記·張耳、陳馀列傳》有“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即此。秦封泥有“邯鄲之丞”[3]174;秦陶文有“邯亭”[4]397,當為邯鄲縣市亭之省文:皆可證邯鄲確為秦縣。
鄗縣,治今柏鄉縣東北固城店。《史記·趙世家》記趙武靈王三年(前323)“城鄗”,二十一年(前305)攻中山,“王軍取鄗”,即其地。秦封泥有“鄗丞之印”[5]121,可證鄗縣確為秦縣。此縣漢初屬趙國,秦時亦當屬邯鄲郡。
柏人,治今隆堯縣西。《漢志》記趙國(邯鄲郡)有柏人,秦時此縣亦當屬邯鄲郡。1984年河北臨城縣東柏暢古城遺址一兵器窯出土的秦兵器“柏人”戈,有銘文“柏人”[6],可證此縣確為秦縣。
封斯,治今趙縣西北。戰國趙國三孔布有“封氏”布[7]20,“封氏”即封斯。以此推斷,趙國已置封斯縣,秦時亦當沿置此縣。《漢志》以封斯屬常山,當為西漢后期之事。據周振鶴等考證,封斯屬秦邯鄲郡[8]73,可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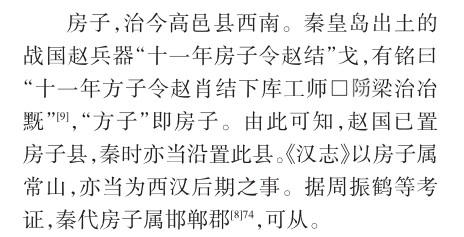
2.河內郡,始置于秦昭襄王時。據《史記·白起列傳》,秦昭襄王四十七年(前260),“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可見至遲此年河內已入秦為郡。此外,《史記·秦始皇本紀》記“十八年(前229),端和將河內,羌廆伐趙”,《史記·張耳、陳馀列傳》有“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另岳麓秦簡有“河內署九江郡”及“其女子當遷者,東郡、叁川、河內、穎川、清河”[10],皆證明河內確為秦郡。按照《地圖集》的標記,河內郡屬縣全部在今河南省境內,然而根據湖北張家山漢簡《秩律》的記載,河內郡屬縣在今河北省境內的有鄴縣、館陶2縣。
鄴縣,治今臨漳縣西南。《史記·趙世家》:趙悼襄王六年(前239),“魏與趙鄴”;九年(前236),“秦攻鄴,拔之”。可見戰國時鄴屬魏,已設置為縣,趙悼襄王九年(前236)起,鄴縣入秦。另外,《史記·靳歙列傳》也有靳歙“別下平陽”(《集解》注引徐廣曰“鄴有平陽城”)、“降鄴”的記載,可知至秦末鄴縣仍然存在。據周振鶴等考證,秦代鄴縣屬河內郡[8]70,可從。
館陶,治今縣館陶鎮。張家山漢簡《秩律》簡459有“館陰”[11]74,即館陶。目前,根據張家山漢簡《秩律》簡所反映的有關地名情況,學者多以館陶在漢初屬河內郡。同鄴縣一樣,館陶漢初屬河內,秦時亦當屬河內郡。在這里還應該附帶說明,根據張家山漢簡《秩律》簡所反映的有關地名情況,今地處臨漳、館陶之間的魏縣、大名、廣平一帶,秦時隸屬河內郡也是符合情理的。
3.上黨郡,《漢志》注云:“秦置。”然此郡原屬韓,后曾一度入趙。據《史記·秦本紀》,秦昭襄王四十八年(前259)“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韓上黨”;《史記·白起列傳》亦云:“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可知早在秦昭襄王四十八年(前259),上黨即入秦為郡。又據《史記·秦始皇本紀》,秦始皇于二十九年(前218)東巡之罘,“旋,遂之瑯邪,道上黨入”,可證秦統一后上黨郡仍然存在。在《地圖集》的郡縣標記中,今河北省境內只有涉縣西北部屬上黨郡,然根據張家山漢簡《秩律》簡的記載,秦上黨郡屬縣在今河北省境內的有武安、涉縣2縣。
武安,治今武安市西南。據《史記·秦本紀》,秦昭襄王四十八年(前259),“王龁將伐趙武安、皮牢,下之”。云夢秦簡《編年記》也有“(昭王)四十八年,攻武安”的記載。可見,早在秦昭王時武安即已入秦為縣。傳世秦兵器有“武安”戈(集成10928)[12]5816,6218,亦可證武安在秦時確已置縣。《漢志》以武安屬魏郡,而魏郡實系由上黨、河內、邯鄲三郡析置而來。張家山漢簡《秩律》簡454有“武安”[11]73。目前,根據《秩律》簡所反映的有關地名情況,學者多以武安在漢初屬上黨郡。由此上推,秦代武安亦當屬上黨郡。
涉縣,治今縣西北。《漢志》以涉縣屬魏郡,而魏郡實系由上黨、河內、邯鄲三郡析置而來。張家山漢簡《秩律》簡454有“涉縣”[11]73。目前,學者多以漢初涉縣屬上黨,由此上推,秦代涉縣亦當屬上黨。另據后曉榮考證,秦代涉縣屬上黨郡[13]333—334,可從。
另外,兩《漢志》涉縣均作“沙縣”,后世遂有“涉”“沙”之議。張家山漢簡《秩律》簡454作“涉”[11]73,可知秦漢原本作“涉”,并不作“沙”。今本兩《漢志》作“沙”,應是傳抄之誤。
二、恒山、清河、河間、濟北諸郡
1.恒山郡,系由邯鄲郡北部地所析置,置年不詳。《漢志》云“常山郡,高帝置”,此說恐非是。《史記·張耳、陳馀列傳》記“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陳馀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史記·樊噲傳》記樊噲“降定常山、清河凡二十七縣”,常山即恒山,可證秦時置有恒山郡。秦封泥有“恒山武庫”[14]、“恒山侯丞”[3]180—181,岳麓書院秦簡有“當戍清河、河間、恒山者”[10]等記載,可證此郡確為秦郡。恒山郡之屬縣,《地圖集》原有東垣、石邑、井陘、曲陽(應為上曲陽)、曲逆、苦陘6縣,目前新發現的有奴盧(即盧奴)、安國、新處、南行唐、靈壽、九門、平臺等7縣,共13縣,皆在今河北省境內。
東垣,治今石家莊市長安區東古城,郡縣同治。《史記·韓信、盧綰列傳》:漢高祖十一年(前196),“上自擊東垣”,“更命東垣為真定”,可證。
石邑,治今石家莊市鹿泉區東南。遼寧寬甸縣出土秦兵器“元年丞相斯”戈,有銘文“櫟陽左工去疾工上武庫石邑”[15],可證。
井陘,治今縣微水鎮西北。中國國家博物館藏有兩件傳世趙兵器“七年井陘令”劍,可知戰國趙國已置井陘縣。秦時亦應沿置此縣。
上曲陽,治今曲陽縣西。戰國時為中山曲陽邑,后入趙,因東有下曲陽,故加上。戰國趙三孔布有“上曲陽”布[16],知趙國已置上曲陽縣。《史記·灌嬰列傳》記灌嬰“從擊陳豨”,“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可證秦置此縣。
曲逆,治今順平縣東南。《史記》之《陳丞相世家》《灌嬰列傳》均有曲逆,可證此縣確為秦縣。
苦陘,治今定州市南邢邑。《史記·張耳、陳馀列傳》:陳馀“好儒術,數游趙苦陘”,可證。
盧奴,治今定州市。《史記·灌嬰列傳》有盧奴,可證。秦封泥有“奴盧之印”[2]233,又有“奴盧府印”“奴盧丞印”[3]167,“奴盧”即盧奴,亦證此縣確為秦縣。
安國,治今市東南東安國城。《史記·灌嬰列傳》有安國,可證。
新處,治今定州市東北。戰國趙三孔布有“親處”布[17],“親處”即新處,可知趙國已置新處縣。《漢志》中山國有新處,而中山國實系由常山郡析置而來。以此推斷,秦時當亦置此縣,屬恒山郡。
南行唐,治今行唐縣北。《史記·趙世家》:“惠文王八年(前291),城南行唐。”另外,傳世趙兵器有“南行陽令”劍,銘文曰:“王立更(事),南行陽命(令)翟卯左庫工(師)司馬合,治導執劑”[18];三晉圓足布也有大小兩種“南行陽”布[19]。“南行陽”即南行唐。可見趙國時已置南行唐縣。《漢志》中南行唐屬常山,由此推斷,秦時當亦置此縣,屬恒山郡。
靈壽,治今縣西北故城村。戰國時,靈壽曾為中山國都,后入趙,見于《史記》之《趙世家》《樂毅列傳》。山西高平出土的趙兵器有“十六年寧壽令”戈,銘文云:“十六年寧壽令余慶上庫工師卓工固執劑”[20],“寧壽”即靈壽。可知趙國時已置靈壽縣,秦時亦當沿置此縣。
九門,治今石家莊市藳城區西北。《史記·趙世家》有九門。據《中國歷代貨幣大系·先秦貨幣》(2477)趙三孔布“北九門”布[7]585,知戰國趙國已置九門縣。《漢志》常山郡有九門縣。以此推之,秦時亦當置此縣,屬恒山。
平臺,今址無考。據《中國歷代貨幣大系·先秦貨幣》(2479)趙三孔布“平臺”布[7]586,知戰國趙國已置平臺縣。《漢志》常山郡有平臺縣。以此推之,秦時亦當置此縣,屬恒山。
2.清河郡,系由巨鹿郡析置,置年不詳。《漢志》稱“清河郡,高帝置”,恐非是。《史記·樊噲列傳》云樊噲“降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此處清河、常山二郡并稱,卻不言及巨鹿,說明秦后期巨鹿郡已經不復存在。秦封泥有“清河太守”“清河水印”“恒山武庫”[14]及“恒山侯丞”[3]180—181、“河間太守”[2]251,岳麓書院秦簡有“當戍清河、河間、恒山者”“清河假守上信都言”[10]等記載,可證恒山、清河、河間三郡確為秦代所置,秦后期巨鹿郡已經被析分為清河、河間二郡。《地圖集》中,巨鹿郡南部有巨鹿、厝縣2縣。一般認為,厝縣治所當在今山東臨清市東北,并不在河北省境內。因此,秦清河郡屬縣在今河北境內的共8縣,除《地圖集》所載巨鹿1縣外,還有新發現的信都、南宮、觀津、東武城、宋子、楊氏、下曲陽等7縣。
信都,治今邢臺市市區。據《史記·張耳、陳馀列傳》云,張耳、陳馀“乃求得趙歇,立為趙王,居信都”,可證秦時置有信都縣。《地圖集》以信都屬邯鄲郡,然根據岳麓秦簡“清河假守上信都言”[10]的記載,可知信都縣亦當屬清河郡。
巨鹿,治今平鄉縣西南。曾為秦巨鹿郡治。秦封泥有“巨鹿之丞”[5]118,可證此縣確為秦縣。上條已論信都屬清河,巨鹿適在信都以東,亦當為清河郡屬縣。
南宮,治今南宮市西。傳世三晉古璽有“南宮將行”印[21]254,知趙國已置南宮縣。漢初亦有此縣,屬清河。由此推斷,秦時當亦置南宮縣,屬清河郡。
觀津,治今武邑縣東。據《史記·樂毅列傳》記樂毅降趙,“趙封樂毅于觀津”,《史記·外戚世家》記“竇太后,趙之清河觀津人”,可見秦時亦置此縣,屬清河。
東武城,治今故城縣南。《史記·平原君列傳》記趙勝“封于東武城”,可知東武城為趙地。易縣燕下都遺址出土的戰國趙兵器有“十四年武城令”戈(集成11377)[12]6133,6247。里耶秦簡16—12有“武成”,當為東武城。《漢志》清河郡有東武城,秦時此縣亦當屬清河郡。
宋子,治今趙縣東北。《史記·燕召公世家》記燕王喜四年(前251)“燕軍至宋子”,知宋子為趙地。1982年山西朔縣(今朔州市朔城區)出土的三孔布有“宋子布”[22],知趙國已置宋子縣。《史記·刺客列傳》云:秦并天下,“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宋子”,“宋子傳客之,聞于秦始皇”,可證秦時沿置此縣。漢初有宋子侯國,屬清河,秦時宋子亦當屬清河郡。
楊氏,治今寧晉縣鳳凰鎮。1979年秦始皇陵西側趙背戶村秦刑徒墓出土兩件瓦書陶文,分別有銘文“楊氏居大(教)”“楊氏居公士富”[23],知秦時已置楊氏縣。周振鶴等考證,秦代楊氏縣屬清河郡[8]74,可從。
下曲陽,治今晉州市西。《史記·灌嬰列傳》有上曲陽,故亦有下。戰國趙三孔布有“下曲陽”布[16],可證趙國已置下曲陽縣。秦時當沿此縣,屬清河郡。
3.河間郡,系由巨鹿郡析置,置年不詳。據《史記·高祖本紀》,項羽“封成安君陳馀河間三縣,居南皮”,可知秦時已置河間郡。據前文已證秦后期巨鹿郡廢除,其地被析分為清河、河間二郡。秦河間郡屬縣,除《地圖集》所載巨鹿郡北部的武垣、南皮2縣外,目前新發現還有樂成、安平、高陽、東平舒、章武、浮陽、中邑、饒陽8縣,共10縣,皆在今河北省境內。
樂成,治今獻縣東南河城街村。秦封泥有“樂成”“樂成丞印”[2]295,296,可知秦時當已置樂成縣。《漢志》河間國有樂成,秦代樂成亦應屬河間,為郡治。
武垣,治今肅寧縣東南武垣故城遺址。《史記·趙世家》云,趙孝成王七年(前259)“武垣令傅豹、王容、蘇射率燕眾反燕地”。傳世趙兵器有“三年武垣令”鈹,舊釋“武平”“武信”,董珊改釋為“武垣”[13]365。二者互證,可知戰國趙國已置武垣縣。秦時當沿置此縣,屬河間郡。
安平,治今縣安平鎮。《史記·灌嬰列傳》記嬰“從擊陳豨”,“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可證秦置此縣,屬河間。
饒陽,治今縣饒陽鎮南東北。據《史記·趙世家》,趙悼襄王六年(前239)“封長安君以饒”,《正義》曰:“即饒陽也。”以此推之,秦時當置饒陽縣,屬河間。
高陽,治今縣高陽鎮東舊城。秦封泥有“高陽丞印”[2]325,可證秦時已置高陽縣,屬河間。
東平舒,治今大城縣平舒鎮。《史記·趙世家》記趙孝成王十九年(前247),趙燕易土,“燕以葛、武陽、平舒與趙”,此平舒即東平舒,當為縣邑。以此推之,秦時當沿置東平舒縣。秦封泥有“新平舒丞”[14],此新平舒為代郡之平舒,可見東平舒置縣,要早于新平舒。
章武,治今黃驊市西北。黃驊市伏漪城遺址出土的陶罐上有秦陶文“武市”,“武市”當為章武縣市亭之省文[24],可證秦時置有章武縣,屬河間。
浮陽,治今滄州市東南。秦封泥有“浮陽丞印”[3]204,可證秦時置浮陽縣,屬河間郡。
中邑,治今滄州市東北。戰國趙方足布有“中邑布”[7]435,可證趙國已置中邑縣。另據《史記·惠景間侯者年表》,呂后四年(前184)曾置中邑侯國。以此推之,秦時當置中邑縣,屬河間。
南皮,治今縣南皮鎮東北。據《史記·高祖本紀》,項羽“封成安君陳馀河間三縣,居南皮”,可證秦時有南皮縣,屬河間郡。
4.濟北郡,系由臨淄郡北部地析置,其北界“緣黃河至今山東德州處東折,自今鹽山北、黃驊南至海”[8]36。《地圖集》“山東南部諸郡圖”所載濟北郡之北部,并不見有縣名著錄。目前,根據考古材料發現,濟北郡屬縣在今河北省境內的,當有高樂、千童、高成3縣。
高樂,治今南皮縣南皮鎮東南董村。秦封泥有“高櫟□□”[25],“高櫟”當為高樂。《漢志》勃海郡有高樂縣,秦時亦當置高樂縣,屬濟北郡。
千童,治今鹽山縣西南舊縣鎮。秦封泥有“千□丞印”[14],“千□”當為千童。《漢志》勃海郡有千童縣,秦時亦當置千童縣,屬濟北郡。
高成,治今鹽山縣鹽山鎮東南故城趙家村。里耶秦簡8-666、+8-2066有“高成”[26]197,知秦時置高成縣。《漢志》勃海郡有高成,秦時此縣當屬濟北郡。
三、代郡、上谷、廣陽、漁陽、右北平、遼西諸郡
1.代郡,《漢志》云:“秦置。”據《史記·秦始皇本紀》,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大興兵,使王翦將,攻燕遼東,得燕王喜。還,攻代,虜代王嘉”。可見代郡亦當置于此年。秦封泥有“代馬丞印”[2]259,可證代郡確為秦郡。代郡之屬縣在今河北省境內的,除《地圖集》所載代縣1縣外,還當有當城、廣昌2縣,共3縣。
代縣,治今蔚縣東北代王城。《史記·蒙恬列傳》:“胡亥聽而系蒙恬于代”,“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知秦時設有代郡代縣。秦陶文有“代市”[4]608,“代市”當為代縣市亭之省文,亦證代縣確為秦縣。
當城,治今蔚縣東北。《漢志》記代郡有當城縣。秦封泥有“當城丞印”[2]311,可證秦時已置當城縣,屬代郡。
廣昌,治今淶源縣淶源鎮北。《漢志》代郡有廣昌縣。據《史記·樊噲列傳》,樊噲“破得綦毋卬、尹潘軍于無終、廣昌”,可知秦時當置有廣昌縣。
2.上谷郡,《漢志》云:“秦置。”《史記·絳侯周勃世家》記周勃“定上谷十二縣”,秦封泥有“上谷府丞”[13],皆可證。上谷郡之屬縣在今河北省境內的,除《地圖集》所載沮陽縣1縣外,新發現的還有茹縣、且居2縣,共3縣。
沮陽,治今懷來縣東南大古城。《漢志》上谷郡有沮陽縣。《史記·絳侯周勃世家》云:周勃“復擊破綰軍沮陽”,可證秦時亦置此縣。
茹縣,治今張家口市下花園區。《漢志》上谷郡有茹縣。戰國趙平首尖足布有“奴邑布”[13]376,“奴邑”當為茹縣。此地原為燕邑,戰國末年入趙。《戰國策·秦策五》:“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六縣,與秦十一。”可見茹縣當為上谷三十六縣之一。以上引幣文推之,趙曾在此地置縣鑄幣。秦時亦當沿置此縣。
且居,治今懷來縣沙城鎮西北。《漢志》上谷郡有且居縣。傳世三晉古璽有趙“且居司寇”印[27]12,可證戰國趙國已置且居縣。秦時亦當沿置此縣。
3.廣陽郡,原為燕內史之地,秦破燕后置為郡。《水經注·漯水注》云:“秦始皇二十三年滅燕,以為廣陽郡”,不知何本。據《史記·秦始皇本紀》,秦始皇二十一年(前226),“乃益發卒詣王翦軍,遂破燕太子軍,取燕薊城”。由此可知,秦置廣陽郡亦當在此年。廣陽郡之屬縣在今河北省境內的,《地圖集》所載有涿、易2縣,另有新發現的容成、方城2縣,共4縣。
涿縣,治今涿州市。《漢志》涿縣屬涿郡,然西漢之涿郡,乃由秦廣陽郡析置。《史記·酈商列傳》云:酈商“食邑涿五千戶口,號曰涿侯”,可證秦時置有涿縣,屬廣陽。
易縣,治今雄縣雄州鎮西北。《史記》之《酈商列傳》和《絳侯周勃世家》分別有酈商、周勃破燕王臧荼軍于“易下”的記載,“易下”即指易縣。1981年容城縣晾馬臺鄉南陽遺址出土的秦代陶罐肩部有陶文“易市”,陶碗腹下部有戳印“易市”[28],“易市”當為易縣市亭之省文,亦證秦時置有易縣,屬廣陽。
容城,治今縣容城鎮西北城子村。戰國燕系璽印有“容城都□左”[29],燕國的“都”相當于縣,故“容城都”即容城縣,可證燕國后期置有此縣。秦時亦當沿置此縣,屬廣陽郡。
方城,治今固安縣固安鎮南方城村。戰國燕系璽印有“方城都司徒”[27]3,“方城都”即方城縣,可證燕國后期置有方城縣。《史記·趙世家》云:趙悼襄王二年(前243),“李牧將,攻燕,拔武遂、方城”,知方城入趙。秦時當沿置此縣。《漢志》廣陽國有方城,秦時此縣亦當屬廣陽郡。
4.漁陽郡,《漢志》云:“秦置。”《史記·陳涉世家》云:“二世元年(前209)七月,發閭左,適戍漁陽”,《史記·絳侯周勃世家》云:周勃平定“漁陽二十二縣”,皆可證漁陽確為秦郡。里耶秦簡8-26、+8-752有“魚陽”[26]35,“魚陽”即漁陽[30]。秦漁陽郡之屬縣,《地圖集》所載僅有漁陽1縣,在今北京市密云區西南。目前發現的漁陽郡屬縣,在今河北省境內的有白檀1縣。
白檀,治今灤平縣北。秦封泥有“白檀丞印”[5]123,可證白檀確為秦縣。《漢志》漁陽郡有白檀縣,秦時此縣亦屬漁陽郡。
5.右北平郡,《漢志》云:“秦置。”《史記·絳侯周勃世家》云周勃平定“右北平十六縣”,可證此郡確為秦郡。秦右北平郡之屬縣,《地圖集》所載僅有無終1縣,在今天津市薊州區。目前發現的右北平郡屬縣在今河北省境內的,有字縣、徐無、夕陽、昌城4縣。
字縣,治今平泉縣北。陜西西安相家巷出土的秦封泥有“字丞之印”[5]123,可證秦時置有字縣。《漢志》右北平郡有字縣,秦時此縣亦當屬右北平郡。
徐無,治今遵化市東。秦封泥有“徐無丞印”[3]231,可證秦時置有徐無縣。《漢志》右北平郡有徐無縣,秦時此縣亦當屬右北平郡。
夕陽,治今遵化市東南。秦封泥有“夕陽丞印”[2]309,可證秦時置有夕陽縣。《漢志》右北平郡有夕陽縣,秦時此縣亦當屬右北平郡。
昌城,治今唐山市豐南區西北。秦封泥有“昌城丞印”[2]310,可證秦時置有昌城縣。《漢志》右北平郡有昌城縣,秦時此縣亦當屬右北平郡。
6.遼西郡,《漢志》云:“秦置。”《史記·絳侯周勃世家》云周勃平定“遼西、遼東二十九縣”,可證此二郡確為秦郡。秦遼西郡之屬縣在今河北省境內的,《地圖集》所載有令支1縣,另有新發現的肥如1縣,共2縣。
令支,治今遷安市西。《史記·齊太公世家》載齊桓公言“北伐山戎、離枝、孤竹”,“離枝”即令支。《漢志》遼西郡有令支縣,秦時此縣亦當屬遼西郡。
肥如,治今盧龍縣北。里耶秦簡8-1619有“為肥如尉□”[30],可證肥如確為秦縣。《漢志》遼西郡有肥如縣,秦時此縣亦當屬遼西郡。
綜上所述,據《地圖集》所載,秦代今河北省境內的郡縣數目為11郡20縣:邯鄲郡,有邯鄲、鄴縣、武安、信都、鄗縣5縣;上黨郡(小部),未見置縣;巨鹿郡,有巨鹿、厝、武垣、南皮4縣;濟北郡(部分),未見置縣;恒山郡,有東垣、石邑、井陘、曲陽、曲逆、苦陘6縣;代郡,有代縣1縣;上谷,有沮陽1縣;廣陽郡(大部),有涿、易2縣;漁陽郡(大部),未見置縣;右北平郡(大部),未見置縣;遼西郡(部分),有令支1縣。經梳理考古資料,并與文獻相結合,將秦代今河北省境內郡縣數目增加為13郡60縣:邯鄲郡,有邯鄲、鄗縣、柏人、封斯、房子等5縣;河內郡,有鄴縣、館陶2縣;上黨郡有武安、涉縣2縣;恒山郡,有東垣、石邑、井陘、上曲陽、曲逆、苦陘、奴盧(即盧奴)、安國、新處、南行唐、靈壽、九門、平臺等13縣;清河郡,有巨鹿、信都、南宮、觀津、東武城、宋子、楊氏、下曲陽等8縣;河間郡,有安平、武垣、南皮、樂成、高陽、東平舒、章武、浮陽、中邑、饒陽等10縣;濟北郡,有高樂、千童、高成3縣;代郡,有代縣、當城、廣昌3縣;上谷郡,有沮陽、茹縣、且居3縣;廣陽郡,有涿、易、容成、方城4縣;漁陽郡,有白檀1縣;右北平郡,有字縣、徐無、夕陽、昌城4縣;遼西郡,有令支、肥如2縣。其中最顯著的變化就是去掉巨鹿一郡,增添清河、河間、河內三郡,多出40個縣。今后,隨著各類考古新材料的不斷涌現,可能還有更多的秦縣浮出水面。就地方史志工作而言,充分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將這些新發現的秦代郡縣信息寫入當地的政區沿革,彌補文獻的缺失,填補歷史的空白,更正一些錯誤看法,已經成為一項亟待解決的重要課題。
————————
[1]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二冊:秦、西漢、東漢時期[M].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9—10.
[2]周曉陸,路東之.秦封泥集[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
[3]傅嘉儀.秦封泥匯考[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
[4]高明.古陶文匯編[M].北京:中華書局,1990.
[5]周曉陸,陳曉捷,湯超,等.于京新見秦封泥中的地理內容[J].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4).
[6]劉龍啟,李振奇.河北臨城柏暢城發現戰國兵器[J].文物,1988(3).
[7]汪慶正.中國歷代貨幣大系:1:先秦貨幣[M].馬承源,審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8]周振鶴,李曉杰,張莉.中國行政區劃通史·秦漢卷:上冊[M].第二版.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
[9]鐘柏生,陳昭容,黃銘崇,等.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匯編[M].臺北:藝文印書館,2006:899.
[10]陳松長.岳麓書院藏秦簡中的郡名考略[J].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2).
[11]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12]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第七冊[M].北京:中華書局,2007.
[13]后曉榮.秦代政區地理[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14]陳曉捷,周曉陸.新見秦封泥五十例考略:為秦封泥發現十周年而作[C]//西安碑林博物館.碑林集刊:十一.西安:陜西人民美術出版社,2006:311—321.
[15]許玉林,王連春.遼寧寬甸縣發現秦石邑戈[J].考古與文物,1983(3).
[16]李零.戰國鳥書箴銘帶鉤考釋[C]//李零.李零自選集.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273—277.
[17]李家浩.戰國於疋布考[J].中國錢幣,1986(4).
[18]于省吾.商周金文錄遺[M].影印本.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599.
[19]裘錫圭.戰國貨幣考(十二篇)[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8(2).
[20]郭一峰,張廣善.高平縣出土“寧壽令戟”考[J].文物季刊,199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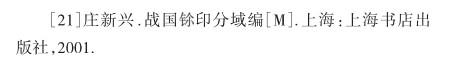
[22]平朔考古隊.山西朔縣秦漢墓發掘簡報[J].文物,1987(6).
[23]始皇陵秦俑坑考古發掘隊.秦始皇陵西側趙背戶村秦刑徒墓[J].文物,1982(3).
[24]俞偉超.秦漢的“亭”、“市”陶文[C]//俞偉超.先秦兩漢考古學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132—145.
[25]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長安城工作隊.西安相家巷遺址秦封泥的發掘[J].考古學報,2001(4).
[26]陳偉.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
[27]故宮博物院.古璽匯編[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28]孫繼安.河北容城縣南陽遺址調查[J].考古,1993(3).
[29]后曉榮,陳曉飛.考古出土文物所見燕國地名考[J].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6).
[30]晏昌貴.里耶秦簡牘所見郡縣名錄[C]//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歷史地理》編輯委員會.歷史地理:第三十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139—150.
〔責任編輯:成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