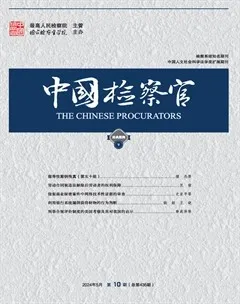網絡性侵兒童案件的定罪與被害人保護
黃輝 董雪
摘 要:辦理利用網絡性侵兒童犯罪案件,應當準確認定網絡猥褻與強奸犯罪之間的關系,對行為人“隔空猥褻”兒童后,又以傳播猥褻所獲得私密照片、視頻相要挾強迫被害人發生性關系的,線上猥褻行為與線下強奸行為應分別認定為猥褻兒童罪與強奸罪,數罪并罰。辦案中要及時審查涉案信息是否不當傳播,發現經網絡傳播的,應主動與公安機關等職能部門協作配合,快速查清網絡傳播路徑,阻斷傳播鏈條,避免對被害人造成二次傷害。在依法辦案的同時,檢察機關應立足職能,協同各方加強網絡空間侵害未成年人權益問題的綜合治理。
關鍵詞:網絡性侵 罪數認定 個人信息保護 網絡保護綜合治理
一、基本案情及辦案過程
2022年1月,隋某某(男,2002年12月6日出生)通過網絡社交軟件添加未成年被害人劉某某(女,2009年2月27日出生,學生)為好友,隨后多次向劉某某發送淫穢視頻,并威脅、誘導劉某某自拍裸照、裸體視頻發送其觀看。2022年2月8日、15日,隋某某以傳播劉某某裸照、裸體視頻相威脅,兩次強迫劉某某與其發生性關系。隋某某還以傳播照片、視頻相威脅,先后三次向劉某某索要錢財,共計得款人民幣840元。2022年3月5日,隋某某將編輯后的劉某某視頻以5元一件的價格出售給王某某等多人,其中7人為未成年學生,獲利人民幣50元。2022年3月11日,班主任發現劉某某表現異常后報警。山東省某市公安局某區分局于當日將隋某某抓獲。
2022年4月11日,公安機關以隋某某涉嫌強奸罪,敲詐勒索罪,制作、販賣、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向山東省某市某區人民檢察院提請批準逮捕。公安機關認為,利用網絡實施猥褻是被告人實現強奸犯罪的手段,應按強奸一罪處理。檢察機關審查認為, 隋某某的線上猥褻是獨立的犯罪行為,不宜評價為強奸犯罪的手段,應當認定為猥褻兒童罪。檢察機關在依法批準逮捕隋某某的同時,與公安機關及時溝通,明確補充偵查方向,督促進一步查清隋某某實施猥褻兒童犯罪的事實。
2022年6月17日,公安機關以隋某某涉嫌猥褻兒童罪,強奸罪,敲詐勒索罪,制作、販賣、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2022年7月15日,檢察機關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訴。2022年8月11日,人民法院作出判決,對隋某某以猥褻兒童罪判處有期徒刑1年6個月;以強奸罪判處有期徒刑8年6個月;以敲詐勒索罪判處有期徒刑6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2000元;以制作、販賣、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判處有期徒刑9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1000元。數罪并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10年,并處罰金人民幣3000元。
二、網絡性侵兒童案件的辦理思路
近年來,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持續多發,強奸、猥褻兒童等性侵犯罪已經成為侵害未成年人最突出的犯罪,犯罪分子利用互聯網的虛擬性、便捷性,通過誘騙、脅迫未成年人發送“裸照”等方式進行“隔空猥褻”,并且出現線上猥褻犯罪與線下強奸犯罪相互交織的情形。檢例第43號“駱某猥褻兒童案”明確了無身體接觸猥褻行為的追訴原則[1],但在辦理利用網絡實施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過程中,仍存在犯罪行為的罪數認定、未成年被害人個人信息保護等難點。
(一)罪數認定難點與分析
被告人隋某某在威脅、誘導被害人自拍裸照、裸體視頻發送其觀看后,又以傳播被害人裸照、裸體視頻相要挾,兩次強迫劉某某與其發生性關系。從形式上看,被告人利用網絡猥褻獲取的被害人私密照片、視頻威脅被害人,才得以實施強奸犯罪,網絡猥褻行為是被告人實現強奸犯罪的手段,猥褻行為與強奸行為之間存在手段與目的的牽連關系。但筆者認為,不應僅因被告人在實施強奸犯罪時利用了網絡猥褻所獲取的照片、視頻,就簡單認定被告人的線上猥褻與線下強奸行為之間存在手段與目的的牽連關系,應從被告人的主觀意圖、客觀行為的密切關聯性以及對法益的侵害等方面進行深入分析。
首先,主觀方面,被告人的線上猥褻犯罪與線下強奸犯罪是在不同犯意支配下的獨立行為,主觀上不具有牽連意圖。通常認為構成牽連關系的,行為人實施的數個犯罪行為在主觀上應具有牽連意圖。所謂牽連意圖,是指行為人對實現一個犯罪目的的數個犯罪行為之間,所具有的手段和目的,或者原因和結果關系的認識。[2]本案中,被告人隋某某最初系以刺激、滿足性欲為目的,要求被害人拍攝裸照、裸體視頻發送其觀看,在收到被害人照片、視頻后,認為被害人易哄騙、好控制,繼而又產生與被害人發生性關系的想法。被告人的強奸犯意是在猥褻行為實施完畢之后才產生,其在第一次實施強奸犯罪時帶有一定的試探性而并非早有預謀。被告人主觀犯意的變化,除了被告人的供述外,從案發當天被告人在確認被害人離開家前來見面后才預定賓館,并在等待被害人的過程中臨時提出讓被害人購買避孕藥具等客觀行為表現也能予以印證。綜上,隋某某主觀上對前后行為并不具備手段與目的的認識,系不同犯意支配下的獨立行為,主觀上不具備牽連意圖。
其次,客觀方面,“隔空猥褻”行為與強奸行為之間既不具備類型化特征,又非密切關聯,是兩個相對獨立的行為。牽連犯事實上存在兩個行為,原本成立數罪應當并罰,只有當手段行為與目的行為、結果行為與原因行為之間具有密切關聯性,行為人實施該目的行為時通常會使用該手段行為,實施該原因行為時通常會實施該結果行為,才宜認定為牽連犯。[3]顯然“隔空猥褻”行為并非實施強奸犯罪的通常手段,實施“隔空猥褻”后也并非通常繼續實施強奸犯罪行為,兩者之間不具備類型化特征。同時,被告人隋某某的線上猥褻行為與線下強奸行為之間也非密切關聯,猥褻行為與強奸行為前后相隔9天,具有明顯的時間間隔,行為發生的空間也相互獨立,兩犯罪行為之間不具有密切關聯性,客觀上也不具備牽連關系。
最后,從對法益的侵害分析,猥褻行為和強奸行為給被害人造成兩次不同性質和程度的傷害,不應作為一次侵害進行評價。猥褻與強奸均是嚴重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犯罪,檢例第43號“駱某猥褻兒童案”,也已明確行為人以滿足性刺激為目的,以引誘、強迫或者其他方法要求兒童拍攝裸體、敏感部位照片、視頻等供其觀看,構成猥褻兒童罪。[4]行為人在利用被害人的照片或視頻威脅被害人發生性關系時,網絡猥褻行為已經既遂,對被害人人格尊嚴、身心健康的傷害已經造成,不應忽視猥褻行為給被害人所造成的損害。如果僅因后續行為人產生強奸的意圖或者實施了強奸行為,便將猥褻行為認定為強奸犯罪的手段,以一罪論處,將使被告人的猥褻行為得不到有效打擊,也將導致案件罪責刑不相適應。
綜上所述,行為人實施線上猥褻犯罪行為后,又利用線上猥褻獲得的私密照片、視頻要挾被害人,實施線下強奸犯罪行為的,是兩個獨立的犯罪行為,應分別認定為猥褻兒童罪與強奸罪,數罪并罰,依法從嚴懲處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二)及時阻斷兒童私密信息傳播
網絡傳播速度快、覆蓋面廣,兒童涉案信息尤其是私密信息的傳播將會給被害人造成更為嚴重的身心傷害。本案中,被告人將被害人私密視頻通過朋友圈售賣,導致視頻在被害人所在學校多名學生間傳播,為盡可能將犯罪行為對被害人的傷害降到最低,檢察機關主動與公安機關等職能部門協作配合,快速查清照片、視頻傳播路徑,及時督促相關部門刪除不雅照片和視頻,并通過“線上+線下”的方式有效阻斷傳播鏈條,避免對被害人的二次傷害。
一方面針對可能擴大的線上傳播,督促公安機關查清相關裸照、裸體視頻的存儲位置、傳播路徑,在固定證據后進行技術刪除。公安機關通過審訊和技術審查查明,被告人除將獲取的被害人私密照片、視頻保存在手機外,還上傳至社交賬號、云盤等處,同時利用微信將視頻、照片轉發給王某某等10人,后王某某等又將視頻轉發給其他人。查清相關視頻的存儲及轉發情況后,檢察機關及時督促相關職能部門對被告人及相關人員保存的視頻、照片進行技術性刪除,并對被告人的涉案社交帳號進行封禁,同時對涉案詞匯、信息進行利用技術手段進行多輪監測,定期巡檢,有效阻斷了被害人照片及視頻的線上傳播。
另一方面針對已發生的線下傳播,聯合公安機關、涉案學校對購買和觀看視頻的學生開展分級干預工作,阻斷線下傳播。對協助被告人販賣淫穢視頻和購買相關視頻的學生,依據《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采取矯治教育措施,向其父母制發“督促監護令”,督促父母依法履行監護職責,重點監督孩子是否對涉案照片、視頻進行再次傳播;對其他觀看視頻學生,督促學校開展批評教育并持續關注學生之間QQ群、微信群等社交軟件的使用情況,及時發現可能出現的再次討論或傳播問題,對苗頭性傾向及時制止;對全體在校學生及家長,建議學校召開主題班會、家長會,倡導綠色文明使用網絡,引導家長關注未成年人網絡使用情況。
(三)積極促推未成年人網絡保護綜合治理
針對案件反映出的未成年人網絡交友不當、防范網絡侵害能力不足等問題,檢察機關開展專題調研分析后,向涉案學校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門制發檢察建議,督促學校建立預防、處置網絡侵害工作機制,落實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制度,采取科學、合理方式培養和提高未成年人網絡素養,有效減少侵害發生。針對未成年人遭受網絡侵害時不敢說不、不善求助等問題研發網絡安全教育主題課程,組織開展“清朗網絡進校園”活動,通過專題授課、短視頻、網絡安全知識問答等多種方式揭露犯罪分子常用伎倆,揭示網絡交友中的風險和陷阱,講授應對網絡性侵的正確處理方式,引導學生理性交友,保護自我,及時求助,提升未成年人文明、安全用網的意識和能力。通過網絡家長課堂方式,指導家長加強對未成年人性啟蒙的引導,增加對未成年人的陪伴與關愛,關注未成年人的成長動態,保護未成年人不受侵害。就未成年人網絡保護問題,邀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及未成年人保護相關職能部門進行座談,推動相關職能部門加強涉未成年人網絡侵害線索移送。
三、辦理網絡性侵兒童案件的注意要點
近年來,未成年人觸網年齡日趨低齡化,犯罪分子利用網絡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手段復雜多樣,新類型、新手段不斷出現,厘清法律關系,準確認定犯罪是依法懲治網絡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前提和基礎。辦理未成年人涉網案件要關注未成年人在網絡空間的合法權益,從線下到線上,全方位維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發現涉案信息不當傳播的,應當及時阻斷傳播鏈條,避免被害人受到次生傷害。對案件背后折射出的網絡空間監管整治難題,要立足法律監督職能,協同各方共同發力,提升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水平。
(一)準確定性是依法懲治網絡性侵兒童犯罪的基礎
近年來,利用網絡社交軟件添加兒童,通過誘騙或者威脅手段索要兒童私密照片、視頻,再以此相要挾實施強奸等犯罪行為的案件較為頻發。強奸、猥褻等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嚴重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已經成為侵害未成年人最突出的犯罪,司法機關始終堅持“零容忍”的態度,依法嚴厲打擊利用網絡侵害未成年人權益犯罪。依法嚴懲罪行的前提是準確認定犯罪事實,精準適用法律,讓罪責刑相適應。檢例第43號“駱某猥褻兒童案”明確了無身體接觸猥褻行為的追訴原則,“隔空猥褻”行為可構成猥褻兒童罪已經達成共識,但對“隔空猥褻”兒童后又以此相威脅實施強奸犯罪的,定強奸一罪還是以猥褻兒童罪與強奸罪數罪并罰,司法實踐中有不同認識,法律適用不一。對罪數的認定不僅關系到罪責刑的適應,還關系到社會公眾對公平正義的樸素認識。在辦理本案過程中,辦案人員從主觀意圖、客觀行為的密切關聯性、侵害的法益等方面深入分析,認為線上猥褻符合猥褻罪犯罪構成,并非線下強奸手段的,應當單獨評價為猥褻犯罪,與強奸罪數罪并罰。對該類案件準確認定為兩罪,數罪并罰,更加有利于保護幼女身心權益,遏制該類犯罪上升態勢。
(二)檢察機關應重視被害人個人信息保護工作
網絡性侵案件中,被告人往往掌握被害人的私密照片、視頻,這些涉案私密信息一旦通過網絡傳播,將會給被害人造成更為嚴重的身心傷害,不利于被害人的創傷修復,甚至會引發自殘自殺事件。司法機關在辦理網絡侵害未成年人案件時,要及盡早審查未成年人信息是否不當傳播,發現有不當傳播風險或行為的,應當及時督促職能部門快速、精準阻斷傳播,第一時間切斷傳播鏈條,將私密信息技術性永久刪除,從線下到線上全方位保護未成年人免受次生傷害。
(三)要協同各方開展網絡空間訴源治理
兒童遭受網絡侵害案件頻發不是一家之責,有網絡監管不力的責任,有社會保護不足的緣由,也有家庭監護缺失的原因,還有個人自護意識不強的因素。檢察機關辦理網絡侵害兒童案件時,要深入分析案件背后反映出的未成年人網絡保護領域普遍性、系統性、源頭性問題,綜合運用四大檢察職能和措施,以檢察之力督促各方協同發力,比如針對職能部門履職不充分的問題,通過行政公益訴訟、制發社會治理類檢察建議、召開部門聯席會議等方式,督促職能部門依法積極履職,開展網絡空間風險防范和治理;針對性開展家庭教育指導,提升監護人的監護能力和網絡安全監護技能;聯合學校,精準開展法治教育,提升未成年人網絡風險認知和自護能力。通過案件辦理促使家庭、學校、社會聯動發力,助力網絡空間的訴源治理、綜合治理、深度治理,為未成年人健康成長構建網絡保護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