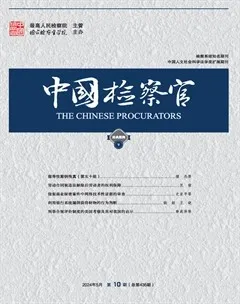騙取型貪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的再理解
鄧駿偉 趙天文
摘 要:騙取型貪污行為應當符合騙取行為本質特征,即行為人事先未占有、控制、支配公共財物。現行司法解釋對貪污罪中“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的界定過窄,與法律規定、司法實踐和騙取行為特征不協調。結合騙取手段轉移公共財物的間接性和貪污行為所侵害的職務廉潔性,騙取型貪污中的職務便利是指行為人的職權或履職事項對公共財物處分權人具有影響力,這種影響力可以是縱向的、基于行政關系的領導力,也可以是橫向的、基于工作流程的控制力。
關鍵詞:貪污罪 騙取手段 職務便利
《刑法》第382條第1款明確將“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作為貪污罪的構成要件要素。通說認為,貪污罪侵犯的法益是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的廉潔性以及公共財產權。[1]而職務便利正是體現職務行為廉潔性的行為要素,因此在適用貪污罪評價犯罪行為時,需要關注對職務便利的解釋。筆者在審查起訴案件中發現,貪污犯罪事實愈發復雜,犯罪行為愈發隱蔽,呈現出從單獨犯罪向共同犯罪發展的趨勢,犯罪手段從單一行為侵吞、竊取型向復合行為騙取型演化,犯罪流程從單一節點實施向多階段貫穿演變。最高檢1999年9月16日公布施行的《關于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立案偵查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試行)》(以下簡稱《立案標準》)中明確了貪污罪中“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概念內涵,但在騙取型貪污中,該概念界定存在范圍過窄的問題,尤其是難以應對相互銜接的工作流程中國家工作人員共謀騙取公款類的案件。
一、相互銜接工作流程中共謀騙取公款“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認定存在的問題
[基本案情]某軍隊單位財務部門負責人甲,人力資源部門負責檔案工作的乙、負責兵員工作的丙,工薪助理員丁等四人共謀通過篡改復員軍士入伍前戶口性質套取復員費。[2]乙偽造數名復員軍士檔案材料,將其中戶口性質由城鎮篡改為農業;丙根據篡改后的檔案材料,制作虛假的復員費結算通知書;甲安排丁根據前述結算通知書編制虛假經費結算單、復員軍士退役經費匯總表等材料,其中虛增復員費數十萬余元。丁將錢款冒領套現,后由四人分贓。[3]
在上述改編案例中,復員軍士入伍前戶籍性質認定和復員費計發為前后銜接的工作流程,即后者需以前者為依據。然而根據崗位職責,乙、丙均不具有主管、管理、經手復員費的權力或方便條件,只有甲、丁對復員費具有主管、管理職權。如果嚴格按照《立案標準》對職務便利的界定,則案件事實應當歸納為:乙和丙分別利用檔案業務經辦人、兵員業務經辦人的崗位便利[4],在復員費結算工作期間時將數名復員軍士戶口性質由城鎮改為農業,并通過甲、丁作為財務部門負責人、工薪助理員的職務便利,騙取復員費,即認為本案中利用職務便利的行為僅是甲安排丁在制作復員費銀行代發材料時虛增復員費。然而,這種事實歸納方式無法從本質上區分騙取型貪污罪和詐騙罪。假設本案沒有甲、丁的參與,或言甲、丁在正常履職過程中,根據乙、丙提供的篡改材料,錯誤地多發了復員費,按照上述歸納方式,乙、丙篡改戶口性質的行為并未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即使騙取單位公款也只能評價為詐騙。那么,僅僅是有無財務人員參與的區別,罪名認定就不相同,難免帶來參與犯罪的職能環節越多、犯罪的隱蔽性越強,反而罪責更輕的直觀法感。因此,筆者嘗試對騙取型貪污罪中職務便利解釋作輕緩擴張,將國家工作人員履職事項在工作流程上的影響力也評價為職務便利。
二、貪污罪中“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的適用困境
雖然《立案標準》明確了貪污罪中“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定義,但這種定義與騙取行為特征、刑法貪污罪的立法精神不相適應,司法實踐中對騙取型貪污中職務便利的理解認定也并非與《立案標準》規定完全一致。
(一)司法解釋對貪污罪中“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內涵的界定
《立案標準》明確,貪污罪中“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職務上主管、管理、經手公共財物的權力及方便條件。最高法2012年9月18日發布的第11號指導性案例——“楊延虎等貪污案”裁判要點對貪污罪中“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也做出相同解釋,并進一步明確這種職務便利既包括本人職務上的便利,也包括職務上有隸屬關系的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便利。因此,并非國家工作人員的任何職權或方便條件都構成貪污罪中的職務便利,而要求這種職務便利應當直接關聯公共財物,或者垂直指向公共財物,這是由貪污罪的經濟性和職務性復合特點決定的,與主管、管理、經手公共財物無關的職權、職務便利,不能構成貪污罪中的職務便利。
對于“主管”“管理”“經手”,有關機關在辦案實踐中進一步歸納,認為“主管”一般是指行為人不具體管理、經手公共財物,也不控制、占有公共財物,人財相對分離,但具有公共財物的處置決定權,主管人包括部門負責人、上級對口領導、本單位領導,也包括領導層中由于工作協作分工而對公共財物職能部門協管的非主管領導;“管理”是指行為人具有日常管控、監督、監守、保管公共財物的職權,管理人可能控制、占有公共財物,也可能不控制、占有公共財物但對公共財物具有調度或安排等支配職權;“經手”是指因執行公務而具有的領取或者支出公共財物的職權,具體實施公共財物的日常運轉和使用,經手人通常控制、占有公共財物。[5]
(二)上述內涵界定與法律規定的不協調
《刑法》第183條第2款規定,國有保險公司工作人員和國有保險公司委派到非國有保險公司從事公務的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故意編造未曾發生的保險事故進行虛假理賠,騙取保險金歸自己所有的,依照貪污罪的規定定罪處罰。國有保險公司委派到非國有保險公司從事公務的人員并非天然具有主管、管理、經手公共財物的權力或方便條件,其職務行為即編造保險事故的行為只是最終處分權人錯誤行使處分權的原因。對于該款規定是注意規定還是法律擬制,存在不同理解,如果理解為注意規定,則貪污罪的騙取手段不要求行為人具有對公共財物的垂直管控地位,即使行為人沒有對公共財物的最終處分權,但其基于職務處理的有關公共財物的事項使其具有實質上公共財物處分人的地位;如果理解為法律擬制,則幾乎只有該款規定的情形可能成立騙取型貪污。[6]前一種理解突破了《立案標準》界定的“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后一種理解則使《刑法》第382條第1款關于騙取型貪污的規定幾乎成為具文。
(三)上述內涵界定與司法實踐的不協調
當前司法實踐對貪污罪中的職務便利以及騙取手段理解、認定不一,部分判決對職務便利的理解并不完全符合《立案標準》規定。如在孫威力貪污案[7]中,孫威力作為民政助理的工作職責是審核上報優撫對象信息,并不具有主管、管理或經手公共財物的權或方便條件,其職責并不會直接導致公共財產所有權力或占有的轉移,孫威力并非單位領導或財務業務鏈條上的領導、負責人,也不存在利用職務上有隸屬關系的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便利的空間,故孫威力并不具有主管、管理、經手公共財物的權力或方便條件,其工作職責和取財結果之間只是橫向的工作流程先后關系。
(四)上述內涵界定與騙取行為特征的不協調
如不考慮量刑上的不均衡,大體可以認為,騙取型貪污罪是詐騙罪的特別法條,前者在行為對象、行為主體方面需要具備特別要素。[8]那么,騙取型貪污應當符合普通詐騙的一般行為特征,在這個意義上,騙取和詐騙二詞文義上并無明顯區分。詐騙的行為特征是財產處分權人因為行為人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產生錯誤認識,基于錯誤認識處分財產,因而導致占有轉移,即在騙取行為中,行為人事先并不占有、控制、支配被騙取的財物。在國家工作人員對公共財物具有管理、經手權力或方便條件的情況下,如果其已經占有、控制、支配[9]了公共財物,則根本沒有成立騙取的空間。對自己單獨或與他人共同占有、控制、支配的公共財物,即使在據為己有的過程中存在欺騙的方式、手段,對行為整體仍只能評價為侵占或竊取。如軍隊財務部門的出納人員,偽造其保管的現金保險柜被砸、現金被盜取的假象,實際將柜內現金據為己有的,雖形式上有欺騙行為,但這個過程中沒有產生任何公共財物占有轉移,所以仍屬于侵吞型貪污罪,其偽造現場的行為,目的在于掩飾其侵吞行為。
《立案標準》中的“管理”“經手”,指向的是行為人已經全部或部分占有、控制、支配公共財物的情況。從這個意義上講,《立案標準》對“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的理解與騙取行為特征具有天然的矛盾。究其原因,在于貪污罪中的“侵吞”“竊取”“騙取”以及“其他手段”本身具有形式和實質上的差異,對應的職務便利范圍也有所不同,而這正是《立案標準》沒有區分的,這種不加區分的后果,就是不當限縮貪污罪尤其是騙取型貪污罪的范圍。[10]
三、對騙取型貪污中“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的再理解
《立案標準》屬于現行有效的司法解釋,在承認其對司法實踐具有法定適用效力的同時,也有必要關注貪污罪中職務便利的共性和騙取型貪污罪中職務便利的特殊性。筆者認為,結合騙取行為本質特征,對騙取型貪污中“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應當理解、解釋為利用職權范圍或具體履職行為對公共財產處分權人形成影響,即除縱向利用職務上有隸屬關系的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便利外,還應涵蓋橫向利用工作流程下游的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便利,當然,后一種情況還要求該工作流程以處分公共財物為目的。
(一)騙取型貪污侵犯公共財產權的間接性
如前所述,騙取型貪污罪中的公共財產權是以間接轉移的方式被侵犯的,而侵吞、竊取型貪污罪中的公共財產權是以直接轉移的方式被侵犯的,這是騙取型貪污罪與侵吞、竊取型貪污罪在手段層面的本質區別,這種間接性體現在行為人本身并不占有、控制、支配公共財物。換言之,較之于侵吞、竊取型貪污,騙取型貪污在職務行為和取財結果之間,多了一層介入因素,即處分權人的處分行為。
本文案例中,乙、丙本不具有公共財物處分權限,而是通過甲、丁公共財物處分權人虛增數額的處分行為,實現取財目的,這正是騙取型貪污侵財間接性的現實體現。
(二)騙取型貪污中職務行為的指向性
根據《立案標準》,職務便利應當直接關聯公共財物(管理、經手),或者垂直指向公共財物(主管)。前文已經論述,管理、經手公共財物的國家工作人員難以成立騙取型貪污罪,因此在《立案標準》列明的范圍內,能夠成立騙取型貪污罪的通常是主管公共財物的國家工作人員,即騙取型貪污罪中職務行為垂直指向公共財物處分行為。然而,還應當注意到,涉及最終處分公共財物的工作流程中,除了縱向審批流程之外,還有橫向的跨部門傳遞、銜接流程,正如本文案例中,財務部門結算、發放復員費用,需以人力資源部門對軍(工)齡、級別、崗位等的認定為依據。在橫向流程中,當在前認定環節作為在后處分行為依據時,前者即具有了對后者的實質影響力。換言之,當在前環節工作人員基于職務做出涉及處分公共財物的認定時,其職務行為就產生對公共財物處分的實質影響力。
(三)騙取型貪污中被侵犯的職務廉潔性法益
職務廉潔性法益是區分騙取型貪污罪和詐騙罪的關鍵,也是騙取型貪污罪相較于詐騙罪多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構成要件要素的根本原因。騙取型貪污中的職務行為與取財結果之間介入了公共財物處分權人的處分行為,即騙取型貪污罪中的職務行為并不直接作用于公共財物之上,而只能作用于處分權人之上,這種作用就是騙取型貪污行為人的職務行為對公共財產處分權人的影響力。如果行為人沒有利用職務行為影響處分權人,或者利用了職務行為但是沒有影響到處分權人,即使獲得了處分權人所管控的公共財物,這個過程中職務行為就沒有發揮作用,不能評價為職務廉潔性受到侵犯。
同時,這種影響力既應當包括縱向的領導力,也應當包括橫向的流程控制力。因為國家工作人員一旦利用職務行為影響公共財物處分權人做出錯誤處分,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廉潔性即遭破壞,而這種破壞與影響力的方向是無關的。
本文案例中,甲作為財務部門負責人,對該部門具有實質上的領導職權,故同屬該部門的丁與甲具有實質上的職務隸屬關系,而且甲正是利用了作為財務部門負責人的職務便利,向丁交代、安排虛增、取現事宜,才使得套取復員費的流程得以實現;乙、丙同屬于人力資源部門工作人員,在部隊復轉退工作中,戶口性質是費用結算的重要依據,且戶口信息由人力資源部門認定后傳遞至財務部門,財務部門以此為據直接套用計發標準而不再實質審查戶口信息真實性,此時應當認為,在與戶口性質相關的復員費用計發項目中,檔案業務、兵員業務人員對相關款項具有橫向工作流程上的實質上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力能夠作用于工作流程下游具有公共財物處分權人。甲、乙、丙、丁利用各自職權篡改復員軍士戶口性質、虛增計發費用,從而謀取不法利益的行為當然侵犯了國家工作人員職務廉潔性。
(四)對騙取型貪污罪中職務便利解釋的輕緩擴張
綜合騙取型貪污罪本身包含的騙取方式和利用職務貪利特性[11],騙取型貪污罪應當具有“行為人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行為人利用職務行為——對自己以外的公共財物處分權人產生影響——處分權人陷入錯誤認識——處分權人因錯誤認識處分公共財物——行為人因此取得公共財產”的典型構造,同時,只要行為人的職權范圍或者具體履職事項在地位或流程上足以影響處分權人做出處分決定,即可認為職務便利產生了影響力。相較于《立案標準》,該種解釋的輕緩擴張在于將履職事項在工作流程上的影響力也評價為職務便利。
貪污罪保護的是職務廉潔性和公共財產權雙重法益。騙取型貪污罪中的職務廉潔性法益對應的就是“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構成要件要素,公共財產權法益對應的就是利用“騙取”手段構成要件要素。那么,對騙取型貪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解釋就應以保護職務廉潔性目的為指導。國家工作人員履行職務行為的目的在于維護公共利益[12],意即具有職務行為外觀,但背離公共利益,同時對公共財物處分權人產生影響的行為,即可認定為騙取型貪污罪中利用職務便利的行為。不可否認的是,對于可能存在職務外觀的行為,其同時具有公共利益目的和個人目的的,如“搭車”虛增申報金額,此時僅需將其中虛增部分對應的行為評價為利用職務便利行為。
本文案例中,犯罪行為流程是“篡改檔案戶口性質——篡改結算通知戶口性質——虛增復員費”,篡改信息經過層層傳遞,最終由不知情的出納人員開具了含有虛增數額的代發復員費轉賬支票。這個過程中出納作為對復員費具有處分權限的人,被丁直接欺騙,受此影響產生錯誤認識,處分了單位公款,而丁對出納的欺騙也正是基于之前乙、丙的篡改行為得以實現的,即乙、丙實施了虛構復員軍士戶口性質的行為,丁實施了虛增復員費的行為,且上述行為均足以影響出納處分公共財產的決定,與出納陷入錯誤認識和處分公共財物具有因果關系,故從整個行為流程看,既符合騙取行為的構造,又體現了職務便利影響。當然,丁作為工薪助理員,單純從其工作職責看,本身對公共財產具有管理職權,按照前文論述,如果獨立評價其虛增復員費數額的手段,應當屬于侵吞或竊取,但丁的行為是全案犯罪流程的組成部分,因此將全案行為手段整體評價為騙取也是合適的。
(五)該種擴張解釋的法理依據
上述認定騙取型貪污中“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的路徑,雖與《立案標準》中的界定存在出入,但并未違背《立案標準》的原則立場,回歸騙取行為、職務便利的本質特征,既可彌補《立案標準》中對“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界定過窄的不足,同時由于指明了職務便利的作用對象、影響力方向,也能避免不當擴大騙取型貪污罪的成立范圍。此外,上述認定路徑只是針對《立案標準》中職務行為與公共財產的直接關系的突破,這種突破事實上是一種法教義學上的修正,筆者仍然認為騙取型貪污罪中的職務便利須與公共財物至少具有間接關系,并未切斷職務便利與公共財物的關聯性,也不違背貪污罪的經濟性和職務性復合特點,而且在法益保護、行為特征方面,仍然與貪污罪條文本身表述是融洽的,契合《刑法》第183條第2款規定的立法精神。
至此,筆者認為,在騙取型貪污中,只要行為人的履職事項能夠對公共財物處分權人形成影響力,并且行為人實際利用了這種影響力,即可認定行為人利用了職務上的便利。本文案例案件事實的歸納可以表述為:甲、乙、丙、丁等四人共謀套取軍士復員費,分別利用甲作為財務部門負責人、乙作為檔案業務經辦人、丙作為兵員業務經辦人、丁作為工薪業務經辦人的職務便利,在結算復員費時將數名復員軍士戶口性質由城鎮篡改為農業,騙取復員費數十萬余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