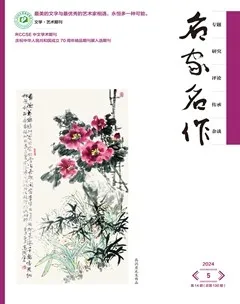肖像·詩意·紀念碑
[摘 要] 在當代影像藝術中,建筑對空間、時間、觀念的延伸,以及對語言表達與形式的再現,可以體現出特定的意向化美學特征。尤其是在一些前衛藝術展覽中,影像藝術不再是反映實體存在的視覺媒介,而是在融合原有主體性質之后,形成“虛化”的意象形態。影像藝術中的建筑意象以“言以盡意”的肖像化內涵,表達出建筑“情景”文化空間中的詩意性和紀念碑性,總體上滲透著情與理的寓合,在“意”與“跡”的交融中形成了對建筑存在語境中的異質性觀念、特殊再現模式等意象表達相關的現代解釋。
[關 鍵 詞] 影像藝術;視覺表現;東方美學;建筑意向
自1932年林徽因在《平郊建筑雜錄》一書中提出“建筑意”的思想后,建筑美學原有的文化語境便得到了重塑和修正,其話語體系逐漸被提升到與詩書畫同樣的高度。以“意”為主導的新的建筑精神價值應運而生,“意”是文化意象的體現,既包含“天然材料”與“地理之和”,又具有美學法式與民族風情。建筑藝術作為區域空間內生活的圖像化映射,本身融入了以“形”“意”“境”為基本價值體系的內在語境。這種語境直觀地體現為建筑藝術的感性表達,與人的主觀意識的互滲性、間接性的內在意蘊相聯系,是面對神秘的、綜合性的、不可企及的抽象對象時所表現出的藝術意志。
一、空間的延展:塑造“肖像模式”化的建筑情景
(一)塑造綜合性的瞬間與景觀視角
法國哲學家讓·鮑德里亞曾經說過:“原始社會有面具,資產階級有鏡子,而我們有影像。”[1]建筑影像是建筑作為既定空間的理性敘事形式,是創作主體意識信息升格的“真實”再現。建筑影像藝術在形成以建筑物的內容與形式構造為核心的敘事媒介后,在媒介機制與精神命題結合下生成的綜合的、非分裂的、觸覺的“情景”,被稱為“肖像模式”。“肖像模式”化的建筑情景指的是將特定的人物、事件或情感以具象化的、視角性的方式融入建筑設計中,此時建筑是一種可敘事性的、情感性的信息載體,是有著特定的藝術理念、文化設定與歷史形態的“情感景觀”。這與居伊·德波(Guy Debord)1968年在《景觀社會》中提出的觀點類似,即:“視覺表現篡位為社會本體基礎的顛倒世界,一個社會景觀的王國”[2]。以影像為中介(如各類電影和影像藝術中的建筑意象)所形成的信息媒介與社會關系打破了景觀社會中單向度、非民主溝通模式的魔鏡,向著更加整體、多元、非分裂式的模式發展。其中,建筑語言被再現為對象性的圖像,受眾成為觀念主體,他們共同組成了影像藝術觀念表達的“情境”,而且這種“情境”性帶有延伸感覺器官等觀念性的特點,呈現為“綜合空間”。這種綜合的形式、非分裂的感覺并不是視覺的,而是類似于人的觸覺,需要參與者全身心地參與。[3]換言之,綜合化以及視覺化延伸所營造的結構空間,將建筑中屬于社會與文化的“自然”之物與影像藝術表達的“再現”之物相融合。例如,我國著名古建筑攝影師蘇唐詩的影像藝術作品《拂》,其中,建筑影像藝術的主體形象是依據不同文化節點的需求設定的,因此無論是寧靜的書院,還是與自然景觀一同構成巧妙碰撞的音符,都達到了對“天人和一”和諧之美的完美詮釋。“肖像模式”化的建筑情景不僅注重由光影、材質、色彩等手段創造的感知意義上的空間延展,而且對具有情景化、布局化、故事性、感染力的藝術氣息的空間體驗探索更為深刻。建筑藝術在文化與觀念上為建筑肌體增添了理情寓合、情理交融的空間,這一過程營造了建筑影像藝術表達中最直接、最穩固的內在情景。如羅永進的《杭州新民居》系列,從建筑影像中的蕭山機場到杭州市區的建筑格局體現出居住環境的變遷,影像藝術表達出具有社會追逐和向往的“暴發戶”的典型特點。作品是當下時代的直觀映射,是社會現實生活的趣味乃至文化生態的視覺圖景,甚至包括時代的相互混雜特征與時序更迭中的47fad51707eeaa2c73bc6082662bb9b4荒誕情景。無獨有偶,羅永進的作品《異物·窗布》,是從建筑情景的視角出發不斷深入結構空間,運用攝影圖像的拼接而混成繽紛且豐富多彩的形象,揭示了在欲望的質疑、揭露與批判中,文化中空狀態、物質化、娛樂化的生活空間。
(二)建立真實且具有隱喻意義的意象體驗
視覺隱喻塑造將建筑空間中的真實狀態延伸到意識層面,具有精神視覺的特點。在20世紀60年代的早期和中期,以邁克爾·斯諾(Michael Snow)、荷利斯·法朗普頓(Hollis Frampton)為代表的電影藝術家就在具有預定性和簡化性的電影中,以精心的安排將潛在意識引導成為目標,不斷將觀眾引入冥想的狀態。這種精神視覺性的引導是對接受主體的階段化與結構化的劃分,主要表現為通過銀幕內與銀幕外相結合,重設人、物敘事的主觀性,具象化主體意識的主旨。伴隨著建筑影像藝術表現的內在世界與建筑物表現的外在社會空間的并置,一同延展建筑藝術的情感空間,并增強視覺的真實性,這種具有隱喻性的意象體驗被李格爾理解為建筑所凝聚的人造物的時間價值(age value)。換言之,視覺隱喻將建筑視覺影像中的結構、空間、肌體、位置、情感等進行總體的視覺聯動,抽象化為一個富有詩意而又態度鮮明的“精神影像”。如吳亞偉的作品《紅墻之外》,形象地刻畫了四川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的建筑肌體語言的豐富性與深刻性,影像中紅墻之內與紅墻之外的建筑形象宛如一個天然的視覺屏風,不僅對富含民風民俗的生活空間進行了劃分,同時也對代表著建筑藝術精神空間的色澤、裝飾、紋理和質感等進行了如“畫中畫”般的意象性呈現,組成一個抽象且生活化的精神畫面。《紅墻之外》將儀式性的建筑體與棲寄在建筑本體中的群體體驗,轉化為具有連貫性和象征性的視覺圖景,一方面飽含個體對地域情感、民族性的內在寄托,另一方面凸顯群體精神世界與外部環境磨合后真善美的外化形式。
二、尋求詩意性:塑造建筑“廢墟”藝術的視覺意象
(一)構建詩意及殘缺性的內在意象
與傳統影像藝術內在模式的一般性表達不同,建筑影像將建筑體視為由多重元素構建而成的有機體,其中凝聚并再現了碎片化、破壞性、傷痕性等多重意象與情感體驗所組成的意象空間,是一種“廢墟化”的表達。“廢墟”化的建筑藝術以最真實、震撼的情感體驗與感染力,凸顯出留存在物質材料之外最動人的底色。這恰如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認為的:“心靈沒有意象就永遠不能思考”[4],這里的意象是對人性和詩意的追求,既包含空間中完整、系統的結構與機制,又涵蓋因殘損、破壞、廢除所導致的殘缺性。建筑藝術中的記憶、文化、地域、情感、行為承載的獨特瞬間并非完全是個體機制經驗的結果,而是一種對缺失的內在意味的找尋,是對因種種原因而遺憾缺席的現場感的回應,是一種殘缺的“廢墟化”。建筑影像內在多重意味的構建實現了意象表達從形式感到本體性的轉變,建筑影像中的“廢墟化”是由精神視覺體驗所引發的對心靈語言的感知。如郭小明的《墟像·黑銹》系列,展廳中的影像以現代工業廢墟的壓迫感帶給人的焦慮感與沉默性引入,雜草叢生、磚石塌落,儼然無人地帶。影像中廢棄的建筑體、銹飾斑斑的設備,營造了以建筑體為主導的私人體驗與對話,建筑黑白灰形成的色階以及空間感受,通過不斷與時間、空間銹跡、建筑、空窗的反復對話,形成畫面語言的詩意化。隨后在日本大阪Gallery0369美術館舉行的“灰筑”和“空窗”的展覽中,把窗玻璃的塵跡之美和窗欞的框線美帶入熒幕,尤其是云天的出現,造就了浪涌的意象,觀眾可以沉浸式融入影像藝術和建筑藝術的詩意空間中,體驗建筑藝術的裝飾性與影像表達的情感性、細微性,并帶有精神感知。
(二)以“在場”性的視角親歷過去與當下
如邁克爾·伊士曼(Michael Eastman)的作品《浪漫都市》,其盡可能以色彩的表現力還原建筑廢墟中原有的生活氣息,使建筑物洋溢著浪漫、生動的意味,其中在對布宜諾斯艾利斯、里斯本及其米蘭的描述中,作者賦予色彩以身份,身份化后的色調具有歷史構成中的塑造性與參與性,可以營造出恰似房屋主人因聚會而離開后的溫馨短暫瞬間,與荒寂的周邊氛圍形成對比。另外,德國建筑師克里斯蒂安·里希特(Christian Richter)則從定格“廢墟化”的視角闡述了建筑廢墟藝術內在的文化肌體,滲透著情與理的融合。其拍攝鏡頭大多集中在廣場、醫院或者廢棄的電影院等被損壞的房間內,尤其走廊和樓梯,以及褪色的圖案和色彩所能體現的腐朽的建筑美,歷歷呈現過往片刻。由此可見,建筑影像藝術是被時間損壞的建筑機體的修復單元,其修復軸線跨越時間與心靈回憶在歷史穿梭中的各個角落。綜上所述,建筑影像藝術中“廢墟化”的視覺意象拓展了建筑的審美空間,以斷裂、“非空間”式的藝術語言豐富了對非物質性、精神主體性的內容,這正類似于米歇爾(W.J.T.Mitchll)對圖像意義中“超圖像”的解釋,是一種圖像中的圖像,影像中的影像。
三、形式的原境:營造回憶、延續的紀念碑性
(一)建筑影像藝術中本體意識表達的持續性
“紀念碑性”一詞來源于拉丁文Monumentum,本意是提醒和告誡,是一種“紀念的狀態和內涵”,主要指與建筑物及其建筑物文化群相關的紀念功能和持續性。換言之,建筑藝術對自身文化、歷史進行建構的屬性形成了建筑的紀念碑性。紀念碑性的特點是具有哲學反思與歷史性的,而紀念碑則可以是任何形式的[5]。著名藝術史學家巫鴻認為,“中國藝術和建筑的主要傳統具有重要的文化內涵,建筑及其相關的藝術形式都有資格被稱為紀念碑或紀念碑群體的組成部分”[5]。因此紀念碑性不僅存在于“有意而為”的紀念建筑或雕塑中,而且包含“無意而為”和虛擬的視覺感知形式。影像藝術作為建筑傳統中紀念性和禮儀功能的統一體,是建筑藝術當代性、永恒性、觀念性、生命力等集體無意識的表達媒介。其不僅以跨越時空的“有意而為”的理性,凝聚時間性、民族性、紀念性等所從屬的文化范疇,而且以無意識的感知,構筑起建筑由紀念碑到紀念碑性的意識與記憶延續的多個層面,并以內外真實生動的儀式性與紀念性體現出歷史的延續性。由此可見,建筑影像藝術中的紀念碑性是一場在不受任何時空限制的跨文化和跨歷史的條件下,觀者禮儀與建筑原境之間的時空對話。如電影作品《血觀音》,影像中的中式園林是構造歷史、社會關系、禮制行為等共同體的紐帶,其中的林家花園是花園主人和文人墨客清談、吟詠、看戲之所,尤其從其方鑒齋的“齋”與“鑒”中可以看出建筑物扮演著重要的儀式性角色,花園的設計具有漸入式的特點。無論是林家花園的書齋區,還是供人賞景休憩的汲古書屋,勻以可視可觸的結構功能和文化意義構筑了恒久、延續的紀念性和禮儀性。
(二)重塑建筑藝術中的形式原鏡與回憶節點
觀念的轉變外化為物質形態功能和象征意義的發展,建筑影像重塑了特定文化范疇內共同體意志表達的片段性與特殊性。策展人潘與華致力于重現臺北市時代發展面貌與文化生態的經典建筑,其影像作品《映像·臺北城——百年經典建筑影像展》在呈現了城市的歷史厚重感的同時,也凝結了共同回憶場域聯結下時代觀念的流變。此影像定格了時空轉變、回憶特定記憶內容的瞬間,從民間記憶的角度對其文化屬性與時代樣貌進行不同層面的還原與構建,找到不同時代人心目中的社會認同性和精神歸屬性,同時映射出以情感為中心的社會及共同體關系。影像中的城市建筑無論是形狀質地還是構建格局,都認為是界定記憶、歷史、狀態和內涵意義的中心共同體的紐帶。建筑影像藝術對歷史節點的還原繼承了傳統禮制體系在現代文化傳承之間的精神性,建筑本體持續的紀念意義以豐富的意蘊進行延展,共同重塑留存在集體回憶空間中的文化片段。
四、結束語
建筑影像藝術的意象表達建立了建筑語言意象敘事表達的主基調,塑造了以“情景”為核心的綜合性建筑空間及其意識化的感性建筑形態。影像藝術中建筑語言的視覺隱喻與回憶性充滿多重的詩意性,是自然、詩意與審美理念化相融合的結果,重塑了建筑影像中客觀物象與文化生態的關系,滿足了對多元文化環境的設定。可見,建筑影像藝術具有包含與獨立于“意”之外的包容結構。地域性、紀念性、詩意性的紀念碑性特征,是對建筑“意象”的延展與再造,不斷向著情與理、景與意的無限想象的多維空間進行融合與轉變,總體形成建筑的內涵與外延。
參考文獻:
[1]羅崗,顧錚.視覺文化讀本[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176.
[2]居伊·德波.景觀社會[M].王昭鳳,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174.
[3]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M]. 何道寬,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9:286.
[4]魯道夫·阿恩海姆.藝術與視知覺[M]. 騰守堯,朱疆源,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579.
[5]巫鴻.中國古代藝術與建筑中的紀念碑性[M]. 李清泉,鄭巖,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3-4.
作者單位: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