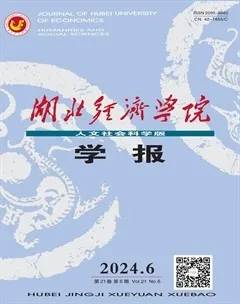論“大農業觀”視域下的農業生產經營組織振興問題
摘 要:樹立以“大食物觀”為基礎的“大農業觀”,實現農村產業鏈的持續發展。組織化生產經營是鄉村產業發展的重要前提。大農業觀統領的大農業生產經營組織不是指其在組織規模上的“巨大”,而是指其在推進大農業生產經營,在構建農業生產經營的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等方面具有獨特的作用。大農業生產經營組織是在“大農業”背景中,提高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重要組織形式。生產經營組織振興是農業產業振興的可靠保障。基于經濟發展需要建立的生產經營組織,遵循經濟發展規律、市場運行規律和共同富裕的價值原則,使農村基層生產經營組織能夠煥發出勃勃生機。
關鍵詞:鄉村振興;大農業觀;大食物觀;農業強國;組織振興
隨著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不斷升級,農業的主要矛盾已經由總量不足轉變為結構性供需失配,一些大宗農產品總量過剩,而高質量、多元化的農產品需求仍然不能得到很好滿足。由此,必然以大農業觀引領農業現代化發展,“樹立大農業觀、大食物觀,向耕地草原森林海洋、向植物動物微生物要熱量、要蛋白,全方位多途徑開發食物資源。”[1]248-249農業生產結構的轉變,要求生產經營組織形式發生相應的變化,以小農生產為主要生產經營方式的農業格局對于化解農業供給側結構性矛盾顯得無能為力,傳統食物觀和農業觀致力于幾種主糧的生產儲備。由于供需失配而導致主糧價格偏低,很容易觸及價格“天花板”,在農業生產成本持續高漲的情況下挫傷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鄉村組織振興的重要目標之一,就是構建適應于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的生產經營組織體系,提高農村全要素生產率、改善供給側結構性問題,通過生產的結構性系統性再造,對以小農生產為主的傳統農業進行現代化整合。
一、大農業觀視域下的農業版圖和發展契機
大食物觀是人民群眾食物結構不斷發生變化,從著重考慮食物的“自然來源”轉移到著重考慮食物的“營養功能”上來的食物觀,是對自然生殖力深入探索的基礎上強化科技創新的食物觀,是關于食物觀念的升級版。其主要的事實基礎是:人們對食物的需求已經由“吃得飽”轉向“吃得好”,由能量充足到營養均衡,由“充饑”“美味”發展到“美味、營養且健康”。大食物觀引領大農業觀的發展,大農業觀為廣義農業生產經營提供思想指導,也為農業生產經營組織體系的構建提供了新的依據。
(一)“大食物觀”引領“大農業觀”的構建
消費引領生產,消費創造新的生產增長。隨著人們對糧食需求結構的變化,在“吃得好”(人民群眾美好生活的實物需求)方面的供需矛盾日益明顯,由于農業科技水平不足和資源稟賦造成的規模生產率較低,我國糧食生產成本高于國際主要糧食出口國,糧食安全問題在多個方面引起我們重視。一方面,大食物觀拓展了人們對“食物”來源的認識。這是結合我國人均耕地面積較少,傳統糧食增長空間有限的現實,也是結合當前生物科學和食品工業的發展,設施農業突飛猛進,農業基因工程取得重大突破的現實發生的食物觀轉變。釋放土地潛能與發展“離土”生產能力并舉。我們需要在大食物觀的引領下構建大農業觀。另一方面,大食物觀建立在人們食物消費觀念變化的基礎上。隨著小康社會的全面建成,我國已經站在了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新起點上,人們美好生活的重要體現就是食物的多樣化、食物結構的多元化和科學化。科學的營養結構支撐人的體質發展,再生食物、綠色食物、高科技農業新產品、人工支持營養等在個人的食物菜單上提供了更多選項。人們對食物類型的新要求不斷升級,高科技產品、綠色新品種、高品質產品、特色產品等成為糧食消費的時尚和趨勢。如果不改變種植養殖的結構,不根據市場需求做出適時適當調整、構建大農業觀,國內糧食市場就會被全球糧食資本所制約,危及國家糧食安全。
(二)“大農業觀”對農業版圖的拓展與改造
生產引領資源布局,市場激發資源活力。科技和市場化改革雙輪驅動是我國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大農業觀通過農業生產資源布局的優化,構建傳統種植業的升級版、發展新型農業的創新版、推動未來農業的預告版。農林牧漁綜合發展、海陸空縱深推進,構建從海洋農業到陸地農業、山地農業、空中農業的全景圖。農業生產要素資源的整體布局更加有利于建立市場導向的農業生產體系。市場化資源配置方式使得農業生產的“經濟性”在某種程度上超越了其充當社會營養體系的“保障性”。農業版圖的新趨勢是在縱橫兩個向度推進農業生產的供給改革,對基于大食物觀的農業消費市場采取針對性較強的定制農業和數字化建設。以農產品生產為主的物質農業和以體驗式休閑娛樂為主的休閑農業并駕齊驅,農業生產作為休閑方式在部分城郊結合區域已經成為一種常見的現象。農業的功能進一步豐富。“藏糧于地”與“藏糧于技”的雙向并軌逐漸成為預防糧食危機的重要方案,設施農業與傳統農業之間的界限日益模糊,設施農業的加快發展和全面滲透正在改變著農業的深層矛盾,土地的貧瘠或肥沃問題已經讓位于農業技術的先進程度和普及程度。土地及其自然力作為物質財富的重要來源之一,其基礎地位依然穩定,但它的競爭性優勢已經有了一些變化,“科技、人文、生態”相結合的綜合性農業生產更加具有競爭力。可見,大農業觀已經在根本上改變著農業的版圖及其發展趨勢。這對構建中國特色的農業現代化,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業優勢,是必要的認識前提和實踐起點。組織介入能夠更好發揮農業生產的“經濟性”功能并夯實其“保障性”基礎,實現農業強國。
(三)農業生產經營組織的歷史主動與切入點
組織彰顯規模效應、發揮專業優勢,更彰顯歷史主動精神。新的農業消費觀念和農業生產觀念,緣于生產力水平的整體提高和農業科技的發展推動。在鄉村振興的背景下,依托產業鏈、價值鏈、創新鏈等,基于利益聯結與分配機制,衍生了鄉村產業發展的多種模式。[2]農業生產經營組織與生產經營模式之間存在著兩種建構秩序:其一,在新業態出現或新生產經營方式發展過程中,由于實際需要的推動建立起相應的組織機構,以指導新業態和生產經營的規模發展和持續增效。其二,在可參照的業態和生產經營發展中,即先進地方已經存在的新業態和生產經營方式被引入的過程中,組織建設與業態或模式建構具有同步性,甚至在少數情況下具有組織現行性。這種組織一般建立在成熟的運行經驗之上,是維系相應業態和經營模式的組織架構或權力系統。大農業觀視域下的新業態、新產業,是現代農業生產技術及管理要素與產業深度融合和創新的產物,通過要素聚合、疊加衍生、交互作用不斷生成新的經濟形態。[3]對于廣大鄉村來說,適應大食物觀和大農業觀,建設新的農業產業體系和發展新的農業生產經營模式是比較困難的。其難點主要在于農業技術的普遍落后、經營管理水平不高、現代化生產條件不足等。農業生產經營組織的先行構建,可以部分避免這些脆弱點。在鄉村黨組織和村委會的主持下,在相關幫扶組織和聯誼單位的協助下,預設鄉村產業經營機構,在有針對性的考察學習和研討分析后,構建適應本村農業生產經營的新模式,通過規定程序使之合法化、通過市場規則檢驗其科學性。具體的農業生產經營組織的設置和章程擬定,建立在使農業“綠色化、優質化、特色化、品牌化”[1]248的客觀需要之上,這也是農業生產經營組織發揮專業特長、主動作為的重要抓手。
二、小農生產到大農業生產的組織變遷與內在邏輯
小農生產與大農業生產的核心區別是生產要素的流動性問題。小農生產對生產要素的流動性要求較低,承續傳統生產內容和方式,在生產力的緩慢變化中延續生產關系的家庭性質。大農業生產在生產要素的流動性增強中,突破了傳統農業生產的時空限制,要素的集聚和組合實現了在更廣范圍內的優化,生產關系高度社會化。農戶家庭是小農生產的重要組織單位;具有社會化屬性的農業生產經營組織,是在大農業生產格局的萌芽和發展中逐漸形成的。農業生產組織方式的變遷,表現了組織進化的內在邏輯和動力源泉。
(一)現代化進程中小農生產的組織形式及其弊端
我們需要從現代化視角去理解小農生產經營組織形式的式微。一方面,小農生產經營方式不適應現代生活方式的變遷。現代化的重要表現之一便是人數眾多的中產階層的興起,這與社會物質財富的豐盛是密切相關的。農業產品作為普遍的消費需求,在技術發展緩慢的傳統生產模式下,需求的差異性主要表現在人數極少的特殊階層對珍稀食物的追求。在現代化取得較大發展的背景下,已經脫離貧困并享受現代生活的階層,對農業產品的需求出現了多樣化的趨勢,并將其作為一種“有價值的生活方式”予以推崇。小農生產完全滿足不了這樣的社會需要,它本身的物質容量十分有限。另一方面,小農生產方式不適應現代生產方式的要求。小農生產組織方式架構在“垂直擴展”和“水平擴展”上的有限性,使新的目標和價值實現必然建立在組織架構的重新設計和徹底改造上。[4]也就是說,小農生產在品質精耕和規模拓展兩方面都存在著價值延伸的限制,如果不改變這種狀況,不但在品牌化建設方面失去機會,也在規模效益上失去優勢。小農生產經營為主的農戶家庭,在生產要素集成和產品價值的拓展上有著先天的局限。由于專業化強度不夠,導致其在農業生產技術和市場經營能力上都無法深度參與國內大市場的經濟分工,更不用說在國際農業價值鏈、供應鏈布局中的位置了。大農業生產經營組織就是將農戶與大規模農業生產經營有機聯結起來的組織架構。在具體的方式上存在著農戶結合密切程度方面的差異,但其主要的目標在于重新獲得農業資源的配置權利,并提高有效要素的利用率。在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的同時,將農戶融入農業經濟發展的現代體系中,能夠有效避免小農生產在大農業競爭格局下掉隊。
(二)大農業生產經營的組織邏輯與動力機制
大農業生產經營的核心不在于“大”的內容,而在于“大”的系統聯結。分工與全景構筑的同步推進,形成了大農業觀視域下的農業生產經營新模式。以家庭經營為主的小農戶,承擔著農業生產的種子甄選與保留、農具制作與維修、灌溉設施建設、耕地維護、作物培植、中期管理、收割、儲存等全部生產流程工作,由于家庭成員主要以自然分工為主,每一位農民都是多面手,從事生產流程中的各項工作,個體勞動的差異性并不十分明顯。生產經驗的家族傳承和鄰里授受,使農業生產的品種、規模和產量在自然條件相近的情況下保持相當的穩定性。大農業生產經營的組織超越了家庭小農生產的局限,分工日益明晰。一方面在區域范圍內實現了精細化專業分工,從而提高農戶和農民在特殊生產領域和勞動技能上的熟練程度;另一方面在區域競爭環境中,區域農業生產作為社會總需求體系中的特殊價值構成而獲得發展空間,在為社會總供應鏈提供有效支撐的過程中,生產和發展具有一定特色的農產品品種、品質和品牌。大農業生產經營組織作為整體功能的“行為體”,凝聚了全村人民的集體智慧和行為意志。“目標一致對任何組織的健康運行都至關重要。”[5]大農業生產經營組織固然有相較于小農生產更大的內容體系,更重要的是它通過組織化的力量擴展了村莊生產體系向外的接觸面,更多的生產要素有機會涌入鄉村,成為發展的新動力和新契機。以組織的形式擴大小農戶和村鎮小企業在社會生產體系中的聯結面——事實上,在更高層次的系統中所發揮的聯結作用越強,子系統在價值鏈中的作用也越重要。由此可見,通過大農業生產經營組織,個體農戶和小型農場或鄉村企業獲得了提高自身價值的機會。
(三)大農業生產經營組織創新的價值與意義
大農業生產經營組織創新的價值指向是實現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躍升。對小農生產及其組織形式的突破和發展,就是大農業生產經營組織的核心價值。大農業生產經營組織創新,需要理解兩個不同的概念:“大型農業生產經營組織”和“大農業生產經營組織”。前者是從組織自身規模來確定的,是生產組織在生產總值、人員數量、結構復雜和完整程度、經營面積、農戶數量和加盟企業的多少等方面具有數據上的絕對優勢的生產經營組織。后者則是在大農業觀的統領下構建的,為實現大農業深度發展,從而在業態聯合、要素聚集、專業深耕等方面強化集體在產業鏈、價值鏈、生態鏈、供給鏈上的地位,并獲得所聯合的企業和農戶支持的生產經營方式和組織體。清晰的概念認知對發展大農業生產經營組織,并推進其創新組織形式和發展組織價值是有益的。江蘇吳中以地區品牌為依托的“長漾特色田園鄉村帶”和“同里農文旅融合發展區”[6];吉林省的集安藍莓、龍井延邊黃牛、東豐梅花鹿、長白山人參等,以地標品牌建設為主。[7]以上兩類都屬于松散型大農業生產經營組織,它以地區組織規劃確定發展方向,整合資源稟賦和各種經濟文化要素,進行大農業生產經營。甘肅蘭州莊園乳業構建的全產業鏈模式“6S生態莊園”,聯結現代牧場和城鄉社區百姓生活[8];河南省平頂山探索創新的“目標市場+龍頭企業(合作社)+基地+農戶”的發展模式[9];等等。以龍頭企業或合作社為中心或紐帶,聯結小農戶和大市場,這種農業生產經營模式是當前我國農業生產經營中方興未艾的主流合作組織。大農業生產經營組織形式創新不在于理念和流程的新穎程度,而在于“三個結合”的表現力度:地方資源稟賦(包括人、自然資源等)與農業生產經營方式相結合;小農生產與大農業生產相結合;農業生產方式、農耕文化傳承與大農業生產經營創新相結合。2016年12月印發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培育農業農村發展新動能的若干意見》指出:“推進區域農產品公用品牌建設,支持地方以優勢企業和行業協會為依托打造區域特色品牌。”[10]在推動農業“綠色化、優質化、特色化、品牌化”發展的同時,全面提高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更好更快推進農業現代化建設。
三、結語
農業農村現代化是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重要內容,而鄉村組織振興是農業農村全面現代化的重要保障。加快“構建集約化、專業化、組織化、社會化相結合的新型農業經營體系,進一步解放和發展農村社會生產力,”[11]就要充分發揮組織功能,使農民合作社在現代農業生產經營中發揮更好作用。在大食物觀、大農業觀、大產業觀的經濟敘事結構發生重大變遷的同時,充分調動農民群眾生產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組建適應于現代農業生產和農業科技發展、適應于節約資源和環境保護、適應于提升品質和增加效用、適應于提高農民收入和促進全面共同富裕的農業生產經營組織,是時代所需,是農情、國情、世情所需。同時,我們也應當看到,農業生產經營組織的發展,必須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要著力調和大農業生產經營和小農業生產經營的關系。當然,“不是所有地方都能搞集中連片規模經營。還要看到,小農生產在傳承農耕文明、穩定農業生產、解決農民就業增收、促進農村社會和諧等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1]246應該堅持“宜大則大、宜小則小”的原則,不能搞一刀切、不顧實際、盲目蠻干。隨著數字農業時代的到來,其他科學技術不斷融入到農業生產經營領域,綠色農業、數字農業、精準農業、定制農業等將會不斷翻新人們的認知,也不斷刷新農業價值閾值的極限,賦予農業生產經營組織新的使命和任務。在此背景下,農業生產經營組織的升級進化,乃是發展大農業觀、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必然選擇。
參考文獻:
[1] 習近平.論“三農”工作[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2.
[2] 張瑞娟.構建共富型的現代鄉村產業體系,見魏后凱、杜志雄主編中國農村發展報告——促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2:297.
[3] 孫景淼等.鄉村振興戰略[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146.
[4] [美]馬丁· L. 阿伯特、邁克爾 T.費舍爾.架構即未來[M].陳斌,譯,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16:250.
[5] [法]讓·梯若爾.共同利益經濟學[M].張昕竹、馬源,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0:176.
[6] 楊軍.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蘇州實踐[M].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2020:130-131.
[7] 農業農村部市場與信息化司,中國農業大學.中國農業品牌發展報告(2022)[M].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22:50-51.
[8] 李志起.大農業模式:改變著名農企命運的100個新銳經驗[M].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13:147.
[9] 周立,李同新,陳明星.河南農業農村發展報告(2021)[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205.
[10] 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715.
[11] 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95.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全面小康社會農村返貧防治機制研究”(20BSH097)
作者簡介:盛德榮(1979- ),女,湖南沅江人,江蘇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管理學博士,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理論與當代中國現實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