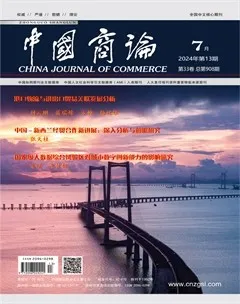中美貿易共生關系的測度與優化
摘 要:中美經貿關系不僅涉及雙邊利益,還是全球貿易網絡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文利用2001—2021年中國和美國對世界125個第三方貿易伙伴的雙邊貿易數據,將中美貿易共生關系分解為融合性、互補性、依存性與競爭性四個維度,并進行測度與數據分析。測度結果顯示,中國正在通過中間品貿易與東盟形成新的產業分工格局,借由第三方市場與美國建立間接共生關系;中國與亞洲市場的貿易互補性和依存性下降,表現為與日韓共生程度的降低,與東盟的上升。最后,從關鍵零部件科技自立自強、深化東亞地區供應鏈體系等方面,提出了中美貿易共生關系優化的相關建議,以供參考。
關鍵詞:貿易共生;中國;美國;第三方市場;東盟
中圖分類號:F7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0298(2024)07(a)--05
1 提出問題
共生概念最初來源于生態學,用于描述種群的生存狀態,最早由德國真菌學家德貝里(Anton de Bary)于1879年提出。20世紀中葉,開始應用于社會科學領域,在經濟學視角下,共生是指作為共生單元的各個經濟體之間通過緊密合作,形成一種相互依存、相互促進、優勢互補的一種持續性特殊物質關系,以應對外界的變化(Moor,1993;袁純清,1998;Zaccaro & Horn,2003)。切入中美共生關系的相關研究,最早的研究在2007年,Niall Ferguson和Moritz Schularick提出了一個“中美國”(Chimerica)的概念,認識到了中美關系的緊密度,雙方間的共生關系對全球經濟持續繁榮有重要影響。同期,國內學者唐小松(2007,2010)從共生理論三要素——單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環境維度,研究認為中美已具備經濟共生關系的主要特征,2008年金融危機加速了兩國從不對稱性依賴走向對稱性共生。劉勝湘、葉圣萱(2019)構建一個新型兩極共生關系,超越了傳統的兩極對抗關系之“修昔底德陷阱”,并認為中美之間在國際體系中的互動模式為新型競爭共生關系。
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新冠疫情和俄烏戰爭,凸顯了高度全球化引致的全球價值鏈斷裂的風險,進一步加速了全球價值鏈向本土化、區域化重構的進程。拜登政府利用區域和多邊主義加速中美經貿關系“脫鉤”,如推動“近岸外包”“友岸外包”等政策,發起印度-太平洋經濟框架(IPEF)等機制,試圖通過聯動第三方市場的方式,達到重塑我國周邊和整個全球價值鏈的目的。根據梳理,已有研究多從中美雙邊層面進行剖析,從第三方市場探索中美經貿共生關系的探討不多,尤其缺乏相關的數據與實證依據。為此,本文依托共生理論,創新性地利用中國和美國分別在世界市場(第三方市場)的貿易數據,從融合性、互補性、依存性與競爭性四個維度,構建了兩者的貿易共生關系。因此,文章為新形勢下優化中美與世界市場中主要經濟體的經濟協作提出對策建議。
2 中美貿易共生關系的測度方法
根據共生理論,單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環境為三個基本要素。本文將中國、美國及其第三方市場作為貿易共生關系中的共生單元;中美與第三方市場的融合、互補和依存關系,以及中美兩國在第三方市場中競爭關系來測度共生模式;中美與主要經濟體或各區域市場以及世界市場三個維度作為共生環境,見圖1。
2.1 融合性
融合性反映了雙邊產業關聯程度,正向融合關系能夠促進外部市場對本國相關產品需求的增長,從而通過外部需求推動國內生產的發展。本文借鑒共生理論中的共生度來構造相應指標,反映了共生單元之間質參量變化的關聯度,可用以測度中美分別與第三方貿易伙伴之間的融合性。指標形式如式(1)所示:
其中,dEXj/EXj可用以描述中國或美國對世界市場出口的變動率,dEXi/EXi可描述為第三方貿易伙伴對世界市場出口的變動率,即中國或美國出口的變動率所引起的貿易伙伴出口變動率。當TSDI>0時,表示融合性較好;當TSDI<0時,融合性較差。
2.2 互補性
互補性反映了貿易產品的相互補充程度,即一國出口產品結構與另一經濟體進口產品結構的契合度。本文選取Drysdale(1969)提出的貿易互補性指數進行構造和計算,用以描述雙邊貿易的互補程度,其表達式如式(2)所示:
其中,Xkw/Xw表示k產品在世界的出口占世界總出口額的比重,Xki/Xi表示k產品在i國的出口占i國總出口額的比重;Mkj/Mj表示k產品在j國的進口占j國總進口額的比重;Mkw/Mw表示k產品在世界的進口占世界總進口額的比重。TCI值越大,說明i國與j國的貿易互補性越強。
2.3 依存性
依存性反映了雙邊國家貿易產品的依賴程度,具體體現在本國出口產品對其他經濟體進口需求的匹配程度上。根據Brown(1947)提出,并經小島清等學者改善的貿易結合度指數度量,表達式如式(3)所示:
其中,Xij為i國對j國的出口額,Xi為i國的出口總額,Mj為j國從世界市場上的進口總額,Mw為世界進口總額。當TII>1時,表示i、j兩國的貿易聯系緊密;反之,表示兩國之間的貿易關系相對松散。
2.4 競爭性
競爭性反映了兩國在第三方市場中出口結構的相似程度以及產品的可替代性,雙邊國家產業的出口結構越是相似,競爭強度越大。本文選取出口產品相似度指數進行測度,它最早由Finger和Kreinin(1979)提出,計算公式為:
式中,X為出口額,k為產品種類,h表示目標市場。該指數取值在0~100,越接近100,意味著兩國出口的商品構成越趨于一致、競爭越明顯;反之,越接近于0,則競爭性越弱。
3 中美貿易共生關系的數據分析
根據CEPII-BACI數據庫,文章選取2001—2021年中國和美國對世界各貿易伙伴的進出口貿易數據。
3.1 中國與第三方市場中間品貿易融合性高、波動性小
從融合性的視角看,中國與美國均與第三方市場主要表現為正向融合。在變動趨勢上,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中國與各第三方區域市場的融合性趨勢上升。然而,受到全球經濟低迷的影響,2012—2016年,中國和美國出口貿易額的增幅有所減緩,尤其是2015—2016年出現了負增長。2020年新冠疫情期間,中國與各主要經濟體從正向融合轉為負向融合關系,而以中間品揭示的全球供應鏈的核心鏈條,仍呈現出良好的融合性。從貿易數據來看,2020年,中國作為選取樣本中唯一實現出口正增長的國家,但中間品出口與其他經濟體變動方向一致,為負增長,即全球價值鏈加劇了貿易下降的波動風險對我國中間品出口貿易的沖擊,但世界工廠地位短期不會受到本質性影響。
3.2 美洲是中美貿易共生的共同第三方市場
從互補性與依存性來看(見表1和表2),在三大主要貿易區域市場中,中國與美洲互補性最強,與亞洲市場依存性最強。美國與亞洲、美洲互補性較為接近,而與美洲地區依存性遠高于其他經濟體。中國與美國分別與亞洲市場的互補性、依存性變動趨勢與日韓保持一致,且東盟、日韓分別與中國和美國的互補性變化趨勢呈反向。其中,中國在亞洲市場的依存性持續在東盟市場得到強化,而與日韓的貿易互補性持續降低;美國與日韓互補性在2012年后持續上升,2021年達到1.12。綜合來看,美洲作為共同促進中美貿易共生的第三方市場,而在亞洲市場中,中國更偏向東盟,而美國更偏向日韓。
3.3 東盟成為中美在全球產業鏈中正向共生的關鍵區域
從整體樣本商品來看,中美在第三方市場的競爭性測算結果值均低于50,表明中美競爭性總體水平較低且趨勢相對穩定(見表3),2017年之前緩慢上升,在此之后小幅回落。但是,深入觀察中間品及其細分的零部件,發現中美在第三方市場的競爭性升高,美洲成為中國和美國競爭性最高的第三方市場,亞洲逐漸成為接近美洲的高競爭性第三方市場。2008年后,中美在亞洲與美洲市場中零部件競爭性均值大于50,亞洲零部件產品競爭性上升幅度最大,由圖4可以看出,這種上升很大程度是由東盟市場所帶動的。圖5進一步從各類產品的情況,2021年中美競爭性較強的依次為零部件、資本品和半成品,其中,零部件競爭性遠高于其他產品,2004年以后均保持在50以上且逐年上升。
結合中美在主要經濟體的中間品出口份額(見圖6),中國中間品貿易集中在亞洲地區,其中,日韓在中國出口中的份額下降最為顯著,而東盟則成為中國日益重要的中間品出口市場,2021年占比18.7%,與美洲20.8%的份額已較為接近。雖然中美雙邊的經貿聯系表現出一定的弱化趨勢,但中美在供應鏈中通過第三方的間接聯系卻在增強,尤其是東盟等第三方國家與中國的緊密度呈現出明顯的上升趨勢。
4 結語
綜上所述,中美與第三方市場的貿易共生關系中,在融合性方面,面對外部沖擊時,中國中間品與外部環境聯動性更強;互補性和依存性方面,中國與亞洲市場盡管依存性最高,但互補性和依存性都呈下降趨勢,特別體現在與日韓的雙邊經貿聯系密切程度降低,取而代之的是,東盟與中國的互補性與依存性持續強化。從中美貿易競爭來看,雖然兩國整體貿易的競爭性較小,但是聚焦在影響全球供應鏈的關鍵商品之零部件,則顯示出較高程度的競爭性;在歐洲市場兩國的貿易競爭性相對緩和。研究的政策啟示為:
(1)美國高技術零部件趨于本地化,須加快我國科技自立自強能力。美國零部件產品出口份額收縮,推動“近岸”和“友岸”國家對中國產業鏈替代增加的背景下,中國應加快提升零部件產業內貿易核心競爭力的迫切性,加快重大裝備、重要基礎零部件、新材料等關鍵領域攻堅克難,保證產業體系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進一步提升中國供應鏈韌性。
(2)深化亞洲供應鏈體系是改善中美貿易共生關系的重要第三方。當前,亞洲地區以RCEP和CPTPP分別為載體的“東亞軌道”和“亞太軌道”形成巨型自貿協定間競合關系的背景下,中國應特別重視通過深化RCEP等區域貿易協定,加強與東亞區域的經貿合作,繼續推動中日韓自貿協定談判,并與東亞各國構建錯位分工、產業聯通的貿易共生關系。此外,中國還應積極推進加入CPTPP和DEPA,尋求與歐盟各國加強產業鏈合作,以部分抵消中美經貿關系的不確定性所帶來的風險。
參考文獻
Moore J F. Predators and Prey: A New Ecology of Competition[J].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9, 71(3):75-86.
袁純清.共生理論[M]. 北京: 經濟科學出版社, 1998.
Zaccaro S J, Horn Z N J. Leade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Fostering an effective symbiosis[J].leadership quarterly, 2003, 14(6):0-806.
Ferguson N, Schularick M. ‘Chimerica’ and the Global Asset Market Boom*[J/OL]. International Finance, 2007, 10(3): 215-239.
唐小松.中美經濟共生關系下的戰略互需及選擇[J].現代國際關系,2007(2):36-39+46.
唐小松,鄧鳳娟.中美經濟共生關系趨向對稱性[J].國際問題研究,2010(2):39-43+31.
劉勝湘,葉圣萱.國際格局新型兩極共生關系論析[J].東北亞論壇,2019,28(2):3-20+127.
胡曉鵬.產業共生:理論界定及其內在機理[J].中國工業經濟,2008(9):118-128.
Drysdale P. Japan, Australia, New Zealand: The Prospect for Western Pacific Economic Integration[J].Economic Record, 1969, 45(3):321-342.
Brown A J. Applied economics: Aspects of the world economy in war and peace[M].Allen & Unwin, 1947.
Finger J M, Kreinin M E. A Measure of ‘Export Similarity’ and Its Possible Uses[J]. The Economic Journal, 1979, 89(356): 905.
盛斌.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與亞洲增長新動能[J].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3(15):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