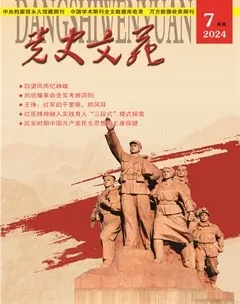以唯物史觀分析東西文明的嘗試
李大釗,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他積極參與東西文化論戰,開始以唯物史觀系統分析東西文明,深入探索中國現代文明發展,創造“第三新文明”,對于新時代推進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亦有價值。
考察文明的方法
唯物史觀是李大釗考察東西文明的根本方法。人類社會以經濟發展為基礎,經濟發展能夠發揮“最終決定性作用”的意義,李大釗指出,“歷史的唯物論者觀察社會現象,以經濟現象為最重要,因為歷史上物質的要件中,變化發達最甚的,算是經濟現象,故經濟的要件是歷史上唯一的物質的要件”。李大釗并不否認其他非經濟的物質的要件對于人類社會發展的價值,而是認為這些“非經濟的物質的要件”相對“經濟的要件”而言,對于社會發展的影響更小一些。所以歷史的唯物論者于那些經濟以外的一切物質的條件,也認為它于人類社會有意義,有影響;不過因為它的影響甚微,而且隨著人類的進化日益減退,結局只把它們看作經濟的要件的支流罷了。因為這個緣故,有許多人主張改稱唯物史觀為經濟的史觀。
李大釗從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出發指出,人類社會的一切精神構造都是表層構造,只有經濟構造(即物質構造)才是基礎構造,基礎構造決定表層構造。李大釗在《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一文中指出,“馬克思一派唯物史觀的要旨,就是說,人類社會一切精神的構造都是表層構造,只有物質的經濟的構造是這些表層構造的基礎構造。在物理上物質的分量和性質雖無增減變動,而在經濟上物質的結合和位置則常常變動。物質既常有變動,精神的構造也就隨著變動。所以思想、主義、哲學、宗教、道德、法制等等不能限制經濟變化物質變化,而物質和經濟可以決定思想、主義、哲學、宗教、道德、法制等等”。
李大釗理解的唯物史觀,又被稱為“經濟史觀”或“歷史之經濟的解釋”,他反對用“經濟的決定論”來稱呼唯物史觀,認為這個概念有傾向于定命論、宿命論的嫌疑,唯物史觀認為“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但“經濟因素不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經濟狀況是基礎,但對歷史斗爭的進程發生影響并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斗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筑的各種因素”。李大釗也認為用“歷史之唯物的概念”或“歷史的唯物主義”這樣的名詞來命名也有所不妥,因為“物質”或“唯物”含義甚廣,把經濟、生物、地理、氣候等都包含在內,而“歷史之經濟的解釋”才是唯物史觀的“真相”,當然,由于“年來在論壇上流用較熟”,不妨繼續采用“唯物史觀”的說法。
李大釗以唯物史觀考察人類文明,把人類文明分為兩大系統,即以農業為本位的南道文明——東方文明系統和以工商為本位的北道文明——西方文明系統,中國文明被歸入南道文明——東方文明系統。李大釗的文明觀,基于地理條件與生產方式的差異立論;視文明為一個不斷隨經濟生活變化而變化的生命體,超越了一些人認為文明不可調和的論調;視文明為可獨立考察的研究單位,超越了以民族國家為研究單位的取向;視文明為一個相互聯系的整體來進行比較研究,超越了脫離世界性聯系而孤立探討文明出路的取向;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西方中心主義的文明觀,較為理性地看待中國文明的未來。
當然,李大釗運用唯物史觀考察文明還具有初步性,用“靜的文明”“動的文明”這樣簡單而抽象的名詞來高度概括東西文明的根本精神,其準確性是值得商榷的,一些具體分析也存在同樣的問題,如說東方文明是直覺的,西方文明是理智的;東方文明是精神的,西方文明是物質的;東方文明是因襲的,西方文明是創造的;東方文明是藝術的,西方文明是科學的;東方文明是保守的,西方文明是進步的等等,這樣的評判在相當的程度上忽視了西方文明古今之別和內部之別,也忽略了東西文明的共通性和東方文明的變化發展性。當然,這種東西文明二元對立的思維并不僅僅是李大釗個人的問題,而是當時普遍的思維方式,如參與東西方文化論戰的陳獨秀、杜亞泉、梁漱溟、章士釗、梁啟超等多是同樣的思維。這種思維在當時亦有時代的需要和積極的意義,因為這種思維能有助于我們主動尋找自身的不足,打破思想的禁錮和僵化,進一步解放思想,積極學習西方文明的長處。
對東西方文明的認識
根據地理條件和生產方式,李大釗認為西洋文明屬于北道文明,北道文明位于歐亞大陸北部,光照條件差,自然環境惡劣,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以工商為本的生產方式,進而發展出以動為本位、移住、小家庭制度、個人主義、競爭、民主政治、樂天主義、創化主義的生活方式,成為一種“動的文明”。“動的文明”有如下特征:人為的、戰爭的、積極的、獨立的、突進的、創造的、進步的、理智的、體驗的、科學的、物質的、肉的、立地的、人間征服自然的。
站在生產方式進步的角度,李大釗充分肯定北道文明——西方文明系統是建立在工商經濟基礎上的構造,具有“動的精神”,即“進步的精神”,其工業革命、物質文明、民主政治、創造發明、個性解放、科學精神、創造發明等方面均為李大釗所激賞,但他并不認為西方文明全是優點,而是認為西方文明既有“種族之偏見”“自高而卑人”,而又過著“物質的機械的生活”,忙于競爭和征服,“疲命于物質之下”“不暇思及人類靈魂之最深問題”,需要借助于東方文明“靜的精神”而進行調和。
根據地理條件和生產方式,李大釗認為東方文明屬于南道文明,南道文明位于歐亞大陸南部,陽光充足,自然條件優越,大自然的供給豐富,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以農業為本的生產方式,進而發展出以靜為本位、定居、大家族制度、重男輕女、調和、專制政治、定命主義、厭世主義的生活方式,成為一種“靜的文明”。“靜的文明”有如下特征:自然的、安息的、消極的、依賴的、茍安的、因襲的、保守的、直覺的、空想的、藝術的、精神的、靈的、向天的、自然支配人間的。
站在工商經濟壓迫和經濟社會進步的角度,李大釗嚴厲批評了南道文明——東方文明系統的八個方面的短處,即厭世主義的人生觀、太重的惰性、不尊重人的個性的權威與勢力、“階級的精神”、對婦女沒有足夠的尊重、缺乏同情心、偏重神權、盛行專制主義。當然李大釗并沒有完全否定東洋文明,而是認為東洋文明亦有可讓西方文明反省其“靈魂最深問題”的長處,故主張東方文明的未來在于吸收西方文明“動的精神”以達到“調和融會”的效果。
中華文明的出路
在李大釗看來,中華文明主體部分屬于南道文明——東方文明系統,以農立國,家族制度發達,支配中國人精神世界的是儒家倫理,政治上層建筑是君主專制制度。李大釗辯證分析中華文明的得失,既看到中華文明于人的精神世界有深刻的洞察力,其“古代文明”曾經對人類進步有偉大的貢獻,對東亞國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又看到中國生產方式的落后性,我們的農業經濟“擋不住國外工業經濟的壓迫”,我們的家庭產業“擋不住國外的工廠產業的壓迫”,我們的手工產業“擋不住國外的機械產業的壓迫”,中國目前的經濟狀況達不到戰勝西洋文明經濟壓迫的目標,“中國文明之疾病,已達炎熱最高之度,中國民族之運命,已臻奄奄垂死之期,此實無容(毋庸)諱言”。
以唯物史觀看來,物質變動必然導致道德變動,經濟變動必然導致文化變動,李大釗深信,中華民族只要吸收西方文明中的“物質生活”“民主政治”“科學的精神”“進步的精神”,則必然復興,對于世界文明將會有“第二次偉大之貢獻”,因此,中華文明的出路并不是以西方文明取而代之,而在于既堅持中華文明的主體性和延續性,又大力發展現代工商業,且根本改變“靜止的觀念、怠惰的態度”,“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長,以濟吾靜止文明之窮,而立東西文明調和之基礎”。
李大釗文明觀的歷史意義與當代價值
李大釗文明觀無疑屬于“新文化”一脈,對于推動新文化運動具有積極作用,他要求主動學習西方文明“動的精神”“進步的精神”“科學的精神”,積極推動中華文明的現代轉型,大力發展現代工商文明,核心是發展工業經濟,同時發展科學技術與民主政治,打破具有“父權專制”“夫權專制”“男子專制”屬性的大家族制度,推翻具有“孝父主義”“順夫主義”“賤女主義”的綱常名教。
李大釗積極參與東西文化論戰,以唯物史觀發揮守正創新、正本清源的作用。李大釗文明觀既不是站在東方文明一面,也不是站在西方文明一面,而是認為兩種文明都有各自利弊,應該進行文明調和,認為“靜的文明”和“動的文明”都不能趨向兩極,靜止和運動、保守和進步都是人類所需要的,缺一不可,兩種文明調和融會才是文明發展的正道,東西文明應該彼此尊重,相互學習,取長補短,以創造“新生命”。在東方文明“既衰頹于靜止之中”,而西方文明“又疲命于物質之下”這樣一個危急時刻,李大釗期待有調和東西文明的“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但李大釗更期待東西文明有“本身之覺醒”,即東方文明“宜竭力打破其靜的世界觀,以容納西洋之動的世界觀”,西方文明“宜斟酌抑制其物質的生活,以容納東洋之精神的生活而已”,以此作為“東西文明真正之調和”。
李大釗文明觀對于新時代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頗有啟發,有助于鼓勵中國人的文化自信自覺,有助于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其文明觀反對文明的封閉和僵化論,反對株守儒家倫理道德永恒不變的教條,認為儒家學說兩千余年能夠成為中國人的意識形態的根源在于存在一以貫之的農業經濟基礎,“孔子的學說所以能支配中國人心有二千年的原故,不是他的學說本身具有絕大的權威,永久不變的真理,配作中國人的‘萬世師表’,因他是適應中國二千余年來未曾變動的農業經濟組織反映出來的產物,因他是中國大家族制度的表層構造,因為經濟上有他的基礎”。只要這個農業經濟基礎發生了重大變化,中華文明亦必將發生重大變化。“深信吾民族可以復活,可以于世界文明為第二次之大貢獻”。李大釗確信隨著中國人學習現代科學技術,發展現代工業經濟,建設現代物質文明,實行現代民主政治,推動傳統的思想、哲學、宗教、道德、法制等方面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指日可待。
結語
李大釗文明觀以唯物史觀分析東西文明的由來、結構和特點,深入剖析了東西文明的地理和經濟基礎,從大歷史角度考察了經濟變動與思想道德變動的辯證關系,得出了中華文明必將復興且將對人類文明有“第二次大貢獻”的歷史結論,其文明觀既具有鮮明的時代針對性,又具有跨越時代的意義,對于新時代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仍有啟發。★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2]《李大釗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3]李大釗.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J].言治,1918年7月1日.
[4]李大釗.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J].新潮,1919年12月1日.
[5]李大釗.由經濟上解 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J].新青年第7卷第2號,1920年1月1日.
[6]李大釗.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J].新青年第8卷第4號,1920年12月1日.
(作者何巖峰系上海理工大學管理學院學業發展中心主任,劉騫系同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責任編輯/陳 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