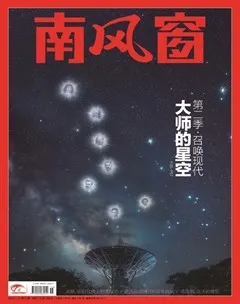漢娜·阿倫特,穿透時間的尖銳

1940年5月,阿倫特從德國出逃法國七年后,又被法國當局收進了拘留營。
按規(guī)定,她要先去一個由賽車場改建的地方報到,只能攜帶兩日份的食物,一套餐具、一個托盤,背包不能超過30公斤。那里有著巨大的玻璃穹頂,她想象過穹頂被炸,玻璃碴傾瀉而下。
后來,她和其他女性被一輛公交車載進巨大的居爾拘留營。一個月內(nèi),6000多名來自巴黎和法國其他地區(qū)的“敵僑”被送了進去。他們剛從張牙舞爪的納粹政權(quán)下逃出,哪知法國也沒有自由。
拘留營里吃得不好,通常只有咸魚干,住得也不好,很骯臟,自來水少得可憐,但她堅持每日洗漱,保持整潔,打掃營房,清理茅廁。
阿倫特一度設(shè)想過自殺。熟悉的舊日世界正在被混亂、瘋狂、荒誕、暴力撕扯得面目全非,“一種世界已無藥可救的壓迫感”,讓人無望。而她的好友、有“歐洲最后一位文人”之稱的本雅明就在這一年于絕望中自殺—為逃避德國的侵略,他努力逃到了法國北邊的莫城,結(jié)果這里是法國唯一一個在1939年秋天遭到德軍轟炸的地方。
6月份,法國向德國投降,拘留營內(nèi),焦慮不安彌漫。在權(quán)力交接的真空期,拘留營內(nèi)的人有一天的時間可以選擇是去是留。阿倫特沒有猶豫地離開了。但更多的人選擇留下來,比起追尋飄渺的自由,她們更擔心外面的世界不安全。
盡管阿倫特告訴剩下的人,這里可能會被德國人接管,但收效甚微。在總共7000名被拘女性中,只有約200人離開。留下的人,后來很多都被送去了德國的集中營,走向更悲慘的命運。
阿倫特,出生在德國的猶太女性,因為自己的種族身份,兩次受到直接迫害,與死神擦肩而過。驚險而痛苦的遭遇切身且真實,觸發(fā)她的思考。這個師從海德格爾修習哲學的女孩,不再是哲學家阿倫特,而是意味深長地自我選擇成為政治思想家、政治理論家。
她投身人類現(xiàn)實,觀察、理解,持續(xù)地思考:為什么在20世紀會發(fā)生如此罕見的大規(guī)模屠殺?納粹的罪行為什么幾乎暢通無阻地發(fā)生卻沒有受到有效阻止?在人類之間,惡是如何變成一種機制而產(chǎn)生作用的?人的思考是否有助于減少惡的破壞?
“深淵之門打開了”
1964年,也是讓阿倫特名聲大噪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出版的第二年,聯(lián)邦德國電視臺播出了君特·格拉斯對漢娜·阿倫特的訪談。這是如今我們能找到的關(guān)于阿倫特為數(shù)不多的真實影像。
在那次訪談中,58歲的阿倫特戴著眼鏡,身著連衣裙,煙不離手,嗓音沙啞,幾乎一直蹺著二郎腿,倚靠在沙發(fā)里,但談吐有力。她談到,最令她震驚的,不是1933年納粹上臺、希特勒掌權(quán),因為那是當時大家都能預(yù)期到的事情,而是1943年她和丈夫突然知道了奧斯威辛的存在。
起初他們并不相信,不僅僅是因為如此大規(guī)模的普通人被集體關(guān)押并遭到虐殺實屬駭人聽聞,更是因為他們認為這在軍事上毫無必要,是多此一舉。她的丈夫布呂歇爾是軍事史專家,他勸阿倫特不要信以為真,從歷史上來看,這根本說不通。
直到半年后,證據(jù)慢慢出現(xiàn),他們不得不相信。
驚駭。她形容那種感覺,是“深淵之門打開了”。“過去人們會相信,任何事都是可以彌補的,但這件事無法彌補,其他事還可以說,這是沒辦法的、被迫的,但這件事完全不一樣。”
這個于1940年開始運作,到1945年被蘇聯(lián)紅軍解放的集中營,五年間,其中被殺害的遇難者達到110萬人,包括20多萬兒童。

阿倫特將它形容為“一個碩大的產(chǎn)業(yè)”“一個生產(chǎn)尸體的工廠”,無辜的、手無寸鐵的人在里面被虐待,像害蟲一樣被毒氣成批地殺死,毫無尊嚴。像這樣為了死亡而存在的集中營,納粹時期多達兩萬個。
這是不可理解、也不可原諒的惡,它讓阿倫特永遠無法釋懷。
而對納粹政權(quán)來說,用毒氣集中且系統(tǒng)性地殺害猶太人,是經(jīng)過了科學討論的“最佳方案”。
1941年,赫爾曼·戈林指示黨衛(wèi)軍首領(lǐng)海德里希,拿出對猶太人的所謂“最終解決方案”,決心在生理上整體消滅猶太人。在此之前,他們設(shè)想過把所有歐洲猶太人海運到馬達加斯加,那個離非洲東南海岸不遠的海島上,也設(shè)想過在波蘭尼斯科地區(qū)建立猶太人區(qū),將他們隔離,但最后因為各種費時、費力、費錢的原因而作罷。
海德里希在萬湖別墅召開了秘密會議,對最終解決方案進行討論。15名副部長級的納粹高官參加,其中就包括艾希曼。會上,在座的官員討論了對于擁有1/2或1/4血統(tǒng)的猶太人,應(yīng)該殺死還是絕育,討論了是否需要保留猶太人里的軍工技術(shù)工人,討論了行動執(zhí)行過程中是否會出現(xiàn)亂子,也討論了執(zhí)行人員的士氣和精神健康是否會受到影響,但唯獨沒有認真討論讓猶太人整體消失是否在根本上違背人類道德。
他們沒有遭遇“良心危機”。至于選擇毒氣室,而不是槍決或注射致死,乃是因為它高效率、低成本,對執(zhí)行者的精神傷害最小。
隨著史實的揭開,人們看到,一種對納粹口中“沒有價值的人”的系統(tǒng)性處決,是如何在那一時期登峰造極的。原來早在1939年,最終解決方案之前的兩年,希特勒已下令對德國的精神病人實施安樂死計劃,并用特別行動隊來屠殺吉普賽人、蘇聯(lián)戰(zhàn)俘、反社會分子、猶太人,以及一些納粹政權(quán)不喜歡的人。
而這一人類歷史上持續(xù)的、大規(guī)模的排斥和殺戮,就那樣發(fā)生了,幾乎是出人意料地容易。
“那里什么都沒有”
為什么?人們急需理解。
阿倫特在1945年的一篇短文中寫道:“惡的問題是戰(zhàn)后歐洲知識分子生活的根本問題—正如死亡是上一次戰(zhàn)爭后的根本問題一樣。”
惡不再是像傳統(tǒng)的宗教戒律那樣,偷盜、殺人、說謊,諸如此類的個人行為;相反,惡成為一種集體結(jié)果,它借著公眾意志、惡政惡法,消除了人的差異,也消除了人的自發(fā)性,“讓人變得多余”。而那些隨大流做出傷害之事的人,不見得在平時待人接物中是多么惡毒。
德國戰(zhàn)敗后,被關(guān)押在紐倫堡的納粹黨徒,曾廣泛接受過不同方法的心理測試和人格測試,大多沒有異常,不是變態(tài)。這包括艾希曼,這個平庸得讓阿倫特生氣的納粹前黨衛(wèi)軍官,猶太人大屠殺中執(zhí)行“最終方案”的主要負責者,是他組織運送歐洲各地上百萬的猶太人到集中營的。
納粹戰(zhàn)敗后,他逃跑了,藏在阿根廷。1960年,艾希曼被以色列特工發(fā)現(xiàn)、逮捕。當時,漢娜·阿倫特已在美國流亡了近20年,她和丈夫也過上了平穩(wěn)安樂的生活。
艾希曼的出現(xiàn)讓阿倫特不再平靜。她渴望了解這個納粹黨徒,是個什么樣的人,為何做出了如此可怖的事,所謂的納粹人格,是否存在。
以色列總理本古里安,特意將艾希曼運作到以色列接受審判。阿倫特向《紐約客》編輯提議,自己可以為之報道,得到了后者的欣然答應(yīng)。而后,她幾乎是急不可耐地飛到了特拉維夫,旁觀了庭審。
但結(jié)果讓阿倫特大失所望,又感到可笑。艾希曼讓她的思考和理解挫敗了,因為“那里什么都沒有”。
艾希曼沒有心理疾病,也不是什么殺人魔,沒有親手殺過人,甚至沒有親眼見過殺人。他乏味得可怕,只是一個平庸的服從者。他不是出于信仰入納粹黨,甚至沒有看過希特勒的《我的奮斗》。
阿倫特觀察到,艾希曼只是一個不思考的人,內(nèi)心極為空洞。“無論他是在阿根廷還是在耶路撒冷寫回憶錄,無論是面對警官還是法庭,他說的總是同樣的話,用同樣的詞。你聽他說話的時間越長,就越會明顯感覺到,這種表達力的匱乏恰恰與思考力的缺失密不可分。確切地說,他不會站在別人的立場上思考問題。之所以同他無法進行任何交流,并不是因為他說謊,而是因為他周圍環(huán)繞著堅固的壁壘,屏蔽他的言辭和他人的存在,從而幫他一并拒絕著真相。”
這樣的艾希曼,并不特別邪惡或病態(tài),他只是非常淺薄,可以適應(yīng)并且順應(yīng)納粹體制的各種要求,能毫不困難地接受完全不同的規(guī)則。比起把成百上千萬的猶太人送進運往生命終點的卡車,他對于自己被指控傷害一個猶太男孩的憤怒反應(yīng)更大。

就是這樣普通的人,日復(fù)一日勤勤懇懇地上著班,在日常生活中似乎還挺有道德,和其他像他一樣的人一起把600萬猶太人送進了地獄。
這簡直讓人難以接受。它昭示著無數(shù)普通人的潰敗,他們擱置了思考和判斷,任由自己變成施害者,而完全不覺得有罪。艾希曼不斷自我辯護,他并不位高權(quán)重,他唯一的感覺只是:“一切都發(fā)生得太快太突然。”
納粹政權(quán)所做的,無論是依靠一些語言的伎倆,如把滅絕、屠殺替換為“最終解決”“外遷”“特殊處理”來減輕人的不適,還是依靠恐怖來壓制反對者的聲音—艾希曼說他身邊沒有其他反思或讓他感到不安的聲音—都讓人們的服從變得沒有阻力,順理成章。
《漢娜·阿倫特:愛與惡》一書的作者如此寫道:“在第三帝國,惡和殘忍并不誘人,它們只是沒有遭到禁止而已。它們就是被頒布的法令。當艾希曼把數(shù)十萬人投進毒氣室時,他并沒有屈從于誘惑。這其中隱含著一個令人不安的真相:人們往往會選擇阻力最小的路徑,忽視自己的良知,從眾而行。隨著對猶太人的排斥、迫害和最終的滅絕日益成為常態(tài),只有極少數(shù)人還能提出抗議并堅守自己的原則。”
“只愛我的朋友”
這場審判,整個猶太人社區(qū)都很關(guān)注。阿倫特的親友們也期待她會怎么書寫。
但阿倫特交出的稿子,在猶太人中炸了鍋。
她的思考不僅沒有讓他們滿意,反而惹怒了他們。以色列甚至派出特工,試圖阻止書籍的出版。
他們譴責道,阿倫特幾乎模糊了受害者和施害者之間的界限。她對于施害者艾希曼,描寫過于輕巧,反而對于她自己的猶太同胞,語含指責之意。
原文中,尤其這段話,刺激了無數(shù)猶太人:“無論在地方還是國際上,都存在猶太社團組織、猶太黨派和社會福利組織。猶太人無論在哪里生活,都有公認的猶太領(lǐng)袖;而這些領(lǐng)袖,無論采取什么樣的方式,出于何種原因,幾乎都毫無例外地同納粹合作。真相是,假如猶太人民的確沒有組織、沒有領(lǐng)袖,那么就會亂象叢生,災(zāi)禍遍地;但是那樣一來,受害者的總數(shù)很難達到450萬到600萬之間。”
阿倫特近乎冷酷的筆觸,在大屠殺未遠的年代,實在是深深傷害了許多猶太人的民族感情。
對于四面八方而來的謾罵指責,阿倫特會認真對待,但并不在情感上太受影響。真正讓她在意的是,她深愛的朋友,也指責她缺乏“對猶太人的愛”,不關(guān)心“猶太人的團結(jié)”。
電影《漢娜·阿倫特》對此有所表現(xiàn)。《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見報后,阿倫特極為珍重的好友、猶太復(fù)國主義領(lǐng)袖庫爾特·布魯門菲爾德恰巧病重,他在病床上從媒體報道中看到了對阿倫特的嚴厲批評,因此對阿倫特非常憤怒。阿倫特趕去見他,辯解說她被誤解了,但最終也沒有被庫爾特原諒。
她對病床上背對著她的老朋友解釋道:“我為什么要愛猶太人呢?我只愛我的朋友。可我的朋友因為我不愛猶太人而不愛我,或者因為我不以他的情感方式愛猶太人而不愛我。那么我的朋友到底愛的是我嗎?”
在現(xiàn)實中,她對朋友的書信回復(fù)是:“不能說因為我是猶太人,我就愛猶太人。”
在同君特·格拉斯的對談中,她再一次談到這個問題:“一般說的愛,是指人們之間直接的關(guān)聯(lián),如果人們把愛帶上談判桌,再說我是邪惡的人,這根本是一場災(zāi)難。”
阿倫特是一個極富于魅力的人。在她的朋友中,她曾對知識分子感到失望。
在納粹形勢最為嚴峻的時候,她發(fā)現(xiàn),是知識分子發(fā)生了最為快速的轉(zhuǎn)變,他們幾乎毫不猶豫地沉淪了。
那時候,“不是我們的敵人做了什么,而是我們的朋友做了什么”。
在和納粹合作的氛圍中,似乎一個人周圍形成了一塊空地。在知識分子中,“合作”成了規(guī)則,但在其他人那里就不是這樣。
阿倫特觀察到,對理念的熱情使知識分子喪失了道德敏感性。他們用看似高深的學說、邏輯,輕而易舉地臣服于納粹,這才是最糟糕的。“如果一個人的合作是因為他必須養(yǎng)活家庭,他不會受到責備,但這些人真的信仰納粹。”
這使當時的阿倫特深感失望,她曾決心再也不和知識分子打交道。她也真的有一段時間遠離了學術(shù)工作,而特別注重實踐和行動。
辨別是非的能力
如何才能抵制惡,這是阿倫特后來思考的重心。“我所要做的,只是去理解,重要的并不是知識,而是判斷是非、分別美丑的能力。”
但是,如何才能辨別是非,尤其對于我們沒有親歷過的事情?
艾希曼為自己辯護的一個重要理由是,他身在其中,沒有別的辦法,也難以退出。他不愿判斷,不想判斷,對這樣的人,可以怎么辦呢?
還有一種人,一種自稱為內(nèi)心流亡者的人,他們從內(nèi)心反抗納粹政權(quán),他們是生活在“盲信的大眾之中而又背棄自己民族的流浪者”,但是他們也保持了沉默和順從,并不明目張膽地反抗。
有一個這樣的人告訴阿倫特,為了保守好自己是內(nèi)心反抗者這個秘密,他在露面時不得不在外表上比普通納粹更像納粹。如果不想像納粹一樣活著,唯一方式就是不露面。
在龐大結(jié)構(gòu)性力量面前,對于不堪重負的個人,阿倫特用哈姆雷特的詩這樣形容:“這是一個顛倒混亂的時代,倒霉的我卻要負起重整乾坤的責任。”
她首先區(qū)分了罪和集體責任。
有些善良的人,他會為了自己所在的國家、族群而對曾被壓迫者感到負罪,比如白人自由主義者對黑人,希特勒時期的普通德國人對猶太人,但阿倫特對這種熱心腸異常地冷酷。她說,那種“我們都有罪”的叫喊實在是沒有必要,因為這反而會為真正有罪的人開脫。
罪過必須是個人的,“在所有人有罪的地方就沒有人有罪”。她舉例說,好比一個人在犯罪組織里,那么要判斷的應(yīng)該是這個人在組織里參與的程度,他起到的作用,而不是以宣判這個組織有罪來代替這個人的具體罪責。
集體責任不一樣,對于前面那種人,他們可以因為良心的不安而感到自己負有一種責任。它的前提是,“要我負責的必須是我沒有做過的事情,這又是因為我是一個組織或集體中的成員,這種關(guān)系不能被解除”。
但阿倫特知道,道德只對有道德的人才管用,只對有良知的人才有效。對于不覺得自己有問題的人,他們只能被擊敗。
而道德,按照阿倫特的解釋,與通常的印象相反,它無關(guān)外在標準,只建立在人和自己的關(guān)系上,它的唯一標準就是是否違背了內(nèi)心,“與整個世界相矛盾要比與自己相矛盾要好”。
這要求人有深入自己的能力,與自己能夠深度對話,知道自己厭惡什么,又相信什么。這些是一個人來自經(jīng)驗而自我產(chǎn)生的。反之,“如果人們只是對事情的表面浮光掠影,或者允許自己不深入事物時,這些自發(fā)的根基就會缺失”。
那些總是高喊崇高的道德原則的人,以及那種堅持固定標準的眼光短淺的道德學家,阿倫特很看不起,她諷刺那種人甚至會比“垮掉的一代”更容易變得無恥,成為罪犯。
類似“勿以惡小而為之”的訓誡所提示的,阿倫特看到,納粹利用了人的弱點。她舉例說,在徹底滅絕猶太人之前存在一系列漸進的反猶措施,“由于人們被告知拒絕合作就會使事情更糟,因此每一項措施都被接受了—直到再也沒有更糟的事情能發(fā)生”。
所以,她告誡說,那些不參與納粹統(tǒng)治下的公共生活的人,可以通過逃避“重大的責任”來拒絕支持,而對于那些軍官、精英,那些喪失或放棄了思考和判斷的責任的人,應(yīng)當問一句“你為何支持”,而不是“你為何服從”。
作為20世紀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漢娜·阿倫特對現(xiàn)實的深度關(guān)切,使她的思辨極富現(xiàn)實感,區(qū)別于沉醉于沉思生活的哲學家。而她的冷酷、她的堅韌、她的思考能力,又使她具有一種足以穿透時間的尖銳。
納粹之后,她發(fā)現(xiàn)了仍然潛藏于現(xiàn)代政治中的下列“因子”:普遍無根的孤寂境況,在于現(xiàn)代社會那種將人逼退回私人生活的趨勢,人的生活內(nèi)容完全變成工作和消費,這將使人退回生理需求而自我封閉,無法“在心靈活動中尋獲他在世界中的安身立命之處”。
對于身處現(xiàn)代境況的人,阿倫特是思想上的友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