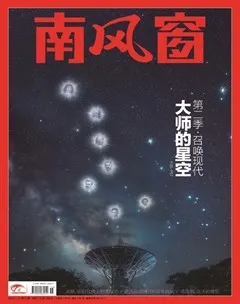抵制全面戰爭的誘惑
不久前,人們紀念了1944年在諾曼底海灘上犧牲的數千條年輕生命。媒體激烈批評英國首相里希·蘇納克,認為他略過了一些紀念活動,但值得一問的是:榮耀歸于什么?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很少有人質疑派遣士兵參戰的理由。19世紀,受到人道主義和資本主義經濟興起的推動,人們才開始質疑要求年輕人參加戰斗的原因,從而引發了第一波現代和平運動。
1914年一戰爆發時,民眾的熱情蓋過了新生的和平運動,歐洲主要政黨團結在各自國家的身后。但戰爭的災難性死亡人數很快又提出了一個問題:這樣的犧牲是否合理?威廉·格哈迪在他1925年的小說《多語種》中寫道:“參戰國中仍有許多失去親人者認定死者是為高尚而有價值的東西獻身,以此安慰自己。”他又補充說,這是一種“惡作劇的錯覺”。他們的死者是成年人愚蠢的受害者—這些成年人把世界誘入了一場荒謬的戰爭,現在建造紀念碑來平息這一切。
一戰期間士兵陣亡900萬、受傷2100萬,二戰期間士兵陣亡1500萬、受傷2500萬。包括平民傷亡在內,這兩場戰爭和相關事件(如所謂的西班牙大流感),共奪走了近2億人的生命,約占當時世界人口的1/10。殺戮值得嗎?
并非所有戰爭都具有相同的道德價值。正如格哈迪所寫,一戰是一場悲慘且不必要的沖突,但二戰并非如此。今天,我們理所當然地認為必須阻止納粹德國,我們譴責那些在抵抗阿道夫·希特勒相對容易的時候不站出來反對,而是采取綏靖的人。從那時起,“綏靖”被視為一個骯臟的詞。
英國歷史學家A.J.P. 泰勒在1961年出版的《二戰的起源》一書中,提出了不同觀點。他認為1938年的《慕尼黑協定》代表了“英國生活中最好和最開明的東西的勝利”。大多數歷史學家都對這種說法感到震驚,泰勒的名聲從此狼藉。但泰勒試圖傳達的是,在一戰殺戮后不愿對德國發動另一場戰爭并不是天生不光彩的,溫斯頓·丘吉爾一開始曾被廣泛視為戰爭販子。
泰勒也明白,民主不是和平意圖的保證,正如他所指出的,“俾斯麥打了‘必要的’戰爭,殺死了‘數千人’;20世紀的理想主義者打了一場‘正義’的戰爭,殺死了數百萬人”。在他看來,民主理想主義者是基督教傳教士的精神后裔—尋求的不是和平,而是皈依。
聯合國憲章第五十一條承認自衛是戰爭的唯一正當理由,但自衛的定義往往有待解釋。例如,以色列利用自衛來證明其1967年對埃及空軍的先發制人打擊是合理的,美國用先發制人的自衛概念支持其2003年入侵伊拉克,俄羅斯也依靠類似的推理為其2022年出兵烏克蘭辯護。
英國作家安東尼·伯吉斯,將從中世紀盛期到二戰結束的歐洲歷史,分為有限戰爭和全面戰爭的交替時期。從1000年到1550年,歐洲經歷了有限的沖突;隨后是1550年至1648年廣泛的宗教動蕩時代。1649年至1789年間的軍事交戰,主要限于殖民斗爭;而1789年至1815年間的特點是,革命和民族主義熱情推動恢復了大規模戰爭。接下來的一個世紀,以有限的殖民和商業沖突為標志;最后,歐洲在1914年至1945年間經歷了兩次毀滅性的世界大戰。
二戰后80年的相對和平,先由美國和蘇聯,后來僅由美國維系。然而,近年來地緣政治緊張局勢激增,引發了多起地區沖突,有可能升級為另一場全球全面戰爭。諾曼底登陸80周年提供了一個機會,供我們反思準備為捍衛價值觀而做的犧牲。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將和平置于全面戰爭之上,并吸取過去全球災難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