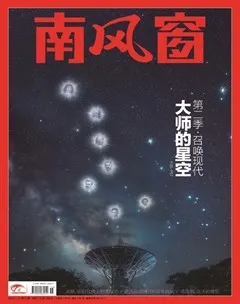司馬光,迂夫的理想

流傳于中國民間故事中的司馬光,是勇于砸缸的少年;大眾常識性認識中的司馬光,是《資治通鑒》的作者,也是站在王安石對立面的“保守派”;歷史上真實的司馬光,則是一個生活和仕途都非常順利的官二代,也是道德標準極高的理想主義者。他生活在北宋政治最好的時代,也親身參與和見證了它的迅速衰落。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趙冬梅的新著《寬容與執拗:迂夫司馬光和北宋政治》,展現了司馬光的完整生命歷程,也貫穿了司馬光時代的北宋政治的興衰變遷。
趙冬梅教授是中國宋史研究會理事,曾出版有《大宋之變:1063—1086》《文武之間:北宋武選官研究》《法度與人心:帝制時期人與制度的互動》《人間煙火:掩埋在歷史里的日常與人生》等著作。
她是專業的歷史研究者,也是積極的公共傳播者,在各視頻平臺開設賬號,分享歷史知識、個人見解,哪怕會遭遇沒由來的攻擊性評論。她相信,“知識是應當被分享的”。在一場北京的新書發布會上,一位小讀者專門從天津趕來,告訴趙冬梅,在她的書里看到了司馬光作為一個寬厚長者的形象,那是之前沒有看到過的。這令她大為感動。
北宋在她眼中,達到了傳統帝制時期儒家政治的最好水平,是一個最接近儒家理想的時代。在政治文化上,它有糾錯機制,寬容公平。盡管它存在的時間很短,但之后的歷朝歷代,再也沒有達到同樣的高度。
近日,南風窗對趙冬梅教授進行了專訪。
一個好的批評家、差的實干者
南風窗:司馬光是你的研究重心之一,這次你的新作《寬容與執拗:迂夫司馬光和北宋政治》圍繞他展開,我也看到你自稱“司馬溫公門下走狗”,不吝于表達對司馬光的喜愛,他為什么打動你?
趙冬梅:這里可能存在某種程度的誤解。我花了很多時間讀司馬光,研究他的生平,寫他的傳記,但事實上想寫的是司馬光所生活的那個時代的政治文化,司馬光是一個線索人物。我選了司馬光,而沒有選王安石,也因為既有研究大部分集中于王安石,關于司馬光更多是標簽式的認識,并不深入。我希望在學術標準和學術積累之上,通過自己的寫作盡量為大家展示一個接近真實的司馬光。
南風窗:可以感受到,你在對司馬光的書寫當中傾注了很多感情,我也看到一些評論,認為你對司馬光流露出來的偏愛,會影響歷史書寫所需要的公允,對此你怎么回應?
趙冬梅:我知道有可能發生這種質疑,不過我甘愿冒著被誤解的風險來寫作。當我們借助材料深入貼近歷史人物,一定要有理解之同情,這種表述就有可能觸犯讀者對公允的認識。寫作過程中,我提醒自己,做到從材料出發,我不能說,也絕不肯說,我一定是客觀的,任何表達都帶有主觀色彩,哪怕是嚴肅的歷史學者,也是如此。我倒覺得那些對此毫無警覺、一味標榜客觀的,讀者要小心。
歷史過去沉睡在黑暗里,只有當一個觀察者把他的目光打上去觀察,真相才呈現出來。所以,歷史本身就帶有觀察者的視角,讀者也應該注意到自己在閱讀的過程中,有主觀視角,這些都無法避免。我們對此保持察覺,就會更接近客觀現實。
南風窗:司馬光給我的強烈印象是,他是個很早熟的人,《宋史》里寫他7 歲就像成人一樣,你的新書也寫,他在17 歲時寫的《功名論》,展現了思想上的驚人早熟。但同時,他的一生很順,在實際事務當中歷練不足,對政治的復雜性認識也不夠,有幼稚的一面。你如何看待司馬光身上這種早熟和幼稚并存的特質?它在文士集團中是否具有代表性?
趙冬梅:司馬光的成長過程確實太順利,他一直受到他的父親司馬池和恩師龐籍的哺育。特別是龐籍,位列宰相,很早就把他引入高層政治,在龐籍兒子死后,又把他作為政治接班人培養。這使他對國家的政治、自己的責任有清晰的認識,有強烈的使命感。但另一方面,他的成長過程沒有經歷多少實際事務的考驗,他沒有做過地方和部門的一把手,缺乏經驗,盡管他在做行政工作時也很努力。
司馬光是一個優秀的批評者,適合站在旁邊觀察,提出意見,讓他來做御史中丞,做諫官,是非常出色的。但當他做宰相,我們看到一個很大的麻煩,他遇到的是宋朝歷史上最復雜的政治局面,而他的歷練、能力、決斷力、行動力、組織力都不夠;并且,他想要的政策轉型和政治轉向,這兩大任務之間存在巨大的內在沖突,而他自己對此似乎完全缺乏認知。這樣的司馬光放到宋朝的政治實務中去,就是一個災難。
另外,司馬光是官二代,他的父輩那一代人總體來講是能干的。他們的歷練來自宋夏戰爭,范仲淹、韓琦、龐籍是在戰場上真刀真槍打出來的,富弼雖然沒有上戰場,但是在外交一線。此外,他們經歷了慶歷新政的挫敗,再度回到朝堂后,都更加成熟。

而司馬光代際的這群官二代,包括范仲淹的兒子范純仁、呂夷簡的兒子呂公著,表現出另一種共性。我感覺他們很厚道,他們對于父輩時代寬容的政治風氣始終有追求,他們希望存大體,保持團結的局面。在政治斗爭中,司馬光不行,呂公著也不行(盡管呂公著的父親呂夷簡是以治術著稱的),范仲淹的兒子范純仁從中年到晚年也越來越寬容,他們對于政治斗爭的殘酷性和復雜性的認識都不夠。
當然,這里可能也涉及政治書寫,但是毫無疑問,他們都不夠狠,當形勢發生變化,或許在心性上可以保持父輩的狀態,但在作為上要調整。一個善良的人,或者對政治抱持著善的追求的人,怎樣才能度過嚴苛,并在之后恢復寬容,這本身也是帶有沖突性的命題。
司馬光偏重道德,有道德潔癖,但他也不能代表文士整體。在他之外,王安石、曾布、章惇,這些人的政治手腕更強硬,在解決宋朝國家所面臨的財政問題上,也更有辦法。
南風窗:北宋的政治設計,有沒有注意把批評者和做實際事務的人區分開,不僅在制度上,而且在人的選任上?
趙冬梅:北宋的前中期,曾經出現過專人專任的情況。比如財政官員,只在財政系統中提拔。宋朝的財政官員,地方有轉運使、轉運判官、江淮六路發運使,到中央是三司,這是一個系統。但是到仁宗朝,甚至更早一點,財政官員的專業化程度和對專業化的高需求,被職位所代表的等級地位取代。
三司使類似國家的財政部長,按道理應該從底下提拔,轉運使、江淮六路發運使做足了年頭,積累了經驗,再到中央來做三司的副使、判官,經過職位迭任,最后被選拔為國家財政部長,如果是這樣運作,還比較合理。但是后來三司使成為一個升遷的梯級,為了往上走去做宰相、樞密,從而進入中央領導集體。結果,這樣一個關系到國家運轉的重要部門的職位,變成了中轉站,官員在這踩一腳,嘣一下就上去了,沒人會好好做事。隨著要升遷的官員越來越多,慢慢地,整個官僚體制也就變味了。這個規律在中國歷史上,一遍又一遍地重演。
司馬光的困局
南風窗:司馬光的身份多樣,做過諫官、行政官員,也是文學家、歷史學家,他寫歷史的時候是旁觀者,做諫官的時候可以批評,但當他去做實際事務就不一樣了,沒有當初那樣寬容。他自己對身份的變化有沒有感知,是怎么取舍的?
jFEpbRFx/pU8tYLycjG/YMMSjMGbNLgU2zs6BonSn0c=趙冬梅:司馬光做諫官時是一個優秀的官員,但是我不認為他做宰相就不再寬容。其實這里有一個邏輯上的調轉。做宰相的司馬光仍然贊同寬容、相信寬容,并且也努力寬容,只是他在相位,并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可以主導,政治的運作是一件極其復雜的事情,是多種力量碰撞的產物。
司馬光的特點是一以貫之。他一直相信秩序,他的思想不具備任何革命性。在這一點上,他比王安石更有代表性,那個時代大多數的統治精英是像司馬光那樣認為的。他理想的朝堂應該是寬容的、鼓勵批評的。哪怕他當了宰相,也仍然鼓勵批評,只不過這個時候做不到了,從邏輯上就做不到。
在司馬光的理想中,首先應該有一個仁慈、英明、神武,有判斷力和決斷力的皇帝,作為最高決策者,也是官員不同派別之間的仲裁者。皇帝底下不同的政治派別、不同的意見之間,在朝堂之上可以相互碰撞、相互競爭、相互討論。在討論結束之后,皇帝做出一個符合朝廷整體和長遠利益的決策,然后就往前走了。這個理想,他年輕的時候篤信,到了晚年也沒有背離,但是在他晚年,并不存在這樣一個能夠有效行使皇權,擁有仁、明、武三德的人物。小皇帝不行,剛剛開始攝政的太皇太后高氏也沒有這個能力。
最初高氏倚重的就是司馬光。所以在邏輯上存在兩個司馬光,一個是作為太皇太后外腦的司馬光,還有一個是在朝堂之上作為多元政治之一元的司馬光。當作為太皇太后外腦的司馬光作判斷的時候,可以推想,他會認為作為多元之一元的司馬光說得對。但是事實上司馬光無法左右朝堂。在這我要再次強調一點,政治是一個特別現實的事情,我們不要把人抽象化,也不要把朝代國家抽象化,當然也不能把那個時代的朝堂之間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抽象化。
我們在他的文集里看到,他在當宰相之前,跟太皇太后之間,不管是口頭的還是書面的交流都非常頻密,可他當了宰相之后,跟太皇太后的交流就被一簾隔開,太皇太后垂了一道簾子,而他在簾子的外頭,他是和其他宰相們一起去見太皇太后的。那也就意味著,他放棄了對太皇太后的引導。
冀小斌教授在他的英文著作《Politics and Conservatism in Northern Song China》里,指出一個很重要的事實:太皇太后雖然非常堅定,但她沒有政治經驗,需要被教導,司馬光最初在教她,可司馬光當了宰相就放棄教她,接下來誰在影響太皇太后?諫官。我們在材料里面可以看到,“臺諫官”幫她預測,接下來要跟誰談什么事,要怎么問、怎么跟對方說話,然后太皇太后就這么問的,一步一步地把宰相駁倒。
南風窗:諫官不再滿足于站在旁邊,走進了場內,帶來什么樣的影響?
趙冬梅:諫官是觀察者、監督者和批評者,但并不是政治的外人。諫官有一大特色,他們往往是中生代的政治家,相對年輕,又由于他們是批評者的角色,我們可以想象得到批評者大概是什么狀態,其實讓他們做也未必做得好。批評者的目標不是寬容,批評者是要被寬容。在批評者調教下的太皇太后,被調動起了對權力的欲望、掌控的能力,所以也未必是司馬光放棄了繼續深刻影響太皇太后。
司馬光曾對自己這時候的處境有一個真實描述。我在《大宋之變》和《寬容與執拗:迂夫司馬光和北宋政治》里都講過,司馬光給范純仁和他家鄉子侄的信里,都提到他當時在心理上是“如黃葉在烈風”,搖搖欲墜。他其實很不篤定,身體狀況又不好,不知道哪天就會去世,他會非常急迫地把他認為重要的事情趕緊解決掉。

但司馬光也有認知偏差,他對于王安石15年的政策措施,沒有持續跟進。英文里有個詞叫update,我覺得這很重要,要不斷地update,但他沒有,所以他對于王安石變法的認知停留在15年前。而且他也有信息繭房,這跟今天是一樣的,我們在朋友圈里已經屏蔽了那些很討厭的人,在微博上也拉黑了一些尖銳的人。留在我們圈里頭的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但我們要提醒自己,保持對于不同意見的開放,尤其是自以為知識分子的人,要保持開放,只有這樣才能了解真實的世界。
南風窗:鄧小南老師在《祖宗之法》里寫道,趙宋雖然推崇讀書,但真正擔當國家要事的、執掌國務的宰執群體,大多并不以儒學著稱,而是比較擅長于治世,這和我們原來的一般印象不太一樣。
趙冬梅:宋朝是一個國家政權,追求的是趙宋統治的長治久安,政府要運作,要維持一個龐大的軍隊需要,當然要用實務的官員。另外,文士在宋朝確實出現了,這些士大夫是一群新人,因為從宋朝,特別是第二個皇帝太宗開始擴大科舉取士的規模,有著深厚儒學修養的文臣的占比提升,當他們受到重用,就變成了國家政治的主導者。用劉子健先生的話來講,他們是文臣中的儒臣,但是這不代表他們沒有行政能力。
如果我們從開國一直看到司馬光代際,會發現后一代的儒學修養在增加,但一部分人的實干能力也是下降的。王安石是既有著深厚的儒學修養(鄧先生說他是宋學的開山祖),還有著非常強的實干能力,他提拔起來的人中,也有很多人有實干能力。
往大了說,幾乎所有在中學語文課里當文學家來處理的古人,首先都是國家官員,或者試圖成為國家的治理者,包括求仕失敗了的李白。唐宋八大家里,王安石做到宰相,蘇轍、歐陽修做到副宰相,曾鞏是高級官員,蘇軾也是能干的。千萬不要把蘇軾僅僅看作一個文人,只會喝酒、吟詩、作畫、彈琴,他做實務不比任何人差,而且他還有一顆為民之心。
不可把王安石和改革者畫等號
南風窗:你強調不要抽象化國家和政治人物,王安石和司馬光這兩派人,一般被抽象為改革派和保守派,或者新黨和舊黨。想請你談一談,你如何評價他們?他們怎么認識朝廷的目標和社會的利益?這場爭斗對宋朝有什么樣的影響?
趙冬梅:劉子健先生曾經對于宋代的官員做過一個分類,有最崇高的理想主義者,他們底下是二流的追隨者,司馬光跟王安石都屬于理想主義者,他們都是為了國家好,如果說愛宋朝是愛國,他們都是愛國主義者,還有,其實我覺得切不可把王安石跟改革者畫等號。
朱熹有一句話說得非常好:“當是時,諸賢都有變更意。”不是只有王安石有變更意,司馬光也有改革的愿望,但是神宗選擇了王安石,而王安石的變更,以及他所追求的,有一些在司馬光看來不可接受。
王安石變法最核心的追求是富國強兵、政府增收,但司馬光看到,之前的宋朝追求的是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平衡。王安石雖然說“民不加賦而國用饒”,但只是不加那種按土地財產征收的稅賦,他采取的是另外一些非常聰明的方法,比如青苗法、免疫法。但司馬光認為,“民不加賦而國用饒”在本質上是不可實現的,如果要富國,可能就會窮民,這是與民爭利。
今天很多人鼓吹王安石變法,其實有一個誤區,就是我們會以改革開放以來的經驗去看宋代,好像社會財富在短時間內的大量增長是可以實現的,但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生產關系有過大的調整,有一個早就富裕發達的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可學,還有以海外華人華僑為主的資金支持,以及全球性的市場。宋朝這些都沒有,所以某種程度上來講,我覺得司馬光講的是對的,但是對王安石變法也不可過度苛責。
這里有一個大問題,就是從唐后期到宋朝,存在著一個財政需求增大的趨勢,國家統治向毛細化發展,養活的官員越來越多,還有募兵制度這樣的職業兵制度,使得國家財政的壓力不斷增加。唐后期以后,中央財政的汲取能力也在不斷增強,但是增強到什么地步是合適的,這個問題我其實沒有想得特別明白。在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對于王安石c1d207666eb6d432d00168af8ff14399變法不做過多的價值評判,還要留在未來思考。
但我關注到王安石變法在政治風氣上的改變。變法以前,宋朝有一個寬容的、鼓勵批評的政治風氣,但是王安石和神宗為了快速推進變法,“定于一”,反對批評,由此造成官僚集團的工具化。神宗曾經表彰過一個叫吳居厚的京東轉運使,神宗給他的批示里說,他能夠不辱使命地完成任務,在“二三年間坐致財用數百萬計”。別人連定額都收不滿,他能增收,這個人就屬于理財第一能臣。但是后來京東地方爆發反政府武裝活動,口號就是要把吳居厚投進煉鐵的爐子里燒死。因為他為了政府增收,支了很多爐子煉鐵,不允許民間修補鐵器,并且他造了很多鍋,規定老百姓必須從他這里買鍋,這就是司馬光所反對的聚斂。
王安石變法后,政治風氣走向了“三不足”,“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天變不足畏”,盡管這不是王安石的原話,但反映了他的思想。拿掉了列祖列宗,拿掉了老天,拿掉了輿論,還有什么能約束皇帝?在王安石的引導下,皇帝變得更專制,這一點是毫無疑問。
南風窗:在這個過程中,原先為了平衡而做的一些制度設計,還有糾錯的機制,事實上很快就失效了?
趙冬梅:是的,比如臺諫官制度。歐陽修曾經給范仲淹寫過一封信《上范司諫書》,里面說真正有志向的學者去做官,不為宰相,則為諫官。諫官要匡正皇帝,在政策出來之后提出批評,他代表朝廷國家的整體和長遠利益,但是王安石變法之后,就變了。
有一個非常極端的例子,王安石推薦了一個諫官李常。李常到首都時,正值王安石變法剛剛開展,青苗法大部分人都反對,李常也提出了激烈的批評。呂惠卿找到李常,威脅說“君何得負介甫,我能使君終身不如人”。后半句就是赤裸裸的威脅,但前面那句話,最近我才讀出更深一層的意思,這是對宰相和諫官之間關系的扭轉。如果宰相推薦了一個諫官,那也是為了朝廷國家,但是呂惠卿說王安石推薦了你,不能對不起王安石。一個諫官需要對得起王安石嗎?對得起國家就可以了。制度還在,但是不再起作用,這是很糟糕的。
我自己是研究制度出身,但我不是一個迷信制度的人,制度設計固然重要,但是制度背后,人的想法也重要。還有就是風氣,不同的風氣之下,同樣的制度效果可以是天差地別的。
南風窗:王安石和司馬光在民間的印象經歷了什么樣的變化?
趙冬梅:司馬光跟王安石這兩個人是捉對認知的。從南宋以來漫長的歷史中,司馬文正公的形象一直積極正面,而王安石本人的形象和王安石變法的歷史形象是分開的。王安石被認為是一個學問很好、個人私德無瑕的人,但是對王安石變法,長期以來的認知是負面的。
近代以來,王安石的形象有所扭轉。比如列寧同志曾批示:“王安石是11世紀的改革家。”這之后,我們的課本一直都把王安石和改革畫等號。最近這些年,有一件事情我自己也很意外,我在《文史哲》上發表過一篇很長的論文,《司馬光最后18個月的北宋政局》,它是我在寫《大宋之變》寫不明白的時候,為了把問題集中理清楚而寫的。我的那篇論文竟然被羅振宇看到并且介紹出去,知道這件事時,我很驚訝。
我想,這說明在今天,社會上至少存在著一種聲音,重新去看王安石變法,重新去看那個時代的國家與社會。一位外國前輩說,歷史學是過去與現在之間無休止的對話,或者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不妨認為我的論文被讀到就是一個小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