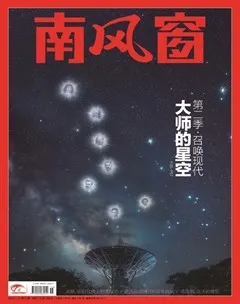英國病再發作,保守黨大敗下臺

7月5日,在唐寧街10號的漆黑大門外,工黨領袖斯塔默作為新任首相發表了第一次演講。在電視鏡頭前,他用“一塊磚接一塊磚地重建英國”這樣仿佛形容災后余生的字眼,來比喻重奪政權后工黨政府面臨的任務。
前一天,在英國提前半年舉行的議會大選中,工黨拿下了412席,保守黨只剩下121席。保守黨籍的前首相特拉斯在自己選區落選,而她的繼任者蘇納克隨后宣布辭去首相職務,并將辭去保守黨黨魁一職。這給長達14年的英國保守黨連續執政期,畫上了句號。
身在中國廣州從事了14年英語教育的大衛,基本上生活軌跡跟保守黨在英國這段執政時期錯開,但他還是決意讓女兒代表自己給工黨投一票。遠隔重洋的大衛,不是工黨的鐵桿支持者,只是策略性地把票投給工黨,以便讓保守黨下臺。“我也許會投給自由民主黨甚至是綠黨。其實選擇還是很多的。但由于英國的選舉制度,只有這兩個大黨才有機會籌組政府。”大衛告訴南風窗。
保守黨過去被英國媒體稱作“理所當然的執政黨”,長期在英國坐大,這次選舉后可能被嚴重削弱。而英國政治版圖在21世紀因應自身國際地位改變而發生的整合與面貌重塑,也得以在這次選舉中初見端倪。
治不好的“英國病”
英國在經歷了14年保守黨執政后,工業生產率掉到主流發達國家的末端。
在1992—2007年那段連續15年相對高速增長的“好日子”里,英國GDP增速還能達到2.68%,在發達國家中算是快速。然而金融危機過后,英國經濟的“舊患”再次發作,工業生產效率從2007年排名G7國家中第二,變成2023年墊底。根據“經合組織”的數據,英國GDP增速在未來三到五年里,將陷入增長率長期低于1%的“停滯”階段,同樣在G7國家中墊底。
可以說,保守黨因應2008—2010年金融危機上臺后,用14年的時間給出了一份讓選民們極不滿意的經濟答卷。
在歐洲金融危機后執政的保守黨政府,推行了5年多嚴酷的財政緊縮政策,在剛走出危機陰影后又迎頭撞上蘇格蘭獨立公投和脫歐公投,爾后又碰上新冠疫情。在保守黨5任首相治下,英國人發現他們的經濟實力和國民收入水平跟金融危機前相比,幾乎沒有增長。當然,國外投資者和市場從業者也被長達14年的動蕩政局嚇怕了。
新一輪大選過后,工黨政府將要面臨嚴峻的經濟形勢。斯塔默上臺后的第二天,英國商界就開始對新政府施加壓力。“英國工業聯盟”首席經濟學家路易斯·海倫姆,呼吁新首相要“像激光那樣聚焦在經濟增長”上。
今時今日若是撒切爾夫人還活著,她會發現那些在戰后糾纏著英國的問題,依然沒有被徹底根治的跡象。當年“英國病”表現之一是,在所有主要發達國家中,英國的地主階級數量和權力最龐大,然而英國的工業生產效率也相應地在發達國家中居于末端,GDP增速長期在發達國家中墊底。
1980年代末撒切爾夫人的一劑市場自由化藥方,曾經讓英國跳出“低效”泥潭,更讓首都倫敦轉型成西歐金融中心。面對1990年代初開始高樓林立的倫敦金融城,以及連續15年人均GDP跑贏G7集團其他成員的高歌猛進日子,撒切爾夫人的支持者歡呼“英國病被治好了”。
的確,英國在這段時期過上了難得順暢的好日子。但激進的去工業化政策以及過度依賴金融產業,也為日后新一輪“英國病”發作埋下了伏筆。
經過起起落落,低效的“英國病”如今再次發作。根據倫敦政治經濟學院2023年的統計數字,英國的生產效率在2010—2022年被美國、法國和德國碾壓。英國勞動力人口的效能處于原地踏步的狀態,從1990年代高于美法德,演變到現在平均落后18%。
僅僅見過“鐵娘子”風燭殘年樣貌的卡梅倫和約翰遜們,沒能像她當年那樣,再次為英國擺正船頭。卡梅倫任內的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嚴謹的“財政緊縮”計劃,旨在遏制不斷增長的英國國債,然而過于緊縮的公共財政,卻沒換來投資者的青睞。此時的英國已經完成了去工業化,西方金融危機讓英國元氣大傷,急需投資的英國又連續碰上保守黨因為脫歐和疫情造成的多個政治危機,投資者因此望而卻步。在2023年,英國的商業投資率在30個“經合組織”成員國中排名第27,在G7國家中也是墊底。
“英國怎么越來越像意大利?”停滯的經濟和不斷洗牌的政府內閣,在過去14年逐漸成為英國展現給世界的面貌。在多年沉疴積累下,斯塔默上臺后試圖“一鍵重啟”英國經濟,恐怕沒那么容易。
“難以被治理的國家”
長期的投資不足,經濟效率在發達國家中落后,其后果最終也投射在選民身上。
14年前,保守黨在卡梅倫領導下,用“破產的英國”來形容金融危機打擊下英國岌岌可危的經濟面貌。然而到了2024年的這次大選,反對黨工黨主打的依舊是當年攻擊自己的那句口號“破產的英國”。
根據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發布的《終結停滯:英國經濟新戰略》報告,英國國民長期處于經濟低增長和階層差距極度不公的環境,導致了大量高技術人才流失,勞動人口素質被對手趕超,到頭來又影響了英國的投資前景,最終陷入“停滯”的死循環。
根據英國“財政政策研究所”的報告,在2019年大選后的5年里,除了最頂層的20%家庭外,英國各階層家庭的收入都處于萎縮狀態。據統計,英國普通家庭要到2027年才能回到金融危機爆發前的收入水平。
“英國病”的一個重要“病灶”是,決策者在下艱難決定時,面對一大堆頂著王公貴族頭銜的世襲權貴總是制造各種“例外”。奧斯本也是在辭去財政大臣職務多年后,才在自己經營的網絡電臺上披露,自己在執行“緊縮政策”時,總是對王室家族的各項開銷網開一面。當涉及平民生活福祉的醫療、教育和治安基礎建設被大刀闊斧地砍掉時,英女王的一通電話,就能保住自己“最喜歡的風笛軍官學校”。
在法國大革命期間對“激進思想”嚴防死守的英國人,從來不是“自由、平等、博愛”的忠實信徒。躲過了流血暴力革命的英國,也就繼承了多個世紀不變的階層意識。即使是在撒切爾主義留給民間最多致富機會的窗口期,英國社會的不平等指標依然遠超其他西歐國家。如今,處于中下階層的國民生活水準下滑得更加嚴重。跟2010年相比,英國在2024年的露宿街頭人數增加了60%,全國有200萬適齡勞動人口(英國總勞動人口是4400萬)由于健康原因不能從事經濟活動。
《終結停滯:英國經濟新戰略》同樣指出,英國中等收入家庭年收入比德國中等收入家庭要少20%,比法國要少9%。在35歲以下的英國年輕勞動群體,也許要經歷一個漫長的“0加薪”時代。
“英國到底還是不是富裕國家了?”1970年代,因為經濟效能乏力導致社會動蕩,煤礦工人罷工、殯儀館工人罷工、電力工人罷工、鐵路工人罷工、醫療系統罷工……當時英國人的記憶就是“罷工”,社會陷入停擺邊緣,普通百姓的生活水準也大受打擊。到了1970年代末,英國會否成為“第一個從發達國家跌回發展中國家”的衰落王國,成為了朝野熱烈討論的話題。
進入后脫歐時期,“英國的衰落”話題再次被提起,盡管社會劇烈波動還沒到1970年代末的“總爆發”程度。那些經歷過“撒切爾革命”、被打爛飯碗的藍領工人們依然健在,但去工業化造成的加工制造業斷層,導致英國在遭遇金融危機打擊后,難以找到新的經濟增長突破點。
保守黨不再強勢
好像英國這樣一個面積和人口規模不大的國家,似乎在世界變革洪流中失去了前列的位置,逐漸成為跟隨者而不是領先者。而這段低迷時期,剛好是保守黨執政的那14年。
曾長期擔任BBC政治新聞主持人的安德魯·馬爾,在特拉斯擔任44天首相后辭職時斷言,英國保守黨將會失去“理所當然的執政黨”地位,背后原因是英國每次被迫調整自身國際地位,其國內的政黨政治面貌都會經歷一次地動山搖。
眼下這次選舉的結果,在他看來就是政黨格局“地動山搖”的表征。英國保守黨被稱為“西方政治史上最成功的政黨”,一個主要原因是,長期以來英國的右翼保守選民,幾乎只能選擇保守黨。但保守黨這樣一個由“廣泛聯盟”組成的政黨,其內部派系之間的理念有著巨大的差異。立場極端右翼而且又是貴族出身的資深議員雅各布·里斯-莫格,跟一直暗中模仿布萊爾、嘴邊總是掛著環保議題的前首相卡梅倫,立場上就有巨大鴻溝。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為了重奪政權,保守黨內的保守派們容忍“進步保守者”卡梅倫的存在。然而隨著英國脫歐公投引發政壇撕裂,保守黨因應歐洲議題產生嚴重分歧,自身的定位也出現了危機。
面對中間選民,保守黨受到了來自工黨和自由民主黨的挑戰,而在右翼陣營內部,一股挑戰者也開始蠢蠢欲動。由“英國獨立黨”前領袖奈吉爾·法拉奇新組建的一個更加民粹、立場更加右翼的“英國改革黨”,在這次大選中異軍突起。在選前一個月的YouGov民調中,英國改革黨的支持率一度輕微領先于保守黨。選舉結果出來,英國改革黨得票率為14.3%,排名第三,只是由于英國小選區的制度,它在國會里只拿到很少席位。
值得一提的是工黨的長期弱勢地位。在20世紀,英國保守黨共執政了65年,產生了11名首相,相比之下工黨僅出了5名首相。如今當選的斯塔默,也是工黨創立以來的第七個首相。對于立場偏左的選民來說,中間偏左的自由民主黨一度是兩大黨以外的第三選項,而工黨一直以來并非他們的唯一選項。
也是多虧英國的選舉制度,工黨這次卷走400多個議席,但這個壓倒性多數的背后,是只有34%的得票率,跟2019年工黨慘敗的那次選舉相比,得票率其實只增加了2%。也就是說,英國選民在很大程度上并沒有對工黨產生多大的熱情,只是由于保守黨被改革黨嚴重分票,才導致了鐵票倉不保的局面。從某種程度上看,由于右翼政黨之間的撕裂,在英國選舉制度保持不變的前提下,工黨贏得大選的難度可以說是下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