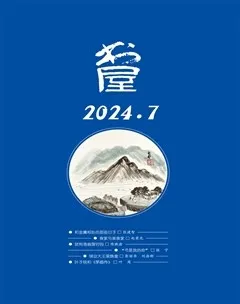2024年第7期書屋絮語
惲鐵樵在錢基博《武俠叢談》序中所言:“童子于古書無不喜《史記》,于《史記》無不喜游俠、刺客諸傳。談荊軻借樊將軍頭,白衣冠悲歌渡易水,非甚窳懦,必愕眙震越,慷慨之氣,現于眉間。是可知勇為達德,實與有生俱以來也。”“《兒女英雄傳》,小說之談武俠者也。兒時讀書村塾,夏夜納涼,嘗為田舍郎道十三妹事,聽者眉飛色動。雖詞俚意淺,而通俗逮下,則為高文典冊所勿如,意頗自信以為小說可為,易能,而又有功。”如此,自《史記》而下,唐傳奇,宋話本,明清公案小說,乃至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勃然而興的武俠小說,作為文類,已成氣勢。湘人向愷然《江湖奇俠傳》《近代俠義英雄傳》,領導南方武俠潮流,繪制江湖譜系,金庸、古龍皆其私淑弟子;此其時,北有李壽民、王度廬、宮白羽、鄭證因、朱貞木所謂“北派五大家”,南北相襯,蔚為壯觀。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以金庸、梁羽生、古龍為代表的新派武俠,炫乎其技,風云江湖。
金庸《笑傲江湖》《射雕英雄傳》等武俠小說出現,頓立新武俠之氣象,樹家國情懷之風格,造英雄之群像,塑兒女之情長,把現代“鴛鴦蝴蝶派”的纏綿和細膩的筆意糅入其中,更添風采。俠之大者,為國為民;俠之為俠,柔情似水。而金庸的家世淵源和所處時代風云變幻,可與其所創作的武俠小說世界“同構”,推己及人,由史而文,因家世而江湖,猶如自話自說,功德圓滿。再其語言,文白夾雜,雅俚兼備,以一當十,意義紛呈,怕應是現代漢語之典范。其小說可作野史筆記來讀,可作范文來借鑒,此乃金庸小說之最大特色。
百年回眸,不勝唏噓。張寶明著《啟蒙中國:近代知識精英的思想苦旅》,“因此,無論對知識分子思想苦旅的梳理,還是對20世紀啟蒙闕失的反思,筆者都并非取一種簡單解構的態度,而毋寧是為了啟蒙理想的重建,這恰如茨維坦·托多羅夫所說的,‘正是通過批判啟蒙思想我們才能始終忠實于它,才可能發揮它的教益’”。作者說出這一段話,是建立在他多年研究《新青年》《學衡》兩本風格迥異雜志的基礎上,二者一正一反,殊途同歸,都在思想啟蒙的坐標上,來確定整個二十世紀知識分子的思索方向與模式;是建立在他念茲在茲的百年思想律動和代表性人物上,牽一發而動全身,環環相扣,以迄止今,諸多糾結,難以清澈見底。
同樣是回顧,夏劍欽編著《傳道濟民與湖湘文化》,他將岳麓書院培育出來的近世湘人先賢,稱為“湖湘巨子”,遴列“湖湘文化八大家”,即王船山、陶澍、賀長齡、魏源、曾國藩、左宗棠、郭嵩燾、楊昌濟。一家之言,自覺可行于世。而趙倚平著《且從詩句看青史》,其題贈有句“錄漢瓦當文,與華相宜”,要之,當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