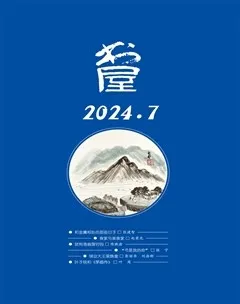《二泉映月》填詞的十條自注
我為《二泉映月》試填之詞,今有男聲、女聲演唱版在網上流傳,瀏覽量過億,質疑聲也不少。為此,我寫過一篇五千字的《關于〈二泉映月〉填詞答網友》,包括“名曲填詞的價值之辨”“《二泉映月》的主題之辨”和“瞎子阿炳的人設之辯”。白話填詞,本不必注釋,就算誤讀也誤不到哪兒去。今閑來無事,加幾條自注,好像也不算多余。
二泉映月,
一城知音半城苦。
一根苦竹,
替我探問人間的路。
泉水悠悠寒與暑,
月光淡淡有與無。
“一城知音半城苦”:有人問此句何意。我想,此句脫口而出,也沒什么深意,大概是說,阿炳在無錫城里知音很多,大家同病相憐,知音也多是受苦人。富貴人家即使春風得意,也不免有失落困苦而能與之共鳴之時。
今日抖音,有語音自動轉文字的功能,有時語音識別有誤,這一句常被誤識為“一城知音半城空”。空就空吧,阿炳琴聲響起,風靡全城,以致萬人空巷,以致一座無錫城,半城為之空,如此這般理解,也無不可。只是這個“空”字沒有落在韻腳上。
“苦竹”:竹子的一種,其筍有苦味。李白《山鷓鴣詞》:“苦竹嶺頭秋月輝,苦竹南枝鷓鴣飛。”白居易《琵琶行》:“黃蘆苦竹繞宅生。”一根苦竹,語言識別為“一根枯竹”,“枯竹”也通。不過,作詩填詞雖不必學江西詩派“無一字無來歷,無一句無出處”,此處“苦竹”其來有自,還是多一點韻致。何況,枯竹之枯,枯在眼里;苦竹之苦,直接苦在人心中。
春夏秋冬,
人生百年能幾度。
東西南北,
不知何處是歸宿。
“春夏秋冬”:這不是一年的四季,而是一生的四季。春夏秋冬,東西南北,這時空的交困、生命的悲傷,屬于阿炳,也屬于天下所有人。
我來到這個世上啊,
誰知我心中的苦?
琴聲有淚淚已盡,
惟愿那山中泉依舊,
惟愿水中月如初。
“我來到這個世上”:這一節三易其稿,改得非常辛苦。2018年8月5日稿:“我不堪天降大任啊,也受不了斯人苦,勞我筋骨,餓我體膚。我只是地上的一棵草,我只要草上的一珠露。”天將降大任于是人,讓他達到音樂巔峰,必讓他先行受盡身心磨難,這也說得過去。但以阿炳的口吻這樣唱,不免有生硬之感。2018年10月23日,前三行改為:“我來到這個世上啊,有受不完的身心苦,光明和自由已不屬于我。”感覺仍不到位。而“我只是地上的一棵草,我只要草上的一珠露”兩句,化用“一棵草一顆露水”的民間諺語,有別于李白“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的狂傲,作為一種卑微人生的寫照,好像也還行,只是游離于《二泉映月》的整體語象。于是我將這五句徹底刪除重寫,斷斷續續,反復推敲琢磨,直到2021年5月27日才算定稿。
命運棄我,
棄我秋風茅屋。
只有那天邊一彎月,
翻過蘆墻來看我,
看我比孤獨更孤獨,
看我比無助更無助。
“秋風茅屋”:“秋風”與“茅屋”結伴,屢見于唐詩,杜甫有詩《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又有詩云“多病秋風落”“自聞茅屋趣”,張繼《宿白馬寺》云“蕭蕭茅屋秋風起”,戴叔倫《題友人山居》云“客懷無計答秋風,數家茅屋清溪上”。本不想襲用唐人語象,卻很難找到替代詞,改“西風茅屋”有點刻意,改“茅廬”則又落入另外的窠臼。詩歌創作要有創意,包括語言的原創、首創,所以要盡量避用前人之語,要“膽敢獨造”(齊白石語),但這獨造之語不能讓人有生造、不文之感。兩難之間,如果不能獨鑄新辭、讓人驚艷,則不妨似曾相識,平易近人。
我知道,阿炳在無錫的故居為磚瓦建筑,并非茅屋、蘆墻,但藝術的再現不必完全寫實。
可恨蒼天不公,
做賊的,眼賊亮,
偏叫樂師去做瞽。
瞎子阿炳已死掉,
沒有死的只是那一把二胡。
“偏叫樂師去做瞽”:瞽,盲人,瞎子。《周頌·有瞽》:“有瞽有瞽,在周之庭。”毛注云:“目無明則耳聰,使為樂官,名之曰瞽。”周朝設大司樂,請失明音樂人去做樂師,是人盡其才。阿炳少年聰慧,精通音律,后染病致盲,流落街頭,“偏叫樂師去做瞽”是憤激之辭,“瞽”在阿炳這里,只是盲人、瞎子。
今中學語文,有文言文《兩瞽》《盲子竊錢案》《召公諫厲王弭謗》《勸學》及《周頌·有瞽》,瞽字頻現,已不算冷僻。
“瞎子阿炳已死掉”:有人說,直呼“瞎子阿炳”不禮貌,說“死掉”也有失敬重,建議改為“阿炳先生已作古”或“已仙逝”。建議者沒有注意到,這首填詞,通篇都是第一人稱,是代阿炳抒懷,代阿炳書憤,從“一根苦竹,替我探問”到“誰為我一哭”,一共用了十二個“我”字。不是毛翰說“瞎子阿炳已死掉”,而是阿炳自己仰天長號:命運棄我,天不容我,但,就算我阿炳瞎了、死了,我的二胡、我的樂聲也會活在人間!
阿炳一生窮,
阿炳一世苦。
弦歌三百首,
首首不果腹。
天生我才有何用,
天妒我才我何辜。
誰為我一哭?
“阿炳一生窮”:這里的窮,有別于貧,所謂日暮途窮,窮途末路,與開頭的“一根苦竹,替我探問人間的路”相呼應。
“弦歌三百首,首首不果腹”:字面的意思,是拉二胡賣藝,艱難謀生,竭其所能,仍食不果腹。字里行間,未嘗不是在感慨世態炎涼,人卑藝賤,質疑著當初“一城知音”的自信。
“天生我才有何用”:“天生我材必有用”是雄心壯志,人所共賞;“天生我才有何用”是人生悲歌,人所共傷,與之相應的是“天妒英才”。
有人問,究竟是“天生我材”,還是“天生我才”?應該說,“我材”是比喻,天生“我”這參天大樹;“我才”是直言,天生“我”滿腹才華。二者皆通,而人們更習慣說“天才”而不是“天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