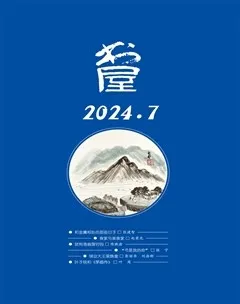《上下五千年》的語言問題
“皇宮招收一批太監。這句話有沒有毛病?”一個小朋友問我。
我回答:應該是想說,皇宮缺太監,要招一批男丁進宮當太監。但歧義是明顯的,好像太監們早已散布于民間,現在皇宮一聲令下要召集他們進宮。你聽起來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這是《上下五千年》里的一句話。小朋友眨眨眼睛,指指腰封上的文字——“中國最具影響力的少兒通俗歷史讀本”,一下子喚醒了我的記憶。從1979年問世算起,這部書倏忽已走過近半個世紀。我這個年齡段的人,多半讀過它。它是否經受住了歷史檢驗呢?
此書作者之一林漢達先生說,寫《上下五千年》是對“新語文的嘗試和舊故事的整理”。可見,比傳播中國古代歷史更自覺的一個寫作動機,是探索歷史故事在文言和白話兩套語言體系中的轉化。這種思路至今不過時,諸如《百家講壇》這樣的節目,以及坊間大量淺近歷史讀物,都繞不開對此的琢磨。林先生沒寫完全書就去世了。接手的另一位作者曹余章先生,盡最大努力保留了林先生(只寫到東漢之前)的稿件文風,而且同樣注意到林先生對“新語文的嘗試”,表示要繼續“用通俗的現代語言寫出來”。可見,對語言的自覺追求,實為此書特色所在。
既然如此,探討一下此書的語言問題想必并不多余。這些語言問題帶有某種共性,也常能在當代文學作品中見到。鑒于兩位作者都已故世,若再重印,也請出版社考慮需不需要在這些地方稍加修訂,以更加切合廣大讀者特別是青少年讀者在語言學習借鑒方面的期待。
先說遣詞不當之處。聊舉五例。
1.他沉思一下,又說:“如果真有天命的話,我就做個周文王吧!”
“沉思”表示經歷一段時間的思考過程,不是瞬間性的,說成“沉思一下”顯然是錯的。
2.沒幾天,這個年紀才五十四歲的丞相終于在軍營里去世。
諸葛亮去世令人悲傷,這個“終于”用在此處,不知要表達什么意思?我多次看到過類似的表達,仿佛是盼著當事人早死,有種償還夙愿、如釋重負的兌現感,這就有點滑稽了。如硬要說這是表惋惜,那也脫不了盼著他快死的嫌疑,終究是別扭的。
3.過了幾天,石勒派了一千頭驢子裝運了糧食接濟桃豹。
只要上下文不是擬人化的童話語境,“派了”的賓語總該是人,因為人才有理智,才會在理智支配下自覺執行指令。說“派了”一千頭驢子去干活,是把一千頭驢子都當成了聽話的軍士,不知驢是怎樣聽懂這種委派的?這里應改為“安排”之類的動詞才是。
4.嘉定軍民堅持抗清斗爭三個月,被清軍屠城三次,犧牲兩萬多人。歷史上把這次慘案稱作“嘉定三屠”。
“犧牲”是指為了某種正義的事業而獻出自己的生命。但在“嘉定三屠”中,盡管有少數反抗者,不幸死亡的“兩萬多人”按書中所述,主要是無辜的平民百姓,包括剛剛到城中避亂的人民,完全是出于被動和無奈而就戮的,不是指有這么多人都上陣拼斗廝殺,因反抗而陣亡,怎么能用“犧牲”一詞呢?
5.張熙無話不談,把他老師曾靜怎樣交代的話都抖了出來。
岳鐘琪誘騙張熙出賣曾靜的言行,張熙是蒙在鼓里而上當的,主觀上絕不想供出自己的老師,這兒卻用了個“抖了出來”的動作性描述——在一般語境下,“抖了出來”的賓語往往是負面的,比如陰謀和機密等,用在不知情的張熙身上顯然不妥,豈非說得他主動作惡似的?
和遣詞不當相關的,是搭配不當,也舉出五例來看看。
6.接著,他又來到棘門,受到的迎送儀式也是一樣隆重。
“儀式”顯然不能和“受到”構成動賓搭配,受到的只能是迎送,應改為“受到的迎送也是一樣隆重”,或者“遇到的迎送儀式也是一樣隆重”才通順。
7.劉表安慰了他一陣。但是劉備心里總在考慮著長遠的打算。
“考慮”即“打算”,說成“考慮著打算”是不通的,“打算”應改為“計劃”。
8.法正這個人心胸狹窄。他有了權,就報個人恩怨。誰過去請他吃過飯,他就回禮;誰向他翻過白眼,他就報復。
心胸狹窄作為貶義詞,和后面報復仇人的行為可以搭配,可是如何能與前面的禮尚往來相匹配呢?請客回禮是正常現象,甚至是值得倡導的做法,扯不上心胸狹不狹窄。
9.李時珍的名氣越來越響,被他看好病的人,到處宣傳李醫生好。
“名氣”和大小相搭配,“名聲”才和響亮相搭配。
10.張居正花了十年努力,進行了大膽的改革,使十分腐敗的明朝政治有了轉機。
“花了十年努力”說不通,“努力”作名詞性賓語,只有“經過十年努力”之類說法,這兒何不直接說成“努力了十年”呢?
這部書中也存在詞序顛倒混亂的問題,像下面四句話即有此弊。
11.后來人們認為屈原是一位我國古代杰出的愛國詩人。
“一位”應移到“古代”之后。
12.自從在秦始皇統治時期打敗匈奴以后,北方平靜了十幾年。
“在”應移到“秦始皇”之后。
13.這樣日積月累,編成一本涉及政治、經濟、史地、文藝等內容極其廣泛的書,叫做《日知錄》。
“內容”則應移到“極其廣泛”之后——“涉及”的賓語是“內容”,而不能是“極其廣泛”。
14.他的兒子和寫序言的、賣書的、刻字的、印刷的以及當地官吏,被處死的處死,充軍的充軍。
最后一句里,正常的詞序排列無疑該是“寫序言的、刻字的、印刷的、賣書的”。
要不要再詳細展開分析一番?似乎不需要了。
主語的缺失問題也時有暴露。
15.按照諸葛亮早已設計的戰略,是打算從兩路進攻曹操的。
多了“按照”兩字,導致全句丟失了主語,誰“打算”?儼然成了另一撥人打算,違背了原意。
16.但是正因為寇準為人正直,得罪了一些權貴,后來被排擠出朝廷,到地方去做知州。
這句的主語表面上是寇準,仔細一推敲卻不然。因為這個主語管的是前面的“正因為”這個狀語,全句真正的主語恰恰被漏了。正確的邏輯關系和說法是:“但是正因為人正直,得罪了一些權貴,寇準后來被排擠出朝廷,到地方去做知州。”
17.在這本書里,一共記錄了一千八百九十二種藥,收集了一萬多個藥方,為發展祖國的醫藥科學作出了偉大的貢獻。
同樣丟失了主語,用狀語“在這本書里”不恰當地替代了主語《本草綱目》,將“在這本書里”改作“這本書”才通順。
18.經過這種稅收改革,防止了一些官吏的營私舞弊,增加了國家的收入。
多了“經過”二字,導致主語不見了。
19.經過他的實地考察,糾正了過去地理書上記載的錯誤。
同理,正確的主語是“他的實地考察”。
有時不只主語殘缺,還出現了其他句子成分乃至整個分句殘缺的問題:
20.這是因為王族內部經常爭奪王位,發生內亂;再加上黃河下游常常鬧水災。
描述的是商朝遷都多達五次的原因。“再加上”,是說前一個原因之外的另一個原因,后面以句號作結,顯然沒把話講完。因為“再加上……”構不成一個自足的句子,理應跟上一句“以至于不得不搬遷”之類的話,句子才完整成立。
和主語缺失相伴隨的,是主語的偷換。
21.燕國本來也是個大國。后來傳到燕王噲手里,聽信了壞人的主意,竟學起傳說中堯舜讓位的辦法來,把王位讓給了相國子之。
在“傳到”和“聽信”這兩個動詞之間,出現了主語偷換,致使后半句的主語也成了燕國,但按作者的本義,“聽信”“學起”和“讓給”的主語都是燕王噲。這種一“逗”到底的長句段,很容易不知不覺發生主語的游移。
22.呂布約了幾個心腹勇士扮作衛士混在隊伍里,專門在宮門口守著。
本意是講,呂布安排了幾名勇士扮作衛士伺機行刺董卓,但一口氣夾雜著說,意思錯變成“呂布約勇士們和自己一起混在隊伍里”,主語成了呂布和勇士們,這和緊接著下文“呂布從車后站出來”矛盾了。
23.曹操認為孫權立了大功,把孫權封為南昌侯,到了曹丕即位稱帝以后,又封為吳王。
對孫權的兩次封王,主語分別是曹操和曹丕,但寫成“到了曹丕即位稱帝以后,又封為吳王”,則“又封為”的主語還是曹操——因為“到了……以后”作為狀語,是不能充當主語的。全句的邏輯表意就不嚴謹。
24.在丈量土地之后,張居正又把當時各種名目的賦稅和勞役合并起來,折合銀兩征收,稱為“一條鞭法”。
這一句里,“稱為‘一條鞭法’”的主語,應該是前面對這套法的整個性質描述,然而這樣順下來寫,主語成了張居正,意思成了張居正將之稱為一條鞭法。而這樣在表意邏輯上也是不通的,因為前面“把”字管的是“把……合并起來”,管不到后面的“稱為”,所以無法理解為“把……稱為”,這就導致了語義上的混亂。
25.他又在研究我國古代歷法的基礎上,吸收了當時歐洲在天文方面的最新科學知識,對天文歷法的研究,達到了很高的水平。
前半句的主語是“他”(徐光啟),后半句則將主語偷換成了“研究”。固然,“研究”是“他”在研究,但“吸收”科學知識是為了“研究”天文歷法,兩個動詞具有一氣呵成的連續性,尤其是在用逗號逗開的情況下,不能被打斷。現在卻被從中間切斷了,造成語義強調重心上的逃逸和發散,語感上明顯不連貫和不通暢。應改為:“他又在研究我國古代歷法的基礎上,吸收了當時歐洲在天文方面的最新科學知識,研究天文歷法,達到了很高的水平。”或:“他又在研究我國古代歷法的基礎上,吸收了當時歐洲在天文方面的最新科學知識,對天文歷法進行研究,達到了很高的水平。”諸君以為然否?
26.李定國是張獻忠手下四名勇將之一,又是他的義子,最大的是孫可望,李定國是老二。
這句更讓人莫名其妙。忽地冒出個“最大的是”,讓人搞不清這是指“義子”里最大的,還是指“四名勇將”里最大的?難道“四名勇將”都是張獻忠的“義子”,其中李定國排在老二?孫可望又屬不屬于“四名勇將”之一?總之,這句話完全把人給繞糊涂了。
句子中出現不同狀態的混淆,是《上下五千年》中屢見的另一種語言問題。看下面七例:
27.商湯建立商朝的時候,最早的國都在亳。
本句問題在于,建立商朝時,就是“最早”時,一個瞬時性動作中不存在早晚之分。“最早”云云,是帶有比較性的事后回溯,和前面的現在進行時混淆在了一起。
28.晉獻公老年的時候,寵愛一個妃子驪姬,想把驪姬生的小兒子奚齊立為太子,把原來的太子申生殺了。
立幼子和殺太子,本來是兩件發生在不同時間段里的截然不同的事,說成“想把……立為太子,把……殺了”,則擰成了一團麻線,把另一件需要作為前提來做的事——殺申生,變成了“想”要做的事,也將之變成“想”的賓語,這就把將來時和現在時混起來了:本意是殺了申生再計劃立新太子,殺申生卻被誤寫成了計劃的一部分。
29.晉文公趁此機會,在踐土給天子造了一座新宮,還約了各國諸侯開個大會,訂立盟約。
至于這一句,問題出在“約了各路諸侯開個大會”這句話多了一“個”字。“開個大會”是將來時意義上的一種意向,譬如說“學校準備開個大會表彰有關人員”。這和前面的現在時“約了”,在時間邏輯上產生了細微的沖突。
30.滅了秦朝以后,他不可能為廣大農民著想。
本句中的“不可能”,是站在將來時角度作出的評價,和前面的現在時描述,不在一個時間層次上。
31.錢镠聽了,表示一定要記住父親的囑咐。
這句同樣多了個“要”字。本來,說“表示一定記住父親的囑咐”就可以了,不但簡潔,而且是從兒子錢镠這邊說的,是在表示承諾和宣誓。然而說成“一定要記住囑咐”,意味上則反過來是從父親的囑咐這邊說的,是要求兒子記住某事的祈使句,使全句出現誤置了言說角度的混淆。
32.狄青每逢上陣,先換了一身打扮。
這句里的“每逢”和“先換了”,同樣混淆了概括和特指。
33.想把英宗贖回來。結果,當然是毫無希望。
“結果,當然是毫無希望”,這樣的造句還是頭一回見到。“希望”與否,是在“結果”出現前的態度,改為“滿懷希望卻毫無結果”才顯得熨帖。
句式雜糅也時而可見。像:
34.曹操把蔡文姬接回來,在為保存古代文化方面做了一件好事。
本句里雜糅了兩套不同的句式。“在……方面”表程度和范圍,“為……”表意圖和目的。只能要么說“在保存古代文化方面”,要么說“為保存古代文化”。
35.這支歌謠傳到明軍那里,使楊嗣昌聽了哭笑不得。
“使”字帶出的是一種狀態,同時接“聽了”和“哭笑不得”這兩種狀態,是別扭的、嚴格說來成問題的,導致全句表述累贅。改為“這支歌謠傳到明軍那里,楊嗣昌聽了哭笑不得”,或“這支歌謠傳到明軍那里,使楊嗣昌哭笑不得”,才清爽。
還存在上下文在語意邏輯上連不起來、失去嚴密照應的情況。
36.在上下五千年的歷史里,有許多動人的有意義的故事。其中有許多是有文字記載的。至于五千年以前遠古時期的情況,沒有文字記載,但是也流傳了一些神話和傳說。
37.我國最早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是從商朝開始的。
第一段說,五千年之前的遠古歷史沒有文字記載,那時的神話傳說是流傳下來的。第二段則說商代開始有文字記載。那么,從距今五千年的那時到商代之間的這段歷史,既無文字記載,后人是從何得知的呢?也是靠神話傳說的流傳嗎?但上面分明把神話傳說的流傳限定在五千年之前那段時間內,于是就出現了一段解釋上的空白。這種地方對于初涉中國歷史的人可能會不太好懂,因為邏輯表達不周密。
這些語言上的問題,不獨為《上下五千年》所有,留心一下即能發現,在不少成名作家筆下也常能見到類似的現象。用中文來準確表達和純熟表達的不易,觀此可見一斑。如今市面上也不乏談語論文的新書,但講宏觀道理的多,微觀剖析具體語言問題的似乎罕見,不禁令我想起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一些好書。比如,1980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語文學習講座叢書》,由中華函授學校編成,其中有本《文章評講》,收錄了葉圣陶、呂叔湘、朱德熙、張志公和徐仲華等語言學、語文學界前輩精心評改的一批文章。把這本書和本文放一起對著看,相信列位看官不至于覺得,我這篇文章是在吹毛求疵吧?要知道,句子殘缺弄不好還可能要命呢!想起一個段子說,某人練《葵花寶典》看到“欲練神功,揮刀自宮”,便忙不迭地自宮成了皇宮外的太監,哪曉得書背面還有一句:“若不自宮,也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