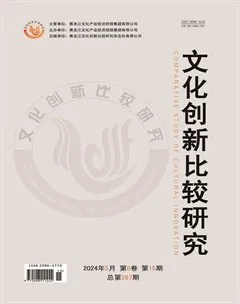文化翻譯理論下地方戲劇黃梅戲的英譯研究
摘要:黃梅戲以其獨特的唱腔、優美的唱詞、極具特色的地方文化表現力深受大眾喜愛,但因中外文化差異,英譯唱詞難以反映地方特色,保留原汁原味,黃梅戲的海外譯介進程較慢,受眾較小。該文在文化翻譯理論指導下,以黃梅戲中的精彩唱段為例,主要探討黃梅戲的英譯策略,具體分析增譯、轉譯及歸化在黃梅戲唱段中的運用,實現文化層面的等值功能,以此為戲劇翻譯提供新的視角,并推動中華戲曲文化的傳播與交流。戲劇英譯是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翻譯的本質歸根結底是目標語群體與源語群體的文化交流,因此,譯者必須注重雙向文化要素,把握戲劇的本土文化特質,同時兼顧目標語的文化要素,推介中華戲曲文化。
關鍵詞:文化翻譯理論;黃梅戲;翻譯策略;增譯;轉譯;歸化
中圖分類號:H315.9;I04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4110(2024)05(c)-0033-04
A Study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Local Drama Huangmei Opera under the Guidance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Theory
FANG Guilin
(Faculty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nhui Sanlian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00, China)
Abstract: Huangmei Opera is widely accepted and popular with its opera tune, libretto, and distinctive local cultural features.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make Huangmei Opera hard to keep its original taste, thus its overseas translation process is slow with limited group audience. The paper specifically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addition, conversion and domestication of Huangmei Opera libretto to realize the cultural equivalence under the guidance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theory in order to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drama trPOQQ138nhY5zDu7FhfcjhA==anslation and promote the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drama culture.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drama is a significant way for 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 essence of translation is th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target language group and source language group. Therefore, translators must focus on the two-way cultural element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loc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drama and balance the cultural elements of the target language, promoting Chinese traditional opera culture.
Key words: Cultural translation theory; Huangmei Opera;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ddition; Conversion; Domestication
在講好中國故事的大背景下,黃梅戲作為地方文化傳承的重要一環,在推動中國優秀文化走向海外,傳播好中國聲音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然而黃梅戲的海外受眾群體較小,海外譯介進程較慢,這與黃梅戲曲本身的特色難以被忠實地還原分不開。黃梅戲以表現湖北黃梅地方特色為主,融合了昆曲、京劇等多種元素,采用安慶官話表演唱念做打,唱詞鮮明,唱腔優美婉轉,尤以襯詞增色。襯詞不同于平詞,平詞即陳述,平詞譯文易懂,反觀襯詞,雖然無實際意義,但給唱詞增添了豐富的感情色彩,如“依子呀子喲”“呼舍”“喂卻”等。然而在英譯過程中,這類襯詞難以找到對應的英文詞匯,海外受眾無法理解此類襯詞的感情色彩。因此,譯文既要結合源語本身的文化語境,向目標受眾輸出源語的內在文化,保證黃梅戲的原汁原味,又要關注目標語受眾的接納程度,滿足目標語群體的文化需求,這給譯者帶來不可小覷的挑戰。實質上,黃梅戲英譯是將中國戲曲推介海外,傳播戲曲文化,弘揚中華文化,翻譯戲劇唱詞的過程即是文化傳播的過程。當今時代,地球村緊密相連,如何將戲曲文化發揚海外成為對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議題之一。本文從文化理論的角度出發,結合黃梅戲著名唱段的英譯本研究黃梅戲的英譯策略,如增譯、轉譯和歸化等,著重詮釋譯文基于文化交流的原則,實現文化層面的等值功能。
1 文化翻譯理論
蘇珊·巴斯奈特在Translation Studies一書中詳細闡釋了文化與翻譯的關系,二者關系密切,譯者不可能脫離文化談翻譯,翻譯的本質即文化交流與傳播,譯文應以轉換文化為基本單位進行。譯者并非簡單地解碼與重構源語,而是要理解、融入、推介源語文化,進而與目標語群體產生文化層面的交流與共振,從而真正實現翻譯的作用——文化交流[1]。其次,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扮演著文化傳播使者的重要角色,這一過程即為源語文化與目標語文化的輸出與交流。不同時期的文化各有不同,語言文化的受眾也不同,譯者在翻譯的過程中,必須注重不同時期、不同地域、不同群體的文化特性,真正實現不同時期、不同地域、不同群體源語文化和目標語文化的功能等值,達到兩種文化之間的交流。
2 文化翻譯理論下黃梅戲的英譯策略
黃梅戲的文化淵源深厚,其唱詞、唱腔及人物動作具有明顯的地方特色,譯文在兼顧目標語受眾文化的同時,不僅要傳遞出唱詞本身的含義,更要讓目標語受眾感知唱詞及黃梅戲曲的內在文化含義[2]。譯者在翻譯唱詞時,可采用相應的翻譯策略,如增譯、轉譯和歸化等多種方式,力求精準地傳達唱詞,調動受眾情緒,感染受眾,讓他們真正地感受中華優秀的戲曲文化。
2.1 增譯
文化等值功能不僅表現在同等層面的文化表現力,還體現在源語文化與目標語文化的共情力上[3]。源語與目標語群體所處的文化、語言環境差異較大,譯者在翻譯時,并非簡單地直譯唱詞,必須在遵循文化可接受性原則的基礎上選擇合適的翻譯策略進行適當調整,讓目標語受眾產生戲曲共情力。比如:黃梅戲唱詞中融入了中國古典神話文化的元素,譯者在翻譯過程中要將中國文化推介海外,就必須展現中國古典元素的意象,但同時要兼顧目標語受眾根植的文化土壤及對中國古典神話文化的理解,才能實現文化等值,有效傳播戲曲文化。
董郎昏迷在荒郊,
哭得七女淚如濤。
你我夫妻多和好,
我怎忍心,董郎夫,啊,
重返凌霄,重返凌霄。
為妻若不上天去,
怕的是連累董郎命難逃。
——出自《天仙配》
Dong Yong fainted in the wild countryside;
My tears ran down like the huge tide.
How sweet and happy I am with my husband.
Dong Yong, my honey, how could I bear to
leave you and return to the Heaven?
But if I do not return to the Heaven,
my Father would make you suffer and kill you.
——朱忠焰(譯)
董永與七仙女的愛情故事流傳至今,七仙女不顧宮規,與凡人董永約定終身,最后被玉帝拆散,以悲劇結尾。《天仙配》融入了濃厚的中國傳統神話故事色彩,其中玉帝即為七仙女的父親。在東方神話中,仙凡有別,等級森嚴,即便凡人羨慕的天上神仙也須遵守森嚴的宮規;而西方的神話體系中,上帝是救世主,人從生下來開始就有原罪,人們通過信仰耶穌基督,洗去原罪,人生便可得救,這一不同的神話背景給譯者帶來了挑戰。譯者既要向目標語群眾表達出唱詞的本義和神話的背景色彩,又要顧及當地群眾對輸出文化的接受度。因此,原文中“怕的是連累董郎命難逃”,譯者并沒有直譯,而是采用增譯的方式,巧妙地將my Father 當作主語。雖然原文中并未提及“我的父親”一詞,但根據上下文含義可知,若七女不返回天宮,玉帝則會處置董永,my Father指玉帝,玉帝即為主語,譯者在此處增補主語,并將Father一詞首字母大寫,與God一詞遙相呼應,當讀者看到首字母大寫的Father一詞時,就能聯想到God。God在西方文化中指上帝,掌管天上人間,救贖一切,Father和God具有異曲同工之妙,實現了源語和目標語文化等值。此外,本句使用主動語態,省略了原文中的董郎,將“命難逃譯成“suffer and kill”,譯文十分清晰易懂。綜上所述,這一譯法既解決了中西神話色彩差異帶來的困惑,同時能夠清晰地交代唱詞含義,并向目標語群體展示中國神話文化,最終實現兩種文化的交流與和諧[4]。
2.2 轉譯
語言是文化的代際符號,語言不同,符號亦不同。簡言之,中文重意,英文重形。意合和形合反映出不同文化群體的思維差異,不恰當的譯文可能導致文化沖突,受眾不理解原文,更無法達到文化傳播的效果。譯者在翻譯過程中,不可拘泥于源語句式及詞性,可采取句序調換、詞性轉譯等方式,結合目標語與源語言的文化軟實力因素,理解雙向文化背后的深層含義,有效輸出戲曲文化[5]。
鐘聲催得眾姐姐回宮轉,
七女我,七女我無心回宮院。
轉身我再把董永仔細看,
他還在寒窯前徘徊留戀。
——出自《天仙配》
On hearing the bell we know it is to go home,
but, I fell so reluctant to go back to the Palace home,
Dong Yong is still wandering in front of the cold kiln,
when I turn round to fix my eyes on him time and again.
——朱忠焰(譯)
“七女我無心回宮院”,譯者將原唱詞中的“無心”譯成謂詞“fell reluctant to”,“reluctant” 本意為“不樂意”“不愿意”,看似與“無心”沒有意義關聯,譯文沒有表達出“無心”一詞的含義,實則傳達出更加精準的譯文。黃梅戲唱詞短小精悍、文風樸實,“無心”將七女聽到鐘聲時焦慮、彷徨的心情描寫得淋漓盡致,從更深層次看,無心反襯內心極度地不情愿,譯者在此將它轉譯為謂詞而非將“回”字直接作謂語,這一譯法能讓觀眾更好地理解唱詞的含義。在英文中,謂詞的作用十分重要,謂語是句子的主干部分,單獨的謂語即可成句,觀眾首先抓住的唱詞即為句子的主干;如果將“回”直接譯作謂語,“無心”作副詞,觀眾便無法感受到七女滿腹焦慮的心思,這將極大地減輕戲劇本身的沖擊力和震撼力。在本唱段中,最后兩句,譯者采用了調換語序的轉譯法,將董永在窯前徘徊的場景作主句,與前一句譯文“七女無心回宮院”形成極強的關聯性,此譯法將七女內心的煩悶與董永的徘徊與留戀展現在觀眾眼前,增強了戲劇沖突[6]。
2.3 歸化
翻譯是源語與目標語的轉換,但文化差異會造成思維、行為習慣等差異。在源語中,對某一抽象物質的表達,難以找到適切的目標語,在此情況下,如果不采取合適的翻譯策略,譯文會顯得十分晦澀,甚至讓目標語受眾感到不適。“龍”在中國被視為吉祥物,而在英美等國,“龍”被視為兇神惡煞之物。因此,在翻譯過程中,譯者必須考慮目標語受眾的文化因素,可以采取歸化的方式,即貼近目標語受眾的思維方式,幫助目標語受眾更好地理解原文,從而推動中華文化走向海外[7]。
馮素珍:舍不得來也要舍,
李兆廷:分不得來也要分!
二人合:這才是流淚眼觀流淚眼,
斷腸人送斷腸人,
斷腸人送斷腸人!
——出自《女駙馬》
Feng Suzhen: We don't want to, but we have to part today.
Li Zhaoting: We have to say good-bye to each other today.
Chorus: Your tearing eyes look at mine.
A heart-broken man sees off a heart-broken woman.
A heart-broken woman sees off a heart-broken man.
——朱忠焰(譯)
此唱段用了大量重復,如舍、分、流淚眼、斷腸人等,這一修辭手法也將戲劇推進高潮。然而,由于文化差異,目標語群眾缺乏源語語言文化背景知識,不當的譯文會使目標語群眾誤解,更無法理解戲劇精髓[8]。在本段譯文中,譯者采用了歸化的方式,“流淚眼觀流淚眼”,雖然原文中有重復,但譯者省略了重復,以“mine”來代替流淚眼,流淚眼指兩人眼噙熱淚,用“mine”一詞來傳達,既交代清楚了唱詞的背景,簡潔易懂,又符合英文的行文習慣。接下來兩句“斷腸人送斷腸人”在原文中重復出現,中國聽眾不難理解,夫妻二人難舍難分、肝腸寸斷的場景,對于目標語受眾,若直接重復譯文,會使戲劇缺乏張力,受眾無法感知對方深切的不舍與離別之情。譯者將原唱詞中的“人”拆分為“man”和“woman”,代表主人公雙方,清晰明了地指出了夫妻雙方難舍離別的場景。此外,唱詞中“斷腸人”一詞切不可望文生義,譯者選擇了目標語言群體熟悉的語言知識,即“heart-broken”來表達“斷腸人”的含義。在英文中,“斷腸人”一詞沒有直接對應的單詞,若直譯“斷腸人”,則屬于望文生義。因此,可采用歸化的譯法,尋找貼近目標語受眾熟悉的文化知識進行替換,“heart-broken”意為“心碎”,與斷腸人意思相近,可指代同一事物,顯然,歸化譯文“heart-broken”更易于讓受眾理解、接受源語文化[9-10]。
3 結束語
翻譯是語言溝通的橋梁,語言是承載文化傳播的重要工具,翻譯的過程本質上是兩種文化交流的過程。戲劇的地方特色濃厚,文化表現力極強,戲曲英譯推動了中華文化的傳播。在地方戲劇的翻譯過程中,譯者必須本著文化交流的原則,以實現文化等值功能為目標,把握好翻譯的起落點——文化交流,兼顧目標語受眾的文化接受度和譯入語的文化環境,選擇合適的翻譯方法和策略,同時注重原唱詞的本土文化和目標語文化的融合,實現文化輸出與交流。本文基于文化翻譯理論,橫向分析了戲曲英譯本的翻譯策略,以黃梅戲《天仙配》和《女駙馬》中部分精彩唱段為例,著重探討了英譯唱詞中增譯主語、同義詞轉換、詞性轉譯及歸化的翻譯方式,希望能為同類地方戲劇的翻譯提供新思路。在后續的課題研究中,筆者將從受眾群體的地域分布、文化程度及行為習慣等方面深度剖析黃梅戲英譯策略如何影響不同受眾群體的思維方式,從而尋求最為適切的翻譯方法,進一步推動戲劇的海外傳播,弘揚中華戲曲文化。
參考文獻
[1] BASSNET S. Translation Studies[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2] 張文明,章二文.文化翻譯觀下的黃梅戲英譯研究[J].滁州學院學報,2019,21(6):52-54,60.
[3] 牛云平. 西塞羅的秤:西方等值論文文化探源[J].外語與外語教學,2008(1):48-51.
[4] 朱小美. 黃梅戲《天仙配》英譯有感[J].語文學刊,2016(9):80-82.
[5] 陳偉,高子涵. 超越“文化轉向”:翻譯研究的軟實力范式圖景[J].外語研究, 2023,40(3):59-66,98,112.
[6] 王茜亞,溫馨兒,趙霞. 文化翻譯觀下《洗冤集錄》麥克奈特譯本翻譯策略探析[J].中醫教育,2023,42(5):61-66.
[7] 趙稀方. 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從西方到中國[J].學習與探索,2017(1):141-145,176.
[8] 王巧英,朱忠焰.黃梅戲經典唱段英譯難點及其翻譯方法與技巧[J].安慶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32(6):94-96.
[9] 馬士奎. 詹姆斯·霍爾姆斯和他的翻譯理論[J].上海科技翻譯,2004,32(3): 46-50.
[10]呂世生,胡茵菰. 中國戲劇對外翻譯的目標語文化接受問題[J].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學報,2015,17(5):11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