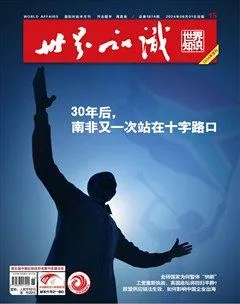北約峰會告訴世人,誰才是國際安全風險制造者
7月9日至11日,北約成員國首腦峰會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召開。今年時值北約成立75周年,但北約沒有心情慶祝,其真正在意的是烏克蘭危機持續膠著,籠罩歐洲的安全陰霾難以消散。從本次峰會公報看,北約已將援烏抗俄、“東進亞太”和應對中國“挑戰”確定為其未來全球戰略的“三大支柱”,意在基于“大國戰略競爭”的總方針,通過拉攏歐盟和拓寬全球伙伴關系網絡,整合“跨大西洋”和“印太”兩大地緣戰略,尋求加強對俄、對華“雙遏制”。
全面升級援烏抗俄力度
援助烏克蘭和遏制俄羅斯是此次北約峰會的最大戰略關切,北約出臺了諸多政策舉措,進一步調整援烏抗俄戰略,具體而言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
一方面,牽頭統籌援烏抗俄。峰會公報明確宣示將建立“對烏克蘭安全援助和訓練方案”(NSATU),協調盟國向烏提供軍事裝備和訓練援助的內容,并稱將在2025年至少向烏提供400億歐元的資金,還將推動建立北約—烏克蘭聯合分析、培訓和教育中心(JATEC),以及任命一名北約駐烏高級代表。
另一方面,繼續以“極限施壓”方式升級對俄軍事遏制力度。一是,強調北約“完全無條件地”支持烏克蘭在其國際公認邊界內爭取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努力,要求俄盡快停止在烏軍事行動;二是,明確承諾逐步提高北約與烏克蘭之間的互操作性和政治一體化程度,強調“烏克蘭的未來在北約”;三是,打造遏制俄羅斯的價值觀聯盟。
加速“東進亞太”進程
本次峰會期間,北約根據《戰略概念2022》的指導原則,基于2023年維爾紐斯峰會以來的政策實踐情況,進一步細化了“東進亞太”的實施方案,增強了有關戰略工程的推進力度。
華盛頓峰會期間,北約與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四個亞太地區的伙伴國家(簡稱“亞太四國”)以及歐盟舉行多邊會議,討論所面臨的“共同安全挑戰”和應加強合作的具體領域,決定通過支持烏克蘭、網絡、反虛假信息和技術等領域的具體“旗艦項目”,與亞太四國加強務實合作。
北約明確宣示,將在朝鮮問題和對華制衡這兩個方面,向亞太四國提供軍事支持,并以開展軍事訓練和加強國防工業為兩大核心領域。北約希望用這種方式換取亞太四國向烏克蘭提供經濟、武器裝備、軍用和民用物資等方面的援助,并且壓促中國在烏克蘭問題上疏離俄羅斯。
地緣政治方面,北約強調“歐洲—大西洋”和“印度洋—太平洋”這兩大戰略區域的安全是相互聯系的,呼吁亞太四國為“歐洲—大西洋安全”作出貢獻,希冀通過不斷強化與亞太四國的戰略聯系,打通兩大戰略區域,整合出一個“東西并舉、雙向聯動”的全新地緣政治空間。值得一提的是,北約“東進亞太”的具體實施路徑和制度框架安排,特別是聯絡機制,依然沒有在此次峰會上得到確定,前景仍不明朗,需要繼續通過談判溝通加以解決,而在上一年的維爾紐斯峰會上,有關在東京設立北約辦事處的動議遭到法國的否決。
進一步提升對華政策的競爭性
華盛頓峰會公報延續了2022年馬德里峰會、2023年維爾紐斯峰會的對華戰略認知,宣稱中國對跨大西洋安全構成“系統性挑戰”,這種“挑戰”集中體現在利益、安全和價值觀三個方面,污蔑中國正在利用惡意和虛假信息等“混合戰爭手段”“威脅”北約安全,呼吁北約成員國凝聚對華政策的聯盟共識,針對中國采取“積極的應對和制衡舉措”。
華盛頓峰會公然指責中國通過“無限制的伙伴關系”向俄羅斯國防工業提供大規模支持,從而成為俄對烏克蘭軍事行動的“決定性助推器”,由此進一步對跨大西洋安全構成“威脅”。即將卸任的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在峰會期間公開表示,中國向俄提供了軍民兩用生產材料,如武器部件和相關設備、可用于武器裝備的微電子產品等。

華盛頓峰會明確要求中國“放棄對俄羅斯戰爭努力的一切物質和政治支持”,聲稱中國不能指望同時與俄羅斯和西方國家保持良好關系,威脅中方如果繼續支持俄羅斯,將產生不利于中國的“嚴重后果”。
北約華盛頓峰會公報雖然明顯增強了對華政策宣示的競爭性色彩,但從中不難看出,北約并沒有完全做好與中國進入全面戰略競爭的準備,更多還是在做口頭強硬的表面文章。北約正自陷于同俄激烈對抗的局面而不能抽身,根本無法充當美國遏制中國戰略的真正后盾。與此同時,此次北約峰會公報仍保留了與中國進行“建設性接觸”的話語和政策空間,其中包括呼吁中方參與降低戰略風險的討論,并通過“提高核武器政策和能力的透明度”來“促進穩定”。
國際安全風險制造者
眾所周知,在布魯塞爾的北約機構發揮的主要是日常行政功能,真正的決策大腦在華盛頓。美國是北約內部軍事實力和資源最為雄厚的成員國,承擔著最大份額的軍費開支,北約各種軍事活動的開展也依賴美國提供武器裝備和軍事基地等資源。這種硬實力的絕對優勢,使得美國在北約內部享有其他成員國遠不能及的特殊地位。
放眼當今國際大環境,美國迫切需要利用北約回應關乎其霸權地位的三大難題:一是如何修復和重建被烏克蘭危機嚴重動搖的歐洲安全秩序;二是如何在美國全球戰略重心東移的背景下,平衡“印太戰略”和跨大西洋戰略;三是如何有效應對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的快速崛起。
進一步整合亞太盟伴體系,推動北約加速全球化,特別是“東進亞太”,以同美國“印太戰略”更緊密、更有效地相互配合,甚至彼此融合,讓北約更多分擔其在全球范圍內的霸權護持壓力,是美國近年操控北約事務的重要目標,北約與歐盟、美英澳三方安全聯盟(AUKUS)、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QUAD)等機制之間的政策協調性乃至軍事互操作性隨之提升。

此次北約峰會,美國充分發揮主場之利,推動作出以新的高度迎合美國霸權利益訴求的戰略部署,體現了極其鮮明的冷戰思維。一方面,美國借助北約,以“集團化對抗”和“極限施壓”的方式,絲毫不顧及他國的安全關切,不斷在歐洲和亞太拱火,尋求對俄、對華的雙重遏制;另一方面,美國將“應對大國地緣政治競爭”當作首要目標,并使北約接受了這一戰略認知,將原本多元復雜的國際關系互動簡化為劍拔弩張的地緣政治對抗,大大增加了大國之間發生正面沖突的可能性,顯著提升了國際安全風險。
一是再次升級援烏抗俄力度,使得歐安秩序更加岌岌可危,不但進一步加大和平解決烏克蘭危機的難度系數,而且可能引發俄與北約之間的直接沖突,甚至爆發核戰爭。
二是警告和脅迫中國在烏克蘭問題上明確“選邊站隊”,向美西方國家的援烏抗俄立場靠攏。這種有意為之的敘事攻擊嚴重損害了中國的國際形象,使中國承受被強加的聲譽成本,同時意在壓縮中國的外交空間,挑撥中俄、中烏正常雙邊關系,試圖使中國陷入“二者選其一,每種選擇皆有失”的政策困境。
三是以“陣營對抗”思維塑造亞太安全局勢,顯著推升亞太大國戰略競爭烈度和安全困境程度,增加中國周邊的戰略和安全風險。一旦北約“東進亞太”的戰略預期最終成為現實,激烈且壓抑的大國戰略競爭將徹底摧毀自由、和平、繁榮的亞太秩序,各國互不信任并相互戒備的零和安全困境成為彼此互動的常態,地緣政治沖突管控的難度陡然增高,經貿往來、科技合作、人文交流等活動賴以維系的良好國際環境也將不復存在,爆發國際沖突的風險亦將隨之增大。
四是推動大國戰略競爭向著“泛安全化”的方向發展。北約以“泛安全化”思維重構其全球安全戰略,無限度擴張安全利益范圍,希冀實現安全的絕對化。這樣的戰略調整在升級軍事、政治等傳統領域大國競爭烈度的同時,引發和加劇了關鍵基礎設施、經濟安全、網絡空間、氣候變化等新領域的競爭,未來相關的戰略部署落實勢必增加其他國際行為體的不安全感,可能爭相仿效,由此大幅度擴大國際安全競爭的邊界,人為地給雙多邊科技交流、跨境數據流動與治理、網絡規范制定等原本并不那么敏感的領域疊加安全敏感性,加深國際體系和全球治理困境。
不過,北約的新戰略部署從文本宣示到完全落地,也面臨掣肘。最重要的變數就是今年美國大選的結果。一旦特朗普重新執掌白宮,“美國優先”勢必再次凌駕于“跨大西洋主義”之上,屆時被“戰時團結”暫時掩藏的美歐矛盾將再次凸顯。此外,北約奉行全體一致的決策原則,美歐在亞太和對華政策利益界定、烏克蘭危機后如何定義俄羅斯身份等議題上的分歧,以及波蘭等中東歐國家要求更多話語權而對北約權力結構可能產生的影響,也會對北約的對外政策實踐造成牽制。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歐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