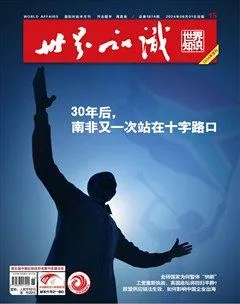特朗普擁有廣泛刑事豁免權對美國意味著什么
7月1日,美國最高法院以6∶3的票數對“特朗普訴美國案”(Trump v. United States,簡稱“特朗普案”)做出裁定,認為在“干涉2020年大選案”中,作為總統的特朗普擁有廣泛的刑事豁免權,即總統在公職行為上擁有刑事豁免權。
2023年8月,因涉嫌推翻2020年聯邦總統選舉結果,美國司法部特別檢察官杰克·史密斯對特朗普發起四項刑事指控。該起案件又被稱為“干涉2020年大選案”。但在庭審前,特朗普律師團隊提出了審前動議。該動議稱,作為前總統,特朗普在任期間的行為應享有絕對豁免權(absolute presidential immunity)。對此,作為初審法院的華盛頓特區聯邦地區法院斷然予以了否決。此后特朗普又向哥倫比亞特區巡回上訴法院提出上訴,上訴法院同樣對該動議予以了駁回。2004年2月12日,特朗普向最高法院提出緊急上訴,申請撤銷巡回上訴法院的裁決。最高法院于2月28日受理了此案。
最高法院的此次判決具有里程碑式意義。美國最高法院雖然在1982年的“尼克松訴菲茨杰拉德案”中裁定,總統在公職行為中享有絕對的民事豁免權,但一直沒有對總統是否擁有刑事豁免權做出解釋。在“特朗普案”中,最高法院做出總統在公職行為上擁有刑事豁免權的裁定,不僅將影響特朗普個人的政治前途,也會對美國憲政史發展產生深刻影響。
總統豁免權的法理依據
美國憲法只規定了總統可以被彈劾,但并未明文規定總統可以被起訴。美國總統豁免權是最高法院大法官在解釋憲法特定條款過程中,創立并逐漸發展出來的。總統豁免權是指總統在任期內,因其行使憲法權力而采取的某些行為,可以免除民事和刑事起訴,且免除其因該行為而帶來的法律責任。1985年,美國最高法院在“米切爾訴福賽思案”中提出,豁免權的核心在于,擁有豁免權的個人或機構不需要在法庭上對自己的行為作出解釋,這意味著他們可以在法律訴訟中免除責任。作為三權分立的一支,總統具有超然于其他權力部門的特殊憲法地位。從法理來說,總統享有豁免權主要基于以下幾個理由:
一是確保總統有效履行職責。總統的職責繁重且復雜,涵蓋國家安全、國際關系、經濟政策等廣泛領域。如果總統頻繁面臨司法訴訟,可能會嚴重干擾其履行職責的能力。豁免權確保總統能夠專注于國家事務,而不必耗費大量時間和精力應對法律糾紛。
二是確保行政分支的獨立性。總統作為行政部門的最高首長,需要在行使行政權力時保持一定的獨立性。豁免權可防止其他政府部門或個人通過訴訟影響總統的決策和行動,從而維護行政權的獨立性和完整性。
三是防止濫訴。如果總統不享有職務行為的司法豁免權,可能會遭到大量基于政治動機的訴訟,這不僅浪費司法資源,還可能被用作政治工具來削弱總統的權威和信譽。司法豁免權有助于防止這種濫用法律程序的行為 。
四是美國歷史和法律先例。美國歷史上多次出現關于總統職務行為豁免權的法律爭議和判例。例如,美國內戰期間,林肯不顧憲法約束,頒布行政命令,下令暫時中止一些不穩定地區的人身保護權,授權軍方可以任意逮捕他們懷疑與南方“叛軍”有關聯的人。盡管首席大法官做出了不利于林肯的判決,但是林肯依舊推行他的戰時政策,并最終獲得了國會授權。關于總統豁免權的解釋,也已有幾個法律先例。例如,1982年的“尼克松訴菲茨杰拉德案”裁定總統具有民事豁免權;1997年,美國最高法院在“克林頓訴瓊斯案”中進一步明確了總統在公職行為方面有絕對豁免權,但如果涉及其個人行為,仍然可以在其任期內被民事起訴。這些判例強調了維持政府運作的連續性和效率的重要性。
甄別工作將非常困難
2023年8月,因涉嫌推翻2020年大選結果,美國司法部特別檢察官史密斯對特朗普發起四項刑事指控。在起訴書中,史密斯對特朗普干預大選的行為分為四類:一是特朗普“伙同”他的代理司法部長、司法部其他高官以及白宮高官等“同謀者”,一起調查所謂的拜登陣營“選舉欺詐”,并向一些州發出了信函,要求徹查此類“選舉欺詐”;二是特朗普向副總統彭斯“施壓”,讓他在阻止國會對拜登勝選進行認證中發揮作用;三是特朗普與聯邦行政部門之外的人互動,“共謀推翻大選結果”,這些人包括州級官員、私人代表、律師以及一些州的公眾等;四是在2021年1月6日美國“國會山騷亂”中,特朗普的種種行為,包括向他的眾多粉絲發布了一系列推文,“慫恿、蠱惑”他的支持者在當天前往華盛頓特區,導致了騷亂的發生。

“特朗普案”的歷史貢獻之一就是根據總統的行為是否屬于公職行為,把豁免權分為以下三類:一是美國總統權力的本質是總統行使決定性和排他性的憲法職權時享有免受刑事訴訟的絕對豁免權。特朗普同他的代理司法部長等一眾高官調查大選中的欺詐行為是總統的職責所在,有憲法依據,該行為享有“絕對豁免權”。二是總統任期期間還至少應享有對其所有公職行為的推定豁免權(presumptive immunity),特朗普“施壓”彭斯阻止國會對拜登勝選認證的行為目前暫時推定為具有豁免權。特朗普“施壓”彭斯的行為比較復雜,是否屬于公職行為還需要進一步深入甄別。三是總統的非公職行為則無豁免權。特朗普與聯邦行政部門之外的人的互動,以及特朗普在“國會山騷亂”中種種行為,是否屬于公職行為,需要仔細而科學地甄別,如果是非公職行為則無刑事豁免權。
在“特朗普案”中,多數派大法官把甄別特朗普公職行為的難題推給了初審法院,使得初審法院法官塔尼婭·丘特坎面臨巨大的壓力。她必須重啟“干預2020年大選案”的審理,甄別特別檢察官起訴書中的哪些指控構成公職行為,從而可能根據最高法院裁決免于起訴;哪些行為不屬于公職行為,可以被起訴。丘特坎這項剝絲抽繭的審理工作將備受矚目,甄別工作需要數月時間,這也就意味著今年大選日前,特朗普不大可能因為該案件而被審判。
甄別工作確實非常困難,主要存在以下兩個原因:一是公職行為與非公職行為界限模糊。2020年美國最高法院在“特朗普訴瑪澤會計公司案”中也承認:“總統個人行為與公職行為界限并不總是清晰的”。二是要求陪審團甄別總統行為存在一定風險。一般來說,美國的刑事案件,特別是重罪案,一般都有陪審團參與審理,“特朗普案”也不例外,這是美國憲法第六修正案所規定的。在“特朗普案”中,美國最高法院多數意見認為,允許檢察官要求或建議陪審團探究總統享有豁免權的公職行為,將引發一個“獨特的風險”,即陪審員的審查將因其對總統在任期間的政策和表現的看法而受到個人偏見的影響。而且,甄別總統的行為是否屬于公職行為,涉及憲法解釋和政治問題,這超出了陪審團的能力范圍。
是“捍衛憲法”還是“對民主的踐踏”?
“特朗普案”的裁決又一次體現了美國最高法院內部保守派陣營與自由派陣營的對決。索托馬約爾代表三名自由派大法官撰寫了少數意見,猛烈抨擊六名保守派大法官撰寫的多數意見,稱其創造了一種“脫離文本、無歷史依據且無法證明的豁免權,將總統置于法律之上”,表達了他們對民主的擔憂。然而,保守派大法官認為,賦予總統一定程度的刑事豁免權不是要庇護特朗普,而是要保護總統行政分支,這恰恰捍衛了美國憲政體制。如果總統不享有刑事豁免權,每位繼任的總統可以自由起訴他的前任,將使得在任總統因為害怕自己可能成為下一個目標而無法大膽地履行職責……這種黨派紛爭的循環所導致的總統和整個政府的弱化,或許正是制憲者意圖避免的。因此,代表保守派的羅伯茨大法官認為,自由派大法官“發出了令人不寒而栗的厄運之音,與法院今天的實際做法完全不相稱”,自由派大法官“在極端假設的基礎上散布恐懼”,且法理依據薄弱。
在當今政治極化背景下,美國最高法院已深陷兩黨無休止的政治惡斗中。兩黨黨爭嚴重危及了美國民主。早在1796年,美國開國總統華盛頓在其總統告別演講中曾提出警告:“黨派之爭的精神,可以在自由的政府中被視為一種威脅。它從某種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但政府需要采取措施防止其過度的增長。黨派精神會造成偏見、仇恨和復仇的惡性循環,損害公共利益,破壞政府的權威。”華盛頓當年的告誡正在今天的美國上演。
美國黨派惡斗涉及政治理念、政策優先事項和選舉策略,這些是立法和行政部門的職責范圍,法院無法通過判決改變政黨的行為或理念分歧。然而,面對兩黨惡斗,法院卻又難以置身度外,司法淪為美國兩黨推行己方政策、打擊對手的工具。從2000年的“小布什訴戈爾案”到“特朗普案”,美國最高法院邁過“政治荊棘叢”,充當了解決兩黨政治紛爭的角色。而最高法院在美國政治制度中的角色是保持司法獨立和中立,其裁決應基于法律和憲法,而不是黨派利益。如果最高法院卷入黨派斗爭,它的中立性和公信力將受到損害。就像在“特朗普案”中那樣,盡管保守派多數意見不斷強調,基于總統的公職行為賦予總統一定程度的刑事豁免權,是為了避免總統遭受濫訴與報復,讓總統安心履職,旨在捍衛憲政,但是出于對最高法院中立性和公信力的質疑,民主黨陣營的官員和民眾很難相信,做出該判決不是基于黨派利益。
(作者為南京審計大學法學院、國際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