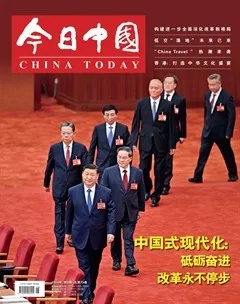張鈸:中國人工智能泰斗


無人駕駛、人臉識別、智能家居……如今,人工智能已融入千行百業,小到居家出行、大到制造研發,智能經濟給生產生活帶來深刻變革。
早在40多年前,中國人工智能領域泰斗級專家、清華大學計算機系教授、中國科學院院士張鈸就開始投身人工智能領域研究,他發表了中國第一篇人工智能領域的學術論文、獲得中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第一個國際重要獎項、組建中國第一個人工智能國家重點實驗室……由此樹立起中國人工智能發展的一個個里程碑,推動中國在此領域發展進步。
闖入未知領域
1956年國際上誕生了“人工智能”一詞。達特茅斯夏季研究項目提出符號AI的基本思路,紐維爾、西蒙等研究者提出物理符號系統假設,最終形成了基于知識和經驗的符號推理模型,即知識驅動模型。
人工智能研究開展伊始,希望機器能像人類一樣思考,是AI創始者們最樸素的期待。回想起人工智能的誕生,張鈸說:“我們解決很多問題都靠理性思考,所以最初就想讓機器模擬人類的思考行為。”
張鈸介紹,符號AI,也就是第一代人工智能,只適用于完成信息比較完全、不確定性較小的工作,如:調度、規劃、診斷等。以下國際象棋為例,下棋屬于一種“完全信息博弈”行為,信息是完全確定的,要素與規則都固定且有限,這類工作第一代人工智能可以做得很好。但是第一代人工智能在面對不確定性較強的情況時明顯不那么好用,如戰爭環境下的決策,人工智能難以辨別信息的真偽,更無法進一步生成成功的指令。此外,第一代人工智能的知識獲取依賴于人工,費時、費力,很多問題有待進一步解決。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開啟了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全會明確提出:“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
隨著國門打開,國際科技合作與交流興起,張鈸獲得了與國際同行交往的機會。1980年初,張鈸赴美訪學,到達了伊利諾伊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然而,他在與外國同行交流中感到一種說不出的尷尬和郁悶。外國研究者對于這批來自中國大陸已到中年的訪問學者的學識與能力抱懷疑的態度。張鈸很受刺激,立志讓中國在人工智能領域奮起直追,迎頭趕上國際先進水平,贏得外國同行的尊敬。
做人工智能,最重要的是選題能否“押對寶”。在第一代人工智能的理論研究中有推理、搜索和規劃等方向,張鈸從事的第一項研究是機器人的運動規劃。當時,對于機器人躲避障礙的運動規劃,國際上流行的方法是根據多關節機械臂的形狀和尺寸,把原來帶有障礙的空間從三維變換為更高維的空間,而機械臂本身縮成一個點。這樣機械臂在障礙空間中的運動規劃,變成高維空間中的路徑搜索,當空間的維數很高時,比如6、7維,則存在搜索運算量極大的弊端。
對此問題,張鈸率先發現數學與人工智能結合的廣闊前景。于是,他與弟弟張鈴展開合作。張鈴學數學出身,當時尚在安徽任教。兄弟倆選擇在人工智能研究中引入數學工具—拓撲理論。通過對高維空間進行拓撲變換,將復雜的空間變換為一個簡單的拓撲空間(二維網絡)。在此思想基礎上,他們提出了全新的基于拓撲的機器人運動規劃方法,大大降低了計算復雜性。這一獨創性研究,讓他們在國際舞臺上引領了人工智能研究方法的創新。
經過約一年時間,他們聯手完成了一篇人工智能領域的論文《機器臂在障礙物之間的無碰撞路徑規劃》,后來成功發表于人工智能領域頂級國際期刊《IEEETrans. on PAMI》,引起了國際同行的高度關注,實際上這也是中國科學家在人工智能領域頂刊發表的第一篇學術論文。這讓張鈸等中國學人頗為揚眉吐氣,也增強了他為中國人工智能發展作出更大貢獻的信心和決心。
建設中國人工智能
從選擇“人工智能與智能控制”作為新的教學與科研方向,迄今已過40余載的光陰。張鈸建設中國人工智能的歷程,曲折繁瑣,經歷過“冬天”,也見證過機遇。
1982年初,張鈸結束訪學回國,著手進一步開拓人工智能研究。為了解產業界對人工智能技術的需求,更好促進科技成果轉化,張鈸與其他科研人員一起深入從西南到東北的很多工廠調研,形成了基本判斷:機器人將來會成為國內一項重大需求。
1984年,張鈸開始籌建中國第一個智能機器人實驗室。這一方向與國家的需求高度融合。1986年,國家制定了“863”高技術發展規劃,其中就包含了智能機器人主題。
要研究機器人,就必須要有機械臂。機械臂是高精度、高度非線性、強耦合的復雜系統,是人工智能在工業應用的典型。但由于技術保護原因,當時的機械臂不允許直接賣給中國人,價格也十分昂貴,達到19萬人民幣。
為此,張鈸與同事們多方奔走、籌措經費,聯系國內外相關廠家,進行洽談協商。最后,張鈸與同事通過福建從香港進貨。他回憶說:“當我知道機器臂已經裝上飛機,正在飛往北京時,那種興奮真的難以言表。”機械臂運抵北京后,張鈸親自跟車到機場“迎接”,直到搬運、裝車、運抵清華園,他才終于松了一口氣。
沒有說明書,也沒有任何經驗調試設備。還記得有一天夜里機器人撞在桌子上動不了,老師們嚇壞了,找張鈸來解決,最終發現是因機器撞到桌子上保護鍵起了保護作用。雖是虛驚一場,但足以看出設備之珍貴,資金之緊張。
1987年,張鈸與團隊又開始籌建國家重點實驗室,名為“智能技術與系統國家重點實驗室”。
然而,正在張鈸等學者奮力追趕的時候,人工智能卻遇到了低谷期。受到算法、計算機算力等原因的限制,人工智能的“冬天”降臨, 出現越來越多的質疑。幾乎同時,國外很多研究機構紛紛停止了該方向的研究工作。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國內一些高校也都很難繼續該領域的工作。當時,張鈸的團隊也面臨著巨大的壓力,但是外界的這些聲音并沒有影響到他的決心,在許多人開始轉行時,張鈸初心不改,迎難而上。他猶如一個“旗手”,帶領著團隊在困難、狂熱抑或浮躁中保持冷靜,砥礪前行。
人工智能領域碩果累累
憑借改革開放的良好環境與中國崛起的機遇,經過不懈努力,張鈸的團隊不僅堅持下來,而且取得了良好的發展,在人工智能領域創造了多項全國第一。張鈸也在人工智能領域碩果累累,大大小小的榮譽數不勝數。
1987-1994年,張鈸出任國家“863計劃”即高技術計劃智能機器人主題專家組專家,承擔國家重點攻關課題;1990年獲得在國家重點實驗室建設中做出重要貢獻先進工作者稱號;1994年在慶祝國家重點實驗室建設十周年大會上獲個人金牛獎,以表彰他對實驗室建設的突出貢獻。
1994年,張鈸當選為俄羅斯自然科學院外籍院士。1995年11月3日,張鈸當選為中國科學院技術科學部院士。對此重大殊榮,張鈸卻說,“我們不能拿院士這樣的頭銜來嚇唬人,也并不是說當了院士就可以高傲自大了,科學研究是永無止境的,我要做的事情還很多。”
2018年,在人工智能領域受到全世界廣泛關注的形勢下,張鈸前瞻性地提出了要將清華大學與人工智能有聯系的相關院系整合起來,成立清華大學人工智能研究院。于是,人工智能研究院組織了清華大學內的18個學院或系共同參與建設,其中不但包括了計算機系、電子系、自動化系、精密儀器系等理工科院系,也有與社會科學、心理學相關的院系。2018年6月28日,清華大學人工智能研究院成立,83歲的張鈸擔任研究院首任院長。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發展人工智能提升到戰略高度,習近平總書記圍繞加快發展人工智能、推動高質量發展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論述。中國人工智能行業受到各級政府的高度重視和國家產業政策的重點支持,國家陸續出臺了多項政策,鼓勵人工智能行業發展與創新。
現在,清華大學人工智能研究院下設10個研究中心,涵蓋了人工智能的大模型研究、視覺研究、自然語言處理、智能機器人、人工智能基礎研究等各個方面。從發表的高檔論文數量而言,已居世界前二。
在張鈸和計算機系老師們的共同努力下,清華大學在全球最權威的計算機科學排名CS Rankings上常年位居前列,2022年位列全球第二,超過了麻省理工學院、斯坦福、普林斯頓等高校;而在張鈸主攻的人工智能方向上,清華大學常年排在全球首位。
但對于這樣的成績,張鈸仍有清醒的認識,雖然清華大學在個別方面成績非常出色,但在更多的領域中仍處于追趕者的角色。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和國際最高水平仍有差距,而張鈸尤其指出需要在基礎理論上下功夫。他認為:“如果中國要在這個領域實現領跑,是要有理論作為支撐的,理論上的突破才能形成優勢”。因此,清華大學并不隨波逐流,而是在理論研究上尋求突破,張鈸退休之后仍繼續參與到理論研究的探索中。
科技創新永無止境
杏壇六十余載,回顧自己的教師生涯,張鈸認為最令他感到自豪的并不是做出的科研成果,也不是建成的實驗基地,而是為國家培養出一批批優秀的人才。
1988年6月,張鈸培養的中國人工智能領域的第一個博士生畢業。此后,張鈸培養的人工智能領域博士生共接近90名,如今已是四代博士同堂。
作為一名教師,如何在高校的學科建設、人才培養中發揮應有的作用?張鈸的回答是“行勝于言”,發揮自身的表率作用。“首先需要我們認真地去對待每一件事,比如每一堂課、每一次報告,甚至會議上的發言,我總是經過認真思考和準備,力求做到言之有物,讓聽眾有所收獲;還需要堅持奮斗在教學與科研的第一線,不斷向周圍老師和學生學習,這樣才有可能跟上時代的步伐,為人師表。”
“雖然退休了,但我沒有休息的計劃。”“80歲以后,除了沒有開車,我其他所有事情照辦。”……已至耄耋之年的張鈸院士,展現出的是蓬勃的生命力。
不久前,張鈸院士迎來了89歲生日,談及如何保持身體與思維的敏捷,他的秘訣是保持童心、保持好奇心,他認為只要做到這一點,就可以活得和年輕人一樣。
在未來的規劃里,張鈸給自己設定了三個目標,讓清華大學在人工智能基礎理論研究上達到世界一流水平、做一個屬于機器人的產業、做智慧醫療……年齡、歲月無法阻擋他醉心一生的科研之路。
張鈸認為,通過人工智能可以減少工作時間、提升工作質量、協助解決社會難題,人工智能將會提升人類整體的幸福感,“我搞人工智能的目的就是為了讓人類更加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