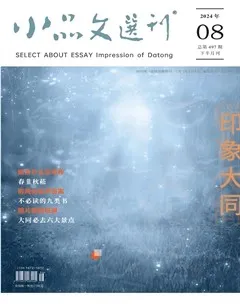籍貫觀念的形成

眷懷鄉土本是人情之常,但直迄晚近,國人對鄉土籍貫的觀念,實較任何開化民族遠為深厚。我國幅員之廣,相當歐洲全洲,雖自秦以降已做到“書同文”的地步,但兩千年來各地區間仍保有不同的風俗和方言。方言的不同是造成強烈鄉土觀念的主因之一。這是常識,無待贅述。
我國傳統籍貫觀念之特殊深厚,必有特殊的原因。特殊的原因有三:一、有關儒家“孝”的禮俗和法律;二、有關官吏籍貫限制的行政法;三、科舉制度。
孝與籍貫
儒家最重視的孝,至東漢已漸成上層社會人士的準宗教。到了唐代,廣義的孝所包括的對親長養生送死的種種義務和儀節,更進一步正式編入法典,宋元明清莫不如此。就唐以后的法律而言,子孫奉養祖父母父母并不一定必在本籍。但自歷代正史及方志中“獨行”“孝行”“孝義”等傳推測,典型的孝子卻應該履行“父母在,不遠游”和“安土重遷”這類古訓,在祖宗墳墓所在的本籍躬自奉侍親長。所以在禮俗上,孝的“養生”方面與籍貫往往發生密切的關系。
至于孝的“送死”方面,法律上對統治階級規定甚嚴,原則上所有官員皆須回籍奔喪,在籍守制二十七個月。雖然自唐迄清皆不乏大員“奪情”實例,但時代愈晚,執行愈嚴,例外愈少。入仕之人須在原籍守制,至少在明清成為通例,偶有“奪情”,物議紛紛,足征禮俗對于丁憂一事較法律尤為嚴格。至于庶民,唐以后法律上僅有服喪二十七月的規定,并未明言庶民服喪必在原籍。大多數庶民既世代從事農耕,事實上服喪當在原籍。至于迫于衣食不得不去異鄉營販的庶民是否也一律在原籍服喪二十七月之久,史例缺乏,無法肯定。但另一方面,自東漢兩晉以降,凡是為父母長期守墓,以及千里迎柩原籍歸葬的人,正史及方志列傳無不大事標榜,認為是至孝的典型。所以自禮俗及法律交互影響來看,廣義的孝與籍貫問題,實有密切的關系。
歷代官吏籍貫禁限
與其他國家比較,我國傳統行政法中特色之一,是對官吏銓選任用的籍貫禁限。地方官回避本籍原是純地緣性的禁限,但往往與血緣性禁限同時并存,所以籍貫回避的意義與范圍便變成非常廣泛。這原本用意純屬消極防范性的行政法規,兩千年來無形中促進深厚籍貫觀念的養成。
秦漢一統帝國建立之后,中央政權為防止強大地方勢力的抬頭,逐漸通過了地方各級官員回避本籍的法令。西漢之世即有地方各級監官長吏不得任用本籍人的禁限,刺史不得用本州人,郡守國相不得用本郡人,縣令、長、丞、尉不但不用本縣人,而且不用本郡人。東漢中葉以后復有“不得對相監臨法”及“三互法”。
兩漢對地方各級官吏任用不但有單層地緣的禁限,且有雙層因血緣而及地緣的禁限,可謂備極周密。
東漢一統帝國崩潰的原因甚為復雜,以上一類禁令的本身無法防阻地方豪族及割據勢力的興起。經魏晉終南北朝之世,中央政權不得不對地方豪族拉攏容忍,兩漢式地方官任用的地緣血緣禁限,大體無法施行。但另一方面,五胡亂華,北方淪陷,士族大批南渡,東晉和南朝紛紛設立僑州僑郡,南遷之北方士族“競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于是地望成為他們門第的標幟,重譜牒,更不得不特重郡望。留在北方異族治下的漢人士族也無不如此。所以在長期南北對峙局面之下,衰弱的中央政權雖無法維持兩漢型地方官吏任用的籍貫禁限,但當時特殊的政治與社會情況卻大大增強了統治階級對原籍或祖籍的觀念。
隋未統一之前已開始企圖削弱自漢季以來強大的地方勢力。
就現存法令鱗爪看來,隋、唐既重建一統之局,多少恢復了一些兩漢對地方官任用的籍貫限制,至于此類禁限實施的程度,則尚有待詳考。
兩宋基本國策之一,是加強中央對地方的統制,企圖永遠防止唐中葉以后藩鎮割據局面的重演,因此兩宋政府對官吏任用的籍貫禁限比隋、唐為嚴密。
元代吏治窳敗,成宗大德(1303)亦有類似律令,惟僅及司吏:江西行省準中書省咨,近據問民疾苦官呈,江西省咨,所轄路府州縣司吏,即系土豪之家買囑承充……本身為吏,兄弟子侄親戚人等置于府州司縣寫發,上下交通,表里為奸……不肯出離鄉土。
《大明會典》簡明扼要,所收律例遠較《宋會要》及《大清會典事例》為少。
降及清代,官員銓選之籍貫禁限粲然大備。僅就“本籍接壤回避”律例而言,即有以下極度周詳的規定。
綜觀官吏銓選的籍貫禁限,前后有兩千年以上的歷史。其間中世數百年間,雖未見施行,但凡中央政權相當穩固,行政較上軌道的朝代,都大體或多或少地遵循兩漢遺規。有清一代,此類禁限周詳縝密,無以復加。中央政府既如此嚴格查對籍貫,一般官吏及有志上進的平民士子,對籍貫問題自不能沒有高度的覺醒。
科舉制度與籍貫
我國制度之中對籍貫觀念之形成影響最大的,莫如科舉。科舉制度成于唐,初盛于兩宋,極盛于明清。自兩宋起已為平民登進的主要途徑。惟兩宋之制,士子先經地方政府考選,保送到禮部,禮部考試及格,方為及第,故只有進士一項最高“學位”,與明清生員、舉人、進士三級“學位”制不同,考試與府州縣學校亦尚無全盤的聯系。
科舉制度對籍貫觀念之養成,還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自五代北宋門第消融之后,科舉成為一般平民名利之藪。登科的人不但可以奠定身家的經濟基礎,揚名顯親,而且可以援引提攜惠及宗族桑梓。甚至州縣之報荒減賦亦與一地人文之盛衰不無關系。所以近千年來,科第不但是個人單獨追求的目標,而且是地方集體爭競的對象。
郡邑間對科第角逐的具體象征,至南宋中葉已很明顯。現存文獻中自淳熙十二年(1185)起,各地就開始捐田置產,籌辦“貢士莊”或“興賢莊”以補助本籍舉子赴首都臨安參加禮部考試。南宋末葉此種制度特盛于江西諸郡邑,亦有稱作“青云莊”和“進士莊”的。湖南常德稱為“鄉貢過省莊”。明初因政府對各省赴京參加會試舉子有正式補助,江南各地貢士莊之制暫趨消沉。但政府補助畢竟有限,所以自晚明直迄清末,府州縣措備賓興基金之制日益普遍。
此外,最晚自南宋起,若干地方已經開始在城區建立狀元坊,以紀念當地科舉杰出人物,并借以鼓舞后進有志之士。到了明代,這種最富于心理激勵作用的牌坊日益普遍,而且決不限于紀念巍科人物。清代更甚,有些地方甚至將本籍以往進士一律入祠奉祀。科舉居然變成廣義地方宗教的一部分,則其對籍貫觀念養成之影響的深而且巨,概可想見。
總之,我國傳統的籍貫觀念,在舉世文明人種中確是一個特殊的觀念。這種觀念是由于兩千年來禮教、文化、方言和特殊行政法規與制度長期交互影響之下,逐漸培養而成的。至于籍貫觀念深強的程度,兩千年間各個時代不會相同,而且很難衡量。不過單就行政法規與科舉制度中所反映的種種社會現象而論,似乎時代愈晚,籍貫觀念愈深,至清代登峰造極,民國以來才趨削弱。會館制度的歷史即可較具體證成此說。但凡一種觀念發達到無可再強的時候,勢必開始衰弱,籍貫觀念也不例外。這一點可從會館制度長期演變之中反映出來。
選自《歷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