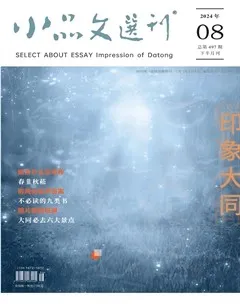“街巷志”原委


我寫《街巷志》初衷很簡單。2015年重讀劉亮程的《在新疆》,突發奇感,感覺自己曾在東北生活多年,應該認真寫一本關于東北的書,書名就叫《在東北》。后來一想,好不容易逃到深圳,不能因為一本書又回到東北,干脆就寫深圳吧。這里雖然沒有異域情調,但是更具都市風情。
其實我剛開始寫的時候并沒有將其概括為“街巷志”。我先是寫自己身邊熟悉的事物,比如我寫了住所附近的西鄉河、鐵崗村、寶安客運中心,還寫了我看到以及我感受到的深圳和其他地方的不同。比如在北方是春種秋收,秋天是花謝葉落的時節,而在深圳是春天落葉,所以我專門寫了一篇文字叫《金黃鋪就春天》,我還寫了春節前后大量深圳人離開的場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里的街巷并非是一街一路一社區,而是包羅萬象的生活。我所走過的每一步,海岸邊,樹林中,草地上,見到的一花一木,一貓一犬,凡是有人有溫度的地方都是街巷,都是人間煙火,而且還不止于濃濃的人間煙火氣,更有煙火之上的“神氣”。有了這個“神氣”,煙火氣才能氣定神閑、裊裊不斷。
正式出版時,我接受出版社的建議,把這些文字用“街巷志”三個字概括起來,第一本書名為《街巷志:行走與書寫》,出版之后有幸獲得了廣東省有為文學獎第五屆散文金獎和“深圳市十大佳著”獎;隨后又出版了第二本《街巷志:深圳已然是故鄉》;第三本《街巷志:深圳體溫》;第四本《街巷志:一朵云來》;第五本是《街巷志:擁擠的影子》,第六本《街巷志:水隨誰睡碎》也將于今年出版。我計劃寫十本以上,形成一個系列。
剛開始寫這個系列的時候是出于熱愛,我把這個城市當成了自己的故鄉,自己的寫作則稱為“城愁”,這是呼應所謂“鄉愁”的。因為在當下的語境里,“鄉愁”差不多已經被窄化為對田園牧歌的想象。事實上,隨著城市化的趨勢撲面而來,人們越來越向一些地方聚集,由此產生的所謂“城愁”的內涵和外延更深更廣。“城愁”總體上可以理解為城市生活背景下的一種情緒。再具體一點來說,就是對當下寧靜生活的撫摸和珍惜,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期待和擔心,對失去的成長場景的悵惘,它更傾向于中產階級的閑愁,而非外賣員的滿頭大汗,生死之下的掙扎和哭喊。當然有些東西也要涉及,但它不會成為我描述和抒寫的主流。
我對自己不做這種大而全的期待和要求。
寫著寫著,最初的熱愛漸漸就變成了使命感,覺得要賦予這個城市一點什么。比如在我看來,深圳缺少兩樣東西,一個是憂傷,一個是傳說。聽汪峰的歌曲《北京北京》,前奏一響起來的時候就有一種感覺:同為一線城市,北京有憂傷的氣質,而深圳沒有。憂傷是從容的,它需要幾百年的醞釀,上千年的沉淀,一個幾十年的城市似乎還不懂得憂傷。在火熱的深圳,成千上萬人時時刻刻都在演繹自己的悲歡離合,但是他們的愛恨情仇沒有憂傷做背景,瞬間就被抹掉了。
再比如我看了姜文演的電影《邪不壓正》,里面提到了一句話,把主人公想象成了“燕子李三”,我馬上把它和北京聯系在了一起。因為“燕子李三”就是北京的符號之一,這就是傳說的力量。當下深圳的傳說是什么?是任正非、馬化騰還是平安大廈?這些都是,但是它缺少一些更“人”的東西,看不到具體的、可以具化為你我的傳說。所以我就想,我能不能用自己的文字,塑造一種緩慢的憂傷情緒,賦予這個城市一些傳說。這種賦予,不是對當下的否定,相反,它是首先認可這個城市的世俗成功之后,有意識進行的文化塑造。
“塑造”,這個詞好大呀,深圳已經在這里,需要我塑造嗎?你王國華是干什么的?我要說,一個文化的深圳,當然需要文化人塑造。尤其是文學,此乃藝術之根。我的塑造體現在哪里?舉個例子,我在地鐵車廂里看到有人坐在你的肩膀上,那個人就是前些年上班時猝死在地鐵口的一個白領。我看到榕樹上住著一群人。我要在平巒山的樹林里挖一個陷阱,等著有人掉入并與我發生連接。我在南山區銅鼓路上找到一條很大很大的長椅,等世界末日來臨時,這就是我要避難的地方。我看到香蜜湖里的水飄了起來,是湖畔一只水鳥把它拽起來的,而那水鳥可能就是我指派的,我自己又渾然不知……是的,我把塑造的深圳原原本本寫到我的文字里,這一個一個遇到,一個一個想到和一個一個記錄,便是我塑造的深圳。
在這里我還要強調兩點。第一,我的文字是典型的非虛構。我并不認同所謂的“散文可以虛構”這樣的觀點。我的作品中的想象,讓人一眼就能看出是想象來。而不是虛虛實實,游刃有余地穿梭于小說和散文中間。這可能跟我的工作性質有關,我一參加工作就在新聞媒體,現在都20多年,已經形成了非常強烈的職業性,比如寫作深南大道時,我多次開車或步行或者坐公交或者騎單車,在深南大道上行走,其中一天就在深南大道上走了兩個來回,共計九個小時,期間開車80公里,騎行15公里,步行18000步,相當于用腳步把這條道路撫摸了多遍。
在寫作茅洲河時,我曾經看到河邊有兩排石墩,強迫癥上來了,一遍一遍地數,確認那是86個。其實完全可以模糊帶過,“河邊有兩排石墩”,這樣一寫就完事,但我一定要寫上“河邊有兩排共86個石墩”。
在另一本街巷志里,有一篇文章寫的是我從街邊走過,看到衣服店的櫥窗里有五個模特,站著四個,坐著一個。編輯也是個較真的人,她看大樣中的圖片,顯示是四個模特,于是向我詢問。我跟她講,我自己拍的圖片肯定沒錯。后來,編輯問了一下美編,原來是美編在處理圖片時切掉了一個模特。你把我這種較真稱為嚴謹也好,稱為強迫癥也好,但我在寫作上確實是這樣要求自己的。
第二,我非常重視所謂的文筆。說一千道一萬,打量一個文本,一個是看你寫了什么,一個是看你如何寫。余華的《活著》,就是寫一個老年人的一生,類似題材也不是沒有人寫過,但他們就寫不出余華那個樣子來。同樣的故事,在你的筆下就庸俗,在他的筆下就超凡脫俗,所以個人的表達能力和表達方式都很重要,而我在街巷志這個系列中非常強調文字的力量和文字之美,這還不是一個個簡單的“文字華麗”就能解決。我在東北生活時,常常去二人轉劇場看二人轉,臺上兩個人,在五十分鐘內,把上千觀眾的注意力集中在一起,靠的就是這種方式,即三句話一個包袱。所以我寫作時,時時注意語言的顛簸,而且也不能是刻意的顛簸,要恰當,潤物細無聲。
當然,我現在的寫作仍然在路上,將來怎么樣,自己也不敢說。有時候寫得越多,越到深水區,就越孤獨。其實我還挺享受這種孤獨的,我完全不期待這個系列大紅大紫,大紅大紫的文字常常會被異化,被誤讀。
選自《回族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