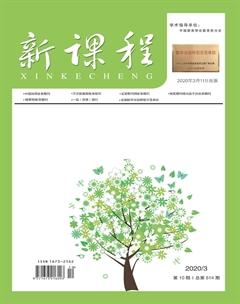初中歷史學科核心素養(yǎng)的培養(yǎng)策略
王劍鋒
摘 要:歷史學科教學中作為初中教育過程中的重要成分,其教學關(guān)系著學生良好認知的培養(yǎng)以及正確道德與價值觀念的形成,有助于學生從歷史中吸取教訓、獲得經(jīng)驗,能夠更好地傳承我國的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和精神。在唯物史觀、歷史解釋、史料實證、時空觀念與家國情懷之下訓練出特色化的學科思維,能夠提升實際教學效果,體現(xiàn)歷史的價值。
關(guān)鍵詞:初中歷史;核心素養(yǎng);培養(yǎng)策略
既有的歷史教學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學生的發(fā)展,學生不能夠真切地體會到歷史學科的人文性,對人類優(yōu)秀的歷史文化缺乏足夠的認知,其也不能在歷史的積淀下受到心靈的震撼與情感的陶冶。教師還應(yīng)該滿足學生在發(fā)展與培養(yǎng)上的不同要求,借助核心素養(yǎng)的培養(yǎng)過程來豐富學生的精神世界,從而進一步推動基礎(chǔ)教育改革的完善與發(fā)展。以下通過列舉應(yīng)用化的幾點培養(yǎng)策略,做到對教學課堂的高效把握,希望對后續(xù)的教學環(huán)節(jié)起到一定的幫助。
一、找到策略出發(fā)點,提高重視程度培養(yǎng)核心素養(yǎng)
課堂模式始終是教學的主場,而對于歷史學科來說,培養(yǎng)核心素養(yǎng)的教學策略始終是為核心教學目標而服務(wù)的,其出發(fā)點始終落在謀求學生的完善發(fā)展上,其教學培養(yǎng)過程是不斷深化與漸進的過程。對此,教師應(yīng)找到教學的出發(fā)點,使歷史教學目標與實際教學內(nèi)容相契合,從而在符合初中生的認知水平中提升學生的心理狀態(tài),在高度重視的前提下使學生在歷史學習中投入更多的精力,理解人物關(guān)系與事件的起承轉(zhuǎn)合,從而在分析歷史、了解歷史的途中定向培養(yǎng)學科核心素養(yǎng),在教學中逐步完善學生的思維結(jié)構(gòu),提升其能力層次。
例如,教師應(yīng)在《統(tǒng)一國家的建立》這一單元中,力求讓學生理解這一單元的主旨,找到自己教學策略的出發(fā)點,使學生能夠在課程的學習中領(lǐng)會歷史的魅力,理解我國文化的源遠流長,從而逐步使其樹立文化自信、制度自信。同時,教師也應(yīng)在教學中去努力強調(diào)這一單元的作用,讓學生能夠聯(lián)系上下文理解這一歷史時期對我國產(chǎn)生的深遠影響,在高度重視之下,學生自己也能逐漸理解歷史的“大勢所趨”,理解“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理解文化與精神中流淌的使命感。進而,在歷史學科的教學中,通過文化的渲染來促進學科核心素養(yǎng)的培養(yǎng),使歷史教學變得更有序而有效。
二、設(shè)計教學活動,合理切入情境培養(yǎng)核心素養(yǎng)
在各類教學模式中,創(chuàng)設(shè)問題情境的方法依舊經(jīng)典而有效,對于歷史學科同樣如此。但是教師也可以進行小小的改動與創(chuàng)新,在情境教學中加入一點新元素,嘗試用更多樣的方法提升教學效果。設(shè)計教學活動就是一項不錯的嘗試,在合理切入情境的途中,有效地思維引導在與情境的結(jié)合下能夠啟發(fā)學生的思考,借助多樣的互動來理解歷史問題,從而在目的性與方法論的指導下體現(xiàn)出歷史學科的知識特征與教學思想,更有效地改變教學狀態(tài),順利地展開后續(xù)的教學。
例如,初三上冊《亞洲與歐洲的封建社會》一課的教學中,教師可以借助話劇、電影、音樂等形式來讓學生理解封建時期不同地區(qū)的歷史與文化,從歐洲中世紀的騎士城堡,到亞洲封建社會的統(tǒng)一王朝,以嚴格的階級制度為例進行引申,講解雙方的異同。同時,在一些風情軼事的雜糅下,教師能夠使歷史教學展示更為鮮活,學生也能理解封建制度下人民的相對幸福與遭受的苦難。綜合上述,在歷史情境的代入中,學生能夠把自己幻想為詩人、騎士、商賈等各種角色,在人物的交織中描繪動蕩與英雄的史詩,從而學生能理解歷史的魅力,對核心素養(yǎng)的理解更上一層樓。趣味性的活動也能有效吸引學生的注意力,在高度的集中與適當?shù)姆潘山Y(jié)合運用下,歷史教學更豐富、更具人情味,在魅力的感染下,學生也能向?qū)W科核心素養(yǎng)逐漸靠攏。
三、展開歷史實踐,提升基礎(chǔ)認知培養(yǎng)核心素養(yǎng)
對于歷史學科而言,史料的存在是推動學科發(fā)展的重要基石。因而,學生的歷史學習與核心素養(yǎng)的存在也必須與史料牽連在一起。在歷史實踐活動中,能夠讓學生獲得更為具體、更多元化的認知,在實事求是的角度上了解書本上的歷史事件,在古跡與文物中理解歷史的厚重感與自身的責任感,從而對歷史形成更多的感悟。另外,歷史實踐的展開也能提高學生的基礎(chǔ)認知,激發(fā)學生探索歷史知識的興趣,在博物館、圖書館中更深入地理解人物的愛恨情仇,理解歷史事件之間的起承轉(zhuǎn)合,理解因果與偶然,從而為自身觀念的塑造打下良好基礎(chǔ)。
例如,對于《中華民族的抗日戰(zhàn)爭》這一課,教師應(yīng)該予以更多的筆墨與篇章去描繪這一段歷史,讓學生了解我們民族所遭受過的屈辱與苦難,了解我們民族的不畏強暴、自強不息與奮發(fā)向上,了解我們歷史文化中的精神內(nèi)核。在資料的收集與整合中樹立愛國觀念,在事件與生活的強烈對比中理解先人的不易與艱辛,在史料實證下提醒學生歷史存在的意義。以此,讓學生形成正確的觀念,在教學中深化自己的認知,從而培養(yǎng)歷史學科的核心素養(yǎng)。
總之,初中歷史教師應(yīng)堅決貫徹落實歷史學科核心素養(yǎng)的培養(yǎng),在正確的教學模式中讓學生更為全面客觀地認識歷史,理解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協(xié)同,在人文素養(yǎng)的提高中逐步實現(xiàn)立德樹人的終極教學任務(wù)。最終,將人才培養(yǎng)落到實處,體現(xiàn)出歷史學科的多重價值。
參考文獻:
[1]王景昆.談在初中歷史課堂上學生核心素養(yǎng)的培養(yǎng)[J].課程教育研究,2017.
[2]武朝元.基于核心素養(yǎng)的初中歷史教學探究[J].中國校外教育,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