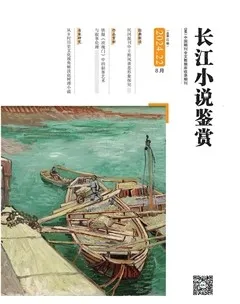論畢飛宇小說《上海往事》的影像化特征
[摘要]畢飛宇《上海往事》的創作契機是由電影《搖啊搖,搖到外婆橋》生發的,或是出于作家自身的文學自覺和電影編劇的雙重影響,《上海往事》的兩個文本“電影小說”和“電影文學劇本”都充盈著“出位之思”的美學特征。其中“電影小說”部分的影像化特征尤為矚目,如鏡頭化的敘事視角、視聽化的敘事語言、極具蒙太奇思維的敘事結構等。但影視思維雖悄然侵入畢飛宇的創作思維,“電影小說”部分文學敘事獨有的特性仍存在著,其靈魂并沒有被電影技巧所抹殺,電影化的想象是以一種正面的力量融入《上海往事》的小說敘事中的。
[關鍵詞]畢飛宇" "上海往事" "影像化敘事特征
[中圖分類號] I06" " " [文獻標識碼] A" "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4)22-0043-05
畢飛宇作為中國當代文壇不容忽視的作家之一,與影視也有著不解之緣。迄今為止,已有自畢飛宇文學作品改編而成的影視作品七部,包含電影四部、電視劇兩部、微電影一部。其影視改編的文學作品大多集中于畢飛宇轉型之后的創作,并且小說為電影(視)的藍本。但《上海往事》不同,它創作于先鋒寫作時期,卻表現出區別于同時期其他作品的現實主義特征。就創作動機而言,《上海往事》也并非滿足個人情感表達的需求,而是畢飛宇受張藝謀所邀,擔任電影《搖啊搖,搖到外婆橋》的編劇,根據李曉小說《門規》創作而成的。畢飛宇曾在文集《這一半》的自序中提到這段創作經歷:“嚴格地說,《上海往事》不是一部小說,它是電影《搖啊搖,搖到外婆橋》的劇本,因為我不熟悉劇本寫作,在樣式上,我依然把它寫成了小說。我惟一需要補充的是,《上海往事》的寫作和我當時的創作并沒有內在的聯系,但是,它是饒有趣味的一段插曲。”[1]
寫作時,影視思維悄然侵入畢飛宇的創作思維,他不可避免地會去思考如何創作才更有利于將其改編成電影,“那時候我對‘人物’‘故事’一點兒興趣都沒有。但是既然是為拍電影寫的,你就不能不考慮人物和故事”[2]。此外,小說與影視在“敘事”層面上天然的可通約性,也使得《上海往事》文本(“電影小說”和“電影文學劇本”)充盈著“出位之思”的美學特征:屬于電影敘事的“電影文學劇本”沾染著文學性;“電影小說”在堅持文學敘事獨有特性的同時,有意無意產生了類似影視藝術的創作思維與敘事方式的特征,視聽表達上的可行性較強。本文試從小說中顯露出的影像化特征切入,探討畢飛宇《上海往事》“電影小說”部分的敘事風格,管窺小說所具有的電影藝術特質及其魅力。
一、隱藏在敘事視角中的影像化特征
在《上海往事》“電影小說”中,畢飛宇并不拘泥于某種單一而固定的敘事視角,而是采用第一人稱回顧性視角,敘述自我與經驗自我之間視角的交替變化,除加強讀者的沉浸感和參與度外,還營造出一種穿越的姿態,增添小說戲劇性。而小說在凸顯人物感知位置,呈現人物觀察到的內容時,也為讀者建立了電影般的框架,如“取景框”一樣對人物所能獲知的信息范圍進行限定,仿佛有一架無形的攝影機隱于文字中,具有精妙的視覺感。故下文將從這兩方面切入,分析隱藏在敘事視角中的影像化特征。
1.視角的交替增添故事戲劇張力
《上海往事》“電影小說”采用的是第一人稱回顧性視角,故事圍繞敘述者“我”的所見所聞所感展開。但作為視角建構中心的“我”具有雙重的屬性——“我”身上交替投射出兩種眼光:一種是敘述者“我”回憶往事的眼光(敘述自我視角),另一種是處在回憶中的“我”正在體驗事件的眼光(經驗自我視角)。故事是以歷經滄桑的老者敘述自己的往事展開的:暮年時期的“我”講述年少的“我”在上海灘的一段傳奇經歷。但在回顧性的場景中,畢飛宇并沒有讓暮年的“我”來主導視角的設置,而是通過經驗自我——涉世不深的少年之眼觀看這個繁華淫逸又血雨腥風的世界。
這種敘述自我與經驗自我之間視角的交替變化在敘事時間上營造出了一種穿越的姿態:在“我”的雙重視角流動中,過去和現在兩條線性時間流程完成了交互。小說開篇,暮年歷經滄桑的“我”道出當初是為何來到上海:小金寶找不到稱心的貼身丫頭,想要個男人來伺候她。隨后敘事視角轉移為經驗自我,透過年少時的“唐臭蛋”看小金寶的一生,其間敘述自我以議論性的抒情語調評論曾經的場景,巧妙穿插在敘事段落之間。如第一章第三節,“我”觀看完小金寶的演出,與小金寶的第一次正式見面前,暮年的“我”以過來人的身份先對小金寶做一番評論,“我的上海故事,說到底就是我和小金寶的故事。我怕這個女人。那時候我也恨這個女人,長大了我才弄明白,這女人其實可憐,還不如我……”[3]小金寶的命運在小說一開頭便揭露,制造了關于人物經歷的懸念;在作者微妙地控制敘述距離后,物是人非的人生蒼涼感也油然而生。
2.敘事視角中的“取景框”意識
在小說情境的營造中,情境感知者位置的凸顯意味著作者有著明顯的“取景框”意識。“框”的存在說明作者對小說畫面所容納的信息有意識地進行篩選、截取、拼接,從而限定接收者的感知范圍,達到對客觀現實中人物所處情境的仿真模擬[4]。這種模擬的過程暗含著某種“鏡頭”意識,如第一章中“我”跟隨二管家來到唐府,“我”的所見所聞便是如此。
我跟在二管家的身后走向那扇大鐵門。大鐵門關得很嚴,在我走近的過程中,左側的一扇門上突然又打開了一道小鐵門。開門人又高又大,皮膚像白蠟燭,滿臉都是油光,他的手背與腮邊長滿亞麻色雜毛,眼珠子卻是褐色的。(……)
唐府的主樓是西式建筑。石階的兩側對稱地放了許多盆花。蘭草沿了墻腳向兩邊茂茂密密地蓬勃開去。院子里長了法國梧桐,又高又大,漏了一地的碎太陽。二管家領著我從右側往后院走。小路夾在兩排冬青中間,又干凈又漂亮,青磚的背脊鋪成“人”字形,反彈出寧和清潔的光。我聽見了千層布鞋底發出了動聽的節奏,走在這樣的路上心里自然要有發財的感覺。
“有錢真好。”我忍不住小聲自語說。
“有錢?這算什么有錢?”二管家說,“大上海隨你找一塊洋錢,都能找到我們老爺的手印。”
“怎么才能有錢?”我把箱子換到另一只手上說。
(……)
對面走過來一個女傭,她的手里捧了一大塊冰,涼得熱氣騰騰。(……)
二管家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把我帶進廚房,而是把我帶進了浴室。(……)我望著浴池,池面很大,正對爐堂口的墻面上晃著橘黃色火光,懶洋洋的。[3]
這一場景描述的是“我”跟隨二管家從唐府大門到浴室,一路的所觀所感。文本中那臺“無形的攝影機”先以“我”為主體,以二管家為前景,伴隨著“我”一起移動,而后以“我”為視點來看唐府。進門的場景先是一個推鏡頭,從環境出發,由大景別的大鐵門推向左側的小鐵門。隨著鏡頭向前推進,開門人的容貌被放在了視覺中心位置。開門人是個有著白蠟燭似的膚色、亞麻色的體毛、褐色的眼珠的白俄人。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灘,這個幫會能讓白俄人為其工作,“我”不禁思索唐府的實力是怎樣的強勁。進門之后便看見院子里的景觀,對稱式的構圖凸顯了院內景致的整潔美麗,也給人一種安靜的嚴肅感。“我”如黛玉進大觀園一般,細細觀察,對一切事物都感到好奇。一路上“我”看到的事物都以特寫鏡頭呈現,如:石階兩側擺放的花,沿著墻角蓬勃生長的蘭草,陽光透過法國梧桐樹葉投下的影子……特寫鏡頭是一種非常態的取景畫幅,帶有強調和加重的含義,故在某種程度上暗示僅僅是院子里的事物都給鄉下進城的“我”帶來了強烈的視覺沖擊,“我”的精神狀態極度緊繃。終于來到了浴室,取景范圍從小變大,視覺沖擊力也由強到弱,“我”看著浴池和墻面上晃著的橘黃色的火光,懶洋洋地,卸下一天的疲憊……在這個過程中讀者全程跟隨主人公的視點一并向前,所展現的情境也遵循著彼此的敘事聯系,讓讀者全面了解了人、事、物的空間聯系和心理內涵,既具有電影特性又不失文學性。
二、隱藏在敘事語言中的影像化特征
自身具有超強文字駕馭能力的畢飛宇在《上海往事》中還用直觀生動的語言調動讀者的多種感覺,構建具體可感的畫面情境,營造聲感空間效果,使抽象的語言形象化,概括性的文字具體化,讓讀者獲得觀影般身臨其境的現場感。并且這種充滿視聽觀感效果的語言文字并非停留于外在形式層面,而是與小說的主題思想相互交融,成為鋪排故事情節、突出小說主題的重要支撐點,讓敘事更加生動,引人入勝。
1.敘述語言的視覺造型性
色彩與光影的造型功能是影像化書寫的內在特質之一。兩者相互關聯、密不可分,“既是視覺造型,又是情緒氛圍;既是色調,又是情調”,既能夠“創造出具有鮮明視覺感的色彩特征”,又“往往蘊涵著某種意味,成為抒情表意的視覺符號”[5]。在《上海往事》“電影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畢飛宇巧用色彩和光影推動敘事,使讀者在閱讀過程中產生視覺性的文本觀感。如《上海往事》“電影小說”中關于人物外形、生活實物、日常場景等色彩都有細致描寫,使小說具有一種真實畫面的質感:小金寶在逍遙城唱歌時一襲紅衣顯得她光彩照人;唐臭蛋思念家鄉時,想起家鄉綠油油的菠菜和白花花的豆腐做成的神仙湯;生活在孤島里的翠花嫂“身穿土藍色上衣,土藍色上衣鑲了白邊,這道白邊與發髻上的一塊白布標明了她的寡婦身份”[3]。
光影的描寫在《上海往事》“電影小說”中往往和色彩描寫同時出現,兩者相輔相成,共同打造可視性的文學畫面;并為畫面注入情感,渲染情緒基調和特定氛圍,對人物情緒和心理進行即時折射。物體的固有色彩和光影共同形成色調,色調的冷暖既是視覺上物理的屬性,也具有產生不同審美心理體驗的效果,紅色、黃色、橙色等暖色調往往會給人一種溫暖、明艷的感覺;而藍色、綠色、灰色等冷色調往往會給人一種神秘、憂郁、悲傷的感受。小說中,夜里我們乘車到小金寶的小洋樓門口,推開門“我”看見馬臉女傭時的畫面便是一個很好例子。“開門女傭長了一張馬臉,因為背了光,我用了很長時間才看清她是個女人。”[3]夜晚室外和室內明暗對比強烈,開門后室內強烈的逆光把馬臉女傭整個人籠罩在陰影之中,只能看見她的外部輪廓,她臉上的五官都處于黑暗中難以辨認。此外,逆光而立的馬臉女傭還身著黑衣,這形成了以深色為主的低調畫面,這種大面積的暗色調與錯落猙獰的、滿嘴長牙的面部特寫搭配,突出了女傭的陰森恐怖和“我”內心的毛骨悚然。
2.敘述語言的聽覺化呈現
《上海往事》“電影小說”敘述語言的影像化特征還體現在大量運用聲音作為敘事手段,給讀者帶來視聽直觀般的感受。對白是人物間的對話,能夠“傳達談話人的心理活動,又能與對手交流,影響彼此的情緒、情感、思想和行為,故又常常稱之為‘言語動作’”[6]。《上海往事》“電影小說”中的人物對白十分貼近人物身份、性格、神態、所處情景,塑造出豐滿鮮活的人物的形象,且清晰簡短、通俗易懂,呈現口語化、生活化、動作性的特點,具有可讀性。如小金寶心情不佳不愿看社戲,拉著阿貴和阿牛玩游戲的情景。敘述語言的聽覺化呈現便在三人一來一回的對白中表現得淋漓盡致,“錘剪子包”“唱戲”“學狗叫”寥寥數語便推動了故事情節往下發展。破折號的使用模擬了他們玩錘剪子包時語速的延長。對白還極富生活氣息,十分符合人物設定的性格。小金寶來自鄉下,沒有接受過良好的教育,在老爺的圈養下,如今她雖享受著優越的物質條件,卻難改語言的質樸、潑辣。言語間,小金寶玩世不恭、膚淺嫵媚的形象躍然紙上。
除極具口語化、動作性的對白外,《上海往事》“電影小說”還巧妙地注入音樂元素對文本空間進行擴充。文本涉及的音樂唱段有《假正經》《花好月圓》、童謠“搖啊搖,搖到外婆橋”等。其中“搖啊搖,搖到外婆橋”還被選為電影名稱。該童謠在小說中共出現過三次,首次出現是在上海時,小金寶和宋約翰吵架后,小金寶讓“我”為她唱歌,“我”便唱了“搖啊搖,搖到外婆橋”。第二次是“我”和小金寶來到孤島,在碼頭余暉水波前,“我”、小金寶、阿嬌一起唱著“搖啊搖,搖到外婆橋”,此時沒有權謀,沒有殺戮,只有和煦的陽光、飄蕩的蘆葦、搖晃的水波。“我”看著小金寶唱歌時發自內心的純真笑容,燦爛又晴朗。隨后幾日小金寶目睹了門派內亂,間接害死翠花嫂和翠花嫂的心上人;自己所托非人,經歷愛人宋約翰的背叛;喜愛的小阿嬌也被唐老爺圈養,重蹈她的覆轍,走進上海灘這個修羅場。小說第十章,小阿嬌再次唱起“搖啊搖,搖到外婆橋”,情境已天翻地覆,曾經溫情的童謠,在此刻顯得無比的諷刺。
三、隱藏在敘事結構中的影像化特征
敘事的情節結構是一個擁有多級層面的復雜概念,最首要的和最基本的一個層面,是指具體敘事文本的結構關系和表達方式。而一個敘事文本的總體結構包含情節事件、時間畸變、空間顯示、敘述方式等各個要素和方面的分解、配置、對應與整合。這與蒙太奇思維不謀而合:蒙太奇是選擇若干處在不同時空的部分(或要素)及其序列以表現某種特定的主題內容的技巧。畢飛宇在構思《上海往事》“電影小說”時便巧用這種蒙太奇思維分切與組接畫面段落,重新排列組合,形成“集聲畫之美,匯視聽之娛”“無狀之狀,無像之像”的敘事畫面。蒙太奇根據敘事與表意的功能分類,可分為敘事蒙太奇和表現蒙太奇,下文也將從這兩方面切入分析《上海往事》“電影小說”包含蒙太奇思維的敘事結構。
1.以敘事為主要目的的蒙太奇敘事
敘事蒙太奇以交代情節、展示事件為主旨,按照情節發展的時間流程、因果關系來分切組合鏡頭、場面和段落,從而引導觀眾理解劇情,包含連續蒙太奇、平行蒙太奇、交叉蒙太奇、重復蒙太奇等。“電影小說”中敘述自我與經驗自我之間視角的交替變化已見蒙太奇的端倪,構成了一個打破時空秩序的電影式的復合敘述結構。其中為主導視角的經驗自我視角帶有明顯的連續蒙太奇思維,以時間的走向為軸線,敘述了鄉下少年唐臭蛋來到上海,被安排在當紅舞女小金寶身邊服侍所引出的黑幫悲情故事。并且故事以小金寶性格的發展史為順序,遵循事件發生的先后順序展開,有頭有尾,環環相扣。畢飛宇分解了作為整體的事件,擇取對事件發展具有實質意義的場景和片段進行組合連接,敘事自然流暢,樸實平順,從而有機結合整篇文檔。
此外,畢飛宇還巧用了其他敘事蒙太奇,例如平行蒙太奇。平行蒙太奇也稱并列蒙太奇,是指兩條以上的情節線并列表現、分別敘述,最后統一于一個完整的情節結構。如第八章中的社戲之夜,斷橋鎮里老壽星的喜喪迎來了社戲,一對紅男綠女在石拱橋上開唱。被軟禁的小金寶住在不遠處的閣樓上,但她并沒有被社戲的情節感染,水邊的歡笑和她沒有關系,接著她換上紅裙,與阿貴、阿牛喝酒猜拳。于是,同一時間斷橋鎮不同地點的兩出大戲上演,此間畫面的描寫不斷在社戲現場與小金寶、阿貴、阿牛間交替。而后興致正濃的小金寶唱起了那首《假正經》,社戲臺上演唱社戲的小丫頭被小金寶離奇古怪的歌唱吸引,呆愣住了,忘記了橋邊琴師們的過門,眾人視線也從社戲臺轉移至身著紅裙盡情演唱的小金寶。“臺下大聲喝彩,他們做夢也沒想到社戲場上還能看到另一出大戲。”[3]兩條并列的情節線索最終整合在統一的敘述結構中。
2.以表現為主要目的的蒙太奇敘事
表現蒙太奇的主要作用是表情達意,它的目的不是敘事,而是傳達出一種情感和寓意,包含對比蒙太奇、隱喻蒙太奇、心理蒙太奇、抒情蒙太奇等。《上海往事》“電影小說”中多以心理蒙太奇、隱喻蒙太奇的形式呈現。心理蒙太奇是人物心理描寫的重要手段,它通過畫面鏡頭組接形象生動地展示出人物的內心世界。在“電影小說”中,心理蒙太奇使用交叉、穿插等手法來表現人物的回憶、閃念、遐想、思索等精神活動,具有敘述的不連續性、節奏的跳躍性。如穿插于文本之中的敘述自我:“她在我的腦子里風情萬種,一眨眼,就成骷髏了。”[3]“我倒是說句公道話,槐根的死真的不能怨小金寶。”[3]這種主觀視點改變了“電影小說”的時空維度,時間由此被拉伸、變形。文本除敘述自我具有心理蒙太奇思維外,經驗自我也呈現出心理蒙太奇思維。如“我”在看到老爺的相貌時,這一段心理蒙太奇頗為生動滑稽。未見唐老爺前,在“我”心里唐老爺幾乎成了一尊神,這個有錢有權的幫派老大應該高大威嚴、相貌堂堂。而看到唐老爺時,“我愣住了。我幾乎不相信自己了,這哪里是老爺?這哪里是上海灘上的虎頭幫掌門?完全是我們村里放豬的老光棍”[3]。高大威嚴的形象瞬間坍塌了,取而代之的是村里放豬的老光棍形象。這樣帶有強烈主觀色彩的內心獨白與富有直觀畫面的描寫結合起來,不過幾十字就為讀者展現出唐老爺的粗野猥瑣形象,和“我”內心的失望、驚訝。
文本中的隱喻蒙太奇也尤為精彩,故事將某一事物和小金寶外在特質、內在精神中的任意一點集合起來,含蓄而形象地表達創作者的某種寓意,引起讀者的聯想并領略事件的情緒色彩。如小說從第七章起便多了關于“太陽”的空鏡頭描寫。“太陽”的色調變化隨故事情節發生變化,也意味著小金寶離開上海后心態與命運的改變。第七章小金寶在看守的監視下逃跑,打算乘纖船離去,但面對長者們詢問“你是誰?從哪來的?要到哪去”時,往日八面玲瓏的小金寶閃爍其詞,回答不上來。她在十里洋場中沉淪,成為權色交易的玩物,她或許還記得自己的來處,卻不知逃離后將來的去處,天地遼闊,但也無處可去。小金寶痛恨現在墮落的生活卻無力反抗,于是小金寶重新返回了斷橋鎮,這時“太陽已黃昏了,像一只蛋黃,扁扁地一晃一晃,在天地之間岌岌可危”[3]。之后,在人跡罕至的孤島上,小金寶遇到了一對淳樸善良的母女(翠花嫂和阿嬌),孤島的鄉村生活雖簡陋,卻透射著淳樸的民風,讓小金寶暫時忘卻上海的糜爛歲月。“這時候太陽極柔和,在夏末的植物上打上了一層毛茸茸的植物光暈。”[3]隨著故事的發展,唐老爺與宋約翰攤牌,奪權之爭和偷情之事暴露,唐老爺決定將阿嬌帶回上海打造成下一個小金寶。此時,“滿天滿地全是鮮嫩的太陽。小金寶貯了滿眼的淚,把我攬進懷里,望著初升的太陽說:‘又是一個乖太陽。’我抱緊小金寶的腰,滿眼是血色的晨光”[3]。“鮮嫩的太陽”暗喻著小阿嬌,一個太陽落下,另一個鮮嫩的太陽又升起,純真與欲望,喜與悲在不斷輪回。“血色的晨光”中小金寶萬念俱灰,放棄了生的希望,揮刀自戕。這些“太陽”意象意蘊深遠,頗具匠心,與敘事蒙太奇組合連接,讓小金寶不同時期的心緒、情感緩緩流出。
四、結語
綜上所述,《上海往事》“電影小說”雖是視覺文化時代作家主動介入與選擇的結果,但畢飛宇作為電影編劇,卻沒有一味迎合影視市場,而是用自己獨特的方式去調和文學的商品性和藝術審美性之間的矛盾。小說文本中仍帶有文學敘事獨有的特性,更多是為故事而寫、為小說而寫,具有顯著的個人性。故而畢飛宇面對文學與影視聯姻的這種應對策略、小說中呈現的影像化特征,歸根到底仍是為文學服務的一種敘事手段,是電影對文學的一種反哺。這也使得小說《上海往事》的靈魂并沒有被電影技巧所抹殺,文學敘事獨有的特性仍存在著,電影化的想象、影像化敘事是以一種正面的力量融入小說敘事中的。
參考文獻
[1] 畢飛宇.這一半[M].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04.
[2] 畢飛宇,張莉.小說生活:畢飛宇·張莉對話錄[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
[3] 畢飛宇.上海往事[M].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5.
[4] 英佳妮.小說的電影化敘事手法及其審美價值表現[D].上海:復旦大學,2012.
[5] 彭吉象.影視鑒賞[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6] 夏衍.電影藝術詞典(修訂版)[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5.
(責任編輯" 夏" "波)
作者簡介:張傳穎,重慶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