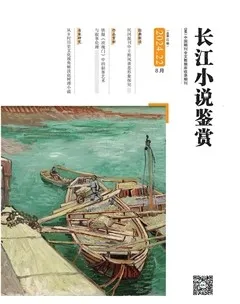場域理論視野中的王占黑小說異質性研究
[摘要]在布迪厄的場域理論中,文化資本有其“開放性”,廣泛地與社會、經濟產生互動。與“90后”作家群體內其他作家的小說創作相比,王占黑的小說作品有著強烈的異質性。從布迪厄的場域理論視野來看,這些異質性受到社會、經濟、文化場域的不同影響:社會、經濟場域中城市化進程加快,商業資本不斷擠壓形成了處于城鄉夾縫中的異質空間——老社區;文化場域中,豆瓣等網絡創作平臺影響了王占黑小說的敘事結構和敘事風格,形成了獨特的作品形式。
[關鍵詞]布迪厄" "場域理論" "王占黑" "小說" "異質性
[中圖分類號] 1206.7" " " [文獻標識碼] A" "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4)22-0048-04
從布迪厄的場域理論視野出發,在中國社會場域中,長久以來的藝術實踐形成了文化資本運作的脈絡。在當代,這條脈絡又重新分散開來,受流媒體等技術環境的變革力量沖擊,當代文學的內外“場域”都產生了復雜的變化。
王占黑1991年生于浙江嘉興,最初在豆瓣平臺以“小伙鍋”的ID活躍,2012年,她在豆瓣主頁拋出第一篇小詩《棄兒》,2018年,先后出版兩部作品《空響炮》和《街道江湖》。王占黑從網絡平臺走向文壇的路途是她的天分與機遇使然,或者從布迪厄的場域理論視角來講,是應社會“場域”變化而生的。被她橫空出世吸引而來的眾多研究者也都反復強調這一點。在以王占黑作品為對象的研究文章中,頻繁出現“城市化”“時代記憶”“社區空間”等有著強烈“場域”意味的詞語。山東省作家協會的孫濤教授抓住“寫作空間”[1]這一視角,透析王占黑對“老社區”的偏愛,挖掘她身處“90后”作家群體,卻與習慣于情緒化青春敘事的群體寫作截然不同的“異質性”。承接其下,2020年華東師范大學的黃平教授在《定海橋:王占黑小說與空間政治》一文中更進一步地從日本城市化進程中的反叛活動談起,試圖從時代和群體的角度探究王占黑對“社區空間”的特殊塑造。
目前研究者們從敘事結構、手法、整體風格到小說的現實意義、寫作立場,從形式、內容再到意義多方位地對王占黑的小說作品進行剖析,不約而同地對其創作的“異質性”給予肯定。誠然,在與同齡人注重技巧與結構的創作對比之下,王占黑的小說創作從各個方面來說都有其鮮明的個性。從布迪厄的場域理論出發探究王占黑的創作在時代與群體中的“異質性”表現和成因,無疑是一條極為合適的路徑。
一、文學外部場域:城市化進程加快造就“異質空間”
從大眾角度來說,新的獎項、新風格的獲獎者是大眾能夠捕捉到“異質”和新風向出現的最直接途徑。2018年9月,王占黑獲頒首屆寶珀·理想國文學獎;2018年12月28日,榮登2018年中國“90后”作家排行榜第二名[2];2019年6月,王占黑又憑借《小花旦的故事》獲得《鐘山》之星文學獎“年度青年佳作獎”[3]。一系列的榮譽將僅在豆瓣平臺活躍的王占黑快速推向大眾。
在運用場域來理解王占黑的小說創作之前,需要先對“場域”作出界定。“場”的概念首先存在于現代物理學中,被用來形容物理意義上的“磁場”“立場”等空間,后被引進心理學領域,作為格式塔心理學派的理論基石,用來形容各種心理現象與其各種現象關系的總和整體。布迪厄將“場域”理論擴充、完善,引用到社會學領域中,并對場域作出解釋:“從分析的角度來看,一個場域可以被定義為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的一個網絡(network),或一個構型(configuration)。”[4]布迪厄認為,場域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空間。
在高度分化的社會里,每一個領域是由大量具有相對自主性的社會小世界構成的,布迪厄在書中指出“這些社會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邏輯和必然性的客觀關系的空間,而這些小世界自身特有的邏輯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約成支配其他場域運作的那些邏輯和必然性”[5],因此這種“關系”網絡有著無限的延展性與包容性,能夠細分出不同的“子場域”,例如文學世界之外是整個社會場域,文學世界則作為一個以文學為關系核心延展開來的關系網絡,成為整個社會場域中的子場域;又例如在一個以“行政區劃”為關系劃分標準的“市轄區”場域中,又以生產、行政區劃等關系標準劃分出“城”“鄉”兩處子場域。王占黑筆下的“老社區”空間正是處于“城”“鄉”兩處子場域的縫隙間,“融合了鄉村與城市的雙重特征,物質空間中它屬于城市,但氣質上卻保留著鄉土社會所常見的熟人社會”[5]。
在王占黑的小說作品中,故事背景大都設定在以作者家鄉為藍本的同一個老社區中,《街道江湖》與《空響炮》里的短篇小說都對這個“老社區”的空間布局做了相似的描寫,比如養老院后的棋牌室(《麻將,胡了》《怪腳刀》)、小區里的水果攤、菜攤、早點鋪、雜貨店(《水果攤故事》《老菜皮》《阿祥早點鋪》《阿金的故事》)等等,同樣的角色、地標穿梭閃現在兩本書中,構成相似的場域。
城市化進程不斷向前推進,對土地和商業資本的爭奪不斷改變著城市結構。在布迪厄的場域理論中,場域“作為包含各種隱而未發的力量和正在活動的力量的空間,同時也是一個爭奪的空間,這些爭奪旨在維續或變更場域中這些力量的構型”[5]。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末,住房由“國家福利制”過渡到“單位福利制”,創造了以“單位”為基本單位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6]。90年代后,上海開始大規模住宅建設和舊城改造,單元樓又被商業資本拆分,住宅社區漸漸成為空間分異的最小單元。21世紀后,人們又爭相涌進高樓大廈,王占黑在《街道英雄》的后記中寫道:“于是小區成了老小區,工人新村成了舊新村,留下來的,多是老人、窮人,以及外來務工的新居民,這構成了舊型社區在新世紀的鋼筋水泥,也恰好代表著三種不容忽視的社會角色:工人群體,日益龐大的老齡化群體,以及低收入的外來務工群體。他們共生于一處,以遲緩的腳步追趕城市瘋狂的發展速度,吞吐著代際內部的消化不良。”[7]
當同時期的作家要么徹底“懷舊”,描寫20世紀的情狀(金宇澄《繁花》),甚至穿越時空去解構、重構歷史神話(莫諾長篇小說《浮生,舊時樓臺》、林為攀的古典系列小說),要么追求現代性,描寫現代城市(路魆《西鳥》中廣州西關大屋、《離開離島區》里香港棚屋和重慶大廈),甚至超前地構建賽博空間(三三《獵龍》、鄭在歡《今夜通宵殺敵》),王占黑選擇站在時代的縫隙,選取兼有新舊二元色彩的老社區空間作為故事背景,自有其獨到的眼光與獨一份的社會責任感。
在這個復雜的小場域中,保留著城市化初期的某些習慣,比如與居民樓間雜的商鋪,卻又在社會大場域的內部競爭中失去了以往的一些資本,比如勞動力、就業機會等。對于這樣一處“競爭失敗”的小場域,王占黑有一份自己的責任感:“我有必要將另一種不成景觀的景觀展示出來,展示出他們臨死而不僵的內部狀態,那種在歷史命運的末路上仍然飽含著的無窮的興致和張力。”[8]
二、文學內部場域:網絡文學襁褓中誕生的“異質形式”
布迪厄的場域絕不是簡單意義上的物理“空間”,一切有著運行“慣習”與各種形式“資本”的關系網絡都可以沿著場域理論解剖。但與其同時代的理論家福柯、德里達等人不同,布迪厄并不是激進的“解構”主義者,他將研究對象建立在“關系”思維的范式中。在文學世界內部,雖然無法界定其物理空間范圍,但布迪厄將文學生產過程中的作者、出版商、批評家以及讀者等多種因素納入到場域的視野中,從而使場域理論具有“開放性”[9],以更為廣博的視角去探究文學的全貌。因此,從開放性的視角來看,王占黑作品異質性的產生并不能片面歸結為社會、經濟場域的沖擊,而應該看到文學場域內部的變化對王占黑創作的影響。
王占黑所處的“90后”作家群體與過往的作家群體在條件上有極大不同,他們緊跟時代潮流,樂于嘗試各種新興技術,在開發多元出場路徑的同時也能更好地與讀者交流。豆瓣、貼吧、知網等也成為“創作”平臺,創作者與讀者的關系更加密切直接,“網絡文學”的所指也不再局限于寫作平臺的產出。
網絡媒介對“90后”作家的影響已充分顯露,多種文化形態出現,依據場域的機制,正是不斷的斗爭推動著歷史的前進,場域內的競爭不會停止,直觀體現在各大文學排行榜中。有研究者評價說:“文學排行榜已經成為‘90后’作家的一種生存方式。”[10]為了在各類文學排行榜中占有一席之地,搶奪文化資本,“90后”作家群體迸發出強大的內部力量,自主改變某些寫作方式。于是在文學場域內部,“創作”一環的慣習改變,“異質”不斷產生。
王占黑小說敘事受其平臺環境影響,采用豆瓣平臺常見的第一人稱作為敘事角度,與王占黑平和冷靜的敘事口吻結合,形成了強烈的代入感和可讀性。這兩點共同構成了作者在平臺上爭奪讀者資源的“入場券”。在這樣的爭奪中,王占黑的作品憑借其特殊的敘事結構和敘事風格吸引了大量讀者。
敘事結構上,由于王占黑出版的小說作品大多在其早期活躍于豆瓣平臺時就已有雛形,或已作為獨立、片段式的小故事發表,比如《預言》《小官》(出版時改為《小官的故事》),出版后也沿用了共享背景卻又相互獨立的故事結構。不同人物的故事在書中各章次第上演,卻沒有連貫的時間、空間順序,每一章故事地位平等,不存在“主線”“副本”,唯有老舊的社區作為背景佇立在城市縫隙。王占黑的故事看似散亂地抓取老社區中的鄰里往事,但奇妙地還原了老社區完整的風貌和人情。龍迪勇在《空間敘事研究》中將這種敘事結構總結為“主題—并置敘事”,即“在文本的形式或結構上,往往是多個故事或多條情節線索的并置”,“構成文本的各條情節線索或各個‘子敘事’之間的順序可以互換”[11]。中國美術學院的沈晴將其形象地稱作“橘瓣式結構”[12]。
王占黑小說的敘事結構源于作者最初在“網絡文學”這個場域中的寫作慣習:“經驗在前,知識在后。”[8]沒有出版的壓力,寫作目的就從“吸引人買”回歸到“表達”,在豆瓣上發表的居民故事就是王占黑“過去很長時間里認識的和聽來的東西”[13]。這也是王占黑與同齡創作者截然不同之處,作為一個“90后”小姑娘,她的私人經驗不像很多青年作家那樣是自己的成長經驗,而是父輩的、他人的故事。王占黑的小說有著同齡人作品所沒有的平靜的“老氣”,也就遠離了大多數網絡創作者容易陷入的“無痛呻吟”的青春敘事。
如上所述,王占黑作品的敘事風格始終有一股平靜的“老氣”。《街道英雄》《空響炮》以三種社會角色為主體,“工人群體,日益龐大的老齡化群體,以及低收入的外來務工群體”[8],老舊的社區就是他們生命的空間表征,即使曾經去大城市歷經大風大浪,回歸到這里后也會選擇安于寧靜,就像年輕時在大西北闖江湖最后回到家鄉當保安的“小官”(《小官的故事》)。“他們的背后,是一座安寧的小區,一片安寧的夢。我們都在等待明天到來。”[14]王占黑在三部已出版的作品中都反復書寫一種寧靜或者向寧靜復歸的生活狀態:徐爺爺、美芬、小官……,即使是后期“走出社區”[15]的《小花旦》,也在人物不斷的波折間傳遞對平靜生活狀態的向往。
王占黑的大多數作品誕生于網絡文學的襁褓中,對個人經驗的自由表達使得她的作品有著自己的個性,雖也難免在敘事上陷入一種“自我重復——故事的重復與敘事的重復”[16],但能在當下的網絡文學場域中突破青春敘事或浮夸炫技的慣習,以特殊的敘事結構和風格敘寫故事,在場域中形成獨特的“異質形式”,已經為王占黑在當下的文學領域中奪得了一處好位置。
參考文獻
[1] 孫濤.社區空間與平民世界的游蕩——論王占黑的小說創作[J].寫作,2019(5).
[2] 網易.2018年中國90后作家排行榜發榜,陳昂、王占黑、李尚龍居前三![EB/OL].2018:[2018.12.30].
https://baike.baidu.com/reference/22885065/533aYdO6cr3_z3kATKbfy6jwZinMMoilvrXSB-FzzqIP0XOpRIfkVYY77tBx8PJwB0Wa5sssY9kY2eyrVB8asKAPcOUqQ7cglGn-Viy3zbnmgK1JntFAoYhKKcxgmam16xg.
[3] 王覓.首屆“《鐘山》之星”獎掖優秀青年作家[N].文藝報,2019-07-05(1).
[4] 布迪厄,華康德.實踐與反思[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
[5] 徐威,嚴東林.論王占黑小說的社區主題與敘事藝術[J].惠州學院學報,2021,41(2).
[6] 胡毅,張京祥.中國城市住區更新的解讀與重構:走向空間正義的空間生產[M].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15.
[7] 王占黑.社區、(非)虛構及電影感[M]//街道江湖.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8.
[8] 王占黑.不成景觀的景觀[J].大家,2018(1).
[9] 布迪厄.藝術的法則:文學場的生成和結構[M].劉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
[10] 田也.文學排行榜:“90后”作家的一種生存方式[J].創作評譚,2022(1).
[11] 龍迪勇.空間敘事研究[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2014.
[12] 沈晴.90后作家王占黑小說的空間敘事研究[J].寫作,2020(4).
[13] 澎湃新聞.專訪王占黑|一個90后作家眼中的下崗潮、老齡化和社區變遷[EB/OL].[2018-10-10].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503093.
[14] 王占黑.街道江湖[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8.
[15] 澎湃新聞.90后作家·訪談|王占黑:我已經走出社區了[EB/OL].[2020-05-27].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565493.
[16] 趙天成.始有意為小說——“90”后作家的驚險一躍[J].青年作家,2018(10).
(特約編輯" 張" "帆)
作者簡介:劉明霞,西華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研究方向為現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