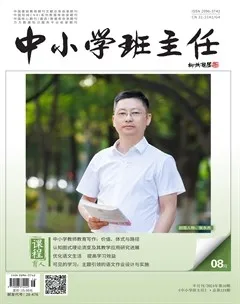論教育寫作的目的:闡釋學的視角
[摘要] 從闡釋學的視角看,教育寫作是關于教育者寫作過程本身的意義研究。重視教育寫作展開過程體現了寫作的真正目的,突破了以往教育寫作經驗性、零碎化的表達形式。以目的為導向,以過程為核心,推動教育者對自我身份的尋求及認同;將經驗性的知識整合轉化為審美意識的能動覺醒;“寫”的過程推動教育者價值觀念的重構;教育者與他者構成的多元主體在時空交錯的多向維度中,形成互動性的辯證循環。最終,有效化解教師“寫不出”的擔心和“寫不深”的焦慮。
[關鍵詞] 教育寫作;目的;闡釋學;視角轉換
人生活在意義世界之中,而意義世界是由語言和闡釋搭建起來的。語言蘊含著意義可能性,闡釋則使意義可能性顯現為現實性。闡釋是語言的重要功能之一。人類世界離不開語言,也離不開闡釋。意識到闡釋的重要性,就有了專門探究闡釋奧秘的學問,即闡釋學。
教學寫作是運用文字符號的形式呈現教育工作結果的有效途徑,其中包含教育者、教育對象和表達形式。當下的教學寫作,要么重視教育者自身的經驗性總結,要么強調教育對象的復雜和多變,卻忽視了寫作表達形式的有效意義,教育寫作本身是教育者對自我身份、自我行為及自我價值的一種具體表現。
一、尋求身份的認同
教育寫作的表達及呈現方式多樣,如教案、教學論文、讀書筆記、下水作文、文學作品等。教師在繁重的日常教學工作之中寫下的作品,是否能表現出寫作者的內在情感體悟和獨到思考,便成為一個問題。真正意義上的教育寫作,不是為了應付常規性的教學檢查、職稱評定和業績考核等事務,而是用文字的形式表達作者自身的形象,以及作者通過寫作的方式尋求最真實的自我。其具體表現在,寫作欲求的沖動、寫作情感的真摯、寫作意志的堅定。
曹禺在《和劇作家們談讀書和寫作》中說:“我想寫作要有對生活的真實感受,逼得你非寫不可,不吐不快。”作家因為對現實世界有發自內心的感觸,所以不得不用“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感受。正如笛卡爾所言“我思,故我在”,它強調意識自為自在,肯定意識的懷疑反思能力。人的自我身份,在此等于純思的意識。笛卡爾式主體的身份認同不僅強調“思”與自我的一致和自足,他還堅信思想的我就是自我身份認同的內在核心。來源于對現實世界的思考是激發教育者寫作的動力,一方面是對教育活動的經驗性總結,將教育感受轉化為獨特的內心體驗,借助文字的形式表達給他者,從而推動經驗的不斷傳播和交流;另一方面是教育者對自身教育方式的反思,是對教學方法的總結性回顧,將教學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及時整理在冊,從而不斷推進對教師身份的自我思辨。
以往的教育寫作更多注重教育經驗的總結,強調對教育心得的優化,注重教育感想的傳播,如同優秀教師傳授心得一般,是個性化、碎片化的經驗性匯總。這忽略了每一位教師主體身份的唯一性、差異性。真正的教育寫作要求落實到每一位教師自我層面,用發自內心的欲望作為創作動力,才能激發出對教育活動獨特的、鮮明的思考。正如《毛詩序》所言“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其不僅呈現真切的教育感悟,更是教師對自我身份的認同,同時通過寫作完成對自我情感的塑造。
于是,確立具有啟蒙價值的身份認同,通過寫作的形式實現自我精神世界的整合。人是完全以自己為中心的統一體,具有理性、意識和行動能力。換言之,教師通過真實的教育寫作過程喚醒自我對主體價值的認同,將過去具有零散性、單一化的教學感想整合為體系化、多維度的教學成果。
二、審美意識的覺醒
如果說教育寫作的內在動力是對自我身份認同的尋求,那么,寫作所呈現及表達的內容便是教師真摯情感的流露。華茲華斯說:“因為一切好詩都是強烈感情的自然流露;并且,雖然這點是真理,但是凡是有點價值的詩篇,并不是可以隨便拿一類主題來創作的,而都是出于一個具有異乎尋常的官能感受力,而且經過深思久慮的詩人之手。”詩人通過栩栩如生的詩行傳達對世界的思考,以求真求善的態度看待世界。艾青用一生的堅守書寫“詩人必須說真話”的信念,“真是詩底唯一深固的始基,詩是真底最高與最終的實現”(《〈詩與真〉序》)也說明了這一點。對于教育寫作而言,更需要一顆求真務實的心去觀照教育活動的意義和價值。
真摯的情感表達是對教育活動的審美創造。用“心靈喚醒心靈”的方式打開教師的審美意識,創造出主體與客體互相契合的審美空間,喚醒教育對象的審美共通感。正如鮑桑葵在梳理休謨的“共通感”時所言:
美給予人的快感大部分是從便利或效用的觀念中產生的。因此,這個似乎值得注意的論點正是把效用觀念和美感精確聯系起來的方式。因為休謨極其明確地判定,美一般來說總是由于效用而起。這種效用同產生美感的觀賞者根本無關,只牽涉所有人或直接關心對象的實際特性的人。因此,只有通過共鳴,觀賞者才能感受美。
教育寫作的過程不僅關系到教師自我與過去的有效共鳴,感同身受,更需要重視教學活動中與學生之間的交流溝通,即師生之間的情感共鳴。而情感共鳴的核心在于審美意識的契合,如劉勰筆下的“神與物游”,謝赫畫上的“氣韻生動”,王士禎詩行中的“興會神到”,王國維詞話中的“無我之境”。回顧性的教育寫作是將曾經體驗過的審美共通感再次凝練,并運用形象的文字形式將其再現出來。寫作的過程即審美意識的再次喚醒,重新回到教學過程之中。這就打破了時間上的距離,將教師再次拉回課堂之上,不僅是知識層面的溫故知新,更是審美方式的再次重構,如闡釋學所言的“視域融合”,即將當下的主體自由再現在自然形象之中,于是,自然形象的各組成部分在主體性作用下融合為一個有機統一的生命整體。
寫作的意義就是將外在于時間、空間的自然事物,再一次“靠心靈灌注給它的生氣”而形成審美的共通感。此刻的教師不再局限于對經驗的闡發,或者對現象的追問,而是轉向審美意識的創造。于此,教育寫作的目的便喚醒了教師內在的自我,“他仿佛忘記了歷史,像古人一樣,開辟一片藝術的新天地,使之從虛無墮入毫無掩飾的混亂的狀態”。將自我與過去經驗世界連接在一起,同時關注學生的課堂表現。一方面,把教師對教學內容的知識性理解傳達給學生,達到“授業解惑”的目的;另一方面,通過與學生的互動交流,將教學內容的審美體驗分享給學生,喚醒學生對教學內容的深度理解,打開審美共通感的窗口。與此同時,寫作的過程也再次激發了教師的創造活力,不斷推動教師去探尋課堂內外的深層意義。
由此,教育寫作的核心內涵轉變為寫作教育。這表明,把知識性層面的教育活動實踐轉化為審美創造層面的主體重構。換言之,教育寫作的過程是對教學經驗的累積和加工,更多的是呈現教師對知識的整合能力。而關注教育寫作的目的,就是重視教師寫作過程本身,即通過寫作達到對教學過程的再次創造,喚醒教師內心的審美意識,并且將其審美意識傳達給讀者,特別是反饋給學生,讓他們再次鞏固課堂內容,同時深化對自我審美意識的理解。
三、價值觀念的重構
從本質上講,教育寫作的目的是關注“寫作過程本身的意義”。因為教育寫作更多的是教師對其主體價值的思考和追問,以“寫”的方式再次回溯教學的全部過程。主要體現在:“寫”是“思”的目的,“思”是對“寫”的重構,“寫”與“思”構成辯證統一的整體。
其一,教育寫作是“思”的目的。胡塞爾認為闡釋的本源在“回到現象本身”,海德格爾強調“世界關聯的目標就是存在者本身——此外無什么;一切科學研究借以發生、從中辨析的那個東西就是存在者本身——此外無什么;唯有存在者——此外無什么”。對于教育寫作而言,亦是如此,以往的教育寫作“人們聚焦的始終是‘經驗構成’,即‘寫什么’,至于‘如何表達經驗’,即‘怎么寫’,要么降入技術層面,要么干脆束之高閣,在‘書寫’慣習的支配下無意識運行”。教育寫作不能離開教師的能動思考,“思”是教師對自我價值觀念的不斷提問,對教育活動的追問才能不斷更新教學知識,而存在于意識觀念層面的“思”又不能被長時間保存,更不能傳遞給學生,所以需要教師不斷地“書寫”,將潛意識形態的思考轉化為可見形態的文字符號。
其二,“思”是對教育寫作的重構。正如“唯有變才是不變本身”,教育寫作的過程是對教師價值觀念的不斷重組,擴充主體的想象力。想象是人對不可能存在、不存在或此時此地不存在的東西的呈現能力。想象作為一種意識,它只能表示意識與對象的關系;換言之,它是指對象在意識中得以顯現的某種方式;或者如有人愿意這樣說的話,它是意識使對象出現在意識中的某種方法。因而拓寬教師關于寫作的想象力,將經驗習得性知識不斷重組、加工、整合,獲得知識層面的提高。此時,寫作能帶給寫作者一種不斷發現生活新意的習慣,甚至是不斷創造新生活的動力,而這便是一個人創造性的基礎,最終能讓人形成創造性的職業人格,從而也會改變教師的職業生活,使其免于平庸和職業倦怠。由此,教師通過寫作的方式打開了關于“認識自我”的窗口,提煉整合原有價值觀念,歸納拓展新的價值原理,創造出新穎的、具有啟發意義的教學思想。
其三,教育寫作與教學思考構成動態性辯證循環。“寫”與“思”不僅僅具有共時性關系,還處于歷時性的不斷重組過程之中,即“思”的本身在于對教學活動的反問和質疑,而“寫”是對教學結果的總結和調整。通常認為,“思”在“寫”之前進行,“寫”是“思”的被動結果。其實,在闡釋學視域下,“教育寫作”的過程一直是處于變動不居的狀態,既是在“思考‘寫作’過程中的問題”,又是在“寫作的過程中‘思考’問題”。
歸結起來,教育寫作是教師自我與教學事實之間連續不斷的、互為作用的過程,是現在與過去無休止的對話;寫作的過程就是將過去經驗所得與自身實踐相結合,以文字的形式將記憶形象化、再現化。實際上,教育事實就是關于個人的事實,不過,不是孤立狀態下的個人行為,不是關于一些真實的或想象的動機,教育寫作記載的是關于社會之中個人之間彼此關系的事實,是關于個人活動結果所產生的那些社會力量的事實,這些結果帶有個人經驗的鮮明特征,同時也呈現出教師在時代背景下的共性樣貌。
用闡釋學的觀點看,對于寫作過程的思考,闡釋學反思所揭示的并非一種封閉自身的心靈、一種純粹內在的自身呈現,而是一種朝向他者性(otherness)的開放狀態,一種外化的、不斷超出自身的運動。只有把自己呈現給世界,我們才能把自己呈現給自己;也只有把自己給予自己,我們才能對世界有所意識。教育寫作是教師對自我教學活動的不斷重構,用“寫”的方式打破對以往經驗的思維定式,此刻的“寫”不再是靜態的文字書寫,而是具有動態性的思維活動。教師在寫作的過程中不斷深化“思”的深度,而“思”的力度又不斷推動教師去探尋“寫”的奧秘。
四、主體超越的崇高
通常意義上,教育寫作的主體是教師或者從事教育教學研究的科研人員,但實際上,教育寫作的主體并不局限于此。一方面是經驗主體的互動,具體是指教師與教師之間、教師與學生之間、教師與家長之間的互動交流,形成多元主體的融合;另一方面是歷時性主體的融合,具體是指教師通過寫作將過去、當下、未來三維時空連接在字里行間。
其一,教育寫作是多方主體經驗的互動。雖然寫作表達主體是單一的教師,但是教師在將教育活動結果呈現出來的過程中,包含了對教育對象的引導、教學內容的整合、教師同行的切磋,以及與家長之間的溝通。誠如海德格爾“將生活世界刻畫為周圍世界、共同世界和自我世界這三個領域的相互滲透,并主張作為世界體驗者的此在從來都已經和他人共在(mitsein)”。對于教師而言,將自身習得的知識傳遞給學生,使其學會并掌握解決問題的能力;而教育寫作的回溯進一步深化教師對知識世界的理解,并且以“寫”的形式重新確立自身的主體地位。
寫作結出的果實——文章,再次反饋給同行或家長,此時,教育寫作的過程才算正式開始,因為讀者的閱讀是打開作者心靈之窗的鑰匙。文本世界的展開是讀者與作者相互融合的開端,用沃爾夫岡·伊瑟爾的話講,寫作本身包含著“隱含的讀者”,包含作者對讀者的“召喚結構(appeal structure)”。對于教育寫作而言,以往教育寫作的終點,即教師文章的完成或者發表,標志著寫作任務的完成。而實際上,教育寫作的文字沒有被讀者閱讀,沒有反饋給學生或家長,沒有引領學生參與教師的回顧性反思,這樣寫作本身的“召喚結構”也就未被打開,教師的寫作也就并不具有現實意義。
其二,在尋求教育主體多重互動的過程中,加深教師對自我時空限度的認識。以寫作的形式聯通當下與過去的時間,在文本世界中展開當下自我與過去自我的有效對話,“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教育生活,很容易造成新鮮感的消退、創造激情的淡化,而對備課、作業、考試這些日常生活的審視與重建,不僅給平凡的教學生活帶來新鮮感,也能不斷積累對教育、對兒童、對課堂等十分豐富的感性經驗,這些恰好形成了一名教師專業成長的資源庫”。寫作,此刻不再是為功利性的教育考核服務,而是回歸自我教學生活的一種途徑。
用海德格爾闡釋荷爾德林的詩句“人充滿勞績,但還詩意地棲居在這片大地上”所言:
“詩意地棲居”意思是說:置身于諸神的當前之中,并且受到物之本質切近的震顫。在其根基上“詩意地”存在——這同時也表示:此在作為被創建(被建基)的此在,絕不是勞績,而是一種捐贈。
從本源上看,時間與空間不具有可回溯性,不能逆向發生。然而在教育寫作的展開過程中,教育者置身于事物的本質,也即“在世界中存在”。寫作將主體的自我帶回歷史時空的場域,通過文字的梳理將思考訴諸當下,而此刻的當下又凝結著過去的自我情感,打破時空閾限,生成新的主體價值觀念。
此刻的主體價值觀念,不再是單向維度的觀念判斷和價值選擇,而是具有三維向度的崇高超越,在連接過去的同時,把當下的寫作投向對未來的思考,具有“向死而生”的超越。可以說,寫作的完成并不是簡單意義上的生命終結,“寫作”賦予了人的生命的無限希望,打破了存在主體對生命有限性的焦慮,突破了“俯仰之間,已為陳跡”的羈絆。顯然,教育寫作,成為教師個體生命不斷延續的有效形式,既能夠將過去經驗匯聚成知識性成果,又能夠在不斷“寫作”中消解時空間隔,同時也把當下的感悟訴諸未來,延展個體生命的三維空間,超脫當下認知的束縛。
總之,基于闡釋學視角對教育寫作的思考,更加重視“教育寫作過程本身的意義”,突破以往教育寫作過多重視原因與結果、問題與措施、策略與方法等層面的考量。回歸本源性問題,落實到“寫”的過程本身,其中隱含著教育者主體對自我身份的尋求,在不斷“書寫”的過程之中,喚醒自身對寫作意義的審美創造,同時激發被教育者對美的追尋。由此,推動教育者從經驗性的知識積累和感悟性的審美欣賞轉變為對教育寫作觀念的反思,把“寫作”與“反思”融合在文字表達的過程本身之中,形成互動性的辯證循環,不僅消解“寫不出”的擔心與憂慮,而且打破“寫不深”的畏懼與虛無。最終,寫作過程本身便成為連接主體與他者視域的橋梁,成為貫通主體時空閾限的紐帶。
[參考文獻]
[1]曹禺.和劇作家們談讀書和寫作[M]//曹禺全集(第5卷).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6:369.
[2]趙一凡,等主編.西方文論關鍵詞(第一卷)[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20:5,466.
[3]馬瑞辰撰,陳金生點校.毛詩傳箋通釋(上)[M].北京:中華書局,1989:1.
[4]章安祺編訂.繆靈珠美學譯文集(第3卷)[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5-6.
[5]鮑桑葵.美學史[M].張今,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235.
[6]伍蠡甫,胡經之主編.西方文藝理論名著選編(中)[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318.
[7]李政濤.教育經驗的寫作方式——探尋一種復調式的教育寫作[J].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13,11(03):149-159.
[8]讓-保羅·薩特.想象心理學[M].禇朔維,譯.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8:25.
[9]顏瑩.教育寫作:教師專業表達和專業發展的必由之路[J].人民教育,2020(06):66-68.
[10]丹·扎哈維.現象學入門[M].康維陽,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3:74-75.
[11]莊華濤,等.教育寫作離我們有多遠[J].小學語文教師,2015(04):21-25.
[12]海德格爾.荷爾德林詩的闡釋[M].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