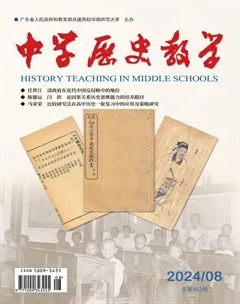清政府在近代中國反侵略中的地位
摘 要:洋務運動的根本目的是維護清王朝的統治,但這不是它失敗的主要原因或根本原因。自鴉片戰爭至19世紀60至90年代中期的邊疆危機,清政府是抵抗侵略的組織者和領導者,是救亡圖存的行為主體。有意將清政府與愛國官兵區別開來的歷史敘事,忽略了近代中國反侵略斗爭的民族性,不能正視清政府在反侵略斗爭中的主體地位,用反封建的情感書寫反侵略斗爭,有悖歷史唯物主義。
關鍵詞:清政府 反侵略 主體
初中歷史教科書八年級上冊第18課《洋務運動和邊疆危機》分別敘述了洋務運動與19世紀60至90年代中期的邊疆危機,包括美日侵臺、新疆危機、左宗棠收復新疆、中法戰爭、新疆和臺灣建省。關于洋務運動的結論,教科書說:“由于洋務運動的根本目的是維護清王朝的統治,再加上內部腐敗和外國勢力擠壓,它沒有使中國走上富強道路。”[1]這句話的邏輯是根本目的決定了最終結果,而且主次原因表述的很清楚,“再加上”就是說內部腐敗和外國勢力的擠壓屬于次要因素。在歷史事件中,當事人的根本目的決定了事件的結果,這種說法符合歷史唯物主義嗎?這節課接下來就要介紹左宗棠收復新疆。左宗棠是陜甘總督,他鎮壓陜甘回民起義和西征收復新疆,直接目的和根本目的毫無疑問都是為了維護清朝統治。劉銘傳在臺灣組織抵抗,馮子材在鎮南關英勇殺敵,為的是什么?不也是為了維護大清國嗎?顯然,以根本目的判斷結果,是主觀唯心的推理;歷史已經證明必須推翻清王朝,因此凡是維護清王朝的行為都是錯誤的,都必然失敗。歷史唯物史觀強調當時的歷史條件和歷史情境,并不以歷史的最終結果評判歷史過程中發生的事件。動機是人的主觀愿望,效果是實踐后的客觀結果,動機可能決定效果,也可能“事與愿違”,歷史上“歪打正著”的事例太多了。教科書對洋務運動失敗的結論不僅存在邏輯問題,史實解讀也有誤區。
長期以來,我們的近代史敘事不承認清政府是救亡圖存的行為主體。鴉片戰爭以來,外敵入侵是王朝國家面臨的最大威脅。以前革命史觀說,農民階級首先奮起抵抗,既反封建又反侵略,肩負起救亡圖存的歷史重任,第一個事實論證就是太平天國運動,清政府作為對立面被批判。2001年教育部頒布的《全日制義務教育歷史課程標準(實驗稿)》,不要求了解太平天國運動,卻在學習主題“列強的侵略與中國人民的抗爭”之下,要求“知道太平軍抗擊洋槍隊的事跡”,以事實說明農民階級反侵略,但這卻是對史實的誤讀——清軍和太平軍的洋槍隊都是雇傭洋人做領隊和教練,與列強政府無關。現行教育部統編的初高中歷史教科書,雖然介紹太平天國運動,但是結論只說它沉重打擊了清王朝的統治,不再說它反侵略。那么,面對民族危亡,是誰在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呢?換言之,救亡圖存的行為主體是哪一個?歷史教科書的敘事一直含含糊糊,不敢正視清政府為救亡圖存所做的努力。
實際上,這節課闡述的邊疆危機足以說明清政府是反侵略的組織者和領導者。19世紀60至90年代中期的邊疆危機是兩次鴉片戰爭的繼續,而且是更為嚴重的危機,而對危機反應最敏感的是清政府。關于“海防”和“塞防”之爭是政府抵抗的戰略之爭,決定收復新疆的是清政府,左宗棠既是主張者也是執行者。他官居陜甘總督又是欽差大臣,既是地方大員也是朝廷重臣,參與朝廷核心的決策。左宗棠收復新疆明擺著就是代表清政府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因為認識到新疆對穩定西北邊陲的重要性,所以才將新疆從甘肅省管轄下剝離出來,新疆建省更屬于政府行為。清政府是收復新疆的主體,功勞不能只記在左宗棠一人名下。
同理,劉銘傳在臺灣的抵抗,馮子材在鎮南關英勇殺敵,都體現了清政府的意志。1884年清政府專門委派劉銘傳督辦臺灣軍務,籌備抗法。馮子材在廣西、貴州提督位置上干了20年,剛退職沒兩年就趕上法軍進犯。他主動組織團練參戰,被兩廣總督張之洞起用抗法。他們兩個不屬于清政府的核心成員,但也是食朝廷俸祿的高官,他們都是為保全大清疆域也就是為王朝國家殊死抵抗。高中歷史必修教科書《中外歷史綱要(上冊)》說“洋務派期望洋務新政可以保障國家安全,抵抗外敵侵略”是實事求是的表述。洋務派也是清政府的代表,洋務運動的根本目的既包括維護清朝統治,也是為了“保障國家安全,抵抗外敵侵略”。那么,將洋務運動的失敗歸結為它的根本目的,豈不是說,抵抗外敵侵略決定了它必然失敗?其實,應以內因是決定因素的理論分析,腐敗和制度的落后才是主要原因和根本原因。
另外,19世紀60至90年代中期的邊疆危機還不能說明洋務運動的結果。《中外歷史綱要(上)》說:“洋務派期望洋務運動可以保障國家安全、抵抗外敵侵略,后來的事實證明這個目的未能達到。”[2]強調“后來的事實證明”主要指甲午中日戰爭。初中教科書在這節課中提前指出洋務運動的失敗,不如用“后來的事實證明”為好。教科書字字珠璣,應該更嚴謹甚至滴水不漏。
教科書的說法并非獨創,褒獎愛國官兵與民眾自發的抵抗行為,貶低乃至無視清政府是反侵略的主角地位,至今仍是中國近代史敘事的主調。這種區分忽略了反侵略斗爭的民族性。反侵略是國家和民族的對外抵抗,上至皇帝下到子民,立場是一致的。皇帝視江山為“家業”,抵抗侵略的意愿比官員更堅決也更用心。盡管深居九重的道光帝,戰敗后都不知英國來自何方,不諳海戰及其武器的變化,但是不能說他消極抵抗。他繼位第一年就嚴厲禁煙,重申:來粵外國商船先行出具貨物并無鴉片的甘結,然后方可開艙。對開煙館者,議絞;販賣者,充軍;吸食者,杖徒。自此鴉片躉船從黃埔移至伶仃洋。之后道光帝每年都有禁煙指令,他的態度影響到各級官員,他組織了“嚴禁”與“弛禁”的大討論,于是才有了鄧廷楨、許乃濟、黃爵滋、林則徐的奏折。而后在他主持制定并頒布的《欽定嚴禁鴉片煙條例》,向世人公開表明了朝廷禁煙的決心。以前教科書說,林則徐奏稿中“若猶泄泄視之,是使數十年后,中原幾無可以御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3]打動了道光帝,其實應該說,道光帝的禁煙決心為林則徐提供了用武之地。林則徐奉命進京的第二天清晨,道光立即召見,接連三次召見并賞賜林則徐在紫禁城內騎馬,這是特殊的鼓勵,令林則徐興奮不已。道光又擔心林則徐不習慣騎馬,允其坐轎,關愛至極。林則徐在京13天,道光帝召見19次,授予欽差大臣重任,并諭令鄧廷楨等配合林則徐“除中國大患之源”[4],鄧廷楨在林則徐未到廣州之前便將道光諭令抄發給下屬文武官員。可以說,沒有道光帝的重視和支持,林則徐禁煙寸步難行。因為在清朝中央和地方大員中,反對禁煙或持保留態度的占絕大多數。林則徐深知潛在的危險,他知難而進既出于愛國熱忱,也是對道光帝信任的報答。那些我們熟知的愛國將領都是這樣,關天培生前說過:“吾以兵丁起家微賤,仰荷天子厚恩擢任大員”,他是道光帝一步步提拔起來的。得知關天培戰死沙場,道光“震悼”,令建祠,并親書“為國捐軀”四個大字,賜謚“忠節”,入祀昭忠祠,命翰林院撰寫碑文。[5]關天培以死報國也是上報天恩。在那個時代忠君與愛國并不矛盾。
開戰后,道光帝基本上是主戰。他不希望“開邊釁”,曾幻想“羈縻”洋人,但面對侵略者的步步緊逼,他是抵抗的組織領導者,調兵遣將非他莫屬。他有用人不當、聽信讒言、指揮失據的過錯,但在兩年的反侵略戰爭中,他部署防御,掌握戰況,籌撥軍餉,獎功罰過,始終堅持抗戰。我們贊揚的愛國將領也得到他的表彰、賜謚、立祠和撫恤家屬等。《南京條約》簽訂后,他一夜未眠,頓足長嘆,痛苦又無奈。戰后八年,道光帝仍不敢松懈,“一再下詔練兵設防,整頓吏治財政,圖謀挽救。”[6]盡管他的目的是守護“家業”,維持清王朝的統治,但是他力主禁煙、堅持抵抗,符合愛國官兵和民眾的意愿,維護了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如此,將清政府與愛國官兵區分開來的歷史敘事有悖歷史事實。在反侵略戰爭中,愛國官兵與清政府是一碼事,自發的民眾抵抗也沒有將自己與清王朝對立起來。魏源《道光洋艘征撫記》中記錄了廣東義民痛斥義律的檄文,其中說:“爾自謂船炮無敵,……倘再犯內河,我百姓若不云集十萬眾,各出草筏,沉沙石,整槍炮,截爾首尾,火爾艘艦,殲爾丑類者,我等即非大清國之子民。”[7]陳旭麓先生說:“民眾是以‘大清國之子民’的立場與外夷相抗的。……人民群眾的反侵略斗爭固然有游離于官府之外的一面,但反侵略斗爭畢竟不同于國內階級斗爭,不同于天地會、白蓮教。共同的民族意識和感情常常使官與民之間還有相通的一面。為今日史學家所稱道的民眾義舉,其組織者和領導者則多是士紳。”[8]士紳是基層社會的地主階級,他們組織和領導了三元里等民眾的反侵略斗爭,這說明反封建服從于反侵略。在近代史的書寫中,將反封建的情感用于反侵略的書寫,這是將清政府與愛國官兵區別開來的根源。
近代中國面臨反封建反侵略兩大主題,這兩個主題不是并列關系。從鴉片戰爭到甲午中日戰爭,反侵略是主題。太平天國運動一度使反封建躍居首位,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兩個主題并列或交錯。太平天國運動失敗后,19世紀60至90年代反侵略又上升為主題,反封建居次要地位,這時主持反侵略的只有清政府。無視清政府在救亡圖存中的主體地位,不符合歷史唯物主義。
【注釋】
[1]《中國歷史(八年級上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3年,第21頁。
[2]《普通高中教科書·歷史·必修·中外歷史綱要(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2年,第97頁。
[3]中山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現代史教研組、研究室編:《林則徐集·奏稿》,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601頁。
[4] 林則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林則徐全集》(第3冊 奏折卷),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1264頁。
[5][6]馮士博、于伯銘:《道光傳》,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201、297頁。
[7][清]魏源著,魏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魏源全集》(3),長沙:岳麓書社,2011年,第469頁。
[8]陳旭麓:《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第6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