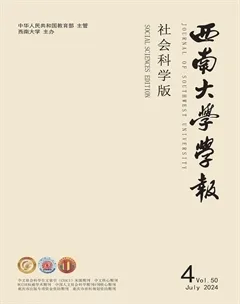明清鼎革期間明將毛文龍與朝鮮關系研究
摘 要:明清鼎革之際,明與后金之間的軍事爭奪時有發生,雙方爭奪的結果直接決定了誰將成為未來東亞宗藩體系的領導者。在看似明確的敵我對抗和表面的新舊交替背后,還潛藏著宗藩體系內部成員的觀望與自保、多方勾連甚至待價而沽。毛文龍作為明將代表明朝在朝鮮履行保護朝鮮國家安全的義務,但卻卷入了明、后金與朝鮮三方博弈的漩渦之中。朝鮮作為明朝宗藩體系最親近的一員,一方面與毛文龍互相袒護與猜忌,一方面又與后金保持半臣屬狀態。無疑,明將毛文龍與朝鮮關系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明清鼎革前夜東亞宗藩體系內部關系實態的理想視角。
關鍵詞:明清鼎革;宗藩體系;兩面外交
中圖分類號:K248;D82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9841(2024)04-0232-11
毛文龍是明朝天啟年間和崇禎初年在遼東地區的重要將領,曾在明朝屬國朝鮮境內的皮島駐軍數年,設立東江鎮開辟對抗后金的敵后戰場,從后方牽制后金,一度讓后金軍隊放緩了對遼西地區采取軍事行動的腳步。近代學術意義上對毛文龍的研究始于民國時期的梁啟超、李光濤等人,但此時的毛文龍研究多從屬于對袁崇煥的研究,且內容以袁崇煥矯詔擅殺毛文龍的原因、過程等為主,涉及毛文龍自身及其東江鎮者甚少。直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東江疏揭塘報節抄》點校出版后,針對毛文龍、東江軍鎮本身及其與朝鮮、后金關系的研究才逐步出現。對毛文龍的評價也由民國時的全盤否定“毛文龍之擁兵島上,抗命海外,牽制雖絕無,釀亂則有余,與唐之安史,宋之劉豫,又何異焉”[1],轉變成兩極分化,學界爭論十分激烈。
關于毛文龍與朝鮮的關系,肯定毛文龍者,認為毛文龍在東江鎮駐軍并企圖聯合朝鮮,依靠來自朝鮮的補給進行軍事行動的目的歸根結底還是為了保衛明朝,對抗后金。如孟昭信即指出:“毛文龍頑強地堅持對敵斗爭,更不放棄聯合朝鮮……他曾致書朝鮮國王,陳述唇齒之形,倡議合作對敵,謀恢復之局。”[2]否定毛文龍者,則認為毛文龍禍亂朝鮮,致使朝鮮在天啟七年(1627)遭受了后金軍隊的入侵,“毛文龍所作所為,使明廷與朝鮮均受其害。于朝鮮,則使其國上憂下怨,疲于應付,正所謂‘主客俱困’”[3]。另有學者堅持功過參半的客觀態度,一方面批評毛文龍勒索、專制朝鮮,引燃戰火,致使朝鮮最終喪權辱國;另一方面,“毛文龍雖然沒能收復一寸土地,但是他監督朝鮮,離間朝鮮與后金之間的關系,迫使朝鮮政府放棄保持中立的‘兩端’外交政策,推行‘崇明排金’政策”[4]。可見,毛文龍的存在使得朝鮮不得不“崇明排金”,對于明朝與后金在遼東的作戰起到了正面的作用。
前述研究運用明朝、后金和朝鮮的史料從不同角度對毛文龍與朝鮮的關系進行了梳理,得出了頗多具有價值和啟發的結論。但論述毛文龍與朝鮮關系者,大多把研究視野聚焦于明、朝鮮二元,兼顧后金者已屬少數。實際上,毛文龍處于明、朝鮮、后金三方關系之中心,而三方關系的真正邏輯卻隱匿于東亞宗藩體系的整體格局之中。是故,本文擬以明將毛文龍與朝鮮關系為視角探討明清鼎革前夜東亞宗藩體系的內在博弈。
一、毛朝聯系之初建
(一)毛文龍從戎遼東
毛文龍,字振南,杭州錢塘人,祖籍山西平陽,于萬歷四年(1576)生于杭州。幼年的毛文龍在父親亡故后,隨母親投靠于其舅沈光祚家中。沈光祚仕途順遂,于萬歷二十三年乙未科中三甲第十九名,賜同進士出身,曾歷任兵部主事[5]38、山東左布政使[6]卷7,天啟元年三月丁未、順天府尹等職[6]卷34,天啟三年五月丙申,且“公正廉潔,綽有政績”,不阿附閹黨,“挺然獨立”[7]卷15,P4,聲名顯赫。自然,沈光祚對毛文龍的仕宦引領作用也在情理之中。天啟三年五月,沈光祚去世。此時毛文龍尚處于東江鎮經營初期。光祚之死使他喪失了朝中的重要依靠。
毛文龍著迷于軍事,對兵法情有獨鐘。《東江遺事》記載毛文龍“幼從學,授經生業,厭之,思棄去。客有講孫吳兵法者,求其書諦視,忽心開”[8]213。早年毛文龍“嘗與人群飲酒樓,酣,拍案呼曰:‘不封侯,不罷休!’”[8]210,有著一番在沙場為國家建功立業,拜將封侯的豪情壯志。
赴遼東從戎是毛文龍人生的重要轉折點。毛文龍歷任海州衛百戶、安山百戶、遼陽千總、叆陽守備等官職。萬歷四十六年至泰昌元年(1620),他先后在遼東經略楊鎬和熊廷弼手下屢立戰功,并得到熊廷弼的上疏贊揚:
管鐵騎營加銜都司毛文龍,棄儒以戎,志期滅虜,設防寬、叆,凡夷地山川險阻之形靡不洞悉,兵家攻守奇正之法無不精通,實武弁中之有心機、有職見、有膽量、有作為者,豈能多得,應與實授都司,以展其才。[9]543
天啟元年遼陽失守后,毛文龍自海路投靠駐守廣寧的遼東巡撫王化貞。由于王化貞與毛文龍之舅沈光祚關系密切,且沈光祚向王化貞推薦了毛文龍,故毛文龍終于獲得重用,并受封游擊,才能得以進一步顯現。
鎮江(今屬遼寧丹東)之捷是毛文龍發跡的直接原因,也是他最終入據皮島的重要條件。天啟元年三月,努爾哈赤下令進攻遼東諸城。同年五月,烏爾古岱和李永芳率軍赴鎮江,旋即占領之,并留佟養真帶領一千軍士駐守。明朝守將王紹勛逃亡入海,但遼東人民進行了頑強的抵抗。明朝若想繼續維持在遼東的脆弱統治,就必須派兵支援遼東義民以牽制后金軍事力量,爭取戰略主動。在獲得兵部和朝中部分官員的支持后,遼東巡撫王化貞決定采取軍事行動。熟悉遼東地形的毛文龍主動向王化貞請戰,得到應允后他便帶領近二百人出發收復遼東失地。七月中上旬,毛文龍先后收復了遼東沿海的廣鹿島、哈店島、石城島等島嶼,并一路誅逆納降,安撫百姓。七月二十日,毛文龍趁鎮江城中部分后金士兵出城執行任務,城內空虛,與鎮江城中的內應里應外合,內外夾擊襲取了鎮江城,并擒獲鎮江守將佟養真及其子佟松年等數人,派人押解至遼東巡撫王化貞處。鎮江之捷震動遼東,激發了明朝守軍和心向明朝之百姓的斗志。毛文龍也趁機招納百姓、義民,嘗試勸說投降后金的將領反正,壯大自身的實力,結果“寬、叆一帶城堡相繼降,數百里之內望風歸附,日扶老攜幼至者百余人”[10]1450。
鎮江之戰的塘報隨即遞至北京及南方諸省。明軍在遼東屢次失利,此報一出,“縉紳慶于朝,庶民慶于野”[11]148。憑借鎮江之戰,毛文龍的威名在君臣朝野之間稱頌不已。因鎮江之功,天啟皇帝將毛文龍晉升為副總兵。內閣首輔葉向高亦給予鎮江之戰積極的評價,“今有幸毛文龍此舉稍得兵家用奇、用寡之法”,將之與“班超以三十六人定西域、耿恭以百人守疏勒”之奇功相提并論[6]卷15、天啟元年十月庚辰。當時的主流觀點是,鎮江之戰在遼東屢次戰敗后直接提振了大明軍民抵抗后金的士氣,塑造了毛文龍的英勇形象,被時人所推崇。
但此時朝中也有部分大臣對于鎮江之戰持否定態度。遼東經略熊廷弼、登萊巡撫陶朗先等人均持此觀點。熊廷弼認為毛文龍在后續援軍還沒有準備就緒之時就發動反擊,很可能會打亂朝廷在遼東的整體布局,進而導致更大規模的失利。對鎮江之戰的爭議使得遼東經略熊廷弼和遼東巡撫王化貞之間的不和逐漸加劇,毛文龍被歸于遼東巡撫王化貞一系,徹底被牽連進了明末糾纏不斷的黨爭之中。
努爾哈赤得知毛文龍出奇兵襲取鎮江后,立即派遣貝勒皇太極和阿敏先后率五千兵馬反擊,欲采取“緩進巧戰”的策略[12]223,奪回鎮江。毛文龍雖向朝廷求援,但由于路途遙遠,援軍無法及時趕到救援鎮江。后金軍隊的緩進給了毛文龍充分的思考時間,最終在前有強敵、后無補給的情況下,經陳良策的勸說,毛文龍決定保存有生力量,率兵撤退至鴨綠江畔,與后金軍隊周旋,對后金軍隊進行騷擾,且戰且退,直至跨過鴨綠江退入朝鮮境內,駐守麟山郡。后金軍隊于十二月十五日在貝勒阿敏的率領下跨過鴨綠江,繼續追剿毛文龍部。兵力不足的毛文龍在朝鮮境內繼續從事抗金活動使得朝鮮君臣十分為難,他們認為“毛將之來往也,啟我國之不測”[13]卷169,光海君十三年九月甲子。這體現朝鮮君臣對毛文龍在朝鮮境內從事抗金活動的擔憂。最終一直奉行“兩面外交”政策的朝鮮國王李琿還是選擇了保護代表明朝的毛文龍,但出于保護自身國家安全的考慮,他先勸說毛文龍移入朝鮮內地避敵,后建議毛文龍躲入海島。毛文龍聽從了朝鮮國王的建議,在十二月避居龍川。毛文龍還向朝鮮國王請兵支援,但朝鮮國王擔心遭受后金軍隊的報復,拒絕了毛文龍的請求。
后金軍隊來勢兇猛,朝鮮邊臣擔心后金軍隊“假道伐虢”進攻或移怨朝鮮,故而縱容后金軍隊渡江,甚至與之私通。朝鮮邊臣并未將后金的軍事行動及時通知駐軍龍川的毛文龍,最終使得后金軍隊得以突襲毛文龍部,斬殺士兵和遼民上千人。游擊呂世舉也在此戰陣亡。后金軍統帥阿敏從俘虜口中得知毛文龍在距離龍川九十里外的林畔散兵向各村乞食,下令急行軍追殺毛文龍。毛文龍部猝不及防,沒有組織起有效的抵抗就再次潰敗,被后金軍隊殲滅殆盡。毛文龍本人則化裝成士兵在朝鮮龍川府使李尚吉的“極力藏護”下[14]434,只身得脫。龍川、林畔兩敗的主要原因是朝鮮邊臣的騎墻,但毛文龍自身的放松警惕也是失敗的原因之一。
(二)毛文龍借勢立足皮島
林畔戰敗后,毛文龍率僅剩的二十騎逃往定州。逃亡途中,毛文龍又收攏殘兵,聚集了一些人馬。朝鮮定州守將只允許毛文龍一人入城,不準其所率士兵同往,使毛文龍憤而出城。毛文龍又欲駐兵平壤,這遭到了朝鮮君臣的反對,朝鮮國王更是對自己的大臣表達了“禍本又來平壤,此賊更搶無疑”的明確厭惡態度[13]卷173,光海君十四年正月戊戌。毛文龍最終決定回師鴨綠江畔,繼續抗金,并在天啟二年三月至六月開展了針對后金的一系列軍事活動,對后金軍隊造成了一定的騷擾作用。
朝鮮君臣素來認為毛文龍為人輕佻,“不量事勢”,又十分狂妄,若其久居朝鮮境內的陸地,定會“橫挑強胡,嫁禍于我國”[13]卷181,光海君十四年九月丁巳,給朝鮮帶來禍事。但朝鮮國王光海君又不愿放棄“兩面外交”政策,徹底得罪明朝。故而,他再次建議毛文龍避居海島。恰好,此時明朝監軍梁之垣率兵赴朝鮮商量戰守事宜。論及毛文龍部進退問題時,朝鮮方面強烈建議毛文龍部退入海島“相時順動”[13]卷176,光海君十四年四月庚辰。毛文龍本人也不愿繼續久寄朝鮮籬下,欲尋找一個能夠容身的根據地以便開展新一輪抗金斗爭,故聽從手下李景先的勸諫,同意前往海島駐軍,并選中“大可四百里,環山峭壁”的皮島作為理想去處[5]39。最終在征詢了梁之垣和朝鮮方面的意見后,毛文龍率殘軍于天啟二年十一月移駐皮島,并于天啟三年初正式設立帥府,號東江鎮。
皮島,又稱稷島、平島、椵島、椴島,屬朝鮮平安道義州府鐵山郡。皮島南有海路與山東半島登州、萊州相通,北可以進取遼東半島,東可以與朝鮮貿易通商,地勢易守難攻,具有重要戰略意義。《明史》記載:“皮島亦謂之東江,在登、萊大海中,綿亙八十里,不生草木,遠南岸,近北岸,北岸海面八十里即抵大清界,其東北海則朝鮮也。”[15]卷259,袁崇煥傳朝鮮方面文獻對皮島的記載為:“椵島,一名皮島,距府南陸路四十七里,周四十里。”[16]34因皮島孤懸海外和毛文龍屢立戰功,毛文龍駐守皮島后明廷給予了毛文龍較大的自主權。毛文龍建立東江鎮,開辟了明朝抵抗后金的敵后戰場。
毛文龍在整體局勢不利的情況下堅持抗金,屢次得到天啟皇帝的嘉獎。天啟二年六月,熹宗下詔“加副總兵毛文龍署都督僉事平遼總兵官”[6]卷23,天啟二年六月戊辰。同年十二月,又“頒給敕印旗牌,授以援遼總兵便宜行事”[6]卷29,天啟二年十二月辛巳。天啟三年二月,再“賜平遼總兵官毛文龍尚方劍加指揮僉事”[6]卷31,天啟三年二月丁丑。可見,在東江鎮建立初期,朝中君臣對毛文龍寄予了厚望。天啟、崇禎年間,朝廷不僅對毛文龍加官晉爵,而且在錢糧援軍等方面對東江鎮給予了一定的實質性支持[17]。然而,明廷向毛文龍提供的錢糧軍需實際上并沒有達到額定之量[6]卷32,天啟三年三月癸卯。
建立東江鎮后,毛文龍一直接納遼民,擴充人口,增強實力。經過了三四年的發展壯大,東江鎮已有士兵三萬余,遼民十數萬,成為一支不可忽視的軍事力量。毛文龍在軍隊中培植親信,試圖將東江鎮的軍隊變成“毛家軍”,客觀上增強了軍隊的凝聚力,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東江鎮在艱苦抗金條件下的分崩離析。
毛文龍用從朝鮮獲得的人參賄賂朝中權貴,以確保獲得更多補給軍需。天啟四年,毛文龍開始與魏忠賢勾結,躲過了“移鎮”風波,勢力得到進一步發展壯大。閹黨倒臺后,由于朝中后援的助力,毛文龍并未遭到清算。直至崇禎二年(1629)毛文龍被袁崇煥誅殺前,東江鎮的發展都呈向上趨勢。
數十萬兵民和明廷提供的大量軍需補給為毛文龍和東江鎮帶來了較強的實力和戰斗力。在與朝鮮的往來中,這為毛文龍爭取了主動的地位。
二、毛文龍與朝鮮間的相互支持
(一)朝鮮對東江鎮毛文龍的支持
天啟初年,朝鮮國王為光海君李琿。他奉行“兩面外交”的政策,一方面與后金通好,另一方面向大明稱臣納貢。他對毛文龍始終秉持著“不得罪,不支持”的態度。努爾哈赤要求朝鮮逮捕毛文龍,押送至后金。對此,光海君擔心明朝怪罪,表示拒絕,并向毛文龍部提供少量糧食和軍需物資,以安其心。出于對后金將來可能之報復行動的擔心,光海君又向后金致書請罪,稱允許明朝駐軍實屬迫不得已。光海君的“兩面外交”政策一定程度上給毛文龍部提供了必要的生存空間,但減緩了毛文龍部的擴張和發展速度。
天啟三年初,朝鮮國內的親明派開始表現出對光海君“兩面外交”政策的不滿,并提出了“親明反虜”的政策建議。同年三月十二日夜,朝鮮國內發生政變,由仁穆大妃出面將朝鮮國王李琿及其世子李祬廢為庶人。李倧繼承王位,是為仁祖,這次政變史稱“仁祖反正”,又稱“癸亥靖社”。李倧繼承王位后,重用主張“親明反虜”的西人黨。朝鮮李朝奉明朝為宗主國、參與以明朝為中心的東亞宗藩體系已二百余年,朝鮮王朝始終奉儒教為國教,遵奉儒家思想,從官紳到普通民眾均對明朝和儒家正統有著十分強烈的認同感。“西人黨‘親明’的姿態不僅是對于傳統封貢關系的繼承,也是朝鮮‘禮儀之邦’、大義名分的延續,更是新政權強調自身合法性的需要。”[18]“親明”可以使剛繼位而立足未穩的李倧獲得大量官員和民眾的支持,逐步掌控朝政。朝鮮政變及其外交政策的改變,使得毛文龍和東江鎮能夠獲得朝鮮的支持,而持續迅速發展。
朝鮮仁祖繼承王位后,立即派遣使者向明廷重申了“以小事大”的外交姿態,又派遣使者向毛文龍表達了聯合消滅后金的合作決心。
由于皮島地處邊陲,孤懸海外,又兼毛文龍招納了大量遼民,明廷輸送的糧草并不能按時按額抵達,使得東江鎮糧草大規模短缺。盡管有部分水兵轉化而來的海商協助糧餉供給[19],但依舊可謂“東江軍民饑寒交迫,軍備不足”[20]。為支持毛文龍,朝鮮仁祖多次應邀或主動為東江鎮無償提供糧草,又通過與東江鎮通商貿易使一些糧食有償流入皮島。與此同時,隨著雙方往來的頻繁,皮島逐漸成了“朝鮮與明朝交通與貿易的中心”[21]。天啟三年至崇禎二年,計有二十六萬八千七百余石糧食由朝鮮流入東江[22]卷21,仁祖七年十月甲戌。在糧食貿易中,東江鎮經常勒索、搶奪、侵害朝鮮,引得朝鮮邊臣不滿,甚至導致了小規模沖突。但這并未改變朝鮮國王對毛文龍的支持態度。
與此同時,由于朝鮮人口和勞動力有限,余糧無法滿足毛文龍的需求,毛文龍還在宣川、定州、龍川、鐵山等朝鮮的土地上進行屯田,以補貼軍需。朝鮮方面“令道臣、伴臣看審濱海五邑閑田,明立界限”[22]卷8,仁祖三年正月丙寅,默許毛文龍屯田。毛文龍屯田所用耕牛,也為與朝鮮貿易所得。
除糧食外,朝鮮也曾應毛文龍要求,提供火銃、戰馬及銅鐵等軍需物資。這些物資雖未達到毛文龍所要求的數額,但也是對毛文龍抗金活動的實質性支持。朝鮮還默許毛文龍派人前往朝鮮境內采參。毛兵所采之參,多半被毛文龍用于行賄朝中達官顯貴以求支持;少半被毛文龍及其手下高級將領享用或出售以換取銀兩。此外,對于毛文龍在朝鮮境內煮鹽之事,朝鮮也予以允許[22]卷1,仁祖元年三月丁未。
朝鮮不僅向毛文龍提供物資,而且對毛文龍進行精神上的支持。天啟四年七月,朝鮮為毛文龍樹立平遼總兵官左軍都督同知毛公功德碑[23]403。此碑雖為毛文龍暗示后所立,但它不僅能夠充分宣傳毛文龍的愛國精神,也能夠使明廷知曉毛文龍聯絡屬國抗金的功績。
朝鮮幫助毛文龍欺瞞明廷,使毛文龍得到明廷的信任,在孤懸海外的情況下獲取支持。很長一段時間內,明廷關于毛文龍的穩定信息來源僅為毛文龍單方面的塘報。朝鮮發向明廷的奏疏中,也出現了只談毛之功,不提毛之過的情況。朝鮮還曾幫助毛文龍夸大戰功。寧遠戰后,明廷一度懷疑毛文龍,下詔要求朝鮮表明毛文龍實情。朝鮮并未揭露毛文龍之過,“且陳毛將有功之狀暨日后難處之形”[22]卷12,仁祖四年四月丙戌。
明廷派遣使者前來朝鮮時,朝鮮也曾幫助毛文龍應對檢查,予以美言。“明朝與朝鮮的陸路交通已被切斷”[24],因此往來朝鮮的使者均需通過毛文龍所鎮守的東江鎮。天啟五年,朝鮮國王在與詔使王敏政、胡良輔的交談中對毛文龍的功績有所肯定,言“毛都督自鎮敝境以來,遼民歸順者,不知其數。加以號令嚴明、威風遠及,奴賊不敢近塞,故小邦恃而無恐”[22]卷9,仁祖三年六月庚辰。天啟六年,翰林院編修姜曰廣奉旨出使朝鮮,“封朝鮮國王”,另受旨意“便閱海上情形,按毛文龍功次虛實”。姜曰廣在赴朝途中親自前往東江鎮,核查毛文龍虛實,并對毛文龍“招輯流亡,節次斬獲,使虜不得用遼人,耕遼地”之功績予以勉勵[25]188。而朝鮮國王在與姜曰廣的交談中也提到了“毛將軍以單騎渡江,義聲所暨,莫不奮起,奴賊不敢近邊,小邦賴以無事秋毫”[22]卷13,仁祖四年六月丙戌。考察過后姜曰廣最終上奏了有利于毛文龍的東江“要領”,表態“若養成一隊精銳之兵,設伏其間,乘弊出奇,文龍自信其能,臣亦信文龍之能也”[26]54,毛文龍留住了明廷的信任,得以轉危為安。
朝鮮仁祖國王對后金采取積極防御的政策,告誡邊臣、邊將加強邊境地區的守備,并表示必要時會以武力驅逐進入朝鮮境內的后金軍隊。這一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毛文龍的安全,使毛文龍部得以避免再次遭受林畔戰敗那種被后金軍隊追殺入朝鮮境內的狼狽情形。
分析朝鮮對毛文龍支持的原因,首先要從東亞地區的宗藩體系入手,長期以來,朝鮮“視明朝為天朝上國,甘愿以臣屬國身份與明朝開展密切的往來”[27],尤其在“壬辰倭亂”中明廷對朝鮮的鼎力支持,更使得朝鮮感激萬分,毛文龍為明朝將領,朝鮮自然對其愛屋及烏,希望用支持毛文龍抵抗后金的方式以報“再造之恩”。所以無論是光海君時期的兩面外交還是“仁祖反正”后更加堅定地親明,朝鮮在毛文龍開鎮東江后始終對其有所支持,只是不同時期的力度大小存在差別。朝鮮對毛文龍的支持除了宗藩體系的歷史傳統外,也有出于現實因素的考量。后金對于朝鮮有較強的軍事威脅,毛文龍作為明朝將領,是域內唯一能對朝鮮施以援手的軍事力量;而通過政變上臺的仁祖國王,只有得到明廷冊封才能穩固國內局勢。毛文龍可以成為請封過程的助力,故而仁祖國王定會加以籠絡。請封成功后,仁祖國王對于毛文龍的感激之情也是其對毛文龍持續物質支持的重要原因。
(二)毛文龍對朝鮮的支持
“周邊諸國要求中國王朝的冊封,既有通過冊封來確立其統治者的國內權威需要,也不乏有利于各國間爭斗的利益動機。對于中國王朝來說也是如此,即:與周邊諸國冊封關系的設定,不僅有利于中國國內皇帝權威的確立,而且對居于冊封體制外圍的化外之國也顯示了中國王朝的權威。”[28]毛文龍對朝鮮的支持主要在于政治認同方面。按照傳統的封貢關系,朝鮮國內發生王權更替勢必要經過大明皇帝的允許,只有經過大明皇帝冊封的朝鮮國王,才能成為朝鮮的正統國王。
通過政變上臺的朝鮮仁祖國王李倧,繼位之初面臨著國內的統治危機,反正功臣李適就曾于天啟四年發動叛亂。明朝皇帝的認可對于李倧在國內統治的穩定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故而登上朝鮮王位后,李倧依舊例以“權知朝鮮國事”的名義向明朝皇帝上奏,請求冊封,“以李琿通奴為名,攘奪其位,今請命天朝,愿出力以報效”[6]卷41,天啟三年十一月丙子。在朝鮮使者到來前,明廷就已經得知朝鮮國內發生政變,朝中官員態度存在分歧,登萊巡撫袁可立、御史田維嘉等官員認為朝鮮政變,以侄廢叔,不合綱常,應予討伐;另一部分官員認為光海君私通后金,應以邊事為重,承認李倧。此時,與李倧有所接觸,受到其厚待的毛文龍適時地上奏,給予了李倧助力:
李倧以嫡派承大妃命,副臣民望,責琿之貢奴,殺遵之陰謀……沿邊操練聲援,以為犄角。于本月二十四日,會臣商榷計議出師。[29]12-13
由于毛文龍的上書,天啟皇帝最終并未完全相信孟養志等帶回的不利于李倧的信息,決定接受禮部尚書林堯俞的建議,由登萊巡撫袁可立與毛文龍共查此事。調查后,毛文龍又一次上書為李倧請封:
李琿當日之罪惡,與李倧今日之忠順,聞見的真,議論合一,誠有如本國臣民甘結無異者等情到臣……伏乞皇上亟賜冊號封典敕于該部,速遣使臣航海前來,不致風高浪阻,誤敕封大典,并誤疆場大事也。[29]33-34
經歷數月朝堂辯論后,天啟皇帝于天啟三年十二月正式決定冊封李倧為朝鮮國王。天啟四年十二月,天啟皇帝接受李倧的請求賜予其誥命和冕服。明廷使者也于天啟五年二月啟程,六月到達朝鮮王京,正式冊封李倧為朝鮮國王。
毛文龍在李倧的請封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毛文龍作為派駐朝鮮的抗金將領,明廷自然是要聽信于毛文龍對于朝鮮時局的判斷。”[30]他不僅多次上奏詳陳利害,說明李倧的得位之正,且多次據理力爭,強調朝鮮的支持能夠成為東江鎮和遼東戰場的助力。由于毛文龍的努力,認為李倧得位不正的登萊巡撫袁可立也改變了態度,支持冊封。毛文龍甚至曾將奏疏給予朝鮮使臣修改潤色[31]054a-055a。“雖然李倧請封得以成功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但毛文龍無疑扮演了關鍵角色。其三次上奏明熹宗,為明臣中主張冊立李倧之最力者。”[32]毛文龍為李倧的奔走很大程度上出于對其自身利益的考慮,但他的確幫助李倧穩定了政治地位和國內政局,也加強了朝鮮的抗金決心。
在戰略意義上,毛文龍東江鎮駐軍與朝鮮軍隊構成掎角之勢,一定程度上加強了朝鮮邊境的防御能力,但成效不顯。朝鮮與后金交戰的丁卯之役中,毛文龍本可以助力朝鮮,卻在鐵山、須彌島失守后,退兵入海,以觀戰局。毛文龍雖曾小規模出兵襲擾后金軍隊后方的義州,協助朝鮮民間義兵抵抗后金,但他的軍事行動并未起到改變戰局的決定性作用。在后金欲與朝鮮簽訂《平壤之盟》時,毛文龍也無力再在軍事上進行回擊。因此,毛文龍與朝鮮間的防御同盟關系有所松動,朝鮮對明朝的離心傾向加重。
萬歷四十七年,清軍襲取明代東亞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開原后,明朝與朝鮮交流的關鍵道路——“開原東陸路至朝鮮后門”即已經中斷[33]。隨著明與后金間戰爭的進一步發展,雙方的陸路往來徹底斷絕,被迫改走海路。東江鎮處在明與朝鮮商路之上,由明廷軍隊把守,又開放了“馬市”,發展了雙方的貿易往來。在明廷與東北邊疆部族、藩國的交流中,貿易的開展與斷絕,“馬市”的開放與關閉,素來對少數民族和藩屬國的影響更大,這也是明廷歷來將關閉“馬市”、停止貿易作為懲戒手段的重要原因。所以于朝鮮而言,毛文龍部所守護之東江商路,于國家發展上是有益的。因此客觀而言,對于商路的維護,亦是毛文龍對于朝鮮的支持。
毛文龍對朝鮮有所支持的原因:首先,為貫徹明廷長期以來對待朝鮮“撫藩字小”的立場。即便經歷了與后金戰爭中的一系列兵敗最終被迫客居皮島,但作為宗主國將領的毛文龍依然有為藩屬國提供軍事保護的義務,毛文龍也始終采取“以朝廷的名義籠絡朝鮮,以朝廷的力量扶持朝鮮”的戰略[34]。其次,由于明廷對于東江鎮的供給并非充足,因此毛文龍需要利用朝鮮提供物質支持以補足皮島軍需。最后是個人利益,此時的毛文龍經歷了多年的軍旅生涯,已經被明軍將領利用職權為自己謀取利益的風氣所感染,維系奢靡的生活、積累大量的財富,需要明廷中樞認可他對東江鎮的絕對控制。而朝鮮作為藩屬國,奏疏可以直抵中樞,也有義務配合明廷對于東江鎮軍事成果的核查。因此,毛文龍必須對朝鮮有所支持才能使朝鮮愿意在明廷為他美言,協助他通過明廷的核查,進而保證毛文龍自身地位的穩固。總體而言,本質上毛文龍與朝鮮相互支持的關系可謂“利”大于“義”,可以視為利用以明朝為中心的東亞宗藩體系進行利益交換,各取所需。
但毛文龍與朝鮮間的雙向多元關系并非只有相互幫助,隨著雙方的長時間接觸和毛文龍自認為在明廷地位的日益穩固,毛文龍在處理對朝事務時日益驕縱。加以明金間戰爭局勢的變化和雙方勢力的此消彼長,毛文龍與朝鮮間的猜忌也開始逐漸積累并接近徹底爆發。
三、毛文龍與朝鮮間的相互猜忌
(一)朝鮮對毛文龍的猜忌
光海君時期,朝鮮對毛文龍的猜忌主要在于擔心毛文龍駐軍會招致后金軍隊入境攻擊、劫掠,為朝鮮帶來兵禍。朝鮮邊臣的縱容使毛文龍遭遇林畔之敗。
由于毛文龍前往朝鮮是敗亡而來,并非直接受命,因此朝鮮自始就對毛文龍部的戰斗力有所懷疑。在林畔之敗后,毛文龍屢次襲擾后金,幾無戰果,朝鮮已經大致明確了毛文龍部的戰斗力。《朝鮮王朝實錄》等文獻中,對東江疲敝的記載層出不窮。自毛文龍處歸來的朝鮮使者柳公亮更是認為毛軍“兵器只于杖頭插鐵,不比我國之精利矣”[22]卷2,仁祖元年六月辛未。毛文龍部戰斗力不足,不僅導致其對后金的牽制力差,而且也給與之互為掎角之勢的朝鮮帶來了安全隱患。當后金軍隊討伐朝鮮之時,朝鮮方面有理由懷疑毛文龍將難以給予真正的援助。
仁祖請封時,毛文龍的全力幫助使朝鮮對毛文龍的猜忌一度有所減弱。隨著東江鎮的進一步發展,毛文龍對待朝鮮使臣的態度逐漸變得驕躁傲慢,再次致使雙方之間猜忌叢生。毛文龍手下士兵還曾對朝鮮“劫奪糧餉”“侵擾居民”[22]卷12,仁祖四年三月己巳“打傷人命”“攘奪財貨”,導致朝鮮“京外之人,不堪其苦”[22]卷18,仁祖六年二月辛亥,嚴重侵擾了朝鮮的社會秩序。礙于明與朝鮮關系,朝鮮并未追究。但是,毛文龍卻將朝鮮方面的深明大義視為對自己行為的默許,不僅沒有嚴格約束軍隊并收斂欺壓朝鮮的行為,反而日益放縱,以“天邦上將”自居,導致朝鮮君臣對毛文龍的不滿與日俱增。崇禎元年,還發生了毛文龍屬官毛永卿“肆其氣焰,亂打伺候下人,侵索食物”,甚至“突入闕門”,在朝鮮王庭“拔劍作亂”的事[22]卷19,仁祖六年七月壬午。事后,毛文龍不僅未向朝鮮方面表示歉意,更是縱容毛永卿,加劇了朝鮮對毛文龍的不滿。
天啟六年,姜曰廣出使朝鮮時,朝鮮方面雖然對于毛文龍給予了一定的肯定,但也表達出了擔憂之情。在會面中,朝鮮國王表達了對遼民問題的擔憂。他認為“遼民之寄生鮮也”,在朝鮮人民生活困苦的情況下,還需“以貿遷貨物,歲輸米若干石”[25]196以供應皮島,故而對毛文龍心生憤恨。而在辭別宴中,遠接使則如實相告“毛帥移文索餉,語涉張皇”[25]198,使得國王不悅。姜曰廣則只能以言辭寬慰,但并未打消朝鮮君臣對于毛文龍的顧慮。在返程途中,姜曰廣為避免朝鮮對毛文龍的不滿加深,故而對毛文龍進行了勸誡,言“將軍以孤軍獨立,所賴朝鮮聲援,而時以乏食之故,悉索于鮮,萬一鮮隙懷二心,并恐將軍無容足之地也”[25]201。但姜曰廣的勸說顯然效果不佳,未能約束毛文龍的行為。此外,“朝鮮君臣也逐漸意識到登撫在明、朝宗藩事宜中的重要性”[35],故而也曾就毛文龍問題向負責處理雙方外交關系的登萊巡撫求助。但求助登萊巡撫同樣未能有效解決問題,反而引起了明廷內部的撫鎮不和。
自林畔戰敗,毛文龍就與朝鮮邊臣不和,故朝鮮仁祖國王出于安全考慮,不得不始終嚴密監視毛文龍動向,以防其與后金共圖朝鮮。丁卯之役后,毛文龍退避海上,朝鮮開始擔心毛文龍叛明降金。根據《滿文老檔》“遺毛文龍書”[12]695-697、《明季北略》“李永芳又致手札”[5]42、《明熹宗實錄》“巡撫登萊右僉都御史李嵩塘報奴酋致毛文龍謾書”等記載[6]卷73,天啟六年閏六月乙亥,毛文龍與后金間始終存在書信來往,甚至天啟五年,努爾哈赤曾勸說毛文龍出兵攻取朝鮮的義州。崇禎帝即位后,毛文龍在朝中逐漸失勢,又開始通過書信往來和談等方式維系與后金的聯系,以圖保存實力、待價而沽,可謂“欲降之心,半真半假”[12]899-904,而曾與毛文龍交戰過的女真將領英俄爾岱(龍骨大)曾評價毛文龍“彼欲覘我,我欲覘彼,以相通也”[22]卷19,仁祖六年十二月壬辰。朝鮮方面擔心促使毛文龍下定決心叛明而降后金,故不敢將毛文龍日益驕縱之事及東江鎮詳情上報明廷,只得幫助毛文龍隱瞞其不法之事。
綜上所述,在對外關系中,朝鮮王朝首先考慮的是自身的生存和發展需求,其次才是所謂的宗藩關系和大義名分。因此,朝鮮王朝對毛文龍及東江鎮雖多有不滿和猜疑,卻礙于種種原因敢怒而不敢言。這使得毛文龍在對待朝鮮時更加驕縱和目中無人,寄人籬下卻又以上邦天將自居。
縱觀朝鮮對毛文龍猜忌的產生和愈演愈烈,首先,由于毛文龍及其軍隊驕縱,客居朝鮮卻反客為主,仰仗宗主國將領的身份欺壓屬國,索取無度。毛文龍貪欲過度,在其所取不能被滿足時上疏反誣朝鮮,被朝鮮得知后,激化了對毛文龍的猜忌。其次,毛文龍在與后金軍隊的多次交戰中明顯戰斗力不足,尤其在丁卯之役中未能幫助朝鮮,迫使朝鮮與后金結為“兄弟之國”,半臣屬于后金。這樣,朝鮮已經認識到了明朝軍隊戰斗力的退化,不再有如萬歷援朝那般保護朝鮮國家安全的能力。再次,崇禎初年朝鮮已經得知毛文龍與后金間有書信往來。由于擔心毛文龍會隨時倒向后金,使局勢對朝鮮不利,朝鮮對毛文龍的猜忌進一步加深。
(二)毛文龍對朝鮮的猜忌
林畔之戰時,朝鮮邊臣對后金的縱容與私通,致使毛文龍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遭遇突然襲擊,最終慘敗。這使得毛文龍對朝鮮作為大明屬國的忠誠性有所懷疑,擔心被朝鮮出賣,于是選擇接受建議移居皮島。結合林畔之敗的教訓,出于自身安全考慮,毛文龍始終對朝鮮進行監視。“仁祖反正”之初,毛文龍曾“故意以‘誣言’奏報于登萊巡撫袁可立”[36],使得對“仁祖反正”一事的不實記載出現于明季野史之中。雖然“仁祖反正”后,朝鮮仁祖國王實行“親明反虜”的政策,但是此時毛文龍卻仍未完全信任朝鮮,沒能抓住時機與朝鮮進行深入的抗金合作,反而要求朝鮮為自己歌功頌德,以增強自身的影響力,從而獲取明廷的信任。
在東江移鎮危機中,毛文龍欲借朝鮮之力,讓朝鮮“上本天朝,挽止其行”,請求拒絕移鎮。但朝鮮仁祖國王考慮到“藩臣事體,偃然陳奏,指揮天朝,進退大將,甚非容易”,婉拒了毛文龍的請求[22]卷13,仁祖四年閏六月戊申。這加劇了雙方的罅隙。在后金與朝鮮簽訂《平壤之盟》后,毛文龍部已經很難再登陸朝鮮進行屯田,上岸后便會遭到后金軍隊的絞殺,唯有部將曲承恩的采參部隊還可以分散活動。因此,毛文龍擔心朝鮮與后金之間會針對東江鎮進行聯合軍事行動,故毛文龍屢次截殺朝鮮與后金間的使臣。朝鮮國王向毛文龍通報朝鮮與后金結為兄弟之國只是迫不得已,懇求毛文龍不要從中作梗后,毛文龍并不體諒朝鮮難處,依然截殺使臣,可見其對朝鮮猜疑之深。
另外,由于擔心朝鮮向明廷匯報其將帥驕縱、交戰冒功、欺壓朝鮮等行為,毛文龍也曾派人搶劫過朝鮮派出的朝天使,在確認其所攜帶的文書無對毛文龍不利的內容后,方才允許其通過[37]344-345。有學者指出毛文龍能夠在東江立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朝鮮與中國使臣往來皆需經過東江,故消息傳遞皆為東江把持”[38]。
后金也曾嘗試離間毛文龍與朝鮮的關系,使毛文龍對朝鮮的猜忌增加,如在天啟五年,努爾哈赤派遣劉維國、金盛晉出使東江鎮,聲稱毛文龍已經得罪了明朝皇帝,明帝已經“遺書朝鮮國王,命其將爾捉拿之”。而據傳朝鮮國王已經接受了明帝的要求,回書“該毛文龍寸步不前,隱身而居,以逃來之人充數欺瞞爾帝,自稱有兵冒領錢糧,實乃禍我朝鮮國之鼠盜也。我將用計將其擒拿解去,或者唆使毛文龍之部下將其擒拿”。努爾哈赤甚至勸說毛文龍出兵攻打朝鮮,言“爾取朝鮮之義州城,與我相倚而居,則朝鮮豈敢犯爾。爾駐義州之后,朝鮮若降則罷,若不降,則來借用我兵。爾若如此與我相倚,迫使朝鮮投降”[12]624-625。盡管此時明與后金間的戰爭局勢尚未明朗,毛文龍尚有渴望沙場建功立業的家國情懷和理想抱負,且備受明廷重用,與主持朝政的“閹黨”來往甚密,不可能完全相信后金使者的觀點而與后金聯合出兵朝鮮,但未免不會在毛文龍心里留下芥蒂,增加毛文龍對朝鮮,甚至對明廷的猜疑。
毛文龍并不體恤朝鮮,依然懷著與明朝強盛時無異的“天朝上國”心態,把朝鮮在明和后金中選擇明朝視為理所應當。毛文龍曾上疏彈劾朝鮮“攜二”[39]332,使得朝鮮不得不派遣使者前往北京辯誣。明廷君臣對朝鮮在明與后金間戰爭的作用認識深刻,“明朝需要朝鮮站在自己一邊,以期共同對抗后金”[40],故而選擇了信任朝鮮,平息事端。但毛文龍對朝鮮忠心的猜疑也為朝鮮得知,言“時椵島帥毛文龍構誣我國,至以‘交通北虜,合勢襲島’等語播告軍門,事將不測”[41]131。最終,毛文龍對朝鮮的猜疑行為使得朝鮮君臣不滿,雙方間離心離德,相互合作的信任度進一步減弱。
由上可見,東江鎮孤懸海外需要依靠朝鮮進行大量補給,毛文龍十分在意朝鮮的一舉一動,擔心朝鮮反叛明朝與后金聯合而使自己失去安身立命之所,使東江鎮失去存在必要和生存空間,所以毛文龍自始至終就對朝鮮有所猜忌,對未來的規劃以自身生存和壯大勢力為首要目標,而并未能與朝鮮齊心協力地進行全方位抗金合作。
毛文龍猜忌朝鮮原因,首先為朝鮮邊臣對后金的縱容,他們自保為先的策略,使毛文龍認為朝鮮并非完全可靠的軍事盟友,猜疑的種子在林畔之敗時就在毛文龍心里埋下。其次是朝鮮未能按毛文龍的要求提供足量軍需補給和安置遼民之協助。但毛文龍并未考慮朝鮮的實際國情與區域的緊張局勢,反而持續貪得無厭地索取。得不到期望的結果就對朝鮮加深猜忌,甚至逐步開始懷疑起朝鮮對明王朝的忠心。而后是“丁卯之役”后,即便朝鮮被迫與后金簽訂“城下之盟”,毛文龍不顧朝鮮君臣感受繼續索取,在供應有所縮減后進一步與朝鮮離心離德,擔心朝鮮完全倒向后金。總之,朝鮮與毛文龍間相互猜忌之產生,主要責任在于毛文龍,他的一些驕縱行為,于國于己皆有不利,使毛朝雙方矛盾逐漸激化。雙方矛盾的激化,“無疑會為后金的進攻減輕阻礙”[42],成為親者痛、仇者快之悲劇。
四、結 語
對毛文龍與朝鮮關系的研究可謂是對明清鼎革前夜東亞宗藩體系內部成員關系研究的突破口。作為明朝將領,毛文龍曾長期駐軍條件艱苦的朝鮮皮島進行“敵后”抗金,至死也未投降后金,精神可嘉。但毛文龍也曾仗勢欺壓明朝的屬國朝鮮,以增強自身實力。朝鮮光海君奉行兩面外交,奉明朝為宗主國的同時修好后金,對毛文龍給予了一定程度上的支持。而仁祖國王則奉行親明政策,曾對明朝抗金予以大規模支持,也對毛文龍的行為有所不滿。另一方面,毛文龍還十分擅長權術,利用后金的存在阻止朝鮮將他跋扈的行為上奏明廷,進而繼續維持鞏固其在東江鎮的統轄。丁卯之役后,朝鮮迫于后金的軍事威脅,對于毛文龍及東江鎮的支持有所減弱。
明清鼎革前夜,宗藩體系的內部成員之間必然經歷一番博弈,才能重新定位自身在華夷秩序中的位置。朝鮮是明朝最親近的藩屬國,更是這場博弈中的關鍵所在。毛文龍與朝鮮之合作,可以消除毛文龍招募遼民、策動后金漢官反正、進行軍事襲擾的后顧之憂,使得明廷在三方布置策中的“敵后戰場”擁有更強的牽制后金的能力,為明軍在遼西走廊正面戰場的布置贏得時間和空間。而朝鮮與毛文龍合作,盡了宗藩體系中藩屬國應盡之義,更可以使得朝鮮免于臣服在朝鮮君臣眼中同為“夷”的后金政權。雖然毛文龍與明廷的關系緊密程度時有變化,但在朝鮮的視角下,毛文龍卻始終是明廷的代表。于整個東亞地區而言,毛文龍與朝鮮間的合作關系能否緊密而長期地維系下去,會對蒙古諸部等在明與后金兩政權間猶豫徘徊的部族提供參照,并影響它們的最終選擇。唯有毛文龍與朝鮮間較少猜忌而相互支持抵抗后金,明與后金在遼東地區的戰局方能趨于均勢。但毛朝雙方間的猜忌日益加劇,終究成為了毛文龍身死的原因之一。而朝鮮和皮島為后金逐個擊破,明與后金間戰爭走向也開始朝著有利于后金的方向逐步發展,直至最終明朝滅亡,后金改國號為清并統一中原,完成東亞宗藩體系的重建。
參考文獻:
[1] 李光濤.毛文龍釀亂東江本末[J].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48(19):367-488.
[2] 孟昭信.“東江移鎮”及相關問題辨析——再談毛文龍的評價問題[J].東北史地,2007(5):20-28.
[3] 李善洪.試論毛文龍與朝鮮的關系[J].史學集刊,1996(2):34-40.
[4] 文鐘哲.毛文龍的抗金斗爭對朝鮮政治社會的影響[J].遼東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2):21-27.
[5] 計六奇.明季北略(上)[M].任道斌,魏得良,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4.
[6] 明熹宗實錄[M].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1962.
[7] (雍正)襄陵縣志[M].國家圖書館中華古籍資源庫藏刻本.
[8] 毛奇齡.毛總戎墓志銘[G]//吳騫.東江遺事.賈乃謙,點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9] 熊廷弼.援將勞苦異常疏[M]//熊廷弼集.李紅權,點校.北京:學苑出版社,2011.
[10] 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補遺[M].北京:中華書局,1977.
[11] 王在晉.三朝遼事實錄[G]//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43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2] 滿文老檔[M].北京:中華書局,1990.
[13] 朝鮮光海君日記[M].首爾: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影印本,1958.
[14] 李肯翊.燃藜室記述[G]//潘喆,等.清入關前史料選輯:第1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4.
[15] 張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4.
[16] 金正浩.大東地志[M].首爾:韓國首爾大學奎章閣線裝古籍.
[17] 王榮湟.明末遼東軍將毛文龍功過研究[D],天津:南開大學,2013:75.
[18] 宗玲.朝鮮“仁祖反正”與明廷“封典”問題研究[D],吉林:北華大學,2019:20.
[19] 王日根,陶仁義.從“鹽徒慣海”到“營謀運糧”:明末淮安水兵與東江集團關系探析[J].學術研究,2018(4):106-113+178.
[20] 王榮湟,何孝榮.明末東江海運研究[J].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6):145-152.
[21] 吳一煥.17世紀初明朝與朝鮮海路交通的啟用[J].歷史教學,1996(12):8-11.
[22] 朝鮮仁祖實錄[M].首爾: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影印本,1958.
[23] 談遷.棗林雜俎[M].北京:中華書局,2006.
[24] 趙世瑜,杜洪濤.重觀東江:明清易代時期的北方軍人與海上貿易[J].中國史研究,2016(3):175-194.
[25] 姜曰廣.輶軒紀事[G]//江西省高校古籍整理領導小組整理.豫章叢書:史部二.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26] 王夫之.永歷實錄[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
[27] 王臻.角色認同的轉變與重建:朝鮮王朝與明清封貢關系的變遷[J].世界歷史,2018(2):60-71+157.
[28] 韓東育.關于前近代東亞體系中的倫理問題[J].歷史研究,2010(6):128-147+192.
[29] 毛承斗.東江疏揭塘報節抄[G].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30] 王臻.清朝興起時期中朝政治秩序變遷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118.
[31] 承政院日記[M].首爾:探求堂出版社,1971.
[32] 王桂東.朝鮮仁祖國王請封述論——兼談毛文龍之助力[J].韓國研究論叢,2015(2):69-88.
[33] 李健材.明代東北[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107.
[34] 李偉強.崇禎二年毛文龍奏本探析[J].黑龍江工業學院學報(綜合版),2017(8):27-31.
[35] 趙亞軍,倪端然.東道之主:明末明、朝關系中的登萊巡撫[J].歷史教學(下半月刊),2023(3):64-72.
[36] 趙亞軍.清代朝鮮“仁祖辨誣”與明臣袁可立形象的書寫[J].煙臺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2):88-100.
[37] 趙慶男.亂中雜錄[G]//潘喆,等.清入關前史料選輯:第3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4.
[38] 徐志豪.毛文龍生平研究[D].新竹:臺灣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2001:101.
[39] 金尚憲.朝天錄[G]//燕行錄全集.首爾:東國大學出版部,2001.
[40] 王臻.天啟年間朝鮮廷臣金尚憲入明“陳情辯誣”考述——以金尚憲的《朝天錄》為中心[J].暨南史學,2018(2):73-83.
[41] 申悅道.懶齋集[G]//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續:第24冊.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6.
[42] 伊寧.毛文龍與《輶軒紀事》[J].黑龍江史志,2015(7):204-205.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ing General Mao Wenlong and
Korea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Revolution
Abstract:At the time of the Ming-Qing transition,the war between Ming and Houjin was inevitable,and the result of the struggle directly decided who would be the leader of the tributary system in East Asia in the future. Behind the seemingly clear confrontation between enemies and allies and the apparent alternation of the old and the new,there were also hidden members of the tributary system who were observing and protecting themselves,colluding with multiple parties,and even waiting for a price to sell. As a Ming general,Mao Wenlong represented the Ming Dynasty in Korea to fulfill his obligation to protect the national security of Korea,but he was involved in the vortex of the three-way game between Ming,Houjin and Korea.As a closest member of the Ming Dynasty tributary system,Korea,on the one hand,protected and suspected Mao Wenlong,and on the other hand,maintained a semi-subordinate status with Houjin. Undoubtedly,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ing general Mao Wenlong and Korea provides us with an ideal perspective to observe the actual state of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of the East Asian tributary system on the eve of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Key words:Ming-Qing transition;tributary system;two-sided diploma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