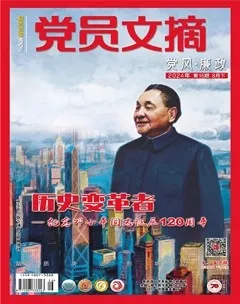“當時譽”與“千秋名”
2024-09-11 00:00:00陳魯民
黨員文摘 2024年16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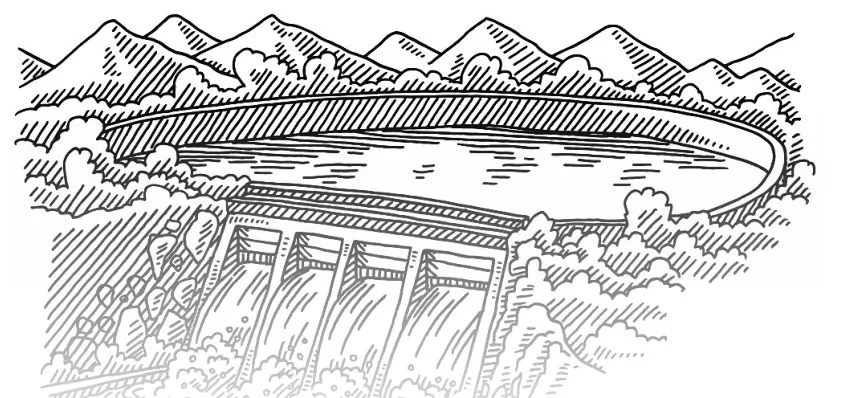
東晉名臣謝安鎮守廣陵期間,一面厲兵秣馬,為北伐作準備;一面助力農耕,造福百姓。為解決因旱澇頻繁導致莊稼歉收問題,他多方籌措資金,組織人手筑起攔水大堤灌溉農田,“隨時蓄泄,歲用豐稔”。此后,廣陵百姓年年豐收,經濟繁榮,成為富裕之鄉。《晉書》評價他,“在官無當時譽,去后為人所思”。
榮譽主要有兩種,“當時譽”和“千秋名”。有時二者是一致的,如謝安指揮淝水大戰,八公山上草木皆兵,前秦軍一潰千里,不僅在當時譽滿天下,且美名傳之千秋;有時則二者只能選其一,“當時譽”或許當時很響,“千秋名”卻寂寂無聲,那些只顧一時的形象工程,急功近利的短期行為,大都是看重“當時譽”。
“當時譽”是顯功,看得見、摸得著,周期短、見效快;“千秋名”是潛功,為后人作鋪墊、打基礎,周期長、見效慢。是求“當時譽”還是“千秋名”,考驗為官者的眼光和胸襟。如戰國時蜀郡守李冰父子帶領民眾修都江堰,殫精竭慮,孜孜矻矻,造福川中平原數千年之久,至今仍在發揮作用,成為世界文化遺產。
留下“千秋名”者,拿出的是經得起歷史檢驗的東西。我們看到蘭考泡桐樹,會想起焦裕祿;看到大亮山林場,會想起楊善洲;看到東山沿海“綠色長城”,會想起谷文昌……他們都未看重“當時譽”,卻無意中贏得了“千秋名”。雖斯人長逝,但精神不朽、事業長存、美名遠播,令人仰止。
“當時譽”與“千秋名”如可以兼顧,并行不悖,自然最好;如二者不可得兼,還是要把責任和擔當擺在第一位,多一些踏實沉穩,少一些急功近利。
(摘自《北京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