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國(guó)援馬耳他醫(yī)療隊(duì)的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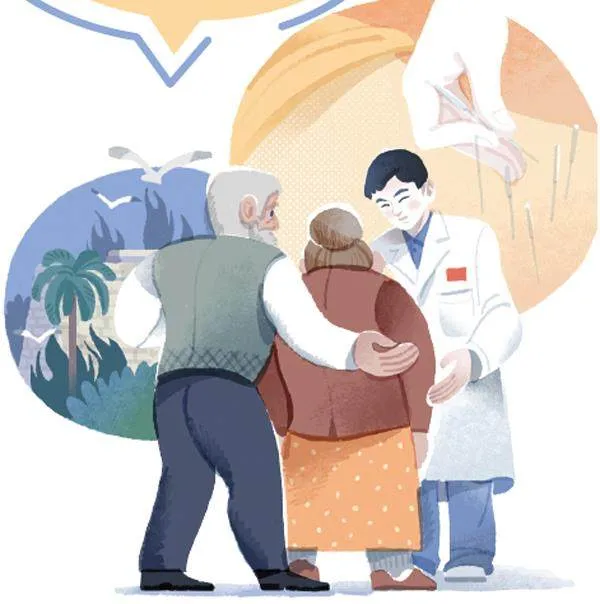
異國(guó)他鄉(xiāng)
馬耳他是我國(guó)提供中醫(yī)醫(yī)療援助的國(guó)家中唯一的歐洲國(guó)家。2023年,我跟隨中國(guó)(江蘇)第十九期援馬耳他醫(yī)療隊(duì)前往此地,轉(zhuǎn)眼間已經(jīng)在這里工作了一年。
初抵此地,我的心中不免忐忑不安,語(yǔ)言障礙、文化差異就像是橫亙?cè)谖颐媲暗囊坏赖狸P(guān)卡。尤其是最初的那幾日,面對(duì)病人,我心中總會(huì)涌出一股莫名的焦慮。我怕他們不了解中醫(yī);怕自己的英語(yǔ)不夠流利,無(wú)法同他們交流;怕他們對(duì)針灸療法有所畏懼;怕治療效果不盡如人意而引發(fā)誤解……然而,隨著時(shí)間一天天過(guò)去,我發(fā)現(xiàn)這些擔(dān)憂都毫無(wú)必要,只要我足夠真誠(chéng),足夠?qū)I(yè),便能消除所有的隔閡。
有一次,門診來(lái)了一位腰椎疾病患者,在詳細(xì)詢問(wèn)了相關(guān)病史后,我提前告知他針灸治療過(guò)程中可能會(huì)出現(xiàn)的狀況及注意事項(xiàng)。他對(duì)疼痛極其恐懼,針灸時(shí),他高度緊張,肌肉緊繃。我每扎一根針,他都會(huì)抖動(dòng)一下。我扎最后一根針時(shí),他終于忍不住了,大叫了一聲。我連忙向他解釋:“針灸時(shí)務(wù)必要放松,如果因肌肉收縮導(dǎo)致滯針,會(huì)讓疼痛加劇。”沒想到他笑著安慰我說(shuō):“親愛的保羅醫(yī)生(我在馬耳他的英文名叫Paul),不要擔(dān)心。沒有疼痛,就沒有收獲。”對(duì)初來(lái)乍到的我來(lái)說(shuō),他的回應(yīng)給了我莫大的鼓舞。
另有一位肩周炎患者,在經(jīng)過(guò)針灸治療后病情明顯好轉(zhuǎn)。當(dāng)他問(wèn)及是否需要再次就診時(shí),我隨口答:“你自己感覺,若有需要就再來(lái)。”沒想到他卻很認(rèn)真地看著我說(shuō):“你是我的醫(yī)生,我相信你,你說(shuō)什么時(shí)候來(lái),我就什么時(shí)候來(lái)。”
這些簡(jiǎn)單卻溫暖的瞬間,讓我逐漸適應(yīng)了馬耳他的生活節(jié)奏。
溫情守望
早晨,太陽(yáng)從東方慢慢探出頭來(lái),給大地披上了一層金色的紗衣,一切顯得寧?kù)o而又充滿生機(jī)。我步入診室,做好準(zhǔn)備迎接新的一天。
叩門聲響起,一位老人攙扶著他的老伴兒緩緩走了進(jìn)來(lái)。他們的臉上帶著溫和的笑意,歲月的痕跡都被這份恬淡沖刷得一干二凈。“是國(guó)立圣母醫(yī)院的一位中國(guó)醫(yī)生介紹我們來(lái)的,他說(shuō)中國(guó)的針灸療法也許能幫到她。”老爺爺?shù)穆曇羧岷投统痢Kf給我一張字條,上面寫著:“記憶缺失、癡呆,請(qǐng)多關(guān)照。”
我簡(jiǎn)單了解了老奶奶的情況,安排她在治療床上躺下。老爺爺?shù)哪抗馐冀K沒有離開過(guò)她。“我該留在這里,還是去外面等呢?”老爺爺沉默了一會(huì)兒,猶豫著問(wèn)道。“在外面等候吧,我這里一會(huì)兒還有別的病人。”我說(shuō)。老人似乎有些不舍,但還是轉(zhuǎn)身離開了,表情中帶著一種難以言說(shuō)的憂慮。老奶奶察覺到了老伴兒的離開,顯得有些不安。
“我可以留在這里嗎?”老爺爺又回來(lái)了,懇切地望著我,用手指向床邊的一個(gè)角落,“我保證不發(fā)出聲音。”我心中一動(dòng),默許了他的請(qǐng)求。
治療開始了,當(dāng)老伴兒因被針刺而落淚時(shí),老爺爺輕撫著她的發(fā)絲,細(xì)語(yǔ)安慰。“她已經(jīng)患病多年,連親朋好友都不認(rèn)得了,這兩年病情更是越來(lái)越嚴(yán)重,只有我還能夠照顧她。”老爺爺輕聲解釋道。
我不知道說(shuō)些什么才好,難以想象這位老人付出了多少。
記憶深處
第一次來(lái)這里時(shí),中醫(yī)中心旁邊的一座廢棄建筑以其獨(dú)特的姿態(tài),驀然闖入我的視野。那棟建筑墻體巍峨,間或有窄窗點(diǎn)綴在墻面上,顯得荒蕪而斑駁。只有它前面的金色巨石在陽(yáng)光下熠熠生輝。匆匆一瞥,我對(duì)它印象深刻。
但做醫(yī)療援助的日子緊張而充實(shí),我在重重疊疊的工作任務(wù)中度日,幾乎沒有時(shí)間品味周遭的風(fēng)景。突如其來(lái)的神經(jīng)性耳鳴如一位不請(qǐng)自來(lái)的訪客,打破了我平靜的生活。我受其所困,變得更加遁形遠(yuǎn)世,成日蹲守于一方斗室,兀自忙碌,憂心忡忡。
翻譯蔣老師敏銳地察覺到我的困頓,溫柔地說(shuō):“你不能總這樣把自己封閉起來(lái),出去走走吧。”于是,我隨她漫步在駐地旁一條隱蔽的小徑上。首次踏足,我吃驚于在都市的縫隙中,竟隱匿著這樣一處幽靜的景致。蔣老師指著那座我初來(lái)時(shí)便已留意到的廢棄建筑,言語(yǔ)間流露出對(duì)它獨(dú)特美感的欣賞。那一刻,我對(duì)它產(chǎn)生了別樣的感覺。
此后,那座廢棄的樓宇便成了我每日必到訪的心靈棲居所。它背后的草坪仿佛是大自然精心鋪就的綠毯,每次靠近,我都能感受到一種清新的慰藉。我常倚靠在銹跡斑斑的鐵絲網(wǎng)上,與草地低語(yǔ),仿佛它們能聽懂我心底的秘密。微風(fēng)過(guò)處,草尖輕擺,似是對(duì)我的回應(yīng)。
在那段日子里,我學(xué)會(huì)了從瑣碎的小事中找尋生活的意義,也學(xué)會(huì)了如何抵御生活中無(wú)常的遭遇。
日復(fù)一日,我的耳朵逐漸恢復(fù)了。
我在馬耳他的日子也像水一樣地流走了。
(本刊原創(chuàng)稿件,老老老魚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