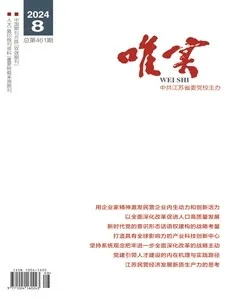基于生命周期的低收入人口認定和幫扶研究



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宣告:“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區域性整體貧困得到解決,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艱巨任務。”[1]在此基礎上,為健全分層分類的社會救助體系,加大低收入人口救助幫扶力度,進一步織密扎牢民生兜底保障安全網,2023年10月19日國務院辦公廳轉發民政部等單位《關于加強低收入人口動態監測做好分層分類社會救助工作的意見》(國辦發〔2023〕39號)(以下簡稱《意見》)。《意見》對已納入和未納入社會救助范圍的低收入人口提出監測要求;對發現低收入人口未納入社會救助范圍或發現困難情形復雜的,提出了解決辦法。
低收入人口及家庭的情況具有動態性,這是因為從人的生命周期來看,動態性是個人和家庭的基本性質。本文從生命周期視角,分析人的不同階段的脆弱性特點,從而幫助分析低收入人口動態性,以便相關部門進行監測,做好分層分類社會救助工作。
人的生命周期中的脆弱性人的生命歷程圖
在社會科學家探討“生命周期”之前,哲學家和詩人早就有此看法。西塞羅(Cicero)就生動地描繪過生命的變化模式、老年人的愉悅,以及他自己在已經成年的孫子死亡時所流露的極度悲傷。莎士比亞對老年的態度則沒有那么積極,他認為人生分七個時期,從“呱呱啼哭”的嬰兒到“沒牙、沒視力、沒味覺、什么都沒有”的老人。[2]52
人的社會生命歷程比較容易理解(見圖1),從新出生的嬰兒開始,經歷青年階段、中年階段,然后邁入老年階段。但事實上,從生理方面看,人的體質、體能、心智、精神等都不是一條直線成長和發展的,考慮到社會和經濟等方面,人的學歷高低、經濟收入、社會地位狀況更不可能是直線發展的,所以,為加深對人生道路及生理、經濟和社會發展狀況的理解,還需轉換視角。
社會學界已有“橄欖型”“啞鈴型”社會結構學說[3]44,童星教授指出,從立體來看,如果社會結構呈“橄欖型”,中間階級數量龐大,成為社會的緩沖區,那么這樣的社會比較穩定;但如果呈“啞鈴型”,那么社會結構也比較容易斷裂。我們嘗試建構“水母型”社會結構(因形似水母而得名,如圖2),靜態地可以看出一個社會低齡、青年、中年、老齡群體的分布,以及低齡、老齡的弱勢狀態;動態地可以看出每一個人從低齡到青年、中年所表現出的由弱變強的特點,以及從中年到老齡所表現出的由強變弱的特點。基于“水母型”社會結構來了解生命歷程,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的成長和變化,特別是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弱勢群體的生理、學習、就業、收入、生活等狀態。
“水母型”社會結構說明
三大群體概念。平常人群體(圖中實線,此處不用“正常人群體”,是為避免與其對應的是“不正常人群體”),就是依靠自身能力,通過勞動和就業獲得收入能夠滿足自己及家庭成員需求的人群,包括占比很大的普通人和占比較小的強勢群體。平常人群體中的低齡因“幼小”、老齡因“體衰”也有“弱”的方面(低齡和老齡時在A軸以下),對其扶助的責任以家庭為主、國家和社會分擔。動態弱勢群體(圖中段狀線),是指因健康、性別、教育、技能、就業機會、地區差異等原因,有勞動能力但就業情況不好、收入不穩的人群,他們在基本生活、醫療、住房、教育培訓等方面可能需要國家和社會扶助。常態弱勢群體(圖中點狀線),包括“鰥、寡、孤、獨、殘”等弱者,即孤兒、殘疾人、孤寡老人等,他們無勞動能力、無收入來源、無法定贍(撫)養人,是在基本生活、教育、醫療、住房、養老等多方面都需要國家和社會扶助的人群。
三條軸線含義。A軸:生命周期中的平均能力線,線的上部表示能力強、下部表示能力弱。平常人群體中低齡者、老齡者能力是弱的。青年和中年人能力是強的。動態弱勢群體隨著年齡變化,低齡者、老齡者能力是弱的;青年和中年人因教育、地區差異、技術升級等原因,其能力在強弱之間變化,表現出動態特點。常態弱勢群體中的人,能力都是弱的。A′軸:低收入(標準)線,按照目前比較多的國家通行方法,即把一個國家或地區社會中位收入或平均收入的50%作為這個國家或地區的相對貧困線,也就是低收入(標準)線。B軸:與能力相應的收入線,該線表示人們以其能力勞動和就業所獲得的收入。向上部分表示能力強,收入高;向下部分表示能力弱,收入低。
哪些人可能成為弱勢群體或低收入人口
幼弱——人的生命早期,因生理弱帶來多方面弱的狀態。每個人的成長都要經過嬰兒、幼兒階段,等他們長大了,就成為成年人、勞動者,做著體力或腦力勞動,并且成為有勞動工資等收入的人,也就不弱了。據學術界的研究觀點,人類在漫長的進化過程中,因直立行走,母體懷孕的身體特點、生理機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新生嬰兒不能成長(熟)得像一些動物的幼崽出生時那樣可以行走,吃固態食物,人類的嬰兒出生后必須依靠母乳喂養一階段之后才能逐步攝入固態食物,并學會站立、行走,學會語言、動作等。此后,在身體成長的過程中,還要經過學前教育、小學和中學教育,以及大學教育或職業教育,幫助兒童在身體、知識和技能等方面成長為青少年,進而成長為成年人、勞動者,從而步入人生由“弱”變“強”的時段。
老弱——人的生命晚期,因生理弱帶來多方面弱的狀態。由青年時的活力四射變為中年的身心沉穩,隨著時光的進一步推移,人們自然會進入老年的身心狀態。按照國際標準,一般將60歲或65歲定義為老年人的界限。進入老齡階段的人會在很多方面表現出“弱”的特點,首先是體質弱,人的體質在達到高峰之后,體質和體力自然會衰退。其次是精力弱,表現在聽力、視力、嗅覺等多方面。再次是記憶弱,隨著年齡的增長,記憶力下降是必然的,包括智力都會下降。最后是反應慢,隨著年齡的增長,體力精力的衰弱,必然會帶來老人的反應和動作慢等問題。也就是說,隨著年齡的增長,老人的工作能力、生活能力甚至自理能力都會下降或喪失。
青/中年人中的常態弱和動態弱——多方面弱的狀態。常態弱勢群體中的青/中年人在其生命周期中,主要是因為生理、身體原因,在學習、就業、收入方面受到影響,從而在生活的諸多方面受到影響。平常人中的動態弱勢群體可能有勞動能力,但受知識技能、經濟社會和地理因素等影響,就業情況不好,收入不穩,生活的諸多方面也受到影響。
由此可見,具有幼弱、老弱以及常態弱、動態弱等特征的人(群)都可能成為弱勢群體或低收入人口。常態弱勢群體或動態弱勢群體中的一些人(家庭)難以或根本不能通過勞動、工作、經營維持正常的生活(也就是收入、生活水平處于圖2中的A軸以下),有些人(或家庭)可能出現極端情況,因此《意見》規定:防范沖擊社會道德底線事件發生。
低收入人口形成的經濟社會因素分析
身處經濟社會轉型過程中的個人(家庭),要想達到普通的經濟收入、生活水平,既容易也不容易,因為蓬勃發展的經濟帶給每個人既有機會也有風險。作為經濟社會主體的個人(家庭)對經濟活動或主動或被動地參與,所帶來的結果都可能表現出很大的差別。
在為《大轉型》一書所寫的《前言》中,斯蒂格列茨指出,波蘭尼的分析清楚地表明,廣泛流行的滲透經濟(trickle-down economics)的教義——即包括窮人在內的所有人都會從增長中受益——得不到歷史事實的支持。[4]1自現代以來,有非常多的證據支持以下歷史經驗:增長可能會導致貧困的增加。我們同樣知道,增長可以為社會的絕大部分帶來巨大的好處,正如在一些更開化的(enlighted)發達工業國家中所發生的那樣。但總是沒有記分卡用來記錄被推向貧困的個體的數量,或者相對于創造出來的就業機會而言那些被摧毀掉的就業機會的數量。[4]8即使是亞當·斯密也以他小心謹慎的方式宣布,勞動工資并不是在最富裕的國家里才最高。因此,當穆法蘭表明他的以下信念時,他并不是在表達一種不同尋常的觀點。他說,由于英格蘭尚未達到它偉大的頂點,所以“窮人的數量還將持續增長”[4]89。
阿馬蒂亞·森則從可行能力視角分析了失業和貧困。失業還會對失業者的個人自由、主動性和技能產生范圍廣泛的副作用。這些多方面的副作用包括:失業助長對某些群體的“社會排斥”,導致人們喪失自立心和自信心,損害人們的心理和生理健康。[5]15
在分析社會正義時,有很強的理由用一個人所具有的可行能力,即一個人所擁有的、享受自己有理由珍視的那種生活的實質自由,來判斷其個人的處境。根據這一視角,貧困必須被視為基本可行能力的被剝奪,而不僅僅是收入低下,而這卻是現在識別貧窮的通行標準。對貧困問題采用可行能力方法的理由如下:一是貧困可以用可行能力的被剝奪來合理地識別。這種方法集中注意具有自身固有的重要性的剝奪(不像收入低下,它只具有工具性的意義)。二是除了收入低下以外,還有其他因素也影響可行能力的被剝奪,從而影響到真實的貧困(收入不是產生可行能力的唯一工具)。三是低收入與低可行能力之間的工具性聯系,在不同的地方,甚至不同的家庭和不同的個人之間,是可變的(收入對可行能力的影響是隨境況而異的、條件性的)。[5]86
可行能力視角對貧困分析所做的貢獻是,通過把注意力從手段(而且是經常受到排他性注意的一種特定手段,即收入),轉向人們有理由追求的目的,并相應地轉向可以使這些目的得以實現的自由,加強了我們對貧困和剝奪的性質及原因的理解。失業對個人的生活還有其他嚴重影響,會導致其他種類的剝奪,這時通過收入補助帶來的改善就會相應地減少。大量證據表明,除了收入損失之外,失業會導致多方面的嚴重影響,包括心理傷害,失去工作動機、技能和自信心,增加身心失調和發病(甚至使死亡率增高),擾亂家庭關系和社會生活,強化社會排斥,加劇種族緊張和性別歧視。[5]91
波蘭尼和森的分析主要是立足于資本主義經濟的考察,可以看出,經濟增長可能帶來對部分人可行能力的剝奪,由此會產生多方面的問題,表現為失業、貧困、歧視等。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經濟增長也可能造成部分勞動年齡段的人成為“低收入人口”,這種“低收入”狀態進而衍生出多種社會問題,如受其供養的低齡者和老齡者也都可能成為“低收入人口”。結合 “水母型”社會結構,我們可以進一步考察不同年齡段的人的低收入情況(見表1)。
表1中,對那些有勞動能力和意愿的青/中年人,由于多種原因導致勞動就業情況不好,“+”表示可能有收入或低收入情況,而幼弱和老弱的人則無勞動收入(部分老人可能有低的勞動收入),常態弱勢群體一般是低收入或無收入的。如果考慮社會保障中的多項目能夠及時提供給相應的弱勢群體,在表1的下面一行,則可以看出弱勢群體都能有社會保障待遇,成為支持低收入人口基本生活的堅實基礎。
加強低收入人口動態監測,做好分層分類社會救助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我們深入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持續用力,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6]《意見》指出,社會救助是社會保障體系中兜底性、基礎性的制度安排。為健全分層分類的社會救助體系,加大低收入人口救助幫扶力度,進一步織密扎牢民生兜底保障安全網。
新中國成立后,得益于中國制度優勢,在不同的階段,對弱勢群體的界定和扶助呈現出變化和發展的態勢。新中國成立初期,主要面向災民、難民、失業人員、孤老殘幼等弱勢群體,采取緊急救濟的方式解決他們面臨的困境與問題。計劃經濟時期,在農村建立了“五保”制度,向鰥寡孤獨社員提供生活救濟;在城鎮向孤老病殘人員和特殊救濟對象提供日常生活救濟。改革開放后,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我國社會政策體系化建設發生戰略性升級,對城鄉弱勢群體進行了包括收入在內的多主體治理、多維度扶助。
政府機制:保護弱勢群體利益的主導。馬克思、羅爾斯的分配正義思想都不同程度地包含著對弱勢群體的關懷與支持,都看到了在分配中不能忽視對社會弱勢群體的關注,都認為無視弱勢群體存在及其困苦是不正義的。[7]45 《意見》 指出, 強化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政牽頭、部門協同、社會參與的工作機制。因此,為保護弱勢群體的根本利益,政府需承擔起幫助弱勢群體維持生存和身心健康發展的責任與義務。《意見》規定,各地對已納入社會救助范圍的低收入人口,重點監測相關社會救助政策是否落實到位,是否還存在其他方面的生活困難;對未納入社會救助范圍的低收入人口,重點監測其家庭狀況變化情況,發現符合救助條件的,應當告知相關救助政策,按規定及時啟動救助程序。發現低收入人口未納入社會救助范圍,但可能符合救助條件的,要根據困難類型和救助需求,將信息分類推送至相關社會救助管理部門處理;發現困難情形復雜的,可適時啟動縣級困難群眾基本生活保障工作協調機制,通過“一事一議”方式集體研究處理。當然,《意見》也規定對那些不符合救助政策的對象,及時讓其退出救助。
社會機制:發現和幫扶弱勢群體的抓手。馬克思指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8]60為避免社會弱勢群體的疏離化,防范沖擊社會道德底線事件發生,應充分發揮社區和社會組織的作用。社區是弱勢群體生活的基本社會單元,應依托社區發現并幫扶弱勢群體,幫助他們融入社區和社會,提升發展能力和機會。需從社會角度出發,創設相應的工作機制來解決弱勢群體中存在的潛在問題,精準發現該類人(群),及時進行幫扶、疏導,杜絕極端事件。農村的“六個精準”和“五個一批”工作機制的延續。在我國農村扶貧工作中,以往的工作機制是區域瞄準,就是由政府選擇一定的貧困區域,并進行有針對性的重點扶持。2015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對貧困區域的扶貧工作予以高度重視,提出了“六個精準”和“五個一批”來提高扶貧開發工作的力度。在完成脫貧攻堅、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征程上,精準發現低收入人口、精準開展幫扶的工作機制還是需要保留并運行的,讓政府的相關政策得以實施,讓社會組織和社會公眾的善心可以起作用,避免和杜絕個人或家庭因特殊原因給生活或工作帶來一時之急、限于困境而走向極端的情況。城市“網格化”治理機制。城市中的家庭和居民,其生活、工作狀態,鄰里之間往往都不易了解到,這有其優點,如隱私權可以得到保護,當然,也有其弱點甚至缺點,就是個人或家庭遇到極端困難,別人也不易察覺。在實際工作中,黨和政府及社會創造出“網格化”治理,這是在確保個人和家庭基本權益的同時,也可以發現需要幫助的人(家庭)的良好工作機制。以單位、園區、樓棟,特別是以居民小區為基本單元的網格,以及基層治理工作站,都可以及早發現并解決城市社區各種低收入人口中的個人和家庭問題,防范和杜絕極端問題的出現。在社會發展的任何階段都存在弱勢群體和低收入人口,關心幫助他們是政府和社會應盡的職責。市場機制的自由—效率成果和自由—不均等問題的嚴重性,值得同時加以考察。特別是在處理嚴重的剝奪和貧困問題時,必須正視不均等問題,在這個領域,政府扶助、社會干預都應發揮重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這正是福利國家的社會保障體系,通過一系列的計劃,包括由社會提供的醫療保健、對失業與貧困的公共扶助等,所試圖實現的目的。[5]118新時代,我國日益完善的社會政策體系及其實踐,在弱勢群體的收入、健康、教育、住房等保障,就業能力提升和幫扶等多維度的“扶弱”方面越來越好。
近期歷史和人類學研究的突出發現是,原則上,人類的經濟是浸沒(submerged)在他的社會關系之中的。[4]40根據商品的經驗定義,勞動力、土地和貨幣不是商品。勞動力僅僅是與生俱來的人類活動的另外一個名稱而已,就其本身而言,它不是為了出售,而是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而存在的,并且這種活動也不能分離于生活的其他部分而被轉移或儲存……因為“勞動力”(labor power)這種所謂的商品不能被推來搡去,不能被不加區分地使用,甚至不能被棄置不用,否則就會影響到作為這種特殊商品載體的人類的個體生活。市場體系在處置一個人的勞動力時,也在處置附在這個標識上的生理層面、心理層面和道德層面的實體“人”。如若被剝奪了文化制度的保護層,人類成員就會在由此而來的社會暴露中消亡;他們將死于邪惡、墮落、犯罪和饑荒所造成的社會混亂(dislocation)。[4]63波蘭尼所說的“勞動力”在市場上的不當使用或不被使用,可能帶來多方面的問題。
當前,我國隨著共同富裕政策的出臺和實施,弱勢群體獲得了經濟支持、發展幫扶和社會保護。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我國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9]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這一偉大目標的確立和實踐,必將在教育、就業、收入和基本公共服務等方面影響全體人民,在人生的各階段、各方面有“弱勢”表現的人(群體)必將得到多方面社會政策的關注和關照,以促進低收入的勞動者就業、提高他們的工資收入為主,加強社會保障多項目的覆蓋,由此也就能夠幫助這些弱勢群體,使他們在就業和基本生活等方面實現共同富裕,也就是他們的收入在“水母型”社會結構圖中B軸上的點肯定高于A′軸。
誠如《意見》所說: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困難群眾,切實兜住兜準兜好基本民生底線。“低收入人口”是需要關心和幫助的人(群體),包括低收入人口在內的全體人民獲得美好生活,必將為中國式現代化做出基礎的也是重大的貢獻。
參考文獻:
[1]習近平.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的講話[N].中國政府網:http://www.gov.cn/xinwen/2021- 02/25/content_5588869.htm.
[2]霍華德·格倫內斯特.英國社會政策論文集[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3]童星.創新社會管理[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4]卡爾·波蘭尼.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5]阿馬蒂亞·森.以自由看待發展[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6]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J].求是,2022-12.
[7]龐永紅.分配正義與轉型期弱勢群體研究[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6.
[8]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習近平.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J].求是,2021-09.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基于水母型社會結構的‘弱有所扶’制度建設研究”(18BSH045)〕
(作者系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殘疾人事業發展研究基地暨南京大學殘疾人事業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責任編輯:張蔚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