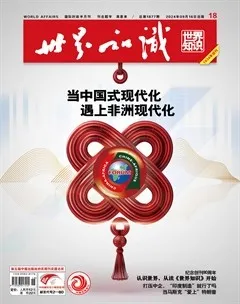非洲現代化進程尚無一個非常明晰的路徑
黎文濤:現代化的概念,一直處于被解構被建構的過程。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亞洲“四小龍”與“四小虎”的崛起,可以說是西方定義的現代化模式的一種體現。而中國在過去二三十年的發展,可以被看作是西方傳統的現代化概念不斷被修正、革新,甚至是被推翻的過程。現代化的實現沒有統一的模式、道路,只有適不適合自己國家的國情。當前,對非洲來講,現代化是一個綜合性的概念,不僅僅是指在物質層面實現現代化目標,還有其他層面,比如政治文明。只有幾方面協調前進,才能夠成功實現現代化。
非洲對工業化或者說現代化一直是孜孜以求的。上世紀80年代初,非洲國家領導人集體提出“拉格斯行動計劃”,旨在增強非洲國家自力更生的能力、推動非洲實現工業化,但是基于種種原因,該計劃失敗了。在21世紀伊始,非洲又出臺了第二份聚焦工業發展的計劃,但也被扼殺在搖籃中。2016年,非洲又出臺了第三份工業發展計劃。從目前來看,非洲工業化進程還是比較緩慢的。
非洲的現代化嘗試迄今為何未能取得成功?或者說,非洲為什么發展不起來?核心問題還是非洲至今沒有找到一條適合自己國情的發展道路,或者說是現代化道路,這也是為什么這次峰會把主題聚焦于“現代化”。非洲的殖民統治遺留問題尚未被完全根除,再加上西方強加的不適合非洲實際情況的制度,所有這些因素交織在一起,導致非洲的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是相互矛盾、不協調的。我曾經去南部非洲調研,發現這些地方的工會組織特別發達,維護正常權益當然是很有必要的,可這些組織很多時候提出了一些很不合理的要求,這對當地工業發展是不利的。當前非洲所需要的,是把所有資源集中起來搞生產、促發展,但這在非洲實現起來非常難。非洲當前如果沒有強有力、負責任的高效政府,怎么來推動工業化發展?
唐曉陽:非洲現代化進程的起步,開始是源于歐洲對它們的殖民以及貿易。在獨立之后,非洲嘗試過采取不同的方案,包括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西方的自由經濟以及結構主義的工業生產,但效果都不是很理想,非洲一直處在世界經濟發展中比較落后的位置。
很多非洲國家在短期內可能會有比較快的增長和工業化發展,但是從長期來講,其工業化進程就是難以持續,到現在非洲國家基本上在世界市場上只能依賴一些低附加值的傳統資源型產品參與世界市場分工,而自己國內的農業沒有產業化,工業化程度也非常低,青年失業現象凸顯。因此,非洲目前的現代化進程還沒有一個非常明晰的路徑,除了少數幾個小國,比如毛里求斯、塞舌爾,因地理mz2v39e2NVE5xSXga68hwD8JKwrUO//TgFdym+llgug=上具備獨特因素,所以能夠通過旅游服務業和貿易實現國家發展。有些非洲國家甚至還出現了現代化、工業化的倒退現象,比如南非。
非洲現代化進程還面臨一個瓶頸,就是非洲政治版圖碎片化,導致各國之間交通不太便利。當然,這也是受到了西方殖民歷史的影響。國家之間聯通不暢,再加上行政上的分割,過小的碎片化的市場顯然不利于現代化的產業發展。

黎文濤:我們也要看到非洲發展的現實困境和不容易。大多數非洲國家是在上世紀60年代才獲得獨立的,獨立時間并不是很長。有些國家為了獨立進行反殖民斗爭,還陷入了內戰,很難專心搞發展。獨立之后,不少非洲國家經歷了大概十年的較快發展,但而后又被西方強加以一套有條件的“結構調整計劃”和以“華盛頓共識”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主張。如前所述,非洲經濟在這個階段受到了很大打擊,工業化尤其遭遇困境。冷戰結束后,在西方的壓力之下,非洲大多數國家一夜之間按照西式制度進行政治改造。在此過程中,非洲付出了很大的代價。上世紀90年代,非洲爆發了多場戰爭和內戰,比如大湖區戰爭、索馬里內戰、盧旺達大屠殺都發生在這個時期。我認為,這是非洲在消化西方強加的制度所帶來的陣痛。一直到本世紀,非洲才算可以比較專注于自身的發展了。某種程度上看,非洲發展時間也就20年左右。
王進杰:非洲國家在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面臨著既要借鑒國際經驗又須結合自身實際的雙重挑戰。西方國家的現代化模式并不完全適合非洲的國情,因此非洲國家必須探索符合自身特點和需求的發展道路。這一過程充滿了曲折和反復,但也是非洲國家自主發展、尋求多元化發展路徑的必然歷程。我想用兩個國別的例子說明非洲國家曲折且反復的現代化歷程。
第一個例子是埃塞俄比亞。梅萊斯1991年任埃塞總理后,領導埃塞人民革命民主陣線,推進“發展型國家”治國理念,強調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主導作用,通過國有化、五年計劃和發展重工業等手段推動國家工業化和現代化,實施農業改革和土地改革。梅萊斯的“發展型國家”道路和強勢統治,曾經造就了埃塞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盡管如此,梅萊斯時期實行的“族群聯邦制”放大了埃塞國內的族群隔閡,為這個由80多個民族組成的國家未來發展埋下了隱患。2018年阿比總理執政后,聯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試圖緩和族群矛盾的措施,但是族群問題不僅沒有解決,反而變得更加惡化。與此同時,阿比的治國理念也不再堅守“發展型國家”道路,開始逐漸傾向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最近幾個月,埃塞經濟出現動蕩,本幣快速貶值,外資撤離。埃塞之所以采取較大力度調整經濟政策,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援助附加條件密切相關。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埃塞的發展非常反復和曲折。
第二個例子是津巴布韋。說起津巴布韋,大家都會回溯穆加貝執政時期推行的土地改革,這是該國歷史上推進現代化進程中非常重大的事件,旨在解決殖民時期遺留下的土地分配不均問題。一開始,津巴布韋還是采取了一種比較溫和的方式推進改革,采取購買土地重新安置的方式將土地分配給沒有土地或者是地少的農民。到了2000年時,該國開始采用激進的方式進行土地改革,強制把西方農場主的土地分配給當地農民,引發了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問題,大量的西方農場主離開津巴布韋。津巴布韋試圖擺脫西方的束縛和阻力,但激進的方式導致農業生產急劇下滑,該國也遭遇了嚴重的糧食短缺問題。農業生產的衰退外加惡性通貨膨脹,導致津巴布韋國民經濟崩潰。2000~2009年,津經濟增長率一直為負數。現在津巴布韋又試圖吸引農場主回來。
從這兩個案例可以看出,一個國家在選擇經濟發展道路、現代化發展道路的過程中,一定要和自身的政治體系配套,政府治理和經濟政策要同步前行,否則就會形成一種撕扯和阻力,導致現代化發展之路充滿反復和曲折。
對中國而言,我們需要做的是去更好地理解非洲國家的價值體系、內在文化,以及它們所經歷的國家起伏發展的過程,這樣中國企業才能更好地融入到當地的發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