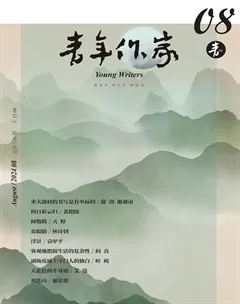新婦
盧灶順的大新婦惠玲守寡時還不到三十歲,有兩兒一女。她的丈夫是臺風天為盧厝鎮守江堤時,被大水沖走的。丈夫的墳墓因此立在江堤上,除了名號,還刻上了“為百姓安危犧牲,貢獻彪炳千古”。墳堆和碑石都是單個一體完整的,沒有為妻留下位置。一年后,盧灶順決定招個人進來補長子的缺。雖然長房香火沒斷,但大新婦這么年輕,守寡到老是不可能的,要再嫁就得抓緊時間了。盧灶順看得定,也緊鑼密鼓地安排著。大新婦要是嫁出去,這兩兒一女跟著會凄涼,不跟也凄涼。所以,不如就招進個兒子,新婦還是新婦。他不容拒絕地把想法告知惠玲。
顧不上禮節,惠玲對盧灶順說:“那你得找個能當你兒子的。”
不多久,盧灶順帶回一個四川人小張,才二十五歲,沒結過婚。媒姨跟著來的,對惠玲說盡好話。惠玲抱著小兒子一聲不吭。
“你自己偷偷走吧。”灶順的細新婦賢妹抓住午飯后收拾碗筷的機會,忍不住悄悄給惠玲出了個主意,還往惠玲手心里塞了一卷錢。賢妹用力地捏了捏惠玲的手心,說:“孩子給我。”
一整個下午,賢妹都沒看到惠玲。但晚飯時候惠玲又回來了,帶回來一只炸得金黃酥脆的童子雞。賢妹接過餐盒,嘆了口氣,也像什么都沒發生一樣,招呼道:“大姆,可以吃飯了。”
灶順大新婦沒有反對,好事便著手開辦了。所謂辦事,只是讓四川人小張拜了盧氏祖宗,并改姓盧。儀式結束,小張就是盧灶順的長子了。他搬進了灶順家。新婚之夜,灶順大新婦極自然地把小女兒抱到床中央,自己爬進里面,兜著女兒的屁股,閉上眼睛。在新丈夫的腳悄悄伸過來時,惠玲猛地睜大了眼睛,瞪了他一眼,把那只腳“瞪”了回去。那是個隨時準備同歸于盡的眼神,嚇得小張整夜都不敢關掉頭上的燈泡。
半年后,惠玲懷孕了。她命令小張去跟盧灶順說,必須分家了。盧灶順招小張作兒子,家里卻像多了個長工。盧灶順喊他小張,灶順嫂喊他小張,灶順細兒子喊他小張,惠玲自己也喊他小張,甚至連灶順的孫子們都喊他小張。小張已經不像剛進門時一樣憨憨應著,惠玲難堪的臉色一天比一天掩藏不住。賢妹悄聲對惠玲說:“不能讓孩子們叫他小張,你這樣叫也不合適。”惠玲吭了一聲,尖利地反問道:“還得叫爸爸?”賢妹沉默了下,說:“叫叔也可以。”惠玲哼了一聲,說:“娶我這寡婦倒是真劃算,一下子房子、兒子全有了。”見賢妹還不走開,她冷笑道:“現在我還得給他生兒子,要不你來試試?”
賢妹一走開,惠玲的眼淚便掉下來了。她生盧灶順的氣,生小張的氣,更生死鬼丈夫的氣。她一秒鐘的好臉色都不想給那個四川仔,但盧灶順一家子對小張的看輕又讓她壓抑得簡直要發瘋。這家人既然看不起四川仔,為什么要招這么個人來?這個外省仔那么年輕,他想從自己身上得到什么?她看見小張不自在,心里暢快得想大笑。但事實上,惠玲幾乎每天都在流眼淚,氣得捶肚子,盧灶順一家人憑什么這樣做?憑什么呢?
盧灶順拒絕分家,對小張說:“現在分家,你出門就得被人吐唾沫。別人當幾十年新婦的,無論被公婆怎么刁難,都不敢說分家一個字,你這上門給人做兒子的,說這話不怕街市人罵?”
小張說:“老人、孩子該我養的,我肯定還是會養。”
灶順反問道:“你拿什么養老婆孩子?我們兩個老的要你養也是你的本分,但我自己還有兒子,不用你養。問題是,你拿什么養老婆孩子?”
小張干笑了兩聲,勉強保住了已經很難看的笑臉,回道:“窮就窮養,富就富養,不都這樣嗎?”
“你打算像你父母養你一樣養我的孫子?”盧灶順毫不客氣地反問,“十二三歲趕出門去打工,娶不起老婆再像你一樣被人招?”小張其實是十五歲出來打工的。
小張反駁道:“我十五歲才出來的。”
那天的晚飯,惠玲沒煮。賢妹剛把碗筷擺齊,惠玲就坐下,端碗吃了起來。惠玲嫁進盧灶順家快十年了,除年節外,她很少上桌和老人、男人一起吃飯,基本都是家人在吃的時候她喂孩子,等人家吃完了她才吃。現在,她不僅上了桌,還絲毫沒有等其他人的意思。
賢妹在惠玲旁邊站了好一會兒,像自己做錯了事一樣地偷聲說:“別這樣……”但惠玲只白了賢妹一眼。賢妹只好叫公婆吃飯。
盧灶順進飯廳一看,氣得直接回了房間,換灶順嫂進來罵。惠玲當作什么都沒聽見,吃完了就回房間。賢妹在飯廳站著,大家都吃不下飯。接下來幾天,惠玲都是這個樣子,小張和兩個兒子也被她趕出房間,小張睡到客房,兩孩子被賢妹帶到自己房間。
一個多月后的半夜,盧灶順突然吼道:“分!分!留這些催命鬼在這收我的老狗命!”
賢妹再見到惠玲,是兩年后了。惠玲一家分得了一座下山虎厝和一百七十萬現金,樓房和生意存貨都給了二房,也就是賢妹一家。這讓賢妹即便是惠玲生孩子的時候,也不敢去看她。自古以來,分家產都是要長子長孫優先的,長孫當細子。說到底,還是認骨肉,還是有私心。家里的每一個人都知道,小張一家和盧灶順一家的關系僅存于祠堂之中及族譜之上了。時年八節,也只有小張過來祭拜,連孩子都不來,何況是惠玲。
這天,賢妹去婦幼保健院上節育環,她連著生了兩個兒子后,覺得自己已經完成了任務,任灶順嫂怎么不高興,也不愿意再生了。碰巧,惠玲剛在醫院生了孩子。賢妹說:“呀,大姆!”惠玲也還挺高興。惠玲和賢妹關系一直不錯,她只比賢妹大四歲,因為賢妹上過大學,結婚晚,所以顯得兩妯娌年紀差很多。賢妹有文化,但一直很尊重大姆,把大姆當長輩一樣敬重。
賢妹問:“大伯呢?”
惠玲說:“老五沒人帶,他在家帶唄。”
賢妹嚇一跳,這回出生的是惠玲和小張的第三個孩子。惠玲看出了賢妹的吃驚,問:“怎么?笑我沒用?要不是老天爺積惡,我又不是沒有兒子,又不是生不出兒子?”幾月前,惠玲做B超的時候,知道肚子里還是個女孩,她和小張都很喪氣。惠玲就像一個裝滿了番薯的鳥屎袋,從中一個接著一個地往外掏,圓滾滾的身體其實只是個空袋子,灌滿空氣,虛張聲勢。但小張還沒有自己的兒子,惠玲還得再接再厲。
賢妹只好問:“還順利吧?”
惠玲哼了一句,怒氣沖沖地說:“哪有你順利!”
“女孩也好。”賢妹沒在意惠玲的態度,輕聲安慰道。
“好的話你抱走,給你了!”惠玲心情似乎更壞了,安慰話換不來兒子,她也懶得跟賢妹客氣應付。
賢妹嘆了口氣,說:“等阿妹大點了再生吧,你也調理下身體。”
“加緊點,早點生夠,以后早點輕松。”惠玲突然變得垂頭喪氣,見賢妹為難著不知如何接話,就說:“帶一個是帶,帶七個八個也是帶,眼一閉牙一咬,就都一起長大了。我任務完成了,才不會一端起碗就覺得欠了誰的。”她又說,“你命好,兩個兒子了,現在生男女都好,你才有底氣說女孩也好。”
賢妹沒有反駁,只勸道:“那也不能挨得太緊。”
“你不生,難道要留給別人生?”惠玲忍不住挖苦道。
“我也是學醫的,你這樣不顧自己身體,過些年有你受的。”賢妹還是不死心地勸道,雖然她很清楚說什么都是白說。
果然,惠玲一臉平靜地回道:“人總是要往前看的。”也沒明說往前看到底是什么意思,自己的身體就不是前面該看的事?
但盧灶順家和惠玲的不幸還沒有完。厄運進了命,就像蟑螂進屋,成群結隊、生生不息,是除不盡的。
惠玲生到第七個孩子,終于是個男孩,大兒子盧木豪已經上初中了,一切好像都安穩下來了。誰知,剛上初中短短的一個學期,不知為何,原本懂事聽話的兒子幾乎成了個小流氓,逃課、飚摩托、拿鐵水管跟人打群架、早戀……盧木豪迅速成了盧厝中學里一群野孩子們的頭頭。老師隔三岔五投訴,別的家長反反復復上門理論。盧木豪的繼父小張不管,母親惠玲道歉了又道歉,把兒子罵了又罵,并沒有好轉。有次吃飯的時候,惠玲氣得拿筷子敲了下大兒子的手背,結果小伙子抓起高壓鍋蓋就甩到母親胳膊上。惠玲揉著瞬間紅腫的手臂崩潰痛哭,盧木豪卻頭也不回地摔門出去了。惠玲下決心把孩子送到寄宿學校去,再放他這樣晃蕩,要么會走上邪路,要么遲早得被人打殘甚至打死。
到學校報名,學校要求惠玲交孩子的戶口本復印件。惠玲的七個孩子都還沒上戶口,她和前面的老公沒領過結婚證,和小張到現在也沒有辦結婚證。盧厝鎮認的是禮俗,不到用時,證件都是多余的。小張的戶口倒是已經遷過來了。盧灶順憑借自己的人脈,又花了點錢,把小張改了盧姓,名正言順地成了父子關系。
惠玲只好先回去,要小張去打結婚證。小張說:“可以,但我要改回姓張,你兒子姓什么隨你,但我兒子肯定得姓張。”
這樣要求,小張是有底氣的。這幾年,他跟著原來的老板學做生意,開了一家小小的絲花廠。他們一家早就搬出了盧灶順分的下山虎老厝,在盧厝鎮起了四間樓房,比杰濤分得的那四間還寬敞,地段也更好些。早在買下地的時候,他就想把姓氏還給盧灶順了。
惠玲把小張的要求告訴盧灶順。盧灶順氣得再次請來了族中的全部耆老,準備教訓這個沒長良心的外省仔。雖然小張松口允諾將來兩邊的祖宗都要拜,盧灶順仍被屈辱激得怒不可遏。自己兒子生意越做越小,原本給人做工的外省繼子卻發了財,盧灶順心里本來就很難消納。有次他路過小張的絲花廠,進去看了看,隨口提起說:“你們現在過得好了,要是可以,多少幫杰濤一點。”沒想到,小張卻認真地說:“要不把破房子還給你們?”盧灶順聽出了其中的威脅,卻還強撐著笑容,說:“家都是你們年輕人打理了,做事憑本心,我們老人也就隨便說說。”小張卻再次認真地回答道:“那就本分點做個老人,多吃幾年飯,別管那么多事。”盧灶順氣得差點甩出去巴掌,但還是攥緊了拳頭,走了。最近一年,小張命令惠玲停止拜神,把守護盧厝鎮風調雨順的神圣事業說成“為了死鬼要熏死活人”,甚至連拜祖也時常不來上香了。盧灶順正積壓著氣,準備找個機會去教訓下這個外省仔,沒想到他不僅不知收斂,還提出這樣背天地良心的要求。
二樓,耆老們擠滿了客廳,每張老得耷拉了的臉上都布滿了替天行道的正義感。但事實上,耆老擺開陣勢也只是勸、罵,講誠信、講仁義,再沒有更多辦法。盧灶順氣急敗壞地質問:“這么多年,你都沒回去過你外省老家,你現在究竟是想干什么?”
“這么多年,你們這本地話我再學也不像,掛著你們的姓總是心里不舒服。你們要是覺得虧了,我可以把以前你們的那座下山虎厝還你們,六年需要多少租金你們可以說說看,合情合理的,我一次性補清給你們。”小張點了根煙,蹺起腿,神色一派悠閑地靠在椅背上,不緊不慢地回道。
“在我們盧厝,就得遵守盧厝人的規矩。做人不是拿市價就能換算清的,要有情有義。你娶了人家女人,讓你從空腳白手的打工仔到今天有樓有厝,有妻有兒有女,你說租金臉不紅嗎?”年紀最大的耆老頓了頓腳,又頓了頓拐杖,手顫顫抖抖地,像隨時要把拐杖揮過去。
“我不是盧厝人。你們還不讓我活了?我做生意少過你們盧厝哪個人的錢?”小張卻并不激動,也不理會對面那些老頭子的憤怒。他經常說盧厝鎮人有點事就叫出這幫連路都走不穩的老頭是愚蠢的,而且沒一點用。耆老講起了從前的誰和誰如何如何,抑揚頓挫,慷慨激昂。小張歪在交椅上,換一條腿盤起,不著急搭話,半瞇著眼睛,像快睡過去了,這讓老人們很不自在,并且越說越氣,有些不耐煩了。但以理動不了,以情也動不了的人,他們也沒有別的辦法。耆老的權威是祖上開始就約定好的,顯然小張并不在約定之內。
正當他們無可奈何,準備起身走人的時候,惠玲上樓來了。沒有人叫她,她也不應該來的,但這會兒她就是出現在了客廳里。小張背對著樓梯口,聽見惠玲的聲音也沒有回頭。他摸出了煙盒,自己咬了一根,又把手伸向最近的老人,說:“抽根煙,歇會再說。”分了一圈煙后,他又遞了一圈火,最后自己點上了,倒回椅背。惠玲站在他背后,沒說話也沒找地方坐下。
挨著小張的老人就說:“后生仔,娶得到這么好的女人,你得知道感恩。姓什么你們外省人對這個也不是那么看重,既然到我們盧厝鎮做兒子了,老話說一諾千金,你也是生意人,應該懂才對啊。”
“一間破厝筒子就要千金?”小張斜乜了老頭一眼,毫不掩飾地諷刺道。
“人家小嫂子給你生兒育女,家內上下打點得流流利利,這些是多少厝可以換來的?做人不能沒良心,想想你們大山角里,有多少年紀比你大得多的還沒有老婆,更別說兒女雙全。你能做起生意,也是盧厝人牽你起來的。你今天所作,別說對不對得起灶順一家,你對得起妻兒嗎?”耆老們一直在強調良心。
可惜,小張顯然是個沒良心的人。他深吸了一口氣,閉上了眼睛,把煙緩緩地從鼻腔里吐出來,才睜開眼輕輕地問:“一個老寡婦?”
惠玲在小張背后,聽到這話像嚇了一跳,臉一下子又青又紅,一會兒就全青了。她一臉不敢置信地瞪著丈夫的后腦勺,前面的人卻是輕松得完全不為所動。惠玲又看了眼氣急敗壞的盧灶順,像來時無聲無息一樣,又靜靜地晃悠悠飄下樓。已經管不得是否失禮了,身后亂得難以辨認詞句的責罵讓她幾乎暈過去。惠玲緊緊摳著扶手,到了最后一級,癱坐在樓梯上。
門一關,惠玲死死抱住賢妹,抑制不住哭腔、渾身顫抖地嗚咽著:“他說我是老寡婦,當著那么多人的面!說我是老寡婦……”
賢妹也被這話嚇了一跳,又不知道怎么安慰,只好挨著惠玲坐下來。惠玲撲到她身上,毫無顧忌地哭到破聲。再也不顧及門外的人和耳朵,他們一定聽得到的,但還能比被丈夫說成那樣更丟人嗎?惠玲胡亂地罵著那個已經死去多年的人,罵給她招來這個沒良心砍頭外省仔的老家伙,罵兒子,罵賢妹……賢妹靜靜聽著,拍著她的背,也掉下了眼淚。
惠玲真的老了,和小張站一起簡直像兩代人。孩子一個接著一個從身體里掏出去,這會兒她趴著痛哭,就像個裝滿了空氣的麻袋一樣晃晃蕩蕩。眼前的人跟賢妹剛過門時記得的那個完全已經判若兩人,靠近了甚至可以看見她耳垂下方的肉已經開始有些松弛,掛出幾條淺淺的褶子來。而小張與當年瘦瘦小小的打工仔也已經判若兩人,如今他膀闊腰圓,每天用發膠把頭發梳得油亮。賢妹哀哀地嘆了兩口氣,就不知道再說什么了。
“我也沒做壞事啊!”惠玲哭了一會兒,抬起頭,定定地看著賢妹說,“兒子不比人少,我也不敗家,勤勤快快的,做祭拜神按時按日,比誰都誠心……”說著她又嗚咽起來,問賢妹:“怎么命就是這么不好呢?
“唉……”賢妹又嘆了口氣,握著惠玲的手更捏緊了些,實在不知道怎么安慰。安慰得了運,還安慰得了命嗎?既是命的事,就只能受著。惠玲不是能對抗命運的人,也不是敢跟命運魚死網破的人。賢妹看得明白,所以沒什么說的。她知道惠玲哭完了、冷靜了就會回家,沒有不回去的理由,也沒有不回去的能耐。
抽抽搭搭的聲音漸漸平息,惠玲從賢妹身上爬起來靠在墻上,剛才哭得太用力,出了一身汗。
賢妹見惠玲冷靜了,就說:“你在這睡會兒吧,中午在這吃。”
近中午的時候耆老們顫顫巍巍地下來,走了。小張沒有下來,盧灶順也沒有下來。灶順嫂照例出去給兩個孫子送午飯,腫著眼睛,匆匆忙忙地出門,匆匆忙忙地回來。賢妹的丈夫杰濤回來了。他已經聽說,全盧厝鎮的耆老都被父親請過來了。
杰濤剛上樓,就看見父親像垂死的人一樣癱在沙發上,小張也沒好臉色,地上已經堆了一層煙頭和煙灰。杰濤擰緊了眉,向灶順嫂三兩句問清了早上的事。他氣得直接把小張踹倒在地,一腳踩在他胸口上。小張還沒回過神,杰濤又咬著牙緊跟著踢了幾腳。盧灶順不得不起身喝住兒子,他一早上已經吼得喉嚨都啞了。杰濤沒有再動手,罵道:“破落外省仔也不抬眼照照自己,賺了幾分錢就不知道怎么做人了!”
“不改姓我不會去打結婚證,你們可以把那幾個死父仔的戶口入到自己戶口本上,我的孩子要不跟我姓張,要不讓你大兒媳婦來求你。”小張坐在地上,一臉譏笑地看著盧灶順父子,故意用潮汕話字正腔圓地說了“死父仔”。
杰濤被激得捏緊了拳頭上前要拎人,這回被小張躲開了。
整個早上沒說一句話的灶順嫂,眼淚已經不知道抹掉幾回了,這會兒又止不住地往下流,“求你們了,積惡啊……丟掉祖宗臉啊,積惡……”她像哭喪一樣拉長聲喉哭道。
賢妹也上樓來了。換做往日,家里大人、丈夫都在場,她是不會開口說什么的。但現在惠玲還在樓下,賢妹覺得該說點什么。想了一會兒,說:“至少你不應該這樣說大姆。”她突然不知道怎么稱呼小張更合適。如果小張還是補灶順長子位置的,那她該隨孩子叫他大伯。但小張此時正在拒絕這個位置。賢妹只好不加稱呼地說了這句話。
“她要是這么一句話就受不了,單這盧厝鎮一天得死多少女人?你爸有錢有勢,你才能天天那么多不情愿。”小張諷刺賢妹道。
賢妹正想說他傷了惠玲的心,杰濤卻搶過話說:“你要不是盧厝人幫你,你現在連一口屎都扒不到嘴里!你還以為真是憑你的能力,你能塞滿腸肚,坐在這里吐屎?”
“那盧厝人怎么不幫你?盧杰濤?”小張猛地站起來,尖利地說,“因為爛泥扶不上壁。”他似乎下定決心再不用客氣了,把客廳的人都掃一遍,最后定在杰濤臉上,堅決卻一點都不激動地說:“你要是心里不舒服,你們父子倆現在就可以去把人領回來。你們盧厝人能耐大,扶得起一個我四川仔,就扶得起兩個三個,你盧灶順的大新婦能嫁第二次,再嫁三、四、五、六個也沒相干了,你們慢慢挑啊,挑到合心意的為止啊!”
“你這外省仔有沒有點良心?”盧灶順從沙發上跳起來,膝蓋哐地一聲撞翻了面前的小板凳。一絲灰白的頭發掉到他眼睛前,但絲毫擋不住兇惡的眼神。
“跟你們用得著說人話嗎?”小張迎上盧灶順的眼光說道,他徹底失去了耐性。
盧灶順抓起茶盅往小張臉上摔去,卻被他輕易躲開了,茶盅砸在地上,茶葉和碎瓷片四散。小張捏緊了拳頭,死死地貼著褲縫。盧灶順在瓷茶盅的破碎聲后,倒向沙發,垂著頭,緊緊抿著嘴唇。灶順嫂一下緊接一下地抹著眼淚,臉色比燈光還更白些,風濕發作似地癱軟著。
誰都沒有心情再吃午飯。賢妹悄悄下樓,惠玲卻已經走了。賢妹又嘆口氣,想著惠玲該是回家做飯了,家里還有七個孩子。
賢妹猜對了。下午,惠玲把孩子送進學校后,坐在幼兒園門口的花壇上,坐了整整三節課,她不想回去看到小張。孩子放學出來,她該帶孩子回家了,卻又走到盧灶順家里。灶順嫂也剛接回孫子,看了惠玲一眼,嘆了口氣,說:“你該回去買菜煮飯了。”“我回去會死的,”惠玲叫道,“要我就這樣回去?他那么罵我!讓我回去給他罵?”她直直地盯著灶順嫂,眼神里滿是恨和憤怒,但很快就又流下眼淚,嗚咽著問:“你們讓我跟他,現在卻拿他一點辦法沒有?你們做大人的不用給我個說法?就拿他沒一點辦法嗎?”
“那你打電話給他,就說阿弟們今天想住爺爺家,讓他明天下午來接你。靈精點,誰都不信的話,你也得這么說。”灶順嫂說完又嘆了口氣,現在她除了自己的嘆息,什么都做不了主了。
她見惠玲沒動作,又勸道:“身長棺材短,屈死也得刻苦領受。”隔了一會兒,灶順嫂把聲音壓得更低了,完全不計前嫌地勸惠玲:“你自己命理不好,父母給你十足,你過得只剩三成,再怨天怨地也沒有用。嫁人就跟去市場買豬肚一樣,外面洗得清白,里面有屎沒屎,得下手翻過來才知道。要吃就別怕臭!哪個夫妻年輕的時候不是捶破頭殼的?難不成會比離了自己過更差嗎?你真要離婚,還是想不開去找死路,他保管連眼皮都懶得跳一下。這四川仔前幾年是賺不到錢才抬不起頭,你以為他還真能隨便給你揉捏?還是你想他一輩子縮頭縮尾地給人打工?你十七八歲的時候賭氣出走,人家得慌慌張張四處去找,現在你再這樣試試,你前腳敢出去,他馬上就敢找個補進去。你作嬌,自己的男人不看,就給滿街市人看了笑話。好過就睜著眼過,不好過就把眼睛閉著過,人又不是紙糊的,哪有人是罵不得的呢?”她見惠玲眼淚停住了,臉色卻更死白,不忍心安慰道:“幸好還是在我們這,不是跟他去外省。罵你一句不會破皮流血,他也不敢真趕你走,那么多眼睛看著,他要在這賺錢,再壞也是要臉面的人……”
灶順嫂絮叨完了,又把電話塞惠玲手里,要她打電話回去。惠玲捏緊了手心,深吸了好幾口氣,才撥了號碼,語氣平靜地說:“阿弟要跟賢妹的兒子玩,今晚不回去了。”話還沒說完,她聽見了電話那端清晰的嗤笑,剛想開口,沒拿電話的另一只手被灶順嫂使勁地捏了一下。她掙開了灶順嫂的手,用力地捏緊桌沿,指甲生生壓裂了,幾乎把自己的手指折斷,才繼續若無其事地說:“你去買點青菜,冰箱里還有排骨,用清補涼熬點湯。晚上讓他們準時睡。”就像平常夫妻一樣交代著,但惠玲說完趕緊掛掉電話。
晚飯之后,大人們沒一個有好臉色,沉默地圍坐著,連小孩子都不敢調皮了,安靜地寫作業。賢妹叫惠玲一起散步,透口氣。但賢妹實在也想不出要講點什么。她覺得即使已經吵開了,這些也還是惠玲的隱私,自己不該去安慰。
“大伯……”賢妹沉默了一會兒,猶豫著安慰道:“他可能也是生氣亂說話,也不是故意這么說的。”
“不是故意?”惠玲回頭看了賢妹一眼,嗤了一聲,質問道:“隨口說出的才更是心里想的。你以為他是個老實人?杰濤也不是個好貨色,前幾天半夜十二點多還載妹子從我家門前過。你說他們去做什么?我能聽到的事,你還會聽不到?你還不是得隨他去浪蕩?”
賢妹變了臉色,杰濤的事情她當然清楚,但被當面挑開還是第一次。
“只要沒鬧到實在過不下去,就都閉著眼睛過。要是都睜開眼過日子,有幾人還過得下去?”惠玲反倒開始勸起了賢妹,“有了幾個錢,外省仔也不會老實的。你不要以為只有我們想不破放不開,放得開的也沒幾個好過的。能跑能跳的時候,誰都要瀟灑。等飯碗都端不到嘴邊了,看還有沒有那么瀟灑,誰會給你端這碗飯去?”
惠玲看賢妹一臉不自在,一下子倒笑了起來——不是開心笑,而只是抽動喉嚨像用力地吐氣,常年罵孩子已經變得沙啞的喉嚨發出的聲音就像刮鐵片一樣,冰涼刺耳。好像真有什么好笑的,她笑了好一會兒,才突然又板起臉來,用教訓的語氣道:“飽鬼別不知道世上還有餓鬼。你指望一個連親生父母都可以不要的人有良心?杰濤再怎么臭,還有爸管,還得在盧厝鎮行踏,多少得要點臉面。妹子載來載去,你看得開,他不敢趕你走。這四川仔連父母都不要了,你以為他會聽這個半路認來的老頭的話?”
“你也別老是叫他四川仔,這太難聽了。”賢妹勸道。
“難聽?是叫錯了?他還不歡喜做個本地人,要把姓還給人家呢,嫌我叫得難聽,他怎么不嫌做的事難看?”惠玲站定,轉身叫了起來,情緒又激動了。
賢妹不再接話,只聽著惠玲接下去又說:“但老實跟你說,四川仔和盧灶順的事我無所謂,姓張還是姓盧,我都無所謂,只要讓孩子上戶口出去讀書。孩子去私立學校,那么多錢還要四川仔來給。他說的那話,怎么我也得讓它過去。我得勸自己一點,老公敢發性說明也是有點本事了,總比一輩子給別人當狗,溫馴得沒出頭之日強些。男人二三十,三四十的時候不安分,到了六七十還花得起來?堅持就是勝利!你說是不是?堅持就是勝利,我真的太大驚小怪了是不是?”
公園還沒走到頭,惠玲的態度已經轉了幾次,賢妹一臉不可思議地看著她,像夢游一樣地應道:“嗯,沒經濟獨立不能輕易離婚。”
惠玲的臉色馬上變得異常嚴厲,毫不客氣地訓斥道:“離婚?別讀書讀傻了!自由的意思就是什么都沒有,連個氣死你的人都沒有!將來死了連個埋的地方都沒有!我告訴你,腦子里千萬不要留這種心思,死路一條。死了老公再嫁都沒好下場,離婚的就更沒好下場!你以為你離婚了,還會有人娶你嗎?”她像聽到了多么恐怖的東西,完全不顧及賢妹的面子,越說越急,越覺得自己義不容辭,擲地有聲,完全失去了賢妹剛認識她時那溫溫柔柔的樣子。
賢妹忍不住起了雞皮疙瘩,搓了搓手,說:“有蚊子。我們回去吧。”
惠玲也沒反對,一路上又嘟嘟囔囔說自己太大驚小怪了。
那一整夜,賢妹心里沉重得睡不著。惠玲隨便收拾了個房間和兒子住下,不一會兒就均勻地打起了鼾。天剛亮,賢妹聽見惠玲起床洗臉。等賢妹起來,母子三個已經回家去了。
但矛盾的起點本來就不是那句“老寡婦”,所以也不會因為惠玲回去而告終。小張是決心跟盧灶順一家對峙到底了,他沒有和惠玲去補結婚證,盧灶順的孫子也遲遲上不了戶口,自然也就不能送出去上學。惠玲求不了丈夫,正在學壞的也不是他的兒子,只好每天去求盧灶順。也不知道是挨不過惠玲的哀求,還是怕長孫變成混混,盧灶順最終還是抗不過小張。
小張成為了名副其實的小張,再也不必為自己戴著盧姓卻講著一口水土不服的方言而感到羞恥。由于盧灶順對他的要求沒有一開始就表示配合,他也就不再遵守拜兩邊祖宗的約定,只答應讓盧灶順的孫子可以去拜祖。依然請耆老來作證人,他把下山虎老厝交還給盧灶順,一并付清幾年房租,按照市場價,一共八萬九千八百元,連湊個圓數的情面都不留。杰濤氣得當場一拳頭打碎了小張的半顆門牙。
小張從地上爬起來,吐掉了血水,瞪大眼睛說:“補一顆牙四百。”說著從桌上的錢里抽了四百,放進褲兜。
杰濤捏緊拳頭,揚手把桌上的錢全摔在小張胸口,叫道:“拿著,我把剩下的房錢全打掉!”
“打了手疼。”盧灶順拉住兒子,心灰意冷地說。
小張扯回衣角,不緊不慢地撫平了,才說:“那我就只拿四百,走了。”他故意往前走了兩步,把地上的錢踏了個遍才出去。
“自己撿走。”杰濤紅著眼睛吼道。小張卻已經下樓了。
“天上要滴下鳥屎,還有處說理啊?”盧灶順低低地說,“明天我去找惠玲,他要是不肯養,我們就把阿大的孩子要回來自己養。”
杰濤沒有聽清父親的話,依然憤憤不平,喘著粗氣,罵道:“這外省仔過來的時候,連條破棉被都沒有。現在就敢這樣?”
“老話說知面知龐,不知肚腹。他剛才沒還手,已經算客氣的了。”盧灶順嘆著氣,又說:“要是惠玲肯把阿弟送過來,你要是不肯養,我和你媽自己養。那間厝還得給他們,我和你媽死前,怎么也還能把孩子帶成人……”
“要不再找找,看有沒有整家人肯過繼給我們的?”杰濤打斷父親看破世事的感嘆,問道。
盧灶順搖了搖頭,說:“算了,把阿弟帶大好了。家奴無定主。雇來拜祖的,你能世代雇下去?大弟十六了,我們也別求十足了。”
把孩子領回來的想法一提出,很快盧灶順把大兒子的三個孩子都帶了回來。他們的戶口也不入小張那邊,暫時掛在杰濤戶下。灶順長孫的名字是費了功夫起的:五行缺木,豪字輩,取名盧木豪。后面的孩子沒有再看八字,木iAi1YU9iHQwVMozP7X2JNw==豪的弟弟就叫林豪,妹妹叫楚賢。錄入戶口的人卻偏偏把木豪的“木”字打錯了,成了“沐豪”。為此,盧灶順氣得差點砸了盧厝鎮派出所。
其實,要是換個人或者換個時間,“沐豪”也就“沐豪”了。盧厝鎮派出所經常出錯,盧厝鎮人并不在乎安名。比如,盧木豪的父輩,幾乎大半人的名字都帶著曉字,查了族譜卻并不是曉字輩,這只是當年的一種潮流。但究竟是從何興起這潮流,起名字的人都記不得了,也沒人去細問。盧厝鎮的每一個人到死后,都會按照輩序和生前品性重命名,把規范的名字刻入祠堂的神龕。生前的名字和政府登記的名字叫什么都不重要,只要順口就行。家里人稱呼,男孩親昵點的叫法是狗仔或者豬仔,更多的就叫大弟、二弟,按年紀編號;大女兒都叫大妹,二女兒都叫細妹,萬一還生了三女兒,要么就搶過二女兒的名字叫細妹,要么二女兒還叫細妹,三女兒叫尾妹,四姐妹以上的基本得叫招弟、來弟之類的了。家外的叫法也簡單,俗話說:“大頭好安名”,長什么樣就叫什么,頭大的叫大頭,發色淺的叫紅毛或者黃毛,皮膚黑的叫烏鬼,不會說話的叫阿啞,眼睛大的叫圓目,眼睛小的叫瞇目,胖的叫肥仔,瘦的叫菜脯……即便父母有慎重安名,平日里連自己都會忘記大名的存在。要是父母不講究,戶口本可能就登記成了大頭、烏鬼之類的名。在盧厝鎮更加普遍的,就是一家之主的名字共享給全家人。誰都沒問過灶順嫂叫什么名字。
但盧灶順的這個孫子是長孫,還是死了父親、母親改嫁了的長孫。盧灶順接過戶口本一看,反手就把本子摔在臺上,質問辦事員:“你眼睛被什么東西糊了是不是?先生算到我這孫子命中缺木,給起個好名字,你還把木抽走!”
“老伯,是名字打錯了嗎?”辦事員聽得有點懵,但見盧灶順氣白了臉,趕緊撿起來,翻開看了看,客氣地問。
盧灶順深吸一口氣,抓起桌上的筆,把戶口本搶過來,直接在“沐”字上重重地改了一個“木”,他手不停地抖,整個人像隨時要倒下去一樣,聲音卻十分洪亮:“要是有根木,他爸就不會淹死,老老小小就不會那么慘!”
辦事員忙道歉:“對不起。我們太疏忽,木和沐同音,沒檢查好。”
“叫所長來!”盧灶順叫道,“木和沐怎么是同音?沒檢查就把別人的名字亂寫?我這是算好的,五行缺木,救命用的,你一個沒檢查就給我抽走了?還加了水,你嫌浸死他爸一個還不夠是嗎?”
辦事員已經變了臉色,再次解釋道:“這倆字在拼音里是同音字,現在已經錄入電腦了,要不我幫你重做一本,這個改成曾用名,你看可以不?”
“誰曾用這名了?”盧灶順又搶過戶口本,這次直接沖大門外甩出去。
在盧灶順的客廳揚眉吐氣的那會兒,小張沒有預料到,他在盧厝鎮的生意會從那天開始,徹底萎縮下去。拋掉了姓氏,就沒有浪子回頭的余地。小張對抗盧灶順的那場斗爭,傷的是全盧厝鎮人的顏面,再沒有回轉的可能。盧厝的耆老們在小張不承認他們的權威時,只能任著他奚落。但小張的言行,很快穿過盧灶順家像紗布一樣透明的客廳。
小張的生意大半是承包大廠里的半成品枝頭,雇工人插上花朵,把成品絲花賣出去,從中獲利。他還沒從擊敗盧灶順的得意中平靜下心情,就一個枝頭都拿不到了。按照往常,每月逢十,不出中午,合作的大廠就會安排三輪車把花枝送到小張廠里。到了送貨的那天,小張等到晚上工人下夜班,還是沒有等到貨。小張已經習慣了盧厝的信用制度,對伙伴的失約有些氣憤。誰知,第二天一早,幾個老板親自上了小張家門,但不是來送貨,也不是解釋為什么沒送貨,而是來結賬。他們說以后都不生意來往了。小張追過去問,他們用潮汕人世世代代總結出來的經商俗諺回答他:“老實終久在,積惡無久耐。”他們還故意用方言說,難得多管閑事一回地幫盧灶順出了口氣。
小張求遍了從前的生意伙伴,但盧厝人早就硬下了心腸。小張對耆老們的輕蔑早傳遍了盧厝,傷的是全體盧厝人的臉面,辱了盧厝全族和祖先。小張在本地商人圈里處處碰壁,只能跟外地人來往。可是盧厝已經沒有多少外地老板了,再篩到絲花這行,就更少了。幾個月后,小張在盧厝賺到的錢再也不會繁殖,所有的經營都奄奄一息。還沒成為惠玲名副其實的丈夫時,他曾對盧灶順說“窮就窮養,富就富養”,為了自己的姓氏,他真得把孩子窮養了。盧厝人要毀掉一個外地人在盧厝的事業是那么容易,這是小張硬氣時完全沒有設想過的。
被逼無奈,小張只能回頭求盧灶順。他忍下屈辱,掛滿假笑,認了錯,表達了想要改回盧姓并且再不胡思亂想的決心。但盧灶順拒絕了他。小張又讓惠玲去求賢妹,請賢妹說個情。賢妹看著幾乎跟宗和嫂一樣蒼老的惠玲,答應了。可惜,她求不下這個情。她對公公說:“孩子還要吃穿讀書。”盧灶順大發一頓脾氣,罵賢妹昏頭,幫外人說話。
賢妹只好向惠玲道歉,偷偷給她點錢,更多的幫助也無能為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