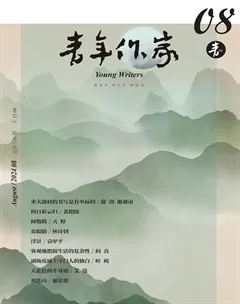客觀地把握生活的復雜性
在今日中國,潮汕地區幾乎成了一個文化特區。在這里,文化形態在時代風潮的沖擊下,幾乎完整地保留了自身的傳統。家族文化、生育文化、女性文化、拜神文化……傳統是如此地頑強,人們可以對它進行激烈的抨擊。但你如果真正體驗到了這種文化的感性狀態,又不得不對它表示贊嘆和尊重。我的學生袁甲平的這兩篇小說,就真實地向讀者呈現了這種生活原生態的復雜性。
《浮景》和《新婦》是兩篇相互照應的小說。《新婦》的主人公惠玲和《浮景》的主人公賢妹都是潮汕家庭里的新婦,也就是兒媳婦。惠玲是一個傳統潮汕女性,沒有受過高等教育,早婚多育,勤勞能干,任勞任怨。而賢妹是一個醫科大學畢業生,走出小鎮,見過世面以后,又半推半就地重新回到傳統新婦的人生軌道上來。
這兩個小說乍一看會以為寫的是很久以前的故事,但其實故事描述的就是當下的潮汕生活,也就是發生在大家普遍認為女性已經能夠自主選擇命運甚至掌握命運之后。因此,我們很容易用居高臨下的視角,以現代化程度更高的城市為范本,去審視潮汕地區的保守、落后、壓抑。這兩個小說中,族權、父權、夫權壓迫無處不在,儼然就是社會進步的逆流,潮汕好像是一個急需被解放的地區。但事實真是這樣的嗎?
從男女平權理論看,潮汕的性別文化肯定是讓人無法忍受的。潮汕婦女享譽海內外的溫婉賢惠、勤勞顧家的美好品質,在對抗性的女權視角下,統統都是要被解放的內容。哪怕像賢妹的母親這樣生活得很穩定甚至很有幸福感的女性,她也沒有人生選擇權,只能說她把人生的規范動作都做到位了,且運氣很不錯。女性在婚戀、生育、工作、家庭等等問題上,需要獲得與男性平等的權利。這是個權利問題,而不是個利弊選擇問題。潮汕的“男主外,女主內”,其實中國傳統社會都是如此,這種模式對絕大多數家庭而言是利益最大化的選擇。內和外,各占一半,女性本來就是“半邊天”,有什么可解放的呢?今天潮汕地區,尤其是潮汕農商家庭,他們依然堅持的家庭、家族觀念,從生存的角度看,不僅有其充分的合理性,且具有非常蓬勃的生命力。對于普通人而言,如果生活不安穩,則自由毫無意義,用自由交換生活的確定性的故事比比皆是。
那么,在文學中我們能不能允許這樣不“進步”的表達?能不能允許主人公選擇用部分自由交換人生的確定性、交換一個更穩定的生活?我非常推崇“貼地而行”的寫作方式,我的小說也都是“貼地而行”的。所謂“貼地而行”,就是生活是什么樣子,作者就按照生活本來的樣子去描寫記錄生活。只有貼著生活的地面來行走,才會行走得踏實,從而不會走偏向“形而上”。文學不是用來講道理的,人不能按照概念去生活,文學不能把主人公當作某種社會理想的大喇叭。說到底,文學無法也無意為社會問題提供解決方案,文學是用來觸動情感,直擊現實生命的痛點,所以文學作品中的主人公必須是具體而真實的人。
《新婦》的主人公惠玲是一個大家庭中的長媳。在傳統潮汕家庭中,女兒依然是沒有財產繼承權的,但長孫享有和兒子相同的繼承權。也就是說,長房能夠得到兩份遺產。繼承更多的家產,當然也要承擔更多責任。惠玲嫁進門后,精心持家,又很快生育了兩兒一女,并且還想繼續生育,是一個標準兒媳。如果不是丈夫在抗洪時犧牲,她會有一個安穩且確定的人生。丈夫突然去世后,盧灶順招了個外省打工人小張作為長子,也就是惠玲的丈夫。這種選擇是完全符合傳統規則的,是為了家族的完整和延續。惠玲當然不愿意。要注意的是,她恨這種安排并不是覺得自己有婚姻自由權,而是因為小張的外省打工人的身份讓她感覺受辱。她想要一走了之,甚至已經悄悄出走。但半天后她就回來了,甚至沒有耽誤大家準時吃飯。這個細節證明,惠玲非常清楚,她沒有經濟能力,不接受公公的安排,就只能帶著孩子改嫁,或者拋下孩子進入工廠,過一種無論如何也難以圓滿的生活。在認清處境后,惠玲毅然將自己的全部情感殺死,投入新家庭。作為個體生命而言,這種選擇是應該被理解,也應該被尊重的。
與惠玲相比,《浮景》的主人公賢妹是個現代知識女性。但這個形象是“不完美”的。這種不完美首先表現在她不是所謂“大女主”,始終沒有獨立的經濟能力,甚至在結婚后很快放棄了工作,回到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軌道上。這是父權對她的壓制。說到底,賢妹能夠接受高等教育,是因為父親允許她出去讀書,當父親要求她回家時,她即便不情愿,已經刻入骨子的順從也促使她沒有激烈抗議。也因為這樣的心理慣性,當她婚后面對種種壓抑,不僅行動上不堅決,內心也十分搖擺。在面對丈夫、公婆甚至父母種種不合理的要求時,她最大的態度只是冷漠,然后便是逆來順受。
這讓我們哀其不幸的時候,一定會怒其不爭。為什么不爭呢?我們能不能要求每一個平凡人都為理想的社會奮斗?賢妹是一個并不具備超凡能力的女性,且傳統文化在她的潛意識里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跡,這兩個因素讓她從一開始就顯得不堅決。比如父親讓她大學畢業后回來當小學數學老師,她是個醫學生,這個職業選擇很不理想。但從現實的層面講,賢妹自己并無能力找到一份滿意的工作且獨立在大城市生活下去,這讓她沒有辦法堅定反抗父親的要求。當然,我們也可以說有很多比她條件更差的人都在大城市里生活,她有什么不可以的?但這是另一個問題了,且是個非常個人的問題,月收入多少錢才能在大都市生活,這有什么標準答案呢。賢妹不情不愿地順從了父親的安排,就像作者所說的,重新回到了古老命運的河流。
前些年潮汕有一個新聞很有意思,一個外地媳婦在電視臺上哭訴嫁進門后婆婆天天要求她拖地,總共七八層樓,一千多平方。把家庭矛盾放到電視上說,讓那個婆婆非常生氣,但也非常困惑,她自己從七八歲開始幫母親拖地,也當了幾十年新婦,天天如此,從白灰地到紅磚到水磨石再到瓷磚,房子越來越大,地面越鋪越好,有那么大的地可拖難道不是最幸福的事嗎?據統計,潮汕地區的離婚率只有萬分之五,居全國最低。大家熟悉的潮汕故事里有潮商、宗族、祭祀等具有鮮明特色的元素,某種程度上說,這些元素其實無不指向壓抑。在巨大的生存、發展、文化壓力面前,每個人都得交出自我。
比如,造成賢妹痛苦的“罪魁禍首”杰濤,他作為一個男性,并沒有獲得更大的自由。杰濤是家中的小兒子,在族權、父權邏輯下,長子要負擔起全部家族興衰責任,小兒子則不會被重點培養。杰濤被父母溺愛,很大程度是因為他不被寄予希望。結婚以前,杰濤在哥哥廠里幫忙,結婚后,他想自立門戶,但屢屢失敗。杰濤遇到生意上的挫折,大哥、父親都沒有想指導他,而只是讓他安分在家呆著,繼續給哥哥幫忙。生活在父親、兄長的羽翼下,是小兒子的福分,也是作為小兒子的本分。而杰濤和賢妹的關系惡化,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杰濤始終沒有在賢妹這里得到作為丈夫的心理滿足。實在過不下去了,杰濤可以離婚嗎?他搬出家里,耍賴,惹禍,甚至有了外遇以后,杰濤也沒有爭取離婚。這一方面是因為他品格卑劣,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深知背叛文化規則的代價。
在傳統社會中,很多時候一個人的名聲比能力更重要,成也名聲,敗也名聲。《新婦》里的外省人小張想要突破這個規律,以為自己生意做起來了就可以背叛文化規則,結果整個盧厝的人都不跟他生意來往了,當然也就可以想到,這一家人一定已經被排除在當地的生活圈之外。盧厝的文化規則一方面對人有強烈的約束和壓迫,另一方面也是一個強大的保護。越過了這個規則,就不再受規則保護。從這個角度看,《新婦》和《浮景》就不僅是女性題材的小說,而是關于潮汕生存文化的小說。在這兩個小說里,作者沒有讓我們看到女性運動、女性解放,而是看到生存規則、文化規則對人的強大的改造能力。而客觀來說,古老的潮汕文化規則在當代依然有效,依然有著頑強的生命力,其復雜的價值狀態,在這兩篇小說中得到了真實的呈現。
同時,我也很高興地看到,袁甲平已經具有了理解并描述生活復雜性的力量。在她的筆下,生活是一種客觀狀態,而不是一種主觀意愿。這是一個青年作家獲得寫作成長空間的必要潛能。
【作者簡介】閻真,著名作家;畢業于北京大學,現為中南大學中文系教授;著有長篇小說《滄浪之水》《曾在天涯》《因為女人》《活著之上》《如何是好》,理論著作《小說藝術講稿》等多部;現居長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