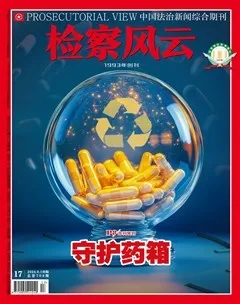直播間里的銀發(fā)經(jīng)濟

2024年1月17日,我國國家統(tǒng)計局發(fā)布了最新人口數(shù)據(jù)。從年齡構(gòu)成看,60歲及以上人口數(shù)為29697萬人,占全國人口數(shù)的21.1%,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數(shù)為21676萬人,占全國人口數(shù)的15.4%。根據(jù)聯(lián)合國關(guān)于老齡化的劃分標準,我國已正式步入中度老齡社會。
在這一社會背景下,老年產(chǎn)業(yè)發(fā)展迅猛,“銀發(fā)經(jīng)濟”一詞開始步入大眾視野。顧名思義,“銀發(fā)經(jīng)濟”是指以老年人為目標客戶,提供產(chǎn)品、服務(wù)等一系列經(jīng)濟活動的總和。大到城市內(nèi)新開的老年食堂,小到樓梯間里增設(shè)的助老扶手,都是“銀發(fā)經(jīng)濟”的體現(xiàn)。
線下如此,線上的老年生活也熱火朝天。隨著智能軟、硬件的適老化升級,網(wǎng)絡(luò)直播從年輕人的“心頭愛”,一躍成為了老人們的“新寵”。
不可忽視的流量
根據(jù)Quest Mobile數(shù)據(jù)顯示,截至2023年9月,銀發(fā)人群網(wǎng)絡(luò)用戶規(guī)模已達3.25億,全網(wǎng)占比26.5%。隨著銀發(fā)人群觸網(wǎng)率的提高,快手、抖音兩大短視頻平臺高居銀發(fā)人群最愛使用App的榜首,人均單日使用時長分別達到2.04小時和1.87小時。短視頻平臺因操作便捷,有效降低了銀發(fā)人群的使用門檻;其豐富的內(nèi)容和智能的算法,能夠快速為銀發(fā)人群提供他們可能感興趣的內(nèi)容。從新聞時事到熱播劇集,短視頻平臺成為銀發(fā)一族與社會連接的新紐帶。
快手、抖音兩大平臺除了通過海量內(nèi)容和現(xiàn)存流量進行變現(xiàn)以外,直播電商也是重要的盈利渠道之一。因其互動性強、形式多樣的特點成功吸引到了銀發(fā)人群的眼球。屏幕后的長輩們逐漸成為平臺直播流量的一大組成部分。在快手、抖音這兩大短視頻平臺的觀看直播用戶中,銀發(fā)人群占比高達21.2%和23%,其中51歲以上用戶占比19%左右,且近三成用戶月度線上消費能力超過2000元。結(jié)合這兩組數(shù)據(jù)和未來直播市場多元化的發(fā)展態(tài)勢來看,老人們的購買力不容小覷。
有需求就有市場。為了瞄準基數(shù)大、意愿強的銀發(fā)人群,直播電商產(chǎn)業(yè)為銀發(fā)一族因人制宜選品、投其所好創(chuàng)作。與年輕人刷到的直播間不同,面向老年消費者的直播間成為了業(yè)內(nèi)另辟蹊徑的存在。在一些頭部平臺,甚至創(chuàng)下了“直播首秀帶貨近百萬”“單月完成上億銷售額”的業(yè)界“神話”。根據(jù)經(jīng)濟觀察報的報道,有從業(yè)者表示一個定位中高端、主要面向老年人的百萬粉絲賬號,日常直播帶貨產(chǎn)品的抽成比例在10%—25%之間,短視頻廣告費則大約在一條10萬元。屏幕前“買買買”的老人成了屏幕后商家和創(chuàng)作者的“金主”,更是這條新開辟賽道內(nèi)不可忽視的流量“大軍”。
快速變現(xiàn)的密碼
銀發(fā)一族除了基數(shù)大、購買力強這兩個特點外,用戶黏度也十分驚人。如何讓一個老人成為直播間的死忠粉,成為了主播及其背后團隊的創(chuàng)作目標。
首先是選品方向,諸如吃、穿、用這些以生活場景為核心的產(chǎn)品大類仍然是選品的基礎(chǔ)。食物品類中,酒類產(chǎn)品在一眾日常吃食中占有一席之地,與其搭配銷售的衍生產(chǎn)品銷量也隨之上升;服裝品類中,“爸爸必備商務(wù)裝”“專為媽媽設(shè)計”“輕便防滑老人鞋”這類屬性明顯的產(chǎn)品長居熱門,部分中老年服裝的老品牌也因直播走紅而煥發(fā)新生;日用品類中,注重便利和解決老年痛點的低單價小物受到廣泛喜愛,成為直播間的引流熱品。在老年人中熱度居高不下的養(yǎng)生保健產(chǎn)品、文玩等也有單獨的直播賽道。
再來看直播形式,年輕人在直播中較為敏感的品牌效應(yīng)、優(yōu)惠機制、湊單滿減等并不是主播努力的方向。銀發(fā)群體進入直播間大部分是被主播發(fā)布的短視頻內(nèi)容吸引,這類內(nèi)容并不追求短平快,而是更追求“感情牌”。比如能夠引發(fā)“回憶殺”的復(fù)古生活再現(xiàn)、簡單質(zhì)樸的田野生活記錄;能夠描繪出理想老年生活的優(yōu)雅奶奶、“老克勒”爺爺;注重強互動的家庭故事等。
情懷之外,互動感和親和力也是吸引銀發(fā)一族的“秘密武器”。當(dāng)年輕人在“家人們”的號召下添加購物車時,家中的長輩可能也正迷失在“遠方的爸爸媽媽們”這樣的呼喊中。殊不知,如此“親切”背后也許暗藏著陷阱。
在2023年的央視3·15晚會上,曝光了一批直播賬號,賬號背后的主播都有一段令人唏噓的“身世”故事,比如身患重病的孤兒帶貨維生、從小被遺棄的殘疾人坐輪椅直播。這些主播通過虛構(gòu)的“苦情戲”博得銀發(fā)人群的信任與同情后,便開始在直播間帶貨,嘴上一口一個“爸爸媽媽”“叔叔阿姨”叫得親熱,手上也不忘推銷自己賣的“神藥”,號稱有“有病治病,沒病防病”的效果。直播間的互動熱火朝天,主播們面帶笑容、語氣親切地回復(fù)著觀眾的問題,銀發(fā)族們在社交和娛樂上的空缺仿佛被這樣的直播所填補,直播間的銷量也只增不減。然而,這些主播的病痛殘疾都是演技,狗血劇情有專人編造,直播間賣的“神藥”也只是一般的保健品或食品,并無奇效。除了這批賬號被曝光封禁,背后的賬號運營團隊與貨品生產(chǎn)所構(gòu)成的供應(yīng)鏈也終于浮出水面,水面之下深受直播間套路之苦的老年人們才被看見,不少年輕人表示家中老人“只信主播,不信親人”,自己也無可奈何。現(xiàn)在這些被曝光的賬號雖已封禁,平臺也給出了相應(yīng)提示,但搜索關(guān)鍵詞,仍能夠發(fā)現(xiàn)有類似的賬號還在活躍,可見,平臺對此類賬號的檢測與監(jiān)督仍需進一步加強。
“反向收割”的主播
除了在直播間當(dāng)觀眾,也有不少銀發(fā)人群選擇成為自媒體創(chuàng)作者,比如通過直播平臺展示自身才藝、分享生活經(jīng)驗,甚至進行直播帶貨。這不僅豐富了老人們的晚年生活,也為老年人的社交圈和日常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比如用戶名為“我是田姥姥”的抖音用戶,因家中小輩拍攝姥姥搞笑日常而走紅網(wǎng)絡(luò),田姥姥直播首秀銷售額就高達150萬元。
見有利可圖,不法分子便動起了歪腦筋。如果在深夜打開直播平臺,會發(fā)現(xiàn)有些直播間內(nèi)只有一位老人孤零零地坐在鏡頭前,背景是破敗的小屋,手上拿著各式百貨,口中喃喃“謝謝大家”,處境之艱難不言而喻。不少觀眾被吸引進入直播間瀏覽,并出于同情進行打賞和下單。據(jù)調(diào)查,這類“老人主播”背后,實際上存在著專業(yè)團隊進行賬號運作,他們通過設(shè)置虛假的身世背景,利用老年人的弱勢地位,博得觀眾同情進行利益獲取。
有B站創(chuàng)作者曾對此現(xiàn)象進行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此類“老人主播”分為兩類,一類是對直播事業(yè)知之甚少,團隊專門找來的真正困難老人,他們得到的信息就是凌晨坐在鏡頭前說謝謝,網(wǎng)上的人就會買東西,團隊的人就會給自己“工錢”;另一類則是完全虛構(gòu),根據(jù)劇本進行“賣慘”的演員。為躲避平臺監(jiān)管,團隊手上往往不止一個賬號,還會同時“簽約”多位老人,并通過多個賬號和不同IP地址來達到“一人多播”的目的,從而進一步擴大收益。
查閱數(shù)據(jù)會發(fā)現(xiàn),這類賬號的受眾是20—30歲左右的年輕女性,她們收看直播的時間多為夜晚休息時間,且具有較強的共情能力和經(jīng)濟能力,因此在深夜看到困難老人熬夜直播時更容易因為同情而付出金錢。甚至其中大部分觀眾早已深知這種套路,卻依舊愿意打賞付費,只為了這些老人能夠早些休息。老年人在這樣的直播間里,逐漸成了“反向收割”年輕人的“帶貨主播”。
這些行為的滋生是因為現(xiàn)行的網(wǎng)絡(luò)直播監(jiān)管體系尚未完全覆蓋老年人直播帶貨領(lǐng)域。網(wǎng)絡(luò)平臺應(yīng)進一步加強對直播內(nèi)容的審核,對于涉嫌欺詐和不當(dāng)獲利的行為進行嚴厲打擊;作為社會公眾,也應(yīng)提高對于網(wǎng)絡(luò)直播帶貨的辨識能力,避免因同情而將錢財送入有心之人的口袋中。同時針對沉迷直播間的老年人,也應(yīng)聯(lián)動社區(qū)居委和家庭成員一同對老年人的網(wǎng)絡(luò)知識進行科普,提高他們的防范意識。
在“銀發(fā)經(jīng)濟”迅猛發(fā)展的當(dāng)下,老年人直播帶貨作為一種新興現(xiàn)象,既有積極的一面,也存在著不容忽視的問題。無論是老人還是年輕人,平臺還是觀眾,都應(yīng)當(dāng)從法治的角度出發(fā),注重對這一現(xiàn)象的監(jiān)管和引導(dǎo),保護老年人的合法權(quán)益,維護社會公共利益,促進網(wǎng)絡(luò)直播帶貨行業(yè)的健康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