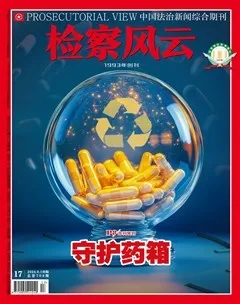傳統中國法律激勵的歷史鏡鑒
法的作用是法理學中的一項基礎命題。一般認為,規范作用是法的主要作用之一,它具體又可以分為指引、評價、教育等多種作用類型,對人類社會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長期以來,法律懲戒是人們感知最深的規范作用,而與之相對應的法律激勵,則容易受到忽視。其實在中國歷史演進過程中,法律激勵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這是一筆豐厚的歷史遺產,可以為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以及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建設,提供豐沛的智慧源泉和歷史鏡鑒。
社會治理與法律激勵
早在先秦時期,中國人就意識到了法律激勵對富國強兵的重要意義,商鞅變法是這一時期最成功的范例。獎勵耕戰是商鞅變法的核心內容,它運用法律激勵的方式極大地提高了秦國的生產力和秦軍的戰斗力。在社會治理層面,法律激勵的作用同樣巨大。比如見義勇為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俠義精神備受推崇,是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中的一大亮點。實際上這一法律文化的形成,與長期以來的法律激勵密切相關。
以《唐律疏議》為例,其用較多的篇幅來對見義勇為等行為進行釋義,有助于良好社會風氣的形成。在《唐律疏議》中,專設“捕亡律”篇來規范抓捕罪犯等事宜。見義勇為的行為一般發生在暴力犯罪案件中,抓捕是這類案件的核心環節,故而見義勇為的相關規定主要分布在此篇中。在“捕亡律”的開篇,唐朝立法者首先明確國家執法機關的法律責任,要求其在執行抓捕任務時,做到盡職盡責。該篇“將吏捕罪人逗留不行”條規定:“諸罪人逃亡,將吏已受使追捕,而不行及逗留,謂故方便之者。雖行,與亡者相遇,人仗足敵,不斗而退者,各減罪人罪一等;斗而退者,減二等。即人仗不敵,不斗而退者,減三等;斗而退者,不坐。”簡而言之,執法人員不積極抓捕,會依情節輕重受到各種處罰。
權責相應是《唐律疏議》高超立法水平的一個重要體現,立法者對執法人員提出了嚴格要求,同時也為他們盡責執法免去后顧之憂。在上一條款之后,便是“罪人持杖拒捕”條,該條規定“諸捕罪人而罪人持杖拒捍,其捕者格殺之及走逐而殺,若迫窘而自殺者,皆勿論”。當然,立法者也考慮到了過度執法的問題,對此也有詳細規定。在明確了執法人員的責任后,緊接著就是有關見義勇為的規定。“道路行人不助捕罪人”條規定:“諸追捕罪人而力不能制,告道路行人,其行人力能助之而不助者,杖八十;勢不得助者,勿論。勢不得助者,謂隔險難及馳驛之類。”在該條的“疏議”中,立法者特別對“勢不得助”“之類”等法律術語進行了立法解釋。“‘勢不得助’謂隔川谷、垣籬、塹柵之類,不可踰越過者及馳驛之類。稱‘之類’者,官有急事,及私家救疾赴哀,情事急速,亦各無罪。”由此可見,法律對道路行人見義勇為的要求并不嚴苛,體現出法律的人性之美。
以上是國家執法人員在場情況下的見義勇為。考慮到此類案件一般情況緊急,案發時通常沒有執法人員在場,這是見義勇為發揮作用的最重要場域,立法者對此作了詳細規制。“被毆擊奸盜捕法”條規定:“諸被人毆擊折傷以上,若盜及強奸,雖傍人皆得捕系,以送官司。捕格法,準上條。”也就是說,有毆打人致折傷、強盜、強奸等嚴重暴力犯罪行為時,即便是沒有親屬血緣關系的旁人,也應立即捕捉,將嫌犯送交官府。抓捕過程中的權責問題,參照上條國家執法人員的規定進行。
與此同時,法律還對鄰里之間的見義勇為作了規定。“諸鄰里被強盜及殺人,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聞而不救助者,減一等;力勢不能赴救者,速告隨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論。”此外,諸如發生火災等危險情形,唐律也要求公眾要及時報告和救援,善盡幫扶義務。《唐律疏議》“見火起不告救”條規定:“諸見火起,應告不告,應救不救,減失火罪二等。謂從本失罪減。其守衛宮殿、倉庫及掌囚者,皆不得離所守救火,違者杖一百。”
律和令是唐代的主要法律形式,律側重負面懲罰,令注重正面勸導。唐代立法者善用法律激勵,在《唐令》中規定了要對見義勇為者給予經濟方面的嘉獎。《唐令·捕亡令》規定:“諸糾捉盜賊者,所征倍贓,皆賞糾捉之人。家貧無財可征及依法不合征信贓者,并計得正贓,準五分與二分,賞糾捉人。若正贓費盡者,官出一分,以賞捉人。即官人非因檢校而別糾捉,并共盜及知情主人首告者,亦依賞例。”這一規定邏輯清晰,思路縝密,且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將法律激勵的功能發揮得淋漓盡致。
到了明清時期,對見義勇為等行為的法律激勵得到進一步鞏固。《大明令》規定:“凡常人捕獲強盜一名、竊賊二名,各賞銀二十兩;強盜五名以上,竊盜十名以上,各與一官。名數不及,折算賞銀。”《大清律例》規定:“如鄰佑、或常人,或事主家人拿獲強盜一名者,官給賞銀二十兩,多者照數給賞。”對于因見義勇為而受傷者,法律也給予妥善照顧,規定“受傷者移送兵部,驗明等第,照另戶及家仆軍傷例,將無主馬匹等物變價給賞;其在外者,以各州縣審結無主贓物變給”。正是在上述法律制度的保障和激勵下,歷史上涌現出許多可歌可泣的見義勇為故事,使見義勇為逐漸成為一種精神與文化,在中華大地上代代相傳。
科技發展與法律激勵
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中華科技文化獨樹一幟,在世界文明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以宋朝為例,陳寅恪先生言:“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宋朝經濟發達,人文薈萃,為科技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環境基礎。一部《夢溪筆談》,堪稱中國古代科技的百科全書。宋朝在物理、化學、天文、工程、數學、農學等科技領域成就非凡。在這些輝煌的科技成就背后,離不開法律激勵的強大推動。
為了鼓勵科技發展,宋朝統治者出臺了大量獎勵科技的法律政策,獎勵方式豐富多元,獎勵對象包羅萬千。對貢獻巨大者,獎勵不但及于自身,還能惠及子孫后代。在獎勵方式方面,既有精神獎勵,包括降詔褒獎、樹碑立傳、賜姓、賜名、賜詩、賜文,也有各種豐富的物質獎勵。比如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京西提點刑獄官、知河陽高紳組織治理黃河水患,“以棄石累之,計省工巨萬,而又堅固”,得到了朝廷的降旨褒獎。同樣是在宋真宗時期,東京汴梁通往江南的運河要經過5個堤堰,結果“糧載煩于剝卸,民力疲于牽挽,官司艦舟由此速壞”。天禧三年(1019)朝廷派人開通揚州古河,自此“漕船無阻,公私大稱其便”,朝廷下旨對工程人員進行褒獎。江淮發運使賈宗覺得這種獎勵力度不夠,上書宋真宗請求皇帝欽賜御制文褒獎,得到了皇帝的準許。
宋朝在天文歷法方面頗有建樹,最高統治者對此也極為重視。河南洛陽人王處訥(915—982)是當時著名的天文歷法專家,周世宗時期,舊歷出現差錯,皇帝命王處訥制定新歷。王處訥尚未完成,樞密使王樸率先完成了《欽天歷》獻給朝廷,受到眾人好評。唯有王處訥看出了這部歷法存在的問題,他私下告訴王樸道,“此歷且可用,不久即差矣”,并且指出了其中的問題,王樸聽罷深以為然。宋朝建立后,朝廷發現了《欽天歷》存在謬誤,下詔王處訥別造新歷。三年之后,王處訥完成了六卷新歷,宋太祖趙匡胤親自為之作序,命名為《應天歷》,此舉可見這位馬上皇帝對天文歷法事業的重視。由于在天文歷法方面的杰出貢獻,王處訥的官職不斷升遷,最終官拜司天監,成為全國天文歷法方面的最高主管。
在軍事方面,宋朝統治者極為重視軍事科技的發展,投入巨大的資源鼓勵軍事技術革新,用來彌補自身騎兵不足的缺憾。在這一背景下,火器、弓箭等克制騎兵的遠程武器得到了長足發展。宋太祖開寶年間,兵部令史馮繼升等發明了火箭法,試驗取得了成功,趙匡胤下詔賜予衣物、束帛。神衛水軍隊長唐福獻制造了火箭、火球、火蒺藜等裝備,也得到了重金獎賞。諸如此類的獎勵還有許多,不勝枚舉。
總體而言,法的激勵功能為中國古代的社會治理和科技發展提供了強大驅動力。但是從客觀角度評價,古人運用法律激勵,可謂有得有失。在社會治理方面比較成功,其立法智慧可以為今天相關領域的立法提供重要參考。然而在科學技術領域,盡管古人也運用了法律的激勵功能,但這些法律大多采用詔令的形式,而非進入法典之中,缺乏體系化和穩定性,未能使法律對科技發展的激勵發揮至最大效用,值得后人深思。
編輯:薛華 icexue032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