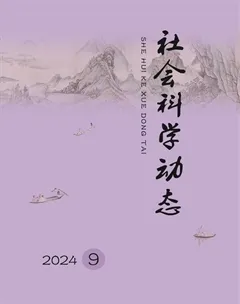深邃與恢宏:荊楚文化的內涵、成就與特征
摘要:《荊楚文化史》以其在荊楚文化研究與闡釋、展示與表達上的突出貢獻與顯著特色呈現出思想之深邃、氣度之恢宏。荊楚文化的核心概念與基本內涵得以闡明,近萬年的歷史發展脈絡和演進軌跡得到明晰勾勒,其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上的地位和影響得到有力證實。荊楚思想與學術群星璀璨、文學與藝術色彩斑斕、科學與技術承前啟后、宗教與風俗別具一格,其重大成就與主要特征得以生動展現。荊楚文化研究的系列史料和最新成果得到充分利用,湖北地區在各時代最為突出的歷史事相集中呈現,文化發展的內在演變規律及其與其他社會因素的互動關聯被深入揭示,提供了區域文化的研究標本與表達范式。
關鍵詞:荊楚文化;荊楚科學與技術;宗教與風俗;表達范式
中圖分類號:G127;K901.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5982(2024)09-0047-08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荊楚文化是悠久的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上地位舉足輕重。”在波瀾壯闊的中華文化長卷中,荊楚文化傲然卓立、明艷多姿。在近萬年的發展歷程中荊楚文化有哪些豐富內涵和突出成就,經歷了怎樣的發展演進軌跡,具有什么樣的獨特稟賦和文化特質,與中華文明的其他區域文化如何交流互動,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上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和影響如何體現?
劉玉堂教授任主編的《荊楚文化史》叢書由湖北教育出版社重磅推出,全面回答了前述問題,將體大思精、源遠流長的荊楚文化史卷呈于案前,其紛華照眼、搖曳多姿令人如入寶山、目不暇接。這部縱跨遠古直至近代的六卷本地域文化通史巨著,分為史前卷、先秦卷、秦漢魏晉南北朝卷、隋唐宋元卷、明清卷和近代卷,由宋海超、尹弘兵、葉植、吳成國、任放、張繼才等學者編纂完成。荊楚文化的時空界定、內容內涵、演進軌跡、主要特征以及地位影響等核心概念與基本內涵得以闡明,從文明初曙照耀荊楚大地以來近萬年的厚重歷史畫卷得到充分展現,數千年來荊楚人民創造的驚采艷絕的非凡文化成就突出呈現,數代學人40年來研究荊楚文化的豐碩成果薈萃一編,荊楚文化的豐厚內涵、獨特稟賦、杰出創造、內在動因、生成邏輯、深遠影響等重大命題,得到了全面系統、史料充分、學理清晰、研討深入、重點突出、表述生動的闡釋,充分闡明并有力證實了荊楚文化作為悠久的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上地位舉足輕重。
一、荊楚文化的核心概念與基本內涵
何謂“荊楚”?荊楚文化史的范疇是什么?《總序》開章明義,“荊楚”的概念始于先秦,荊、楚二者互稱并舉,有族類名和地域名之分,即楚民族和湖北地域。荊楚文化的空間范圍大致與今湖北行政區劃相當,時間范圍是從遠古到當代,則荊楚文化史研究的主要范疇是從遠古至當下的湖北文化誕生、發展和演變的歷史。
天賜荊楚,山環水繞、溫暖濕潤造就了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地處中國地理單元的東西之中、南北之間,壯侗、苗瑤、緬藏、漢藏語族構成了在荊楚民族東、南、西、北四個方位上的民族文化氛圍,自然環境、區域位置、歷史氛圍為荊楚地域接納四面八方的文化信息提供了優越條件,構成了其外求諸人以博采眾長、內求諸己而獨創一格的文化稟賦。
荊楚文化近萬年的歷史發展脈絡和演進軌跡得到視野宏闊的梳理和流變清晰的勾勒,荊楚文化的基本內涵和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上的定位有了簡明恰當的提煉和精當扼要的闡述。
湖北境內已發現200多處舊石器時代遺址,反映出舊石器早、中、晚時期以及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較為完整和清晰的發展序列,表明荊楚地區是中國古人類的發祥地之一,對于研究中國古人類的起源及演化具有重要意義。新石器時代荊楚地區的文化遺址近3000處,文化譜系相對完整,年代最早的是距今8000年前的城背溪文化,繼之大溪文化興起,而后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相繼勃興:屈家嶺文化興起,打破了荊楚境內四大文化主體并立格局,實現了文化統一,使長江中游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達到空前繁榮,開啟了長江中游地區史前文明的新歷程;繼屈家嶺文化而起的石家河文化代表了長江中游地區史前文化發展的最高水平,對探討多元一體民族國家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
夏、商、西周三代,中原王朝大力經營南方,將中原文化傳播到長江中游。商末羋姓祝融后裔離開中原進入楚地,西周初年羋姓首領熊繹被封為諸侯,始建楚國于楚蠻之地。東周時期,強大起來的楚國盡有江漢之地,并將長江中游地區的族群整合為統一的楚民族,創造了高度發達、震古爍今的楚文化,造就了荊楚文化發展的第二個高峰。楚國、楚民族、楚文化的發展,使原來華夏文明的邊緣地帶發展成為華夏文明的核心地帶之一,初步形成了以長江為軸心的整體性的南方華夏文化,奠定了中華文化南方與北方、黃河與長江的二元格局。
秦王掃六合,荊楚地區慘遭洗劫,漢初楚族遷徙關中,漢武帝獨尊儒術地方文化發展空間受到阻遏,秦至西漢前期荊楚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陷入百余年的困頓期。至東漢光武帝軍功集團勃興,帶動了南陽盆地文化學術階層的崛起,江夏儒學異軍突起,儒學宗師馬融在荊州治經講學,文化學術在楚國故地核心區煥發生機。漢末荊州成為全國學術文化教育中心,荊州學術在今文經學向魏晉古文經學、玄學轉變中承上啟下,荊州學派士人分流入曹魏、蜀漢政權,對政局產生了重要影響。
魏晉南北朝時期荊楚地區先后處于孫吳、東晉和南朝宋、齊、梁、陳統治之下。東吳在荊楚地區沿長江建立軍事據點,推動了一批重要城邑的興起。由于文學作品《三國演義》和關帝信仰的傳播風行,使荊楚地區成為三國歷史文化資源不竭的富礦;東晉南渡,荊楚地區人口總數增加、勞動力資源充實,諸多鄉聚城邑得以設置,北方移民尤其是南遷大族極大推進了荊楚文化開發創造。
隋唐政治格局統一穩定、經濟重心南移,得中獨厚的區位使荊楚文化在南北、東西碰撞中蓬勃發展;宋元之世中國由南北分裂至天下一統,荊楚文化在曲折中生生不已。荊楚大地孕育了一批具有全國性、歷史性影響的文化人物,如天臺宗創始人智顗、山水田園詩派的開創者孟浩然、創立東山法門的禪宗四祖道信和五祖弘忍、開創中國茶學與茶道的陸羽、書畫名家米芾、推動理學北傳的趙復。荊楚山水也滋養了諸多載入史冊、光耀千載的寓居客,如視湖北為第二故鄉的李白、在黃州脫胎換骨的蘇軾。
明清時期湖北地區可列為全國的文化發達區之一,也是數千年荊楚文化發展的高潮期之一,荊楚文化在眾多方面構成中國文化史的“重頭戲”。“惟楚有才”,思想領域“嘉魚二李”“黃安三耿”卓然成家,長期生活在湖北的思想家李贄如彗星閃耀夜空,漢陽熊伯龍的《無何集》是我國古代無神論思想的總結之作;文學領域“公安三袁和”竟陵鐘惺、譚元春獨樹一幟引領文學風尚;戲曲領域諸多曲藝形式和聲腔類型各擅勝場,民間戲曲演繹活動繁盛,造就了在全國腔種占有重要地位的漢調,催生了獨步一時的京劇。
近代是中國從傳統向現代過渡的時代,處在沿海與內陸過渡地帶的湖北在各個文化領域都呈現出新舊嬗變、東西雜糅、沖突融合的特征,在整體的中華文化變遷中起著傳播橋梁與輻射紐帶的作用,風云激蕩的社會思潮、革舊立新的教育、融匯中西的文學、推陳出新的藝術、異彩紛呈的新聞出版、風格多樣的建筑等無不在繼往中迎開來之新風,在破舊中尋變革之生機,“締造多從江漢起”的“湖北新政”“此復神州第一功”辛亥武昌首義在近代社會經濟轉型、政治制度變革中開風氣之先。
二、荊楚文化的重大成就與主要特征
(一)荊楚思想與學術群星璀璨
先秦楚國思想與學術一方面吸收中原文化精髓,一方面融合本土蠻夷文化營養,春秋至戰國晚期,接納諸子百家學說,成為南方的思想學術交流中心,其中道家學派發源于楚國并得以壯大,是荊楚地區對中華文化思想學術的突出貢獻。生活在楚屬國陳國的道家哲學創始人老子著述《道德經》,賦予“道”形而上學的意義,以之為世界萬物的本原,建構起陰陽對立的宇宙生成觀、“反者道之動”的事物發展觀、無為而治的政治倫理觀、少私寡欲與全生避害的人生觀;莊子繼承“道”的哲學思想,發展了“忘我”“物化”“逍遙”的自由觀,提出養生保真的人生觀和樂死而生的生死觀,也主張政治的無為而治。“作為南方文化表率的楚文化,其哲學否定性的特征,于傳說的鬻子哲學中已見其濫觴,于老子哲學中自成其系統。”(1)
漢代淮南王劉安組織門客編輯百科全書《淮南鴻烈》。東漢漢安帝時“蔡陽三劉”劉珍、劉騊駼、劉毅參與《東觀漢記》續修,使該書初步具備了國史規模。漢末劉表大興文教,創建荊州官學,獎掖學術,招攬人才,搜羅整理文化典籍,使荊州成為全國的學術文化教育中心,催生了荊州學派。荊州學術在從漢代今文經學向魏晉古文經學、玄學轉變中承上啟下,魏晉玄學的奠基人物王弼受荊州學派浸染熏陶,是荊楚文化影響中國學術發展走向的標志性事件。
東晉南北朝時期習鑿齒著《漢晉春秋》,主張以蜀漢為正統、以晉繼漢、崇漢抑魏的史觀,他的史學思想和該書的史學價值備受后世推崇。荊楚地區優越的地理環境、豐富物產和杰出人物,催生了數十種內容豐富多彩的地志,歷史學、地志學、佛學、玄學等都取得了突出成就。
楚故地思想家皮日休面對晚唐腐朽黑暗、民生凋敝的社會現實,強烈推崇孔子“仁愛”和孟子“民本”思想;北宋著名諫官、江陵人唐介坦率耿直、嫉惡如仇之名載于史冊,可為中國古代“直臣”、君子人格的代表;“程門四先生”之一的楊時仕荊南府教授,在荊州傳揚洛學、推廣師說,為存續洛學薪火、引領荊楚學術作出貢獻;南宋哲學家、永嘉學派創始人之一艮齋先生薛季宣任武昌縣令,推行多項善政;著名政治家張孝祥任荊南知府,重建金堤、萬盈倉,“蒞政揚聲”、治荊有方;“南軒先生”張栻任江陵知府,肅貪腐、崇先賢、正禮俗,凸顯了理學家戒慎憂懼、奮發進取的理性精神;宋元之際的著名經學家“江漢先生”趙復將程朱理學傳至北方,為北方儒士帶來了新的理學思想洗禮,促進了南北學術思想交流。
唐代學者江夏人李善的《文選注》是唐代文選學的集大成,該書征引了近1600種文獻資料,在注音、釋事、釋義、校勘等方面取得了輝煌成就;天門人陸羽系統總結唐代及以前有關茶葉與飲茶的科學知識和實踐經驗撰成《茶經》,該著不僅是世界上第一本茶文化百科全書,而且以精行儉德、三教融合、天人和諧的思想為中國茶道思想奠基;晚唐志怪小說家段成式晚年閑居襄陽,他編撰的《酉陽雜殂》大量記錄了唐代荊楚地方的風土人情,其內容博雜,史料豐富;進士余知古《渚宮舊事》博采各類典籍,記載荊楚地區上起鬻熊、下迄唐末兩千年來的人物事跡、掌故傳說,是研究古代湖北地方史志的重要文獻;五代宋初學者孫光憲在江陵撰寫了史料筆記小說《北夢瑣言》,其資料采自唐五代史籍和實錄,是保存晚唐五代史籍最重要的筆記之一;“安陸二宋”之“紅杏尚書”宋祁、“孤風雅操”宋庠皆有文名,宋祁編修《新唐書》列傳部分筆意俱佳;安陸王得臣著筆記體史學著作《麈史》,是研究北宋典章制度和社會風俗的重要史料;襄陽魏泰采唐人傳奇手法寫志怪小說,《括異志》開志怪小說新局。
程朱理學創始人程顥、程頤兄弟在黃陂度過少年時期,“魯臺望道”的典故反映了他們學術思想的起點;荊門沙洋人、著名理學家、易學家“漢上先生”朱震精研《周易》,兼采象數、圖書與義理等方法治易,獨創了綜包并舉的易學體系;經學家胡安國隱居荊門漳水之濱二十余年,他的春秋學繼承程頤將《春秋》納入理學范疇,而又多有“微言大義”“理欲之辨”的引申發揮;哲學家陸九淵治荊門軍一年余而卒于任上,荊門民眾感其德政,亦以象山心學的巨大精神財富相激勵;江陵經學家項安世《周易玩辭》綜合參政史事、玩辭見義、象數等方法發明辭義,獨具新意。
晚明長期寓居黃安和麻城的“反叛者”李贄銳意突破程朱理學的思想籠罩,強烈批判傳統,追求人性自由,是具有時代啟蒙意義的思想家;明末清初應城陳士元的經學研究兼擅考證與義理,京山郝敬遍治諸經、力倡實學;漢陽熊伯龍被視為前清文運開濟的代表,在《無何集》中構建起系統的無神論思想體系;漢陽熊賜履是前清譽滿天下的理學家,作《學統》“倡導程朱,傳承道統”;天門理學家胡承諾處江湖之遠,而立意以20萬言《繹志》發揮淑身心、治天下的濟世功效;史學家章學誠長期寓居湖北,主纂《湖北通志》及湖北多地府縣志,其方志學實踐和理論對中國方志學作出了開創性貢獻。
近代著名學者蘄州黃侃在文字、音韻、訓詁方面造詣精深,形成了一套小學科學體系,是當之無愧的國學大師;羅田王葆心一生著述豐富,重視搜集整理鄉邦文獻編成《湖北文征》,以《方志學發微》“集方志學之大成”,全面總結前代修志經驗,提出系統的修志理論;宜都楊守敬的輿地學成就獨步當世,《歷代輿地圖》是中國歷史地圖研究的奠基之作,《水經注疏》是《水經注》研究的集大成;宜都曹廷杰的東北邊疆地理研究具有極強的經世致用價值,在論證邊境歷史問題、處理邊疆國土爭議、加強邊疆防務和維護民族團結方面等具有重大意義;黃岡熊十力是現代新儒學的代表人物,《新唯識論》構建了他自成一家的哲學思想體系。
(二)荊楚文學與藝術色彩斑斕
屈原以南方民歌為基礎創造了新的詩歌體裁——楚辭,其奔放的情感、瑰瑋的想象、繁麗的辭賦、“賦”的表現形式、香草美人的象征意象,開辟了中國詩歌浪漫主義的源頭;《莊子》散文“汪洋辟闔,儀態萬方”,象征體系恢詭譎怪,辯對藝術縱橫捭闔,對后世的散文創作和文學思想體系的構建影響深遠。
漢代“文尚楚風”,劉向將屈、宋及其模仿作品匯編成《楚辭》一書,王逸著《楚辭章句》對《楚辭》進行訓詁釋義,綜匯諸家、別出己意,是楚辭整理研究的奠基之作,對漢代樂府詩、賦影響巨大;東晉南北朝時期流行于荊楚地區的民歌西曲引領了南朝文學清新自然的風格,推動了樂府新聲的創造。
在詩歌的黃金時代唐宋之世,荊楚大地培育的杰出文人璀璨閃耀,尤以襄陽籍才人最為繁盛:杜審言《和晉陵丞早春游望》是初唐近體詩體式定格的奠基之作,被稱為初唐五言律詩第一;在襄陽度過了一生大多數時光的孟浩然,創作了大量描寫襄陽山水名勝的詩歌,確立了盛唐山水田園詩派的高峰;張繼一首《楓橋夜泊》之情致深遠歷來受人稱頌;北宋女詞人魏玩的詞作成就與李清照并稱;南宋詩人張嵲被時人稱為“南渡巨擘”,其五言古詩“詞語高簡,意味幽遠”,七言絕句“精麗宛轉有思致”。此外,唐代荊州“號衣冠藪澤”,荊州籍著名詩人濟濟可觀,特別是江陵人岑參“語奇體峻”的邊塞詩創作,無論是體裁形式的創新還是藝術風格的獨特性都堪稱空前絕后。元代最重要的南人文臣之一程鉅夫為京山后裔,他引薦諸多南方文人入仕,40余年間掌朝廷典冊,文章雍容典雅、詩歌磊落俊偉;黃岡散曲家滕斌名列鐘嗣成《錄鬼簿》。
或游歷、或仕宦、或途徑荊楚大地的唐宋文人在此光芒四射。陳子昂途徑楚地詠史懷古,諷“荊王樂荒淫”(《感遇詩》),嘆“猶悲墮淚碣”(《峴山懷古》);崔顥一首《黃鶴樓》為唐人七律第一,黃鶴樓因此千古絕唱而聲名大噪;李白寓居安陸10年,飽覽荊山楚水秀美風光,留下許多名篇佳作,“江城五月落梅花”之句賦予武漢“江城”的雅號;杜甫晚年來到湖北,在一年左右的時間留下了50余首詩作,抒寫“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江漢》)的漂泊流離,批判“況聞處處鬻男女,割慈忍愛還租庸”(《歲晏行》)的沉痛現實,“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風煙含越鳥,舟楫控吳人”(《江陵望幸》)的神來之筆成為千載以下湖北自然地理與人文地理最為經典的標識;詩海留“劉隨州”之名的劉長卿,在隨州刺史任上的名作《逢雪宿芙蓉山主人》突出代表了其五律的精深造詣;元稹謫居江陵四年詩歌創作題材內容和藝術表現力都得到極大拓展,他的《遣悲懷三首》等“情文并佳,遂成千古之名著”(2) 的悼亡詩即作于此間;白居易數次途經湖北,記錄旅程風波“秋風截江起,寒浪連天白”(《襄陽舟夜》),歌詠湖北人物“秀氣結成象,孟氏之文章”(《游襄陽懷孟浩然》),贊美湖北山水“百花浪濺頭陀寺,紅葉林籠鸚鵡洲”(《盧侍御與崔評事為予于黃鶴樓致宴宴罷同望》);劉禹錫自夔州沿江東下經黃石西塞山,一首《西塞山懷古》成為歷代吟詠西塞山詩的扛鼎之作;杜牧在任黃州刺史的兩年間不僅政聲卓著,而且創作了最好的幾首詠史懷古詩,“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赤壁》)的佳句精妙絕倫、膾炙人口;李商隱途經湖北,作《楚宮》《夢澤》《楚吟》諷詠楚國歷史。宋初寇準任巴東縣令三年,留下了“寇巴東”的卓著政聲和60余首優美詩篇;青少年時期在湖北求學、后被貶夷陵(今湖北宜昌)縣令兩年的歐陽修,作有涉及夷陵的詩文140余篇,對記錄和傳播宋代偏僻的夷陵之山水風物有重要價值;在謫居黃州的四年多蘇軾完成了從“蘇軾”到“蘇東坡”的人生嬗變,750篇詩詞文賦標示了他文學創作的巔峰,心境曠達超越成就了其詩文的豪邁雋永,亦澆灌了黃州的文化沃土。
明代“公安派”以“性靈說”的主張和創作實踐反叛復古派,“公安三袁”成為文學變革的旗手;以鐘惺、譚元春為代表的竟陵派張大“性靈說”,影響詩壇至清初,“浸淫三十余年,風移俗易”(3)。
晚清至近代在“俗語文學”和白話文運動沖擊下,“武昌先生”張裕釗承續桐城派傳統,秉持文以載道主張,張揚古文雅健文風;新文化運動中,浠水聞一多對新詩理論的探索和新詩創作實踐,使其成為近現代詩歌發展的里程碑式人物;黃梅人廢名的田園小說藝術風格獨特,在近現代小說的園地中獨樹一幟;蘄春人胡風是思想深刻、具有獨創性的20世紀現實主義文藝理論的旗幟性人物。
楚金文書法變體“鳥蟲篆”,代表了楚地書法靈動優美的藝術體傾向;楚簡帛書寫已運用了毛筆,其字體處于篆字轉化過渡的階段;秦漢簡牘反映了篆體弱化和隸書逐漸形成并走向成熟的特點;隋朝丁道護任職襄州時作《啟法寺碑》在中國書法史上有上承漢魏六朝、下啟唐宋元明的重要地位;南朝庾肩吾書法受人稱道,其《書品》是書論史上品第類著述的開山之作;唐代江夏人李邕以行書入碑、成就卓著;蘇軾《黃州寒食詩帖》、黃庭堅《松風閣詩帖》均為我國古代行書書帖中的極品;襄陽米芾書法名列“宋四大家”;清末張裕釗、楊守敬的書法流播日本,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不可忽視。
楚國先秦帛畫遺珍長沙陳家大山楚墓“人物龍鳳圖”、長沙子彈庫楚墓“人物御龍圖”堪稱我國早期帛畫的雙璧,漆畫精品荊門包山“人物車馬出行圖”、曾侯乙墓“彩繪鴛鴦盒繪畫”等藝術成就突出,出土絲織物紋樣種類繁復,鳳鳥靈動飄逸的身姿是其代表性題材;漢代楚風畫像磚(石)表現形式豐富、藝術手法精妙,折射了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南朝畫家宗炳的畫作沒有留存于世,而其《畫山水序》在繪畫理論史上具有開創性貢獻,開啟了山水畫理論和技法的寫意之途;梁元帝蕭繹擅畫人物肖像,《職貢圖》構圖嚴謹、設色精當、人物生動,是難得的藝術珍品;宋代米芾、米友仁父子的“米氏云山”開創了江南山水畫的審美新風尚。
楚地音樂盛行,出土樂器種類豐富,曾侯乙編鐘、編磬呈現出的樂律理論、樂器制造及音效成就堪稱民族藝術瑰寶、世界音樂史奇跡;漢代以劉邦為首的統治階層對楚樂情有獨鐘,楚歌由民間深入宮廷,樂府加工楚地民間歌曲成為一種新的歌曲形式——相和歌;西曲代表了南朝時期荊楚民歌的最高成就;唐宋時郢中田歌、采蓮歌、襄陽白銅鞮等歌舞形式反映了荊楚人民勞作、戀愛、娛樂的多彩生活。楚國巫舞盛行,催生的“楚腰纖細掌中輕”的審美風尚反映了樂舞在楚人生活的影響;兩漢畫像石、畫像磚、陶瓷俑等反映了荊楚地區多樣的舞蹈類型,楚舞表演具有柔軟、敏捷、飄逸的特點。
明清時期,湖北戲曲的唱法、聲腔和表演程式尤為多樣,戲曲名角、民間藝人各擅勝場,越調、秦腔、山陜梆子交流融合,推動了漢劇的形成和發展,其西皮、二黃的獨特聲腔為京劇定型打下堅實基礎,湖北籍京劇名角余三勝、譚培鑫名震京師;潛江人曹禺的現代戲劇創作為中國話劇成型奠定了堅厚的基石。
(三)荊楚科學與技術承前啟后
春秋戰國時期楚人的冶煉采礦工藝已達到很高水平,使用了地質找礦、工程探礦、植物找礦等方法,進行了露天開采和地下開采,采用了多種地下治水、通風、照明辦法,能夠冶煉出大規模、高品質的粗銅,在鑄造中不僅將范鑄法發揚光大,還發明了失蠟法等新技藝;楚墓中出土了數量眾多、品類豐富的漆器,木、夾纻、陶、皮、竹、金屬、絲麻等多種漆器胎質,素面、彩繪、描金、貼金、鑲嵌等裝飾工藝,特別是透雕、浮雕等工藝與髹漆的結合,使得楚國漆器造型優美、形象生動,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
唐代襄陽的襄式漆器“襄樣”成為整個漆器行業的標準樣式,其造型奇異瑰麗,圖飾豐富多彩,色彩飽和雅重。北宋英山人畢昇發明活字印刷術,極大提升了印刷效率、降低了印刷成本,為我國乃至世界的知識傳播與文化普及作出巨大貢獻。
鄂東醫學底蘊深厚、名家輩出,北宋蘄水龐安時、明代蘄州李時珍、羅田萬全以及清代廣濟楊際泰并稱為“鄂東四大名醫”。龐安時是公認的中醫傷寒學大家,為溫病學派的形成和發展奠基,他的著作《傷寒總病論》具有重要的醫學價值;李時珍《本草綱目》堪稱世界矚目的中國古代醫學巨著和明代最偉大的科學成就,不僅是中國醫藥學的權威指南,而且具有超出醫學范疇的文化史價值。
清代數學家鐘祥人李潢闡發《九章算術》《海島算經》《緝古算經》等歷史上的數學典籍,推動了中國古代數學知識的傳播和研究;江夏人劉湘煃是清代最優秀的天文學家之一,他的“五星之說”“歲輪說”對推動天文學發展有重要貢獻;黃岡人陳大章研究《詩經》物種分類撰著《詩傳名物集覽》,在中國生物學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京山人李元撰寫了生物學博物全書《蠕范》。
近代自然科學的杰出人物氣象學家武漢人涂長望開創了中國長期天氣預報、中國氣團和鋒面研究,并致力于推動氣象學在旱澇災害預報、空軍高空飛行等方面的應用和實踐;著名地質學家黃岡人李四光在中國有第四紀冰川的論證、利用生物地層劃分含煤地層和中國石油勘探研究方面有卓越的貢獻。在張之洞幕府中研制無煙火藥的徐建寅、從事煤礦建造開采的工程師高壽林,是湖北近代走在前列的科學技術探索者。
(四)荊楚宗教與風俗別具一格
魏晉南北朝時期荊楚文化中對整個中華文化產生影響的重大事件是襄陽和江陵成為佛教在南方地區的傳播中心和主要集散地。東晉釋道安在襄陽等地長達15年的譯經活動,開創了利用中國傳統思想文化、思維模式、語言習慣翻譯佛經的路徑,大大促進了印度佛教中國化的進程,其僧團南下江陵、東進廬山、西上巴蜀的傳教活動推動了佛教傳播,在教制和僧團建設等方面影響了南朝佛教和中國佛教的歷史進程。
隋唐時期荊楚地區宗教繁榮,這里“既是佛教初傳南方的重鎮,又是隋唐之際孕育天臺宗、禪宗發展的搖籃”(4) 。荊州人智顗創立了中國佛教史上第一個宗派天臺宗,他總結了“五時八教”的判教體系,制定了“制法十條”規定僧侶行為,首次提出“農禪并重”,其思想理論融匯南北,具有推動佛教與中國本土文化相適應的實踐意義和社會價值。智顗在當陽玉泉寺講經弘法,使該寺名列天下叢林“四絕”(與棲霞、靈巖、天臺并稱)、被譽為“荊楚叢林之冠”。“上接達摩一脈,下傳能秀兩家”,四祖道信在禪宗形成過程中承上啟下,五祖弘忍進一步完成了禪宗的創建,弘忍弟子神秀、慧能進而創立禪宗兩大派別,使禪宗思想成熟、派別壯大。
唐朝崇道的歷史背景下,荊州道教文化空前繁榮,江陵成為湖北道教中心。荊州道士孟安排編著《道教義樞》,收集了當時主要的道教教義,并系統梳理相關論述及其歷史演變,為南北朝至隋唐的道教教義研究提供了集大成的資料匯編;宜城人王士元偽托老子弟子亢倉子作《亢倉子》一書,該書受到唐玄宗重視并被列為道教“真經”之一。五代宋初的傳奇隱士和思想家陳摶在武當山修隱20余年,他的內丹理論和修煉方法為武當道教內丹功和內家拳提供了直接的理論來源。北宋安陸人張君房在宋真宗時組織《大宋天宮寶藏》的編纂,較為全面地收錄道經并建立了分類和目錄體系,又修成被稱為“小道藏”的《云笈七簽》,在《大宋天宮寶藏》失傳后該書的史料價值尤為重要。武當山真武信仰在宋元皇室的支持和推重下發展迅速,宋代武當山出現以信奉真武神為主要標志的道團組織,形成武當道教;元代武當道士張守清受皇室禮重,融合全真與清微道派而開創武當清微派;內丹學家陳致虛往來九宮山,推動了全真道金丹派南宗與九宮山御制派的融合,反映了在元代大一統格局下道派的大融合。明代武當山被推崇為皇室家廟,武當道教的地位臻至鼎盛,武當山成為全國最具影響力、宮觀規模最大的道場。
端午節是深具荊楚淵源和特色的節日,東漢時期對文化人物屈原的崇敬和紀念,已經賦予了這個節日遠超乎驅避“惡月惡日”的文化內涵,隋唐之際龍舟競渡成為人們期待的娛樂活動,也具有了祈望豐收的寄寓。七夕節的乞巧活動在南朝時已與牽牛織女的動人傳說交織,唐宋時人們舉行拜祀牽牛、織女星的儀式,宋元時女乞巧乞子、男乞富乞壽,全民參與。穿天節的傳說可遠溯至周代,而“游女弄珠”故事的成型在西漢劉向《列仙傳》,唐宋文人的演繹使襄陽一地的民俗成為文化史的一道浪漫風景。
青銅酒器見證了先秦楚地的飲酒傳統,漢代宜城醪享譽天下,唐代鐘祥“郢州春秋”進入名酒之列。唐代荊門的冷盤名菜“餳絲結”屢見于唐詩,民間流傳的蘇東坡在黃州自制美食遠不止東坡肉,明清時期楚菜系列逐漸成熟,魚類烹調是其特色,因嘉靖皇帝而得名的蟠龍菜是江漢平原蒸菜飲食系統的代表。
三、荊楚文化研究的深入推進與表達范式
(一)荊楚文化研究的深入推進
在深入總結和吸收荊楚文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關于荊楚文化諸多問題的認識得到深入推進。秦漢時期荊楚文化的文獻記載缺略,且考古發現數量有限,此前荊楚學者對這一歷史時期本地文化系統的深入發掘、研究、闡釋不足。 《荊楚文化史》著力于利用出土文獻和考古發掘研究成果,力求真實全面地展示這一時期荊楚文化面貌,綜合梳理和總結了秦漢簡牘在思想、學術、醫學、數學、文學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如睡虎地秦簡《為吏之道》中的政治思想,張家山漢簡《蓋廬》中的軍事思想,秦漢簡牘中的法律思想,王家臺秦簡的易學研究價值,出土簡帛中的宇宙觀和哲學思想;周家臺秦簡中的病方與祝由術,北大秦簡《醫方》對疾病治療,睡虎地秦簡《封珍式》關于法醫檢驗,張家山漢簡《脈書》《引書》對疾病、經絡、導引的記載等反映了荊楚醫學的面貌;北大秦簡《魯久次問數于陳起》《算書》等材料反映秦代數學,張家山漢墓出土《算術書》、云夢睡虎地漢墓出土《算術》代表了西漢早期數學水平。通過出土畫像石、畫像磚、陶瓷俑的形象反映兩漢時期荊楚地區的舞蹈類型,依據簡牘文字分析秦漢書法的特點和演變規律,根據畫像石、畫像磚上刻畫的藝術圖案探究刻繪技藝以及社會日常生活的諸多方面。
集中闡述了湖北地區在各時代最為突出的歷史事相,并深入分析了其對社會文化發展的影響,闡明了不同時代影響荊楚文化形成的特殊因素,彰顯了荊楚文化獨特的風格特征。“明清卷”論述了“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的兩大移民事件,指出這是明清時期對荊楚地區影響最為深刻的歷史事相,即“當今所謂的‘湖北人’,其淵源可追溯到遠古,其定型大體在明清”(5) ,明清移民運動塑造了湖北人口構成的基本框架,也促成了“湖廣分治”、湖北省級行政單位的確立。作者通過族譜、方志等扎實的史料分析和廣泛的研究成果吸收,論述了這兩大移民事件的歷史原貌、移民原因和遷移模式、移民潮的多樣性和社會矛盾,深入反映了湖北地區遷入和遷出移民的生存樣態,這種生存樣態也正是其時湖北普通民眾的生活境遇,體現了“人們的生活日常構成了歷史文化最為深厚的基石”(6) 這一觀念。“近代卷”呈現了近代湖北是最早傳播革命思想的地區之一,辛亥革命由武昌首義吹響號角并非偶然,其遠源是荊楚文化精神傳統中“不服周”“問鼎中原”“鳴必驚人”“亡秦必楚”的進取精神和創新意識,其近因是經世派士大夫林則徐、胡林翼在湖北扶危救弊、張之洞以“中體西用”思想和系列新政求強圖存,其流波是武漢成為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重要陣地,湖北是最先建立共產黨組織的省份之一。
注重闡發政治經濟軍事背景對文化的影響和文化事相內在的演變規律,使文化史的呈現不停留于文化內容的鋪陳,而是構成有歷史縱深和邏輯關聯的闡發,能夠加深讀者對文化史的認識和理解。“秦漢魏晉南北朝卷”闡明了兩晉南北朝時期北方大量移民和出山蠻族的到來促進了荊楚地區人口數量的回升,在政治體制上體現為僑州郡縣和蠻左郡縣的設立,在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同時也重塑了荊楚地區的文化面貌。其對荊楚文化的影響突出表現在東晉南渡的北方大族、南陽世家、文人集團為保持家族勢力注重子弟文化修養,客觀上推動了文化人才的培養和文化脈絡的傳承,后梁歸附北朝后,關隴大族自荊楚地區回遷關中,其文化造詣對隋唐文化成就亦有深遠影響。“隋唐宋元卷”論述了穩定的氣候與肥力增強的土壤保障了農業經濟的發展,從而為荊楚文化勃發提供了優越的自然條件,湖北南北交會、水陸兩宜的交通格局和人口聚集、人才匯聚的人口面貌為荊楚文化勃發提供了長足的動力,而官民對教育和科舉的重視則是荊楚文化勃發的深厚根基。
(二)荊楚文化研究的表達范式
跨長時段的區域文化通史視角在做到體例整飭、內容統一基礎上,又兼收并蓄、量體裁衣。各卷緒論均對各歷史時期荊楚文化的時空界限、基本面貌、演進軌跡、突出特點做了統一梳理與概括,對讀者把握較長歷史時期中紛繁的文化內容有提綱挈領之效。而在各章內容設置上,如“總序”所言,將文化史研究的內容定位介于宏觀與微觀之間的“中觀”視角,一方面重點考察精神文明層面的思想、學術、文學、藝術、教育、科技、宗教、民俗,另一方面也不忽視在特定時代背景下對文化生成和發展產生重大影響或突出反映該時代文化形態的生態、移民、城建、商旅、交通等。前者體現為除“史前卷”外,各卷均基本包含思想、學術、文學、藝術、教育、科技、宗教、民俗等內容,且在章的設置上以文化內容為主題分別命名。后者如“史前卷”作為全書開篇,對荊楚文化所處的自然環境進行專章論述,該卷在章的主題設置上遵循史前文化認識的基本規律,在呈現縱向時間歷程的同時以章的標題凝練文化特點;再如“先秦卷”對楚國形成過程中的族群及其考古文化面貌的交代獨立成章,對闡明創造了800年輝煌歷史的楚族與楚國的源頭脈絡必不可少。
荊楚文化史得到理論功底深厚、邏輯結構合理、學術規范嚴明的構建。作為一套集眾人之力合作撰寫、跨長時段貫通古今、涉多學科研究領域的文化通史,各卷的主編及章節的作者均為所涉時段該領域深耕不輟、功底深厚的研究者,各卷審稿專家不僅是關注荊楚文化研究的學者,而且不乏相關專業研究的權威名家,使得相關內容的專業性、學理性、邏輯性、規范性得到堅實保障。“史前卷”大量運用專業考古資料、考古文化研究方法和文物研究成果,“先秦卷”博采兼收數十年楚文化研究的各個門類,“秦漢魏晉南北朝卷”充分利用出土簡牘和文物研究成果,“隋唐宋元卷”在豐富的傳世文獻基礎上以人物和事件為主線建構敘述體系,“明清卷”充分運用史料并深入客觀分析、個案縱深研究與分類概述相結合,“近代卷”秉承開放理性發展的史觀統攝新舊變革的歷史階段,均反映了相關內容在學術研究上挖掘的力度。
各擅所長的研究理路反映作者對不同歷史時期荊楚文化史的深入思考與獨特關注。例如,“明清卷”獨辟一章論述茶與中外交流,這固然是由于湖北是誕生了《茶經》、茶產業和茶文化歷史悠久的傳統茶區,更是由于在明清時期現代與傳統、西方與東方交融激蕩的時代背景下,茶葉構成開埠后的漢口對外貿易的重頭戲,圍繞茶葉貿易形成跨越南北、水陸并行、貫通中外的“萬里茶道”在中外交流史上意義深遠。這體現了作者打通經濟貿易與文化事件內在關聯,將區域文化事件放在整個國家和時代發展變遷背景下觀照的思考維度。
關注文化事件與政治、經濟、人口、商貿等因素的相互關聯與多元互動,并將荊楚地區放在全國范圍內考察其文化地位和影響,這是各卷共有的認識邏輯和思考自覺,體現了學術視野的廣度和思考的深度。
注釋:
(1) 張正明:《楚文化史》,湖北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230頁。
(2) 陳寅恪:《陳寅恪集·元白詩箋證稿》,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版,第109頁。
(3) 錢謙益撰集,許逸民、林淑敏點校:《列朝詩集》,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5360頁。
(4) 吳成國主編:《荊楚文化史·隋唐宋元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22年版,第366頁。
(5)(6) 任放主編:《荊楚文化史·明清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22年版,第17、8頁。
作者簡介:李詠秋,武漢商學院通識教育學院講師,湖北武漢,430056。
(責任編輯 劉曉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