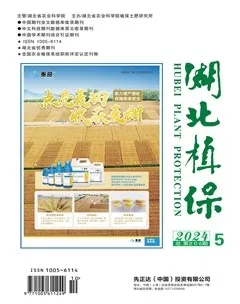4種藥劑對稻縱卷葉螟的田間防治效果




摘要:本文研究了5%甲氨基阿維菌素ME、20%氯蟲苯甲酰胺SC、15%茚蟲威EC、24%甲氧蟲酰肼SC等4種藥劑對水稻稻縱卷葉螟的田間防治效果。結果表明,在稻縱卷葉螟發生程度重且僅防治1次的情況下,15%茚蟲威EC(30 mL/667m2)對稻縱卷葉螟的防效最優,殺蟲效果和保葉效果分別達90.96%和94.67%;對稻縱卷葉螟的速效性和持效性在供試4種藥劑中表現最佳,有推廣應用價值。
關鍵詞:稻縱卷葉螟;田間藥效;速效性;持效性
中圖分類號:S435.112.1文獻識別碼:A文獻編號:1005-6114(2024)05-032-03
稻縱卷葉螟(Cnaphalocrocis medinalis Guenee)屬鱗翅目螟蛾科,是一種具有季節性遠距離遷飛習性的重大害蟲[1]。作為應城市水稻重大“兩遷”害蟲之一,稻縱卷葉螟隨著氣候、耕作制度等條件的變化,其發生危害也越來越嚴重,給當地水稻生產造成了嚴重損失。當前稻縱卷葉螟對于阿維菌素、甲維鹽、氯蟲苯甲酰胺等都有了一定的抗性水平,防治效果越來越差[2-4]。為了解當前生產過程中常用藥劑對水稻稻縱卷葉螟的防治效果,科學指導水稻害蟲的防控工作,保障水稻用藥安全,應城市農業技術推廣中心在2023年5~10月開展了幾種藥劑對稻縱卷葉螟的田間藥效試驗。
1材料與方法
1.1試驗地概況
試驗地安排在應城市蒲騷家庭農場有限公司生產基地,位于應城市田店鎮暢馬村,經度113.47°,緯度31.01°,年平均氣溫16℃,降水量1 100 mm,有效積溫5 884℃,無霜期241 d左右。壤土類型,有效氮170.94 mg/kg、磷13.0 mg/kg、鉀129.63 mg/kg、有機質34.56 g/kg、pH值6.03。水稻品種為紅糯1號,中稻,2023年4月25日播種,5月23日機插,防治對象為稻縱卷葉螟。
1.2試驗藥劑
5%甲氨基阿維菌素ME,安道麥輝豐江蘇有限公司;20%氯蟲苯甲酰胺SC,美國富美實公司;15%茚蟲威EC,美國富美實公司;24%甲氧蟲酰肼SC,紹興上虞新銀邦生化有限公司。
1.3試驗設計
本試驗共設5個處理(表1),每處理3次重復,共15個小區,采用隨機區組排列,每個小區面積30 m2,小區之間留0.5 m作業行,防止施藥時相互干擾。
1.4施藥方法
根據田間蛾峰的監測情況,在稻縱卷葉螟幼蟲孵化高峰期施藥。于2023年7月28日下午5點,采用背負式電動噴霧器噴霧,每667 m2用水量30 kg,施藥時田間保持3~5 cm 淺水層。施藥當天天氣為多云,日平均溫度27.5°C,偏南風1級,施藥后12 h內未降雨。
1.5調查時間及方法
安全性調查:施藥后不定期采用目測法觀察各個藥劑處理對田間水稻的生長有無藥害發生[5]。
防效調查:在施藥前調查蟲口基數,在藥后3 d、7 d和14 d各調查一次防治效果。采用平行跳躍式10點取樣,每點查5叢,每小區共調查50叢水稻。前二次每株剝查上部三片葉,記錄活蟲數,計算殺蟲效果;最后一次調查總葉數和卷葉數,計算卷葉率和保葉效果。
計算公式:
殺蟲效果(%)=處理區蟲口減退率-空白區蟲口減退率1-空白區蟲口減退率×100
卷葉率(%)=卷葉數調查總葉數×100
保葉效果(%)=空白對照區卷葉率-施藥處理區卷葉率空白對照區卷葉率×100
1.6數據分析
采用SPSS17.0版Duncans新復極差法進行差異顯著性分析。
2結果與分析
2.1對水稻的安全性
施藥后不定期的目測觀察發現,各藥劑處理區水稻生長正常,無藥害現象發生,說明供試藥劑在本試驗劑量下對水稻生產安全。
2.2防治效果
施藥前,對各藥劑處理和空白對照區稻縱卷葉螟為害程度進行了調查,5個處理小區50叢平均活蟲量均在100頭以上。施藥后的調查結果表明,施藥后3 d和7 d,供試藥劑對稻縱卷葉螟均表現出一定的防治效果,其中以15%茚蟲威EC(處理4)的殺蟲效果最佳,分別達84.38%和90.96%;20%氯蟲苯甲酰胺SC(處理3)的殺蟲效果最低,施藥后3 d和7 d的防效分別僅為41.85%和48.37%(表2)。
藥后14 d的調查結果表明,供試藥劑對于水稻植株的保葉效果不同,其中以15%茚蟲威EC(處理4)處理后的保葉效果最優,達94.67%;其后依次為5%甲氨基阿維菌素ME(處理2)、24%甲氧蟲酰肼SC(處理5)和20%氯蟲苯甲酰胺SC(處理3)(表3)。
3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發現,在稻縱卷葉螟發生程度重,幼蟲基數大、蟲齡不一致,且僅防治1次的情況下,供試4種藥劑中,以15%茚蟲威EC(30 mL/667m2)殺蟲及保葉效果、速效性和持效性最佳,在大田稻縱卷葉螟的防治實踐中可以推廣應用。5%甲氨基阿維菌素ME(40 mL/667m2)和24%甲氧蟲酰肼SC(17 g/667m2)對稻縱卷葉螟的防效一般,殺蟲率和保葉效果均在80%以下,在大田生產中,建議使用其復配制藥劑進行稻縱卷葉螟的防治。20%氯蟲苯甲酰胺SC(10 mL/667m2)藥后的殺蟲率和保葉效果均在60%以下,防效不太理想,抗藥性較明顯,建議在稻縱卷葉螟的防治實踐中盡量不用氯蟲苯甲酰胺。
參考文獻
[1]徐云珂,李寬.不同藥劑防治水稻稻縱卷葉螟和二化螟的效果研究[J].湖北植保,2023(6):43-45.
[2]宋小艷,謝志娟,馬麗云,等.不同藥劑對六(4)代稻縱卷葉螟的防效試驗[J].湖北植保,2023(1):48-49.
[3]周建,費丹,吳文山,等.不同殺蟲劑對水稻二化螟及稻縱卷葉螟的田間防效[J].安徽農業科學,2022,50(23):3.
[4]王小玲,夏海生,夏文明,等.不同藥劑對稻縱卷葉螟的防效試驗[J].現代農業科技,2021(12):124-125.
[5]馬麗云,杜曉君,謝志娟,等.不同殺蟲劑對水稻稻縱卷葉螟的防效試驗[J].湖北植保,2023(2):45-46.
作者簡介:金云云(1990-),女,農藝師,長期從事農業技術推廣工作。E-mail:625784002@qq.com